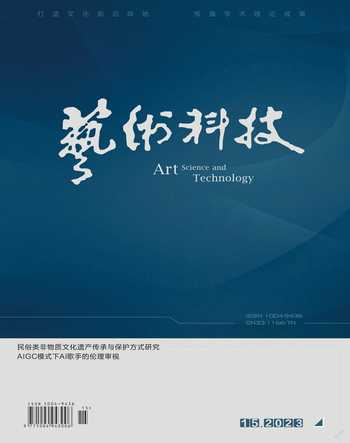抖音短視頻中性別反串表演策略分析
摘要:反串表演是以性別扮演為基礎的一種傳統藝術表演形式。在我國的傳統戲劇中,一直都有男性飾演女性角色的慣例,稱為反串。一般來說,反串的角色為青衣、花旦和老生,反串的男性需要揣摩各個角色的神態、動作,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女性。新媒體環境下,反串表演在短視頻平臺中愈演愈烈。隨著短視頻浪潮的興起,反串角色有了新的走紅路徑,反串的舞臺已經不再局限于戲曲舞臺和大屏幕中,而是走向了移動小屏。一系列創作者依靠反串完成了走紅,如抖音博主“多余和毛毛姐”憑借對女性角色的洞察,通過演繹精準擊中了廣大網友的痛點,這些角色在視覺上帶來的反差,擁有極強的沖擊性,增強了短視頻的可看性。“多余和毛毛姐”的性別反串短視頻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理想化、生活化以及男性化的特質。基于此,文章基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從身體、話語、場景策略三個方面對“多余和毛毛姐”性別反串短視頻中的性別形象塑造機制進行分析。“多余和毛毛姐”這一類性別符號的盛行,反映了當下社會傳統性別觀念的變化。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為性別解放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目標,挑戰傳統性別框架在社交媒體的日益發展下有了更廣闊的發揮空間。
關鍵詞:反串表演;性別操演理論;形象塑造;“多余和毛毛姐”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15-0-03
性別反串源于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戲曲,指的是演員通過易裝進行跨越生理性別的表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我國傳統戲曲中的“乾旦坤生”①。比如,1963年上映的越劇版《梁山伯與祝英臺》中樂蒂飾演的祝英臺。隨著影視劇的快速發展,反串表演在熒幕上有了更多的精彩呈現。比如,港劇《新白娘子傳奇》中葉童飾演的許仙、《霸王別姬》中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近年來播出的火爆劇《花千骨》中馬可飾演的殺阡陌等一系列經典角色。
當下,在短視頻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以“男扮女”為主題的性別反串短視頻大受歡迎,一些“男扮女”博主通過塑造與日常生活極為相似的女性形象,刻畫出“媽媽”“職場精英”“單身女生”等女性角色,并收獲百萬或千萬粉絲。而博主們在塑造女性形象時,也根據自身性格打造出符合自身特色的女性畫像,如“毛毛姐”“毛光光”“大姨張大霞”等。隨著短視頻時代的到來,性別反串表演逐漸走出以往的熒幕、舞臺,以生動形象的表演刻畫出現實社會中的女性形象。由此可見,當今媒介場域中存在的性別表演,對中國性別文化的研究與性別對立的重構具有較大意義[1]。
1 性別反串表演相關研究
在大眾媒介盛行之前,學界對“性別反串表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戲曲和文學作品領域,通過研讀作品文本,闡釋表演者性別反串的意圖。比如,“有學者認為寫作者會在自己的文學敘事中預先設想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角色,并讓演員通過性別反串的演繹方式獲取性別平等的地位”[2],“有的學者認為影視藝術源于生活,并關注到作品中展現的兩性之間的模糊化界限,得出性別反串表演是對現實社會問題的表征,并在虛擬空間里實現了對性別僭越的幻想”[3]。
隨著大眾媒介的不斷發展,學界開始關注綜藝節目中的性別角色扮演,認為綜藝節目中的性別反串者是基于對名利、娛樂以及流量經濟的追逐。有學者認為,“這種表演方式在經過大眾媒介傳播的過程中,會對受眾固化的意識形態產生影響,但這種試圖挑戰傳統性別規范的力量依然薄弱,更多的是媒體為受眾打造的‘身體消費狂歡”[4],還有一部分學者“研究分析了表演中存在丑化甚至顛覆傳統女性形象的原因,認為是大眾媒介按照傳統父系權力的標準創造的,其中包含了社會對男性優勢地位的肯定,同時反諷了這種依靠反串表演顛覆傳統父系文化的行為”[5]。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中提出了性別操演理論,認為扮裝徹底顛覆了內在和外在心靈空間的區分,有力地嘲弄了真實身份的概念。”[6]性別本身是人們按照性別規范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表演的結果,那么性別反串在本質上就是模仿重復人類本身性別行為的結果。“巴特勒認為通過性別展演的實踐,能使人們了解現實被復制以及在復制過程中改變所依據的機制”[7]。在這一過程中,性別表演具有三個維度的復制策略,分別是戲劇維度的身體策略、語言維度的話語策略和儀式維度的場景策略。
2 “多余與毛毛姐”的形象塑造
2018年10月,抖音博主“多余和毛毛姐”憑借一支具有魔性的短視頻《城里人和我們農村人蹦迪的不同》迅速走紅,視頻中的“好嗨哦,感覺人生已經到達了高潮”一時間紅遍網絡,引起各大網紅博主的拍攝模仿。截至2018年的第四季度,“多余和毛毛姐”的粉絲量達1539.6萬人次,成功進入千萬粉絲達人行列,并且85%以上的抖音視頻點贊數為百萬量級。截至2023年5月,抖音“多余和毛毛姐”的粉絲量為3073萬人次,點贊量為5.7億次。視頻創作者余兆和通過分視角模仿,加上相對浮夸的演技和搞笑、接地氣的故事劇情,以及炫彩的假發、極具辨識度的貴州口音,成功塑造了“多余”、反串性別“毛毛姐”“三姐”等角色,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吸引了無數粉絲的關注。
性別角色是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形成的,具有刻板化印象的專屬特征。為扮演被選中的女性形象,表演者在形象塑造中,主要從身體、話語和場景三個方面進行角色建構。
2.1 戲劇維度的身體策略
巴特勒希望性別解放能在身體塑造上得到實踐。其認為只有通過被性別化的身體塑造,才能找到去性別化的道路。從“多余和毛毛姐”性別反串短視頻中的形象塑造來看,余兆和一共塑造了兩類性別形象:一是他頭戴橘紅色假發的“毛毛姐”“三姐”等多個女性形象;二是他身著男性衣裝扮演的男性形象,即“毛毛姐”的男朋友“多余”。作為本色人格表演的“多余”小哥哥,人物俊朗陽光,口述普通話,性格溫柔大方,表現力較為穩重。而作為女性人格表演的“毛毛姐”則性格灑脫幽默,操著一口充滿魔性的貴州普通話,加上招牌假笑“呵呵呵”,通過夸張的表情和豐富的肢體動作,展現了傲嬌、作怪、嬌嗔、嘴上一套心里一套等一系列女性化特征。
2.2 語言維度的話語策略
福柯認為,話語即權力,且是社會語境下的產物。在此基礎上,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性別構建也是話語的產物,主張必須在話語體系中為性別實踐創造合法的語匯。從語言維度對“多余和毛毛姐”的性別反串短視頻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毛毛姐”的角色建構中,主要呈現出兩大語言特征:一是通篇使用貴州方言,比如用貴州口音說出來的口紅顏色“xuan紅”“lu幽幽”等;二是在一些對話中出現了“中英混雜”現象,比如“老天爺謝謝你,thank u so much”。話語主題圍繞著女性日常生活內容展開,如相親、購物、減肥、朋友聚會等。通過這些話語策略,構建了一個貼近生活、性格活潑、自信灑脫的年輕化的女性形象。
2.3 儀式維度的場景策略
朱迪斯·巴特勒認為,反串表演行為需要故事情境的加持,表演者只有通過各種故事場景進行不斷的表演,才能使塑造的角色深入人心。“多余和毛毛姐”的短視頻場景大部分是以余兆和家里的衣柜為主,他把寫有場景名字的白紙張貼在衣柜上,作為虛構社會場景的方式,如“飛機上”“KTV”“吃火鍋”等。在短視頻劇情建構中,“多余和毛毛姐”的話題大多從女性視角出發,通過陳述或者吐槽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比如在“閨蜜減肥吃火鍋”場景中,以順口溜的方式表達女性不要刻意減肥的看法。在以“感情”為主題的劇情中,會涉及“分手”“吵架”“生小孩”等情節,使“毛毛姐”在與男朋友“多余”和閨蜜“三姐”的互動中完成角色的塑造。“多余和毛毛姐”的短視頻通過結構明確、銜接有序的故事內容以及本人精彩的演技,把各個人物形象的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
3 “多余和毛毛姐”的性別形象重構
通過朱迪斯·巴特勒性別操演理論帶來的啟發,對“多余和毛毛姐”進行以上三個維度的分析,可以發現,其性別反串表演相較于傳統性別反串表演,既有延續,又有一定的突破。
3.1 父權審美體系的強化
巴特勒曾提出,大眾媒介提供了個人展演的虛擬空間,人們會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對性別的認知作為參考依據。余兆和在接受《百姓關注》采訪時表示,“多余和毛毛姐”的人物特色符合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氣質,他把自己性格中火辣和沉悶的一面單獨拿出來,無限放大后就是現在火熱的“毛毛姐”和無聊的“多余”。這恰好符合了巴特勒的觀點。
“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中闡釋了好萊塢主流電影中‘看與‘被看的關系:女性作為男性觀眾欲望的對象,總是處于被看和被展示的位置。”[8]從“多余和毛毛姐”的粉絲數據來看,其女性粉絲居多,當女性觀看視頻時,其實是把自己放在了一個“被凝視者”的位置。首先,“毛毛姐”之所以能對女性的神態、妝容進行惟妙惟肖的模仿,實則源于日常生活中對女性的凝視,無論是身體、話語還是場景情節,均通過對傳統性別刻板形象的凝視來塑造性別角色。他通過凝視女性,提高自己“被凝視”的價值,通過易裝展演創造出一個個女性形象。“毛毛姐”的熱門視頻往往以情景喜劇的方式,再現女性生活的日常場景。比如,對朋友聚會、相親、購物、學車等看似十分平常卻又受到很多女生歡迎的場景進行模仿。
另外,“毛毛姐”的生理性別是男性,他所表現出的性別符號屬于女性,因此,當短視頻中的女性形象被大眾凝視時,實則是他身上具有的“女性特色”被凝視。所以,在這個凝視的關系中,女性其實是透過“毛毛姐”的視頻凝視著自身,只不過轉換了凝視視角,塑造了主體地位提升、主動凝視他者的假象。
3.2 對二元性別邊界的僭越
在巴特勒著名的性別操演理論中,跨性別表演絕不僅是二手的模仿,它實際上說明了社會性別本質上是文化屬性的建構,即社會性別在現實中可以通過表演發生置換。
“多余和毛毛姐”等男主播的反串表演在表面上顛覆了傳統的社會性別二元對立的范疇。但他們塑造的女性形象與以往的戲劇和文學作品有所不同,是大眾修辭里對女性情緒與場域的一次粗糙的符號化模仿,傳統社會兩性規范中進行的“性別表演”非但沒有受到挑戰,反而促使社會給定的女性特質,如熱愛化妝、沉迷消費等,被進一步強調、再度認同及固化。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表演者往往會在同一個視頻中“扮回”男性本身,笑點和包袱往往集中在被扮演的女性角色身上,而男主播則通過俊朗的外表進一步吸引著女性粉絲,并且使觀眾因為這種倒錯產生贊許,如“明明可以靠臉吃飯,卻仍然要靠才華”。在“比女人更加了解女人”的話語體系形成的背后,這些貌似以女性視角展開的性別跨越的重點往往在于表演本身,而非性別。
3.3 解構“性別”,追尋重塑與賦權
首先,性別操演理論對改變人們對性別本質深層認知的意義深遠。從理論意義上講,性別操演理論為性別認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批判性視角,指導人們重新思考固化的性別二元對立模式。從實踐意義上講,身份認知構建對整個社會的性別平等和諧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也能為性別動態研究提供更廣闊的視野。
其次,性別反串博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兩性之間的傳統界限,打破了傳統經驗習俗,體現出對性別賦權的追尋。在追尋性別平等的過程中,“短視頻平臺提供了反抗儀式的媒介,成為他們進行‘解構的場所”[9]。性別反串博主借助新媒體平臺重構性別角色,通過堅守思想獨立,實現了對性別的賦權。
最后,反串表演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社會對性別演繹的接受與容納。作為一種性別文化符號,很多反串表演者對女性角色的塑造不再以丑化吸睛為目的,更多呈現的是積極樂觀的一面。雖然“毛毛姐”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按照傳統性別框架評價,但也收獲了眾多好評。在性別反串的背后,亞文化現象以性別展演的形式進入大眾視野,得到廣泛傳播。
4 結語
本研究運用性別操演理論,通過對“多余和毛毛姐”這一性別反串表演個案的分析,得出“多余和毛毛姐”的反串形象通過運用戲劇維度的身體意象、語言維度的話語行為、儀式維度的場景情節塑造而成。通過對“多余和毛毛姐”進行三個維度的分析,可以發現,其性別反串表演相較于傳統性別反串表演,既有對父權審美體系的強化,又有對二元性別邊界的僭越,甚至試圖解構“性別”界限,追尋性別上的重塑與賦權。在此基礎上,自媒體博主通過短視頻塑造性別形象,試圖挑戰傳統性別框架,有重構性別之勢。就此而言,巴特勒以“爭取性別平等”“為婦女爭取權利”為動力,為性別解放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目標。
參考文獻:
[1] 王蕾,朱雯文,常博.媒介中性別反串形象的塑造及社會張力研究[J].當代傳播,2018(1):37-40.
[2] 劉永杰.《九重天》中性別角色反串的女性主義意圖[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06(2):59-66.
[3] 邊靜.性別越界的狂歡:華語電影中的“易裝”審美[J].藝苑,2006(11):50-55.
[4] 吳世文.警惕電視選秀節目中的“性別反串風”:兼論電視娛樂的底線[J].今傳媒,2010(8):179-181.
[5] 李進超.丑化與顛覆:變態女性假面具下的真容:芙蓉姐姐與小沈陽現象的文化解讀[J].社會觀察,2010(8):72-74.
[6] 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M].宋素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9.
[7] 范譞.跳出性別之網:讀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別》兼論“性別規范”概念[J].社會學研究,2010,25(5):232-242.
[8] 趙曉芳.凝視的快感:“身體寫作”中的“看”與“被看”[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5(12):1-5.
[9] 幸潔.性別表演:后現代語境下的跨界理論與實踐[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193.
作者簡介:張春紅(1998—),女,河南濮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新聞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