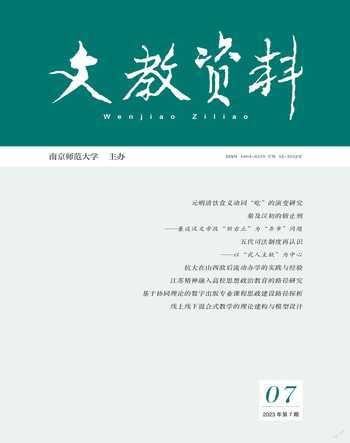抗大在山西敵后流動辦學的實踐與經驗
任晶晶 夏文華 趙梓君


摘 要: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由1936年6月在瓦窯堡成立的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發展而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高等學府。1939年抗大主動挺進山西敵后與日偽斗爭,經歷了艱苦的流轉和發展,克服了敵后威脅、物資匱乏、思想斗爭等困難,積累了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理論聯系實際、靈活流動辦學等豐富經驗。作為抗大敵后辦學的重鎮,山西特殊的環境鑄就了抗大獨特的辦學風格和模式。抗大在山西敵后流動辦學的實踐與經驗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
關鍵詞:抗大 敵后 流動辦學 山西
目前學界關于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的研究多以隴東、陜西、河北等地的抗大分校為主要研究對象,涉及山西地區抗大辦學實踐的研究較少。這些研究也大多考察屯留、武鄉等個別重要地區,對山西全省敵后流動辦學的實踐缺乏系統性深入研究,對山西的特點及敵后條件也少有涉及。本文以抗大在山西的敵后辦學為研究對象,從其挺進敵后的原因和路線發端,分析該校在山西辦學的特殊性,希望通過考察抗大先輩在山西敵后的學習與生活、困難與成就,探討抗大在敵后辦學的成效、教育特色,總結抗大在山西敵后辦學的實踐經驗與歷史價值。
一、抗大成立與挺進山西
1936年5月8日,在陜北延長縣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目前形勢與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提出創建紅軍學校的問題。[1]同年6月1日,紅軍大學克服人手少、設備不足、資源匱乏等等困難,如期在瓦窯堡開學。隨著抗日救國運動的高漲,許多愛國青年與有志之士抵達延安,尋求救國之路。中央軍委于1937年1月19日決定將“抗日紅軍大學”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2]自此,抗大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抗大前四期共為前線培養了5000余名抗戰骨干,到1939年第五期時,抗大接受了到敵后辦分校的任務,開始挺進敵后辦學。
抗大挺進敵后,有利于防患未然,也能緩解邊區的壓力。首先,這一舉措便于吸收人才和培養更多抗日干部,從而能夠更好地發動和組織群眾,進一步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創建和鞏固革命根據地。抗大的學員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部分是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和長征考驗的紅軍老干部、老戰士……一部分是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干部或戰士……還有一部分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和來自海外的愛國華僑青年。”[3]邊區被封鎖后,學子求學不易,抗大挺進敵后減輕了學子赴學的壓力,也為培養干部擴充了來源。同時,從學員構成看,學員有的缺少實戰經驗,有的缺乏理論知識,在敵后學習,可以兼顧經驗的積累與理論學習,培養優秀的中共干部。其次,抗大挺進敵后也是對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攻邊區的反擊。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的態度,不失時機地進攻是最好的防守。羅瑞卿在抗大東遷大會上表示,既然日本帝國主義要來,我們就和它換防。就在同年9月下旬,東遷尚未完成的抗大便與晉察冀軍區部隊、八路軍一二〇師聯合作戰,殲滅襲擊陳莊的日偽軍1500余人,從側面證明了其特殊價值。
抗大以總校為先導,挺進山西敵后,開啟了它“越抗越大”的輾轉辦學。抗大挺進山西緣于山西在抗戰中無可比擬的價值。首先,山西與陜西隔河相望,作為離邊區最近的省份,對于邊區的防務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敵后根據地在山西的建立和發展以及抗大的深入敵后,一定程度上擾亂了日偽軍在淪陷區的統治,減輕了對邊區的壓力,拱衛邊區的同時也便于相互聯系。不僅如此,山西也是延安黨中央聯系華北、華東、華中和華南各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通道。
山西的戰略地位還體現在地理位置、軍事意義和經濟條件上。抗戰時期,山西是全國敵后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作為華北的屋脊,山西相對周邊的冀、魯、豫、陜、綏、察諸省具有居高臨下的戰略優勢。對于日軍來說,想要在華北平原站穩,必須占領山西,所以山西也成為中日爭奪的重要前沿陣地。而山西復雜的地形地貌,在敵我力量差距較大的情況下,是我軍開展游擊戰的理想戰場,同時在積累敵后作戰經驗和保護教學安全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山西的特殊性使其成為抗大挺進敵后的首選也在情理之中。表1詳細梳理了抗大總校與分校在山西敵后流動辦學的時空變化。
二、抗大在山西敵后流動辦學的實踐
(一)敵后的生存考驗
抗大在敵后辦學的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危險和困難。處于敵后的抗大缺乏中央保護,又處于日、偽、頑三方的包圍和限制之下,生存環境非常艱難。當時,日本帝國主義面臨的戰爭壓力越來越大,為獲得更多的物資,加強了對淪陷區的掠奪。抗大在山西流動辦學的過程中時常遭到日軍的掃蕩和圍剿,如1939年7月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就曾被日軍調集5萬多兵力進行大規模掃蕩,一分校也因此被迫轉移到太行山南部的山岳地帶。1942年2月,日軍糾集1.2萬余兵力對太行、太岳進行春季“掃蕩”,接連進行“鐵環合擊”“輾轉抉剔”,實行“三光政策”,還慘無人道地施放糜爛性毒劑,殘害根據地軍民。[4]面對日軍暴行,抗大因時制宜,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在百團大戰等戰役中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與此同時,蔣介石集團繼續堅持“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針,除了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打壓中共,甚至還派兵掠奪根據地,中共則在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原則下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斗爭。[5]
除了處境危險,抗大還面臨著物資奇缺的困難。在嚴峻的敵后辦學環境中,抗大最基本的糧食供給主要依靠教職學員參加生產勞動來實現。1943年和1944年抗大總校廣大教職學員響應黨中央“建立革命家務”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先后開展兩次大生產運動,成果豐碩。[6]又如,為響應第一二九師師部的生產號召,抗大六分校的學員們采用了避免與民爭地,利用零散土地種菜的“麻雀戰”。此外上級和群眾也為抗大的糧食供給提供了一定的支持。1941年,晉東南抗大總校突破敵人的封鎖,安排人員輪流到幾十里外的和順縣去背糧。[7]此外,抗大還開展與敵奪糧斗爭作為補充。糧食供給問題的緩解為抗大教育的順利開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除了糧食,抗大還面臨著衣物布匹、學習用品、醫療用品等方面的短缺,經濟困難也使得辦學環境更加惡劣。
然而,困難的環境也密切了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抗大學員節衣縮食、參與生產、救助貧民,幫助群眾搶收糧食和對抗日偽,贏得了群眾的擁護,擴大了我軍的政治影響,樹立了良好的聲望,進一步密切了軍政、軍民關系,也提升了學員、黨員干部的能力。
(二)敵后辦學實踐與特色
抗大重視思想作風建設。抗大挺進山西敵后,繼續開展群眾大會、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保持黨性,肅清黨風,同時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開展整風運動。1942年,七分校進行整風運動,有效地整頓了黨風、學風和校風,使全體教職學員劃清了真假馬列主義的界限,打擊了教條主義,使教學內容更切合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端正了辦校治學的政治方向,對學校的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8]
1. 教學內容切合實際
根據教學任務和方針,抗大以政治課、軍事課和文化課為主干。政治課的內容包括三民主義、政治常識、馬列主義、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日本問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9]當時有些學員文化程度較高,但也受閻錫山影響較深,抗大六分校調整教學內容,加強了對這批學員的思想政治教育。[10]軍事課則側重游擊戰:游擊戰術、連以下之步兵戰術、初步的軍事理論的知識——戰略學以及其他軍事學術上(如筑城、地形,射擊、兵器,特種兵等)必須具備之初步知識。[11]學校教員中也有不少身經百戰的戰士,抗大六分校擔任炮兵教員的是全軍著名的炮兵射擊專家趙章成,教刺殺的是第一二九師有名的刺殺尖子高孚,他們授課時也會適時補充自己的實戰體會。文化方面,曾任抗大總校副校長的滕代遠在1942年7月撰寫了《抗大文化教育試驗教學的幾點經驗》,供抗大諸分校以及其他類似的訓練班、教導隊與組織在職干部文化教育時參考。[12]此外,抗大還會依據學員文化狀況因材施教,如六分校將學員分為中學班、小學班和初小班,對少數學員則安排干部進行重點掃盲。
2. 教學常常與民運、戰斗、生產相結合
客觀來說,由于敵后環境艱苦,抗大學員缺乏教材、安全的學習環境以及充足的學習時間,無法進行系統理論的學習,但抗大趨利避害,利用敵后流動辦學的靈活性,積極參與實踐,如憲改運動、社會文化教育、武裝建設與訓練等。學員趙麥玲就曾回憶抗大啟發女子參加群眾集會抗日的活動。在戰斗中,教員也注重教授學員如何把實際經驗和理論相結合。此外,學員通過參加大生產運動將學習與勞動相結合,很好地實現了教學內容與生產、戰斗相結合。
敵后緊張的局勢迫使抗大加快了人才培養的速度,為此,抗大實行采用靈活學制、開展行軍教育等舉措。[13]由于處在敵后,抗大的學制不同于其他高校,教學周期從6個月至3年不等,具體的課時分配也會根據實際進行調整,因時制宜地壓縮課程以適應敵后需要。有限的課時、緊張的抗日局勢讓抗大更加惜時,即使在行軍時每名學員也都背著“學習牌”,寫上字詞、題目,讓身后的學員在行軍中學習。第六分校黨委還提出背糧和教學相結合的方式,每次背糧前做好教學準備,把背糧當作有計劃的教學活動。除此之外,短時休息時,學員常用木棍在地上練字;長時休整時,教員會上課或者組織學員討論;宿營前,教員組織學員觀察地形,擬定作戰方案,防止敵人突襲。[14]
3. 十分重視應急性人才的培養
首先是軍官,當時中共軍隊雖驍勇善戰但文化水平略低,缺少具有系統理論的將才。對此,黨中央便要求抗大設置戰略課,即使排長也應有戰略思維、全局意識。許多紅軍戰士自愿或在上級指示下到抗大學習,開國元帥、大將中有17人在抗大深造過。其次是干部,由于軍隊擴大,戰爭需要等原因,我軍一度出現軍政干部不足的情況,抗大采用非常規性人才招收方式,招收學員門檻較低,除政治標準這個硬性條件外,其他標準較為寬松,極大地滿足了戰時需求。此外,抗大還設立特科營培養軍事技術干部,組建防化訓練隊應急對抗日偽毒氣攻擊,等等。
4. 積極開展文體活動,秉持著樂觀主義精神
總校文工團認真貫徹黨的文藝方針,用話劇、京劇、活報劇、歌舞等多種文藝形式創作并演出了大量富有戰斗性、藝術性的節目,極大地充實了軍民的精神生活。[15]體育鍛煉方面,在1941年9月18日到27日八路軍一二九師舉行的全師運動大會上,六分校學子在射擊、投彈等項目上斬獲佳績。在日常生活中,抗大也經常開展排球、集體操和爬山等體育運動,與軍事訓練相結合,豐富課余生活的同時也增強了學員的身體素質。
三、抗大在山西敵后流動辦學的經驗
抗大總校與各分校在山西敵后流動辦學,直接置身于敵后抗日戰場,為抗大的教學提供了廣闊的課堂和豐富的營養,抗大在艱難探索中逐漸形成了其獨特的辦學經驗。
1. 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
這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于民族而言,抗大與當時四萬萬同胞一樣,堅持抗日的正確主張,挺進敵后與敵寇周旋是抗日救亡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是造就抗日軍隊中之初級軍事政治的干部[16];二是于黨而言,抗大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高等學府,堅持黨的領導,學習馬列主義,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采用《黨的建設》《論持久戰》等教材與讀本,提高學員的政治覺悟,在政治思想上與其他學府涇渭分明。正是由于抗大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重視思想教育,才培養出了一大批對黨忠誠的干部,與群眾保持緊密關系,使得抗大在敵后的艱難環境中得到發展。
2. 堅持理論聯系實際
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列主義的重要原則,也是整風運動的一大主旨。在教學上,抗大自成立以來便堅持這一方針,始終堅持因材施教等教育理論,對知識基礎薄弱的學員,著重“先講必要的前提,然后才來發問……在教員誘導之下,從問題的各個側面,了解到問題的全面”[17];對理解能力較強,但缺乏實際經驗的知識青年,采取講演式和啟發式為主,問答式為輔的教學方法;對于斗爭經驗豐富、理論基礎扎實的干部,則開展研究性自學。[18]除此之外,抗大堅持生產與學習相結合,開展大生產運動。在整風運動后,中國共產黨不僅克服了理論上“左”傾等錯誤,也深化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觀念,為理論與實踐更好地結合打下基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還有一個重要表現便是教學、戰斗有機結合,抗大將戰爭中的經驗與課堂緊密相連,很多學員學習的過程其實就是參與革命工作的過程,學員在這種有機融合中加速成才。
3. 堅持靈活的流動性辦學
從教學方式的靈活性來看,抗大采取“向一切自然物學,向工人學、向農人學,向知識分子學”的措施,從啟發式到研究式、實驗式,學員通過自學與討論配合課堂獲得了長足進步。同時,從教學地點的流動性來看,抗大分校經常因為國民黨頑固派和日偽軍的侵擾而不斷轉移辦學地點,艱險不僅是抗大發展的壓力與阻力,也是其發展的動力,其利用教學方式的靈活性、教學地點的流動性等特點,將戰爭中的經驗與課堂緊密相連,為新的戰斗做好準備。
四、抗大在山西敵后流動辦學的意義
在敵后辦學的過程中,抗大創造性地總結了許多制度、經驗、方法,開辟了一條在戰爭環境下培養人才的新途徑。抗大在山西辦學的7年時間里,共培養人才4萬余人[19],他們在山西敵后環境中學習、戰斗、生產,鞏固了山西敵后抗日根據地,也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很多抗大學子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先鋒人物,一些擔任了國家的領導干部,還有一些成為教育、文化、藝術、新聞及科研領域的專家學者和社會名流。[20]
抗大既是培養干部的陣地,也是與敵周旋的先鋒。在山西敵后,抗大的辦學與戰斗已經融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參加八路軍的對敵斗爭、鞏固敵后根據地、殲滅敵軍、收復失地到對抗掃蕩、幫助群眾、保護糧食、協助轉移等方面,抗大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如紅嶺戰役、三十畝地戰斗、河凹反襲擊戰斗等,都是鮮活的例子,加速了抗戰勝利的歷史進程。
抗日戰爭年代,山西支持了抗大的生存、發展,而抗大也為山西留下了許多寶貴的遺產。抗大挺進山西是在客觀環境下積極主動的嘗試,這種嘗試減輕了邊區的壓力,擾亂了日偽的進攻,回應了抗日的潮流,也為抗大本身的生存發展創造了條件。山西多山的地形也為抗大的教學與敵后斗爭提供了便利,使得抗大能夠靈活地與敵軍周旋。而且,抗大在山西的敵后辦學也為其在河南、江蘇等平原地帶進行敵后辦學積累了經驗。可以說,山西是敵后辦學的前沿試驗田,在抗大敵后辦學模式的形成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抗大也為山西培養了大量具有先進政治意識和軍事理論的革命人才,如劉鼎、李紹璞、肖慶云等,不僅推動了山西物質層面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山西地區的封建殘余和落后思想,促進了當地精神層面的解放,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等先進理論與黨的主張,更是在解放山西與當地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五、結語
抗大的敵后辦學經驗也深刻影響了現代教育。抗大在辦校治學實踐中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將戰斗實踐與辦學治學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教育理論。抗大的教育教學模式深刻地影響了當今高等教育,包括國防大學在內的眾多高等院校都承襲了抗大的教育理論,傳承了抗大的教育方針和校風。同時,抗大精神也為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借鑒,指引了正確的辦學方向。
參考文獻:
[1] [2] [3] [4] [5] [6] [8] [14] [18]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14,28,4,238,115,171-172,249-250,240,364.
[7] [15] 周來聚.戰斗在太行山上的抗大文工團[J].黨史博采(紀實),2015(12):52-54,58.
[9] [11] [16] 羅瑞卿.抗大工作的檢查總結與今后工作(續完) [J].八路軍軍政雜志,1939(6):61.
[10] 劉忠.回憶抗大六分校[M]//院校·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324.
[12] 《滕代遠傳》寫作組.滕代遠傳[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258.
[13] 胡興臣,焦秀鑾.少將張衍[J].黨史縱覽,2001(6):22-24.
[17] 海燕.抗大動態[M].陜西:動員社,1938:76.
[19] 郭新虎,郭御劍.抗大辦學在山西[J].黨史文匯,2013(2):48-51.
[20] 殷學繼.論抗大一分校敵后辦學的歷史功績[J].臨沂大學學報,2012(1):110-114.
基金項目:2021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項目“山西地區‘抗大’遺址調查與研究” (202110118001),2021年度山西省藝術科學規劃課題“山西抗日根據地廉政文化建設研究” (2021A080),山西省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1年度規劃課題“山西抗日根據地科學教育研究” (GH-2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