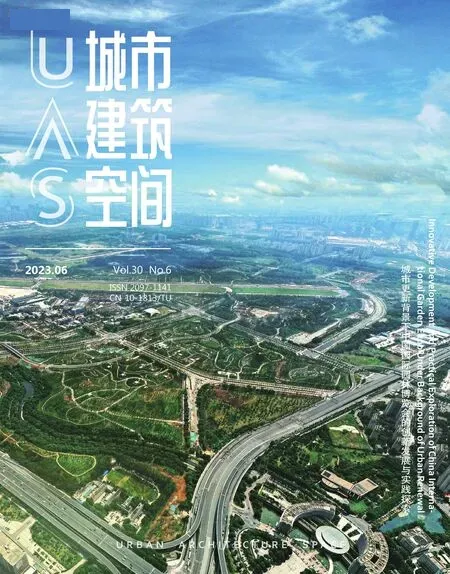園博會展園生態景觀系統營建研究
——以第十四屆中國(合肥)國際園林博覽會展園為例
牛萌 NIU Meng
第十四屆中國(合肥)國際園林博覽會展園是城市更新背景下以“生態優先,百姓園博”為主題的城市民生建設工程。為實現“永不落幕的百姓園博,生生不息的城市森林”目標,其生態景觀系統營建突破傳統意義上的植物景觀專項設計,通過多樣生境再造、文化景觀再現、生態系統循環將生態系統構建、文化內涵表達與植物景觀營造深度融合;運用土壤修復改良和植物景觀與海綿功能融合的生態技術方法織補生態空間,探索城市生態基礎設施的價值和未來意義。
生態景觀;生境營造;文化植物景觀;土壤改良;海綿功能
0 引言
中國國際園林博覽會(以下簡稱“園博會”)是我國園林景觀行業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盛會,旨在傳承我國優秀傳統園林文化,服務現代城市建設。園博會經歷了從單純的園藝展示向關注城市生態文明建設轉變,如園林城市、生態園林城市、綠色發展、城市雙修、海綿城市、公園城市等歷屆園博會主題均反映出我國城市建設的發展歷程。第十四屆園博會申報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對《中國國際園林博覽會管理辦法》(建城〔2019〕79號,以下簡稱《辦法》)進行了修訂,《辦法》中明確提出“園博園的建設應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原則。因地制宜保護自然風貌和山水格局,改善提升城市生態和人居環境;要充分利用新理念、新方式、新技術,鼓勵通過生態修復方式建設園博園”。合肥作為《辦法》修訂后首次申報園博會的城市,充分考慮了展園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踐行新發展理念,打造的綠色展會。
1 場地概況
第十四屆中國(合肥)國際園林博覽會展園(以下簡稱“合肥園博園”)選址于合肥廢棄的駱崗機場,現存長3000m的機場跑道、108棟建筑及大片鋪裝,硬質空間多、藍綠空間少。故合肥園博園以“生態優先、百姓園博”為主題,以城市更新為手段,營建園博園生態景觀系統。除機場跑道及展園空間外,其綠地面積達168hm2,但多分布于北部片區,占70%。合肥園博園生態景觀系統營建既包括植物景觀設計,還包括生態基底構建、多樣生境再造、經典文化再現、生態系統循環等。
為實現“永不落幕的百姓園博,生生不息的城市森林”目標,以“生態為底、文化為魂、植物為介”為設計原則,在規劃設計之初將生態系統構建、文化內涵表達與植物景觀營造深度融合,營建合肥園博園生態景觀系統[1]。以植物群落為核心,構建多樣生境;以植物景觀為媒介,展現文化風韻;以生態措施為手段,實現綠色循環。
2 生態景觀營建
2.1 生態本底保留
合肥園博園場地內現狀用地類型復雜,包括農田、林地、河流、村莊、辦公區、宿舍等,因此現狀植物眾多,經統計胸徑在10cm及以上的喬木達12891株,尤其在原機場辦公樓和宿舍區,分布大量胸徑在20cm以上的喬木,如香樟、玉蘭、水杉、雪松等。村莊周邊則分布成片的楊樹林、構樹林及眾多鄉土樹種,如烏桕、桂花、重陽木、楸樹、廣玉蘭等。本著“生態為底”原則,設計團隊勘測普查了園內所有木本植物,為每株木本植物建立“一圖一表”,采用“伐、留、改、移”的方式保留全園喬木,形成合肥園博園現狀喬木保護檔案。最終保留喬木7713株,移栽喬木1037株(見圖1)。
2.2 多樣生境營造
合肥園博園本質上是城市更新項目,用地紅線包含公園綠地、商業用地、道路交通設施用地、市政公用設施用地等,故其并非單純的城市公園。基于此,可將其看作城市綠地系統,外部是以自然生態空間為核心的區域綠地空間,結合山水格局營建山地、谷地、坡地、河湖濕地四大類生境;內部集中建設區可看作城市綠地,進而構建城市社區生境(見圖2,3)。

2 合肥園博園綠地系統結構

3 合肥園博園生境類型布局
結合5類生境將群落結構細分為8種植物景觀類型[2],包括彩葉林、果林、花灌叢、杉林葦蕩、花海、花溪、花境花園及疏林草地。彩葉林、果林、花灌叢、杉林葦蕩為生態主導型生境,以鄉土植物為主,構建近自然、低維護,兼具觀賞價值的林地,以提升多樣性。花海、花溪、花境花園為景觀主導型生境,以開花木本或鄉土宿根植物為主,提升景觀觀賞價值。疏林草地為游憩主導型生境,營造疏林草地、五彩花海景觀,并為鳥類、昆蟲提供蜜源和棲息地(見圖4)。

4 合肥園博園植物群落類型
2.3 植物種植優化
“生態園博”在設計理念上突出生態,而城市中的生態需與百姓需求相結合,更需因地制宜。項目組調研發現市區園林綠化存在2個方面的問題:①常綠植物占比高,植物種類少,合肥城市公園常綠與落葉植物數量比約5:5[3],植物景觀季相變化不明顯,與長江中游城市物種豐富、季相多變的特點不相符;②植物景觀類型單一,景觀同質化,特色植物景觀、規模化植物景觀與精致園林景觀較少。景觀類型以“喬木+常綠灌木”為主,花海、草坡、色葉林等較少[4]。
為實現生態景觀營建,將常綠、落葉植物數量比調整為4:6,模擬合肥自然生態特征,大幅增加植物種類,尤其是鄉土植物、落葉喬木、花灌木及宿根類草本植物。全園鄉土植物種類占比達70%,最大程度保證了植物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3 文化植物景觀營造
在歷史演進中,安徽省特定的區位與環境使其受中原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和吳越文化等影響形成三大地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地域特征的不同造就了自然人文景觀的差異,如黃山奇松、天峽杜鵑、廣德竹海、懷遠石榴、祁門紅茶、亳州白芍、徽州梅花等。
合肥園博園植物景觀塑造融合傳統園林意境和徽州文化內涵,依托“徽山皖水”的山水格局,塑造“一軸一帶,四區十景”的植物景觀格局(見圖5)。一軸為合肥園博園的主入口區——園博大道;一帶為串聯全園的主園路——錦秋大道;結合安徽文化特色,構建安徽苑、田園詩、茶花丘、芳菲院4個景觀主題區;結合北部的“五峰兩谷”、錦繡湖、如意湖和園博小鎮,利用安徽本土植物如梅花、菊花、竹子等,打造松梅嶺、攬翠峰、杜鵑坡、胭花坪、群芳谷、茶花丘、菊花臺、海棠灣、百花園、盆景園十大植物景觀(見圖6~11)。

5 合肥園博園植物景觀格局

6 松梅嶺效果

7 攬翠峰效果

8 杜鵑坡效果

10 群芳谷效果

11 茶花丘效果
4 生態措施
4.1 專屬土壤改良配方
由于合肥土質黏性大,滲透性較差且場地內存在大量建筑垃圾,為保證植物栽植成活率及持續健康生長,需對全園土壤進行改良[5]。通過向當地專家咨詢、場地內外土壤檢測、樣地試種等方式,制定了針對合肥園博園的土壤改良配方及評估指標,形成“檢測—配方—評估”全流程技術方法(見表1)。

表1 合肥園博園土壤評估指標
根據土壤條件檢測,提出適宜場地的土壤改良配方,采用有機肥取代泥炭土(泥炭土為不可再生資源),并建立合肥園博園有機肥準入標準(見表2)[6]。針對不同植物類型給出特定改良配方,喬木及單株栽植的灌木按照樹穴規格體積摻拌20%有機肥及10%粗砂,摻拌后回填樹穴。片植灌木按照深50cm種植土層進行土壤改良,根據該體積計算有機肥和粗砂量,旋耕摻拌20%有機肥及10%粗砂;草本地被按照深30cm種植土層進行土壤改良,根據該體積計算有機肥和粗砂量,旋耕摻拌20%有機肥及10%粗砂。而針對杜鵑、映山紅等特殊種類,根據合肥現有種植地土壤條件調整配方[7],建議攜帶原土種植。專屬土壤改良方案有效解決了合肥園博園土壤改良問題,減少換土量約40萬m3,節約泥炭土8萬m3。

表2 合肥園博園有機肥準入指標
4.2 植物景觀與海綿功能融合
合肥園博園的海綿系統與地形豎向融合,以綠色雨水設施為主,主要包括雨水花園、旱溪、植草溝、前置塘等,干濕情況不一,且需滿足區域雨洪調控功能。因此雨水設施水位變化較大,干濕交替區域范圍較廣,一方面植物景觀要發揮雨水凈化、滯緩功能;另一方面要兼顧景觀效果,實現干濕景觀的自然過渡,達到雨水設施的“隱形化”。
連通渠1是園內最長的雨水傳輸設施且為旱溪,長1280m,寬8~28m,坡度1:2~1:4,根據水位變化進行植物設計,由外至內可分為邊緣區、緩沖區和蓄水區(見圖12)。邊緣區為坡岸以上區域,基本沒有淹沒風險,主要通過植物配置與周圍環境融合;緩沖區為旱溪坡面區域,植物種類以草本為主,在坡度<1:3的區域可適當種植耐水濕喬木;蓄水區為旱溪的季節性過水區域,存在淹水期,植物選擇應以濕生草本植物為主[8],且過水斷面草本植物高度不宜超過過水區域(見表3)。

12 雨水傳輸設施植物配置斷面
園內主要調蓄水體為園博小鎮的如意湖,為常年有水區域。根據合肥園博園海綿目標,如意湖水位設計包括常水位、豐水位、極限水位等,按照植物與水體位置關系從內至外可分為深水區、淺水區、緩沖區、泛洪區和邊緣區(見圖13)[9]。

13 植物與水體位置關系13a平面13b剖面
深水區深0.5~1.8m,應選擇根系發達、凈化能力強、耐較深水淹的水生植物,如浮水類與沉水類植物;淺水區深0~0.5m,一般選擇根系發達、凈化能力強且耐水淹的水生植物,如濕生類與挺水類植物;緩沖區是在常水位和豐水位之間形成的消落帶,屬于干濕交替地帶,季節性有水,需結合駁岸坡度選擇濕生植物形成濕生植物群落,自然過渡水陸交接區域;泛洪區位于豐水位和極限水位之間,常年處于無水狀態,應選擇長期耐干旱、短期耐水淹的植物,如城市中大多數草坪、常見花草和木本,抗性較強的觀賞草;邊緣區位于極限水位之上,基本不受雨水影響,可根據場地景觀條件選擇植物種類(見表4)。

表4 常用濱水植物
5 結語
合肥園博園采用生態景觀系統營建手法將生態修復、文化再現、景觀建設融合,并通過土壤修復改良和植物景觀與海綿功能融合的生態技術方法織補生態空間,提出城市綠地的價值和未來意義。園博園本身并非城市事件,而是城市重要的生態基礎設施,作為城市生態文明發展的載體,既是美化城市的錦上之花,又是反哺城市生態的雪中之炭,讓其為城市提供持續的綠色開放空間,使生態文明建設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造福子孫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