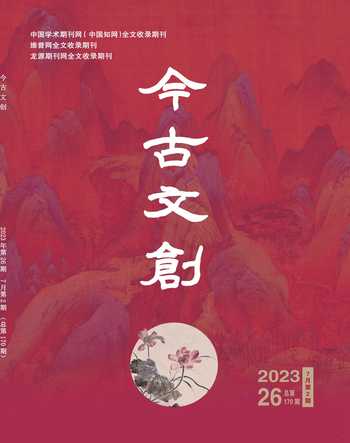鄉土中國:《白鹿原》與《大地三部曲》比較研究
【摘要】陳忠實的《白鹿原》與賽珍珠的《大地三部曲》都刻畫了鄉村土地上的家族變遷,其中存在多組類似但不同的角色,而這些不同展現了兩位作者在創作目的、對待傳統與現代的態度和塑造女性成長的方式等方面的差異:陳忠實的創作旨在傳達對歷史與文化的反思,而賽珍珠則更側重于展現中國農民的真實生活;陳忠實希望從傳統走向現代,而賽珍珠更傾向于回歸傳統;陳忠實將女性的成長歸因于時代,而賽珍珠則從女性自身需求的角度建構女性的成長。這些差異都與兩位作者的身份、文化背景、性別等因素息息相關。
【關鍵詞】《白鹿原》;《大地三部曲》;鄉土;傳統;女性成長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26-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6.010
陳忠實的《白鹿原》與賽珍珠的《大地三部曲》雖隔著半個多世紀的時光,但都描述了鄉村土地上的家族在傳統與現代交替時期的變遷。《白鹿原》描述了白、鹿兩大家族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與斗爭,刻畫了一段恢宏的鄉村歷史;《大地三部曲》則介紹了王家三代的不同人生,展現了真實的農民形象以及他們的家庭生活。本文將《白鹿原》與《大地三部曲》進行對比,旨在通過分析三組類似但不同的人物形象探討兩位作者創作目的、對待傳統的態度和塑造女性成長方式的不同以及造成這些差異的根本原因。
一、鄉土的堅守者:白嘉軒與王龍
陳忠實筆下的白嘉軒與賽珍珠書中的王龍都是鄉土的堅守者。在《白鹿原》中,當鹿子霖等人追求政治權力與官職時白嘉軒選擇耕種和處理家族事務,哪怕腰被打斷,他也仍然不顧阻攔下地耕種。而王龍更是將賣地看作是家庭末日,他曾多次阻止兒子的賣地行為,并表示“我們從土地上來的……我們還必須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們守得住土地,你們就能活下去” ①。
但兩者守土行為的本質卻大不相同。對白嘉軒而言,他堅守的是“耕讀傳家”,而王龍僅僅是守衛土地本身以及土地帶來的財富。所以在家族興盛后兩人做著不一樣的事情。在《白鹿原》中,白嘉軒為整個白鹿村打算,他帶領村民修祠堂,辦學堂,找朱先生寫下鄉約約束村民,使整個白鹿村“從此偷雞摸狗摘桃掐瓜之類的事頓然絕跡,摸牌九搓麻將抹花花擲骰子等等賭博營生全踢了攤子,打架斗毆扯街罵巷的爭斗事件再不發生” ②。而王龍只是為自家謀劃,利用財富享樂。他去“富人享受、闊少爺尋歡作樂的地方” ③,娶了荷花做二房,甚至晚年跟兒子王虎搶奪丫鬟梨花。
這種守土行為本質的不同源于兩位作者不同的創作目的。陳忠實想要借白家、鹿家在白鹿原上的生活展現時代的變遷和他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所以他筆下的人物大都與歷史事件有著明晰的聯系,同時也體現著某種文化。以白嘉軒為例,他被塑造成儒家文化推崇的“仁義之人”,但正是這樣一個“仁義之人”會為了“白鹿精靈”算計別人,會為了維護所謂的禮不向田小娥低頭,哪怕代價是死去更多的人。就此而言,白嘉軒不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而是儒家文化在世間的象征,他行為的錯與對反映著儒家文化的好與壞。而賽珍珠創作《大地三部曲》是為了借王家人的生活展現中國農民的真實生活,讓來自最底層的農民“如同他們自己原來一樣的真實正確地出現” ④。所以她筆下的王龍更符合當時對底層農民的定義:只顧得上自己的生活,有著自己的道德觀念,很容易被欲望操縱。也正因為賽珍珠將重點落在了人的身上,《大地三部曲》中的歷史事件不像《白鹿原》那般頻繁地出現,而是退居次位,為人物服務。
此外,兩位鄉土守衛者與土地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
在《白鹿原》中白嘉軒一直堅守土地,但在最后,曾經為自己得到有“白鹿靈魂”土地沾沾自喜的白嘉軒表達了對于自己算計鹿子霖獲得風水寶地的懺悔,這意味著他開始反思自己對待土地的態度。而《大地》中王龍與土地之間的關系更是多次發生變化。最開始他將土地視若珍寶,腦子里天天“想他的田地,想田里的麥子,想要是下了雨收成會怎么樣” ⑤。哪怕是逃荒到江蘇他也一直惦記著回去種地。后來發家后他雇人種地,但一段時間后“一個比愛情更深沉的聲音在他心中為土地發出了呼喚” ⑥,他又開始種地。但在老秦死后,他又對地里的活感到厭倦,并去城里住。但在死亡前,他卻意識到,雖然他已經離開了土地,安家在城里,但他的根仍然在那里,所以他選擇回到老房子并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這種與鄉土的關系本質上反映著對傳統的態度,因為“對鄉土的眷戀難舍某種程度上即意味著對儒家文化的服膺與愛重” ⑦。換句話說,守土是對傳統的堅持,而離土是對現代的追尋。白嘉軒對于土地的堅守與他封建形象高度契合,但最后他對自己守土行為的反思暗示他開始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傳統,邁出了走向現代的第一步。 而在王龍身上,守土與離土交替發生,在這個過程中他意識到自己離不開土地,這就意味著王龍在傳統與現代間徘徊,最終還是回歸了傳統。
二、鄉土的逃離者:白孝文與王虎
作為白嘉軒的長子,白孝文從出生就注定成為族長,擁有一眼望得到頭的人生。王虎亦是如此。他雖不是父親王龍的長子,但卻被定為是留在家中照管土地的人,甚至因此被剝奪了讀書的機會。但兩位土地繼承人最終都賣掉了土地,逃離了既定人生,選擇追逐權力,雖然初衷與程度有所不同。
對白孝文而言,賣掉土地是迫不得已。因為田小娥的引誘,他被傳統禮教壓抑的欲望顯露出來,開始和別人的妻子廝混,抽大煙,從高高在上的族長變成和別人搶飯吃的乞丐。面對這樣的局面,為了生存下去,白孝文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土地,換取銀元抽大煙。與白孝文不同,王虎是主動出售土地。因為與父親之間的矛盾,王虎一直對土地很是厭惡。所以在分家產時他明確地說:“我不要房產也不要地!年輕時,爹總想叫我務農,可我不干,我對地早就膩透來了!” ⑧
但戲劇的是,被迫賣地的白孝文最終真正地逃離了土地,而主動賣地的王虎卻始終與土地藕斷絲連。在離開土地從政成功后,白孝文提出回鄉祭祖,但他的目的是為了洗刷過去的屈辱,而非思念這片土地,所以祭祖結束后他便急匆匆地離去,甚至在離鄉途中發出感嘆“誰不走出這原誰一輩子都沒出息” ⑨。由此可見,白孝文已經將鄉土視作阻礙,對于鄉土的眷戀和對于“耕讀傳家”的推崇在他心中已不復存在。與白孝文賣完土地再去從政不同,王虎權力的獲得離不開土地。他通過賣地獲取資金購買槍支彈藥、為士兵提供吃穿,就連出去混的目標都是成為整個領地的主人并擴大自己的領地,甚至最后死在了父親王龍的那間土屋,埋葬在他曾經厭惡的那片土地上。
正如前文所提到,對鄉土的眷戀本質上是對傳統的堅守。白孝文從推崇“耕讀傳家”到賣掉土地從政成功地轉變展現了陳忠實對于傳統文化的態度:不做任何改變的堅守是錯誤的,傳統必然朝著現代發展。王虎對土地一直有著恨意,但又不得不依靠土地,最終還是回歸土地的懷抱,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賽珍珠對待傳統的態度:傳統總是被批判,但人們卻無法真正擺脫其影響,最終還是會選擇回歸。
這種對于傳統的不同態度其實與兩位作者的身份有著很大的關系。陳忠實是一名中國作家,而賽珍珠是在中國生活的美國作家,他們的文化背景、讀者群體都大不相同。對于陳忠實而言,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正朝著現代化大步邁進,傳統文化衰落已是既定事實。面對這樣的局面,他只能為儒家文化的發展指明“變得現代”這個方向。但賽珍珠雖成長于中國,卻在美國接受教育,她已經見證現代化的弊端,意識到傳統文化并非毫無價值,所以她對待傳統更加包容。
另外,陳忠實面對的是對儒家文化熟知且持批判態度的中國讀者,但賽珍珠作品的主要讀者是西方讀者,“在那個時期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造成精神匱乏,西方不少人便倡導起返璞歸真, 回歸原始” ⑩。不同的讀者期望也導致兩位作者在書中表達了不同的對待傳統的態度。
三、鄉土的邊緣人:吳仙草、白靈與大太太、梅琳
在《白鹿原》與《大地三部曲》中,與鄉土有著直接聯系的大多為男性,女性從未擁有屬于自己的土地,最多起輔助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對于男性的依附和從屬。但兩部小說不僅僅停留于此,還通過對不同代女性的描寫展現了女性的成長。
吳仙草是白嘉軒的第七任妻子,她為他帶來了子嗣與財富,與他構成了儒家文化推崇的生活圖景——男耕女織。對于白家人來說,她是賢妻良母,“能夠井井有條地處置一切應該由女人做的家務” ?。她很少違背丈夫的計劃,唯一一次也是想替白嘉軒擋災。而白靈是白嘉軒唯一一個活下來的女兒,深受他的喜愛。白靈與母親相比擁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不裹腳,甚至可以去學堂學習,但這種自由是在白嘉軒覺得可行范圍內。當超出范圍時,例如白靈想去城里念書,這種自由就會被限制。但幸運的是,白靈敢于反抗自己的父親,也不害怕被家族拋棄,她逃到城里上學,參加黨派,拒絕包辦婚姻。
但從吳仙草到白靈并非女性自發的獨立與反抗,而是時代的推動。白靈因為在城里接受新式教育,意識到國家處于危難之中,需要自己盡一份力,所以她會因為給戰死的人們抬尸首而反抗父親。另外,她的成長離不開男性角色的引導。最開始她選擇國民黨,因為鹿兆海又改投共產黨,與鹿兆鵬接觸后她堅定自己的信仰并前往延安。由此可見白靈選擇什么政黨、做什么事情取決于她目前接觸的環境與人,離不開他人的引導。
王虎大太太與吳仙草一樣承擔著生兒子的使命,但卻只生下了女兒,逐漸被丈夫忽視,接受過教育的她選擇帶著女兒前往海濱大都市,想要把女兒培養成新時代的女性。而梅琳是王虎大太太的養女,是一個勇敢沉著的姑娘,很有自己的想法。她很少在乎與依靠男人,將愛情置于事業之后,愿意為自己的學習、工作付出很多。
相較吳仙草,大太太敢于違背丈夫的計劃,幫助王源逃離包辦婚姻,有自己的錢財,愿意傾聽并支持年輕人的想法,已然是一個新式女性。但她與梅琳相比缺少了對自我需求的追求。王源在美國時曾將大太太與師母進行對比,他表示“她們之間的確存在著區別,因為這位太太的神情中有種靈魂上的充實和滿足,而他家中的太太卻沒有。這一位仿佛已在生活中獲得了心中欲求的一切,而哪一位并沒有” ?。這說明大太太其實有自我需求,但她卻沒有將自我需求置于第一位,而是花更多的時間去為女兒、兒子制定培養計劃。而梅琳與之不同,她更看重自身的需求,清醒地知道自己想成為什么,目前現階段什么更重要,會將自我成長置于第一位。
所以筆者認為陳忠實對于女性成長的構建是從男性視角出發。他將女性放置于時代洪流中,讓時代的變遷與他人(主要以男性角色為主)引導女性轉變思想,有所成長。而賽珍珠是從女性本身出發,她將女性追求自身需求作為成長的標志。這兩種不同的視角是由作家性別決定的。此外,文化背景也有影響。儒家文化對集體的推崇讓陳忠實將女性群體置于整個社會中去觀察,而賽珍珠因為西方對于個體的推崇會將女性群體單獨觀察,淡化男性對于女性的影響。
四、總結
《白鹿原》與《大地三部曲》都刻畫了許多與土地有著緊密聯系的角色,其中存在多組類似但不同的角色。這些差異反映了兩位作者不同的創作目的、對于傳統與現代的不同態度以及他們對于女性成長的不同認識。
首先,對陳忠實而言,白家與鹿家的故事是為了展現時代的變遷和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所以《白鹿原》中的角色大多參與了重要歷史事件,也是刻畫為儒家文化的象征。但賽珍珠的創作目的是展現真實的中國農民生活,所以她筆下的角色更加貼近現實,時代背景也只是在人物口中被隱晦提及。
其次,《白鹿原》中的鄉土守衛者白嘉軒最后開始反思自己對于土地的堅守,而他的繼承者白孝文更是徹底逃離了土地,但《大地三部曲》中守衛者王龍數次離土最終又回歸土地,兒子王虎雖然厭惡土地卻沒辦法完全擺脫土地,這樣設置反映了兩位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陳忠實是希望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走向現代,但賽珍珠卻希望可以回歸傳統,這是為了應對浮躁的西方現代文化。
最后,兩位作者的性別和文化背景也決定著他們筆下女性成長的塑造也不一樣。陳忠實將女性的成長歸因于時代的推動,她們或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反抗,是時代裹挾著她們前行,但在賽珍珠筆下,女性的成長是因為她們意識到自我的需求并將其置于第一位,盡自己的努力去滿足。
注釋:
①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頁。
②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頁。
③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頁。
④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⑤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頁。
⑥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頁。
⑦周明鵑:《儒家文化視域下的〈白鹿原〉》,《中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3期,第170頁。
⑧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頁。
⑨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頁。
⑩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
?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頁。
?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791頁。
參考文獻:
[1]陳忠實.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2]賽珍珠.大地三部曲[M].王逢振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
盧施琰,南京理工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