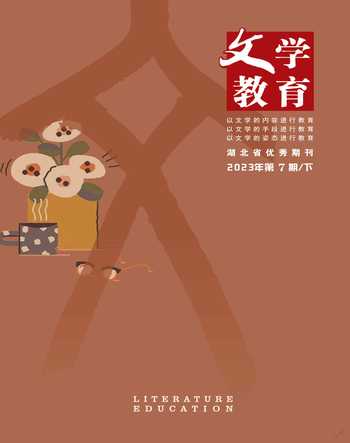論作為文化產業的網絡玄幻小說
張莉
內容摘要:探討伴隨網絡發展的一種類型文學——玄幻小說興盛與貧血的原因,并通過小說人物與情節結構的形式分析來揭示其作為文化產業與當下意識形態的同構性。
關鍵詞:玄幻小說 想象 貧乏 意識形態
訓練有素的演員與觀眾究竟怎樣,《楚門的世界》已經為我們揭示了。楚門從出生起便生活在一個海濱小城,小城卻是一個龐大的攝影棚,周圍的人都是演員,而主角卻是楚門自己——一位不由自主的演員。楚門的世界無疑是個虛假的世界,但這個世界被作為公開播放的電視劇每天都在繼續。制作這個世界的電視公司卻恰恰打著真實的招牌來吸引觀眾,日復一日的重復播放,終于,觀眾習慣了收看這個電視劇,并將之作為生活的一部分。楚門的世界內外都不過是電視公司所掌控的,無論楚門還是觀眾都處于不由自主的零件狀態,都處于電視資本為他們指定的固定位置,正如霍克海默等人的斷言“整個文化工業把人類塑造成能夠在每個產品中都可以不斷再生產的類型”①。先進的技術如電影、廣播、網絡在資本的操縱下每天都在輸出種種意識形態,讓人們習以為常,并再也離開不了。看看我們周圍,《喜洋洋與灰太狼的故事》總是以灰太狼“我還是要回來的”為結尾,《越獄》的主人公總是在進出監獄,冗長的劇情同廣告一樣每天都在引誘著日漸貧乏的大眾。
任何先進媒介的產生,都潛在的影響著藝術的制作與接受,在技術更新頻繁的時代它經歷著怎樣的命運。我們的時代還是機械復制的時代,本雅明早已指出攝影等復制技術的飛躍,已改變了藝術生產的方式,人們感受藝術作品的方式也因此變化,從原來少數人的膜拜到大眾的隨意消遣②。本雅明不無感傷的懷念傳統藝術所具有的原真性或光韻,到霍克海默與阿道爾諾那里,大眾批判理論更為激烈,認為現代技術與經濟已經將藝術納入了工業,藝術實現了標準化和大眾生產,“一切業已消失,僅僅剩下了風格”,這里所謂的風格是貶義的,即“具有替代性特征的一致性”③,而藝術的個性與創造力蕩然無存。經歷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技術大爆炸的詹明信(另譯詹姆遜),不同于上述法蘭克福學派經歷法西斯戰爭的悲愴與失望,能坦然面對技術所造就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特征,他認為個人的主體性消失,真正個性的“風格”已經消失,“拼湊(pastiche)作為創作方法,幾乎是無所不在的,雄踞了一切的藝術實踐”,所謂“拼湊”,即是“憑借一些昔日的形式,仿效一些僵死的風格,透過種種借來的面具說話,假借種種別人的聲音發言”④。詹明信揭示了這一藝術特征的多種可能性,“這表示當代或后現代主義藝術將成為別具一格的藝術;甚至,這也表示它的基本信息之一將關系到藝術和審美的必然失敗、新事物的失敗,以及囚禁于過去之中”⑤。
本雅明等法蘭克福學派在他們的年代悲觀的看到技術超越人類承受的范圍成為了極權統治的邪惡工具,詹明信幸運的經歷了技術爆炸帶給現代人的且喜且憂的復雜的未來。我們必須看到,社會發展多元化的發展,為藝術提供廣闊的空間,無論嚴肅藝術抑或通俗(輕松)藝術都面臨著繁榮與貧乏,而對于大眾來說,輕松藝術更具魅力,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大眾文化的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性,盡管它不盡如人意。之下我就新產生的一種類型小說——玄幻小說,來探討網絡技術與文化產業的影響,探討這類小說的興盛與貧血,并通過小說人物與情節結構的形式分析來揭示玄幻文學自由想象的背后所折射的虛假意識形態。
玄幻小說的興起不過十年,廣義上是指連載形式憑借網絡存在的包容大量幻想材料的“架空”小說⑥,從原創文學網站到紙質出版物的發行,它已經取代了武俠小說的通俗文學地位。其產生的背景是互聯網的發展,這一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創作與接受方式,網絡為寫手提供自由書寫的平臺,每個觸網的人都可能成為潛在的作家,而作品也能不受限制的及時為大量讀者接觸。玄幻小說脫胎于傳統武俠,受黃易小說、西方奇幻小說、日本動漫等直接影響,因對材料的極大包容性,為寫手提供極大的想象空間。如詹明信所言,“拼湊”手法作為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特征,“從世界文化中取材,向偌大的、充滿想象生命的博物館吸收養料,把里面所藏的歷史大雜燴,七拼八湊地炮制成為今天的文化產品”⑦,這也明顯的體現在玄幻小說上,其取材縱橫古今中外,傳統神話仙話、西方傳奇小說、日式動漫、科幻等傳統元素均進入寫手的視野,正如網上所言“它的創作原則就是無原則,它的幻想基礎就是無基礎”。
同八十年代一樣,進入新世紀后,大眾仍處于閱讀的饑餓狀態,網絡文學卻填充了這一空白。現實的嚴肅文學傳播不廣,因其過于先鋒的形式實驗或拘謹的主題探索,而使其僅僅局限于少數的圈子中,同時通俗文學還停留在武俠的金庸時代,而網絡為文學的新變提供技術支持。大眾需要新鮮的想象與廣泛的知識,玄幻小說通過一種輕松的形式滿足了這種需求。玄幻小說有對古老的想象,將傳統神話、仙話熔于一爐,取材《山海經》、《搜神記》以至傳統章回小說《封神演義》、《西游記》等,如《佛即是道》、《仙路煙塵》、《誅仙》,上下縱橫,規模宏大;有對全新空間的設計,如《小兵傳奇》的未來太空戰,《師士傳說》的機甲,沒有硬科幻的言之有據,卻不乏想象與刺激;有對各種專門知識的介紹,如《鬼吹燈》的盜墓,《活色生香》的電影藝術,《被上天詛咒的天才》的商戰,幾乎涵蓋了現代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對專門知識的淺顯介紹卻滿足了普通大眾的求知欲和好奇感。
新世紀初期的玄幻小說基本是愛好者的即興試筆,因此多對文字和技巧的打磨,但進入2003年,幻劍書盟、起點等原創文學網站相繼進入經濟運作,采用收費制度或VIP制度,尤其是后者的成功實踐,使得網絡玄幻的制作進入產業化階段。作為文化產業的玄幻小說,正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所言,標準化和批量生產也隨之而來。《誅仙》、《飄渺之旅》、《小兵傳奇》因初期的轟動效應甚至被冠以“網絡三大奇書”之稱,伴隨玄幻文學產業的正規化、嚴密化,一些作家因此年收入過百萬,這刺激了大批寫手,目前玄幻小說占據各大原創文學網站的首位。玄幻小說的批量化生產,大多喪失了文學所應有的光韻或個性,而且折射并參與了當代社會的意識形態。
玄幻小說基本上未吸收傳統寫作的龐大財富,與現代主義以來的先鋒傳統幾乎是絕緣的,其形式與技巧停留在很幼稚的階段,如基本采用全知敘述視角、單一的順敘、扁形人物、多講述而少展示。通過作家的自述可知,他們所受的影響基本上屬于通俗文學的傳統,如寫《誅仙》的蕭鼎坦言自己受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的影響,寫《飄渺之旅》的蕭潛甚至以《水滸傳》為典范。因此我就人物與情節結構這兩種基本的小說要素來分析其形式的程式化特征,并探索此特征與當下意識形態的應和。
丑小鴨的童話在眼下似乎變成了現實,超級女生、快樂男生之類的選秀節目已經舉行了好多屆。眾多少男少女相信這個充滿夢想的平臺,而節目制作組也在竭力讓人們相信這是一場充滿機遇的舞臺,似乎人人都有機會進入十強,但人們偏偏忘記了幾率,這不過是文化工業對普通人做出的虛假的承諾。我們整個社會都在醞釀一種狂熱的情緒,每個人都在追求百萬富翁的夢想,每個人都充滿激情,都好像處在龐大的選秀舞臺上。多元化的生活,人們可選擇的機會增多,但不幸的是,用來衡量個人的標準卻出奇的單一,即擁有的金錢。玄幻小說也正參與了這一虛假意識形態的營造,小說所架空的世界規則基本上是以冷冰冰的能力為衡量標準,這個世界永遠圍繞一個主人公轉,其他的角色都是可以替換的零件,可有可無,而這唯一的主人公卻是毫無個性的,其主要特征可歸納為唯利是圖。唐家三少,已經創作了十本玄幻小說,近1500萬字,其所有的主人公無一不是高大全型,一出場便是讓人炫目的出身,接下來便是一系列的奇遇與成功。這種單調的人物個性卻贏得大多數的讀者,因為讀者們在跟隨主人公發達的歷程中仿佛自己得到了滿足。尤其是修真小說,在小說所虛構的修真世界里,人人信仰的都是能力至上,只有同一等級才能講道理,而對于其他低等級動輒玩弄于鼓掌之中,如《佛即是道》中的主人公簡直毫無道義可言,純粹一修煉機器,這代表了極端人物的典型。即使是其他題材的小說,如未來機械類的《小兵傳奇》,人物所尊奉的價值也是單一的弱肉強食。人物刻畫的平面化在通俗文學中向來如此,但玄幻小說集體表現的可以量化的人格追求卻是我們時代的特色。玄幻小說又被稱為YY小說(即意淫小說),恰說明了我們時代所追求的價值在小說中得到最充分的宣泄,同電視選秀等一起加入虛假意識形態的塑造。
小說結構中的各個要素都是相關的,人物的單一性正呼應著情節結構的程式化。玄幻小說的作者大都很年輕,盡管年輕不是偉大作品的阻力,但在中國這種浮躁的土壤上,年輕卻恰恰是藝術不成熟的原因。這批年輕的玄幻作家們,盡管有新奇的想象與樂觀的精力,但因為VIP制度的引誘,成為速度的犧牲品,如唐家三少,被網友戲稱為“打字舒馬赫”,每月三十萬字的驚人寫作。他們來不及構思精密的情節,因為連載的更新方式,他們也來不及修改,盡管竭力將每個細節寫的精彩,但他們無力把握整體結構,這導致作品整體的失敗。如未來機械類的《師士傳說》可謂這一題材的精品,但整個情節純粹圍繞主人公一個人展開,經常是剛展開一個線索,但因主人公的離開,而被迫放棄,這使得作品成了有干無枝有枝無葉的光禿禿的直線模式。類似的如太空戰爭類的代表作《小兵傳奇》,為了增加敘事線索,作者毫無邏輯的找線索,如唐小兵的父母突然強大以及偶然的看到網上同學聚會的郵件,而原有的一些伏筆又沒有很好的展開。另外《鬼吹燈》集合了眾多盜墓奇觀,名為長篇卻實在是中篇的集合,作者根本不在整體的銜接性上著力,從東北到西藏再到云南,每一次探險都引人入勝,但究其根本僅僅是地域上的變化。
同樣以修真小說為例,小說一般講述主人公通過一級級的飛升到達更高的境界,其修真的級別基本上就是筑基(后天期、先天期)、金丹、元嬰、出竅、分神、合體、度劫、大成。這一模式最早由《飄渺之旅》設定,其后的小說大多大同小異,到我愛西紅柿的《星辰變》等書又增加兩重空間即仙界、神界。這類小說的情節結構可稱之為升級模式,盡管細節各不相同,但“文化工業的發展使效果、修飾以及技術細節獲得凌駕于作品本身的優勢地位”⑧,因此細節也都是可以替換的,在批量化生產的過程中遵循著固定的程式。許多人之所以沉迷于此類小說,也正是被一個個零散的細節所吸引,如《飄渺之旅》中對古陣探險的設置,《誅仙》中對奇獸出場的設置,《狼群》對遭遇戰的設置等等,各書中出現多次甚至構成了固定情節。作者們的想象力局限在每一個細節上,如《誅仙》中一段取自《山海經》的話對應一個異獸的出現,初看有滄桑的歷史感和新奇的沖擊感,但這些細節卻可以替換的,這種不斷的自我重復正宣告想象的萎縮。自我重復除了細節和結構的重復,還有作品之間的重復,當然不同作家的互相重復更是舉不勝舉。如我愛西紅柿的《寸芒》《星辰變》直到《盤龍》,其中人物多為一人一獸組合,結構上為幾重空間,具體情節多為歷險殺怪再升級。
這種升級模式也正符合現實意識形態對人們的暗示,它讓人們充滿信心與激情,但同時讓人們局限于一種生活方式,讓人們成為房奴、蟻民,盡管一直在努力,卻總看不到盡頭。作為文化產業的玄幻文學,其細節與整體都成為可以替代的復制品,想象力的貧乏在我們的時代越來越明顯。平面化的人物與升級的情節模式,都在迎合著虛假的意識形態,讓人們相信人生的各個階段都是可以被量化的,迫使每個人都成為孤獨的個體,但又與其他人保持驚人的一致性。
當人們沉浸在玄幻小說的細節中時,為局部的想象而神魂顛倒時,人們卻喪失了起初的目的。為了追求輕松,卻陷落在冗長的連載情節中;追求自由的想象,卻迷失于程式化的瑣屑中。正如詹明信指出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的多種可能性,可能是新的出路,同時包含著失敗,文化產業已經籠罩著我們整個時代,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認清某些制度造就的虛假的意識形態,為藝術指出可能存在的陷阱。玄幻小說因人們向往自由的個性與想象而產生,但也因成為文化產業的一員而貧乏與混亂,契機與陷阱并存,但它們不應成為虛假的宣傳物,不應成為欺騙的合謀者。真正平民的藝術,應當是作為民間的真正活力的意識形態的代表,而不屈服于官方的呆滯意識形態的俘虜,正如本雅明在《經驗與貧乏》一文中所說的“對時代完全不抱幻想,同時又毫無保留地認同這一時代”⑨。
注 釋
①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第142頁,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②見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③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第146頁,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④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454頁,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⑤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403頁,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⑥架空,指的是作者對其小說中的虛構世界作出設定,從而創造出一個真實的奇幻背景。在這個世界里,通常有著自己獨特的規則,這種規則取決于作者的想象深度,里面充滿各種詳細的設定(有時這種設定長度超過作品長度)以及翔實的細節描寫。
⑦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454頁,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⑧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第140頁,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⑨瓦爾特·本雅明《經驗與貧乏》,見《經驗與貧乏》第254頁,王炳均、楊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科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