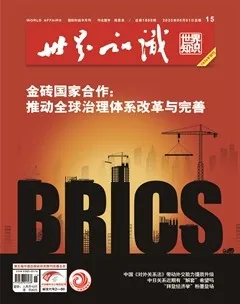歐洲政治共同體:區域合作新趨勢還是“清談館”?
張健
6月1日,第二屆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在摩爾多瓦布爾博阿克舉行,顯示了歐洲政治共同體這一新的平臺正在嶄露頭角,謀求發揮作用和影響力,以確立在歐洲乃至全球的角色定位。
沒有美國參與的重要平臺
2022年5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歐洲議會全會發表演講時提出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后,經過短短幾個月的磋商和協調,這一設想便從倡議變成現實。同年10月6日,歐洲政治共同體首次峰會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此次會議確定了每年召開兩次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分別由歐盟輪值主席國和非歐盟成員國輪流主辦的機制。目前看,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影響力相對有限,受到的媒體關注度也不高,未來將走向何方也不確定,但其背后的邏輯和相關國家的考量值得關注。
其一,歐洲政治共同體倡議意圖從政治上重新建構歐洲,強化歐洲意識,增強歐洲自主性,確定歐洲角色,打造“歐洲人的歐洲”。這主要反映了法國的設想,也是馬克龍總統提出該倡議的主要考慮。法國一直有較強的自主性和獨立意識,希望歐盟成為全球一支真正的地緣政治力量,更加獨立自主,在全球事務中發揮平衡作用。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和升級凸顯了歐洲的脆弱和對美國的依賴,打亂了法國的對歐外交議程,即一方面推動歐洲與俄羅斯緩和關系,另一方面推動歐盟構建戰略自主。這兩項議程是一體兩面,沒有健康的歐俄關系,就很難有戰略自主的歐盟;反過來,沒有戰略自主的歐盟,就很難有健康的歐俄關系。當前,歐洲再次陷入嚴重對抗和分裂。與冷戰開始時不同,這一次歐洲的處境更為艱難,其與美國的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歐洲國家甚至整個歐盟都有完全淪為美國跟隨者甚至附庸的可能,將越來越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正是法國的擔心之處。
歐洲政治共同體意在團結所有的歐洲國家,而不只是歐盟成員國,其通過每年召開兩次峰會,欲加強了解和聯結,以政治對話為抓手打造歐洲共同體。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重要平臺,凸顯了“歐洲人的歐洲”這一理念。
刻意回避歐盟的影響力
其二,拓展法國和歐盟對非歐盟歐洲國家的影響力。歐洲并非只有歐盟,歐盟也不能代表歐洲。歐盟之外有西巴爾干國家及烏克蘭、摩爾多瓦等希望加入歐盟的國家,也有冰島、挪威等不愿入盟的國家,還有地位特殊的土耳其,以及退出歐盟的英國。法國和歐盟認為,如果自己不爭取這些國家,那么它們就會受到域外國家的影響,比如英國會進一步向美國靠攏,土耳其會加強與俄羅斯的關系等。在烏克蘭問題上,法國和歐盟還要考慮到并非所有的非歐盟歐洲國家都與歐盟保持一致的立場,如塞爾維亞、土耳其等。另外,如何處理好與脫歐后的英國的關系,也是歐盟面臨的一個關鍵課題,因為英國極其不愿與歐盟機構打交道,更愿意進行國家間的對話。
不過,歐洲政治共同體刻意回避了歐盟的影響力,雖然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出席了兩屆峰會,但兩個機構均沒有正式參與這一平臺運作。所有歐洲國家,不論是歐盟成員國還是非歐盟成員國,都是以平等的身份參與歐洲政治共同體平臺。

2023年6月1日,第二屆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在摩爾多瓦舉行,與會領導人在會議期間合影。
過去歐盟為了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建立了諸多機制,包括“鄰居政策”“東部伙伴關系”“柏林進程”等,但收效甚微。歐洲政治共同體已召開的兩次峰會表明,這是一個政府間、非專業性的平臺,主權平等的原則在這一平臺上得到尊重。這表明,法國和歐盟正在調整過去處理與非歐盟國家關系時居高臨下的方式,試圖重新贏得相關國家的好感。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期間,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創建有助于樹立團結的歐洲形象,以便更好地孤立俄羅斯。
打造入盟替代模式
其三,打造新的入盟替代模式,為法國和歐盟內部改革爭取時間。法國對于歐盟擴大一向持較為謹慎的態度,擔心“消化不良”,影響歐盟的正常運轉,主張先深化再擴大,也就是說,歐盟只有在相關機制和機構有能力應對擴大帶來的挑戰后才能擴大。事實上,馬克龍提出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倡議后,一些中東歐國家就懷疑法國意圖通過這樣的替代模式,阻攔烏克蘭等國入盟,烏克蘭對此也有相似的疑慮。2022年6月歐盟峰會決定給予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兩國歐盟候選國地位,一定程度上打消了這些國家的疑慮,從而烏、摩兩國對參加歐洲政治共同體會議也沒有了抵觸情緒。盡管如此,法國仍然希望歐盟先進行內部改革,再接納西巴爾干和東歐諸國。從西巴爾干國家的情況看,入盟并非易事,甚至需要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而政治共同體提供了一個替代平臺,可以讓這些候選國每年有兩次與歐盟所有成員國聚會議事的機會,減輕它們的被排斥感,同時增加它們與歐盟在法律、外交政策等諸多方面的趨同性,為最終成為歐盟成員國打好基礎。
顯現出法國國際關系新理念
其四,顯現出法國的國際關系新理念。歐盟倡導價值觀外交,但過去幾十年的事例表明,其價值觀外交基本上是失敗的,并沒有達到其目標,甚至適得其反,削弱了自身影響力,損害了自身利益。這是因為歐盟無法在價值觀外交方面奉行統一標準,而是選擇性適用,如對以色列等國是一個標準,對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標準。世界上多數國家將歐盟的價值觀外交與虛偽劃上了等號。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全球南方”國家的反應表明,歐盟及整個西方的價值觀敘事只在西方內部適用,在西方之外并未被接受,比如西方國家歡迎烏克蘭難民,但對來自非洲、中東等地的難民則是避之唯恐不及。馬克龍在今年2月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出感慨,“為什么西方失去了南方的信任”。
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建立不是基于共同的價值觀,貫穿其中的理念是主權平等,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從此方面看,這一平臺的建立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回歸。法國提出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倡議,體現了其外交新思路,但這種新思路能否轉換為歐盟對外交往新思路,還尚待觀察。
發展前景評估
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倡議從提出至今只有一年多時間,要評判其未來發展是否能實現歐盟特別是法國的戰略意圖,還為時過早。但任何一個倡議或合作平臺,如果不能為與會方提供額外價值,那么各方參與的熱情也會下降,這一倡議或平臺就發揮不了作用,最后可能無疾而終。從歐洲政治共同體兩次峰會的情況看,這一平臺還是發揮了一些作用。
一是有利于強化與會各方的歐洲身份。與歐洲業已存在的其他泛歐機制如歐安組織或歐洲委員會等不同,歐洲政治共同體具有獨特性,其主要召開的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層級的會議,而且每年舉行兩次峰會。而歐洲委員會迄今只召開過三次峰會,今年將召開第四次峰會;而歐安組織迄今也只召開過五次峰會,最近的一次還是在2010年。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圍繞泛歐議題進行討論,會后不發表共同宣言,也不出臺具有強制性的決議,因此各方的參與性較強。
二是有利于化解地區性矛盾和沖突。歐洲范圍內還存在不少國家和地區間的矛盾和沖突,如希臘和塞浦路斯與土耳其之間的領海爭端,以及科索沃問題,等等。歐洲政治共同體這一平臺為平時很難進行的雙邊和小多邊會談創造了機會。因為歐洲政治共同體會議的非正式性和靈活性,使得各方甚至是敵對方較容易坐在一起,比如今年峰會期間,法國總統馬克龍、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德國總理朔爾茨就與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及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舉行了會談,試圖化解阿亞兩國矛盾。這些雙邊或小多邊的會談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相關國家間的了解和互信,從而避免小矛盾和小沖突上升為大問題甚至軍事沖突。在調停、化解這些矛盾和沖突的過程中,法國及歐盟的角色和作用得到體現,也避免了美國或俄羅斯的介入。
三是有利于促進各方的務實合作。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上討論的議題相對務實。第一屆峰會討論了能源安全、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安全、青年、移民及高加索和黑海地區合作等問題。第二屆峰會討論了安全、能源、互聯互通以及移民等問題。這些問題是所有參會方都關心的問題,共識性強,有利于形成歐洲“一盤棋”的合作局面。比如,關于能源安全,各國在天然氣共同采購、來源多元化、管道設施的互聯互通和加快綠色能源轉型等問題上進行討論和交流,更易形成覆蓋全歐、具有戰略性的合作。
據報道,共有44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了第一屆峰會,今年6月舉行的第二屆峰會這一數字達到47個,僅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未與會,顯示各方對這一平臺參與興趣很高。但由于歐洲政治共同體是新生事物,其發展前景面臨不確定性,各方對其發展走向持有不同看法。有聲音指出,這一平臺未設立秘書處、沒有資金保障,完全由主辦國召集舉辦,運行模式與七國集團及二十國集團類似,為了確保峰會的生命力和議題的連續性,主張歐洲政治共同體應設立秘書處、建立相應機制。而反對的聲音則認為,這一平臺最大的優勢就是非正式性和靈活性,若讓其成為一個正式的組織,可能會適得其反。
因此,歐洲政治共同體這一平臺未來若能有效地引導、促進歐洲所有國家基于共同利益進行對話、交流與合作,有效彌合地區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分歧,可能會獲得較大發展。反之,也有可能淪為“清談館”,默默無聞,終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