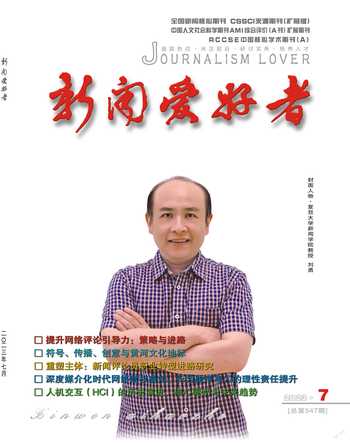技術、藝術與權力:數字藝術城市傳播的三副面孔
陶陶 詹蕤
【摘要】傳播學意義上的城市傳播研究,在數字技術的時代背景下呈現出嶄新的面貌與發展形態。數字藝術作為技術與藝術交織融合的前沿藝術樣式,在城市傳播的“場域”中同時具備技術特征、藝術特征和權力特征。技術,作為數字藝術城市傳播中的物質載體;藝術,作為數字藝術城市傳播中的人文生成;權力,作為數字藝術城市傳播中的資本符號。而數字藝術城市傳播中的這些特征又動態建構著其城市傳播的過程;同時,城市又動態推動并影響著數字藝術的傳播。
【關鍵詞】數字藝術;城市傳播;技術;藝術;權力
“數字藝術作品的外觀不似傳統藝術作品那樣純粹,前者是數字技術、互動體驗內在整合在一起后呈現出來的。”[1]數字藝術的獨特表征,既有VR幻景虛擬現實中觸摸到的科技感,也有現代數字技術賦能傳統藝術所交織迸發出的嶄新表現力;它是在傳統藝術基礎上被數字技術激活之后,實現的一次跨時代意義的美學融合。城市自藝術誕生之初就是藝術的文化母體,數字藝術作為藝術的前沿形式與時代翹楚,與城市相育相生,以數字的科技發展速度及獨特的傳播結構占據城市空間與城市文化陣地。城市作為“權力交鋒的場域,社會關系匯聚的地方”[2],本身就是傳播學重點關注的對象,而城市這一“空間”也是參與到人類藝術傳播活動中的關鍵因素。
有關城市傳播的研究情況,學界通常以美國城市傳播基金會為中心而延展出的城市傳播概念、思路及路徑等作為起點和發展的考量。此外,有關城市傳播研究成果的出版物《城市傳播讀本》和《國際傳播學刊》,也成為以城市傳播基金會為核心的世界性的城市傳播學界影響力。關于“城市傳播”這一概念,學界并沒有明確而精準的定義,其本身就是一個發展的動態形成的傳播過程。而各個國家研究者對于“城市傳播”的研究及其發展過程也正是這一動態發展形態的最佳說明。它提供了一種觀察城市及其轉型的嶄新視角,“強調城市作為傳播活動的中介,連接人、地方與傳播技術的功能”[3]。而依照岡伯特和德魯克所稱的“可溝通的城市”這一概念,也闡釋出城市傳播動態的實踐過程。
一、數字藝術城市傳播的技術面孔
技術是數字藝術當之無愧的存在基石,是數字藝術城市傳播的物質載體:城市技術語境為數字藝術創設了穩定的生存空間;城市技術手段為數字藝術提供了廣闊的傳播空間;在傳播的過程中,數字藝術對城市進行反哺,推動新型智慧城市建設。
首先,數字技術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城市。一方面,城市居民的需要是數字技術產生的直接動因。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環境的復雜化及計算機帶來的海量信息生產,人們無法直接從周圍環境和海量信息中獲取所需要的信息,迫切需要一種手段從復雜的信息中獲取個人所需。為了滿足人們的信息需求,幫助其更好地適應外部環境,數字技術應運而生。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作為人腦的延伸,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從周圍復雜環境中獲取個人所需的信息,從而幫助人們更好地適應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城市高度發達的外部環境為數字技術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城市居民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較好的媒介素養也助力數字技術在城市的推廣與傳播。因此,數字技術產生于城市,以城市為基地廣泛輻射。
城市技術環境培育數字藝術。依靠城市物質所創設的穩定生存空間,既包括由城市基礎設施所搭建的物質實體空間環境,亦包含由城市數字技術所搭建的數字化編碼系統、高新科技運作機制與數字虛擬空間等,數字藝術得以在城市環境中生成、培育、發展。如近年來備受矚目的數字文物,它們是由數字信息模擬出的超高清影像,并通過計算機設備進行線上展示。又如城市特色燈光秀,需要借助城市組群建筑、局部自然景觀交聯形成燈光巨屏,實現城市建筑物與炫彩燈光的交相輝映。
其次,技術是數字藝術城市傳播的動力與支撐,技術為數字藝術的傳播提供開闊的傳播環境、多元的傳播媒介等助益,編織建構而成數字藝術得以傳播的廣闊空間。從傳播環境上看,城市依靠其空間人口集聚為數字藝術供給了數量龐大、分布稠密的傳播者、傳播受眾,還依靠其生產力發展與信息化建設水平為數字藝術提供了廣泛的互聯網傳播設備與較高的互聯網普及率。同時,依賴于城市提供的數字設備存儲與傳送,數字藝術的傳播走向開放與共享,數字藝術不會因時空的延伸而消磨,反而能夠在傳播中進行不斷的復制、重構乃至增值,繁衍出不可計數的可能性。從傳播媒介看,城市則為數字藝術提供了多種多樣、可選擇性高的傳播媒介。同時,數字藝術天然與數字媒介水土相依,數字媒介可交互性強、傳播瞬時化、打破時空限制、兼容多種多媒體形式,極為適合作為數字藝術的傳播載體,城市也為數字藝術供給了豐富的數字媒介支持。
最后,數字藝術的傳播反哺城市數字產業發展。透過數字藝術的廣泛傳播與“出圈”,欣賞、消費數字藝術成為城市居民生活中的新時尚,也帶動了數字藝術產業齒輪的咬合轉動,推進數字藝術全鏈條產業的發展。目前,我國數字藝術產業發展已初具規模,各地城市也在積極探索數字藝術產業發展創新之路。
二、數字藝術城市傳播的藝術面孔
藝術,作為數字藝術城市傳播中的人文生成,其天然具備城市化屬性。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藝術領域出現重大變革,數字技術逐漸與藝術本體融合,既豐富了藝術表現形態又充實了城市審美文化,此外,數字交互藝術與數字電影藝術也應運而生。
首先,數字藝術在城市沉浸式生成以及與此相關的人文造像,作為城市景觀連接動態化城市傳播,建構新型城市文明。人類城市發展中以往的城市文明形態,如較早的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文明,“芒福德把古代希臘城邦,尤其是古風后期至古典時期的雅典看作是人類理想的城市形態”[4]。這是一種以公民民主權為表征的公民政治,因而城邦文明是一種政治文明形態。近代開始出現較為小眾的以教育和科研為中心而生成的“大學小鎮”城市文明樣態,如魏瑪小鎮、牛津小鎮、劍橋小鎮以及后來在中國珠三角建立的珠海大學小鎮等。這些是以學術及其學術精神為城市表征的教育文明形態。而融合了科技硬實力和藝術軟實力的數字藝術占據城市傳播高地并引領城市文明發展也即將成為又一種城市文明樣態。人們開始以時代廣場的巨幕來指代時代廣場這一空間存在物或紐約這一城市;以東方明珠塔的光電射燈藝術來指代都會上海;以元宇宙技術賦能下的古典畫卷般的黃鶴樓數字藝術景觀來指代旅游城市武漢。
人們借助技術性手段來展現城市性內核,其具體表現形式為數字交互藝術和數字電影藝術。數字化技術拓寬了藝術創作空間,藝術自然融入城市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延伸了審美主體的參與度,人們由以往對當代城市藝術形式的單向感知走向交互,“它強調人與機器之間的相互作用,交互藝術還強調觀眾的積極性和能動性。”[5]數字交互藝術更具有時效性、真實性、體驗性,受眾能與藝術作品進行實時交流,獲得沉浸式體驗。
數字電影藝術是數字技術與藝術本體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另一樣式,數字技術介入,將傳統電影藝術帶入數字時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應用領域的擴大,以數字為載體的影視藝術占據了統治地位”[6],電影中的城市景觀既汲取了現實世界的靈感,又添加有電影導演對城市性的看法。數字技術又進一步拓寬了電影導演的想象空間,目前賽博電影中的影視特效就利用計算機動畫來構造其獨有的城市景觀。
其次,嶄新的城市文明借助數字藝術人文生成,形塑城市品牌影響力,重塑城市定位。正如徐國源曾在《空間性、媒介化與城市造像——文化詩學與城市審美》一書中提出的那樣:由傳播媒介創造的擬像世界成為現代城市社會、城市空間建構的一部分,數字藝術樣式也已經成為現代城市審美文化的一部分。數字藝術的城市傳播也以各種各樣的景觀現象和“可溝通的城市”屬性與城市的個體日常生活產生密切關聯。在城市的密集人群和居民文化認同的背景下,數字藝術的城市傳播使得原初城市迸發新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從藝術的存在形態來看,藝術分為空間藝術、時間藝術與時空藝術。這些藝術形態一直與城市生活相互交織,尤其是現代的公共空間藝術更是基于城市這一特定空間才得以形成。城市公共空間的廣場、博物館、圖書館、園林等既具有視覺審美功效,又反映城市空間文化內涵,“從公共空間構成上,通過景觀、雕塑、公園、道路系統的意義表達提供城市精神空間的意義陳述和人文陳述”[7]。不過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這些建筑皆存在于特定的物理空間,人們通過實地觀賞這些城市景觀,來觸摸城市的文化內核、精神內核,重新審視城市的歷史定位與人文精神,在技術浪潮的加持下,以藝術增添情懷與想象,給城市空間更多的藝術存在感,提高品牌競爭力,樹立城市新形象。
再次,數字藝術賦能城市審美,動態化提升居民城市生活體驗,更好地實現科技宜居。不可否認,一方面數字藝術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對城市的傳統審美認知,人們由審美主體變為建構主體,動態性參與到與城市共同發展、對話和溝通過程中。城市化進程,本身就是對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關系造成影響的動態性進程。數字藝術生產的城市景觀,正潛移默化地改變并重塑著人們的生活和審美。另一方面,藝術形態擁有新的審美表現:虛擬美與多模態美。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的無縫銜接,能夠提升人們的代入感,給人以更好的城市多模態體驗。
三、數字藝術城市傳播的權力面孔
“從最表層上看,城市中的物和人都與資本密切相連。”數字藝術在進入城市傳播的一開始,就具備了城市中資本符號的特性。“從較深層面上看,城市的增長和發展受到資本投資的極大影響。”而作為集合新式科技、產業運作、藝術審美以及資本屬性等為一身的數字藝術形式,其本能地成為城市傳播中的資本符號,甚至“從最深層面上看,資本投資的變動不可避免地帶來城市之間以及同一城市內部的不平衡發展”,因而數字藝術的城市傳播天然地具備一副權力面孔。[8]
首先,數字藝術產生于城市權力“場域”。城市權力“場域”決定數字藝術生成和傳播的結構。法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思想家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基本概念里,有“習性”(actionofhabitus)和“場域”(field)及“資本”(capital)的概念,也是其理論標志。“場域”是布爾迪厄社會學一個極其關鍵的空間性隱喻。而城市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由資本組成的權力“場域”,任何“實踐發生于被稱為‘場域的結構化的斗爭領域”。“布爾迪厄把現代社會闡釋為一系列相對自主但具有結構同源性的、由各種形式的文化資源與物質資源組成的生產場域、流通場域與消費場域”。[9]無獨有偶,對于數字藝術的城市傳播來說,城市這一權力“場域”既是作為數字藝術城市傳播的生產場域,也是流通場域,更是城市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場域”。布爾迪厄認為人類的社會生活是由結構、性情和行為交互作用的實踐活動,這些社會結構和結構的具體化知識,生產出對人類行為具有長久影響的定向性,而這種定向性又反過來影響社會結構。因而,這些定向性一方面形成社會實踐,另一方面又被社會實踐所形成。以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邏輯,可以推斷數字藝術城市傳播與城市文化生活(藝術審美活動)亦交互作用,在這一交互作用之下,數字藝術城市傳播結構以及這些結構之中具體化了的(如數字藝術傳播情境等)內容,生產出了對城市人們行為及審美持久定向性的影響,這些影響又可以反過來影響并建構其城市傳播結構。城市權力“場域”決定數字藝術生存和傳播結構;反過來,數字藝術又在城市傳播過程中影響并塑造著城市權力“場域”。數字藝術若想在城市權力“場域”中發展和再生產,需適應城市傳播的習性和規則,在城市場域中形成并穩定投資結構,成為資本符號;但其作為新入場者需付出成本并掌握在城市“場域”傳播中的游戲規則,進而成為城市傳播權力“場域”的一部分。數字藝術在掌握權力后會將這種規則和資本投資結構傳遞或施加給后入場者,進而形成權力“場域”中的動態循環,與城市權力實現互融。
其次,動態的城市權力“場域”推動并影響數字藝術傳播。城市權力能決定數字藝術作為資本的投資過程。數字藝術對城市定位的契合、對城市建設的形塑和影響以及未來所帶來的潛在價值,都是影響這一權力決策的因素。而數字藝術的傳播效果也會動態地影響著城市權力的決策和再投資,城市權力“場域”也會推動并動態地建構數字藝術的城市傳播過程。
參考文獻:
[1]楊慶峰.數字藝術作品的現象學意義解析:以《甜蜜點》為例[J].新美術,2017,38(10):82-86.
[2]孫瑋.城市傳播:地理媒介、時空重組與社會生活[C]//孫瑋,編.中國傳播學評論:第七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6.
[3]郭旭東.城市傳播研究的起源:理論回溯、發展歷程與概念界定[J].新聞界,2022,356(11):16-25.
[4]裔昭印.論芒福德的城市文明史觀[C]//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杭州師范大學.中國劉易斯·芒福德研究中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10.
[5]柴秋霞.數字媒體交互藝術的沉浸式體驗[J].裝飾,2012(2):73-75.
[6]張歌東,數字時代的電影藝術[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5.
[7]馬欽忠,公共藝術基本理論[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8:9.
[8]周文.資本、政府、沖突:城市發展批判分析范式的研究主題[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31(6):71-78.
[9]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M].陶東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10.
(陶陶為湖北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學院講師;詹蕤為澳門城市大學藝術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
編校:張如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