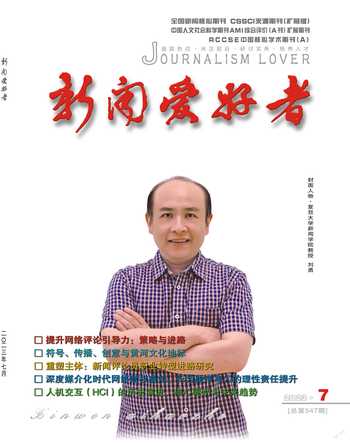人工智能介入視覺圖像的藝術生產與傳播路徑
楊冬
【摘要】當下人工智能對視覺藝術的跨界與融合具有可行性研究,它以風格分析與深度學習、模仿與跨越、圖像建構與空間轉化等藝術生產的方式呈現出與人類藝術創作相媲美的圖像空間。人工智能通過算法技術模仿生發的視覺圖像,是對人類藝術創作的挑戰與推動,其以數據技術與視覺信息的交互、媒介工具與審美價值的共生等傳播路徑,衍生出具有當代性的多元美學,引發對藝術本質和未來發展的現實思考,進而期待技術與藝術的融合在科技發展中的美學傳播。
【關鍵詞】人工智能;視覺藝術;圖像空間,美學傳播
人工智能作為一門學科技術已有半個多世紀之久。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思維進化的途徑,其延伸發生在有機體之外,與人類思維相比,其運行要快得多。人工智能對藝術的跨界與融合,在當下或未來的后消費時代,或許是一種有趣景觀。
技術進步在改變意識形態的同時,也改變了時下的藝術觀念。人工智能是技術與藝術結合的另一種模式,被稱為“人工智能模擬時代的藝術品”。[1]在人工智能搭建的算法平臺上,我們看到的是魔幻現實如何借助藝術進行轉換,人工智能如何關聯藝術?因此,人工智能以物化的藝術生產介入藝術,不失為一種全方位的空間考慮。同時,人工智能和人類藝術創作融合,科技發展必然導致精神觀念的變化,其意識形態承載著藝術形式的高度語境化聯想。
一、人工智能介入圖像空間的藝術生產
在模擬人類邏輯推理與經驗學習的過程中,人工智能的高效率或許會排除人類關系中的各種復雜性,但也要認識到其潛在的風險。
(一)風格分析與深度學習
藝術家形成風格需大量臨摹他人作品,人工智能“從一開始就是記憶的載體”[2],它不僅看,而且記住風格,并融會貫通到自己的“靈魂”中。人工智能處理人腦神經元最重要的工作原理是對多層神經的深度學習,在模擬人類行為上具有較強的自主性。程序設計師已考慮到藝術家和計算機之間的模擬需根據自主性調整。同傳統繪畫相比,人工智能的關鍵是:GAN(全稱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用公式算法探索藝術和人工智能之間的接口,然后以神經網絡生成圖像,生產出的作品沒有署名,只有機器學習任務的目標函數,創作作品與人類作品很難辨別區分。在人工智能的推動下,視覺藝術的圖像空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無限潛力。
然而也有創意團隊有意區分人類與機器的創作作品。如Facebook研究院2017年提出的CAN,它是 GAN衍生的一種創作對抗網絡,其目的是獨立生產出有別于藝術家創作的大眾藝術,而不是對其風格的模仿復制。CAN專門設計了藝術辨別器和風格分類器,辨別器是判斷作品是否屬于藝術品,分類器是讓生發的作品風格模糊化。人工智能藝術與藝術家創作在實驗中混淆于一起讓觀眾辨別,結果有些生成的藝術作品反倒評價更高,“人機”難辨。然而,對CAN藝術作品的接受可謂毀譽參半:如人工智能藝術在成本上不能同藝術家創作相提并論,很多人質疑智能藝術是否具有靈魂。因為藝術家付出的不僅是技術、時間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思想情感。而智能藝術成本主要是團隊設計和服務器費用,大量現成資源都是互聯網共享的。基于此,智能機器對人類藝術的深度學習與風格分析,在接受上并不能保持一致。
(二)模仿與跨越
21世紀初的媒體藝術研究者認為藝術作品作為一種對象在場的消失,計算機技術無法記錄或再現藝術的感性存在。藝術家強調實踐是基于過程的體驗,在“藝術品”“觀眾”“社會背景”之間有著本質關聯。十幾年過去了,今天科技與藝術融合的意義遠超藝術作品本身。如今,用于虛擬現實的3D建模、數字裝置甚至VR虛擬空間都被視為數媒藝術。媒體藝術家創造的視覺將藝術和觀眾的關系置于比過去更為行為化的圖像語境之中。反之,公眾也在所有層面上——經驗的、概念的、情感的和身體的參與到創造中去。數媒所形成的圖像泛濫使觀眾放棄理性思辨,視覺奇觀的感性審美似乎將取代邏輯思辨。而目前人工智能作為“進行中的作品”,具有“無限的意義儲備”,將來更是如此。
在藝術生產中,人工智能是儲存、復制圖像風格的媒介工具。與藝術家創造的自由想象力相比,計算機似乎體現了技術的確定性。一定程度上,實體的人與計算機之間具有某種互補共生。藝術作品某種微妙的敏感性需要藝術家和媒介工具形成協同式的互補,其將這種計算機系統集成到創作中來擴大個人能力,讓電腦探索不同的可能性,然后穿梭于織機的編織項目中,人工智能支持了織工的這種靈活性。這個典型例子顯示了智能機器作為變革工具跨越創作空間的潛力。
(三) 圖像建構與空間轉化
藝術作為人類意義生成的一面鏡子,它為科技提供了一個實驗室,可探索精神、情感、信仰、恐懼、希望、期望和經驗等,討論想象、創造、發明和技術。正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說,比知識更重要的是想象力。關于人類與技術的關系,藝術告訴我們了什么是人文技術的潛力。一個時代的藝術和技術通過形式呈現給觀者一個可觀可感的視覺圖像。圖像是直觀的,人工智能將使用程序作為棱鏡,通過它來觀察人類的頭腦。而人類大腦的空間識別則是人工智能系統建構圖像最強大的想象空間機制。
在人工智能中,研究者正嘗試開發特定的藝術知識來模擬藝術家的情感與思維。在科學理性與藝術感性之間,人工智能迫使我們不得不對人類精神與肉體的關系進行重新審視[3],人工智能為這些提供了一個透鏡。如英國藝術家凱瑟琳·羅杰斯(Katherine Rogers)采用人工智能模擬《失眠之夢》系列作品,描述身體在位移工作中的現象,參與者同時進入兩類空間:一個是現實世界的畫廊,沿著一個移動并反復出現的房間走廊,穿過門口,沿著墻壁到另一個空白空間;另一個空間是運用電腦生成的、圖像和聲音重構的虛擬空間。在藝術生產的話語機制中,虛擬的圖像空間是以人工智能和藝術相互融合并轉化視覺空間的媒介傳播。
二、交互與共生:人工智能與當代美學溝通的傳播路徑
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成為藝術表達的主體,傳達與人類藝術相同的內在張力呢?誠然,在與當代美學碰撞的過程中,其溝通路徑與人類創作相比,是技術理性與視覺圖像的互生,其傳播路徑終究是從理性至上的媒介技術出發。
(一)數據技術與視覺信息的交互
數據技術對視覺圖像的信息傳播是其建模在審美識別上的重要體現。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在其《人工智能仍然不能做什么》中認為:“我們應該通過對大腦的學習能力建模而不是對世界的符號性表征來創造人工智能。”[4]其觀點一定程度反映了對數據技術思考力與審美力的懷疑態度,也與多數人形成共鳴。人工智能與藝術作品之間的邊界真的是牢不可破嗎?誠然,人工智能藝術呈現的某種美感并非我們的美感,但它們之間有相似性,這一相似性存在于仿若如此的美學之中。隨著科技對藝術的介入,一件作品可兼容影像、聲音、繪畫與表演等多種形式,人工智能作為模擬與延伸人類智力的科技,它在信息儲存、分類、提取、輸出、模仿應用等方面,大大改變了人類的意識觀念和生存狀態。
在人機交互技術不斷進化之時,技術性復制為當代美學提供了新的契機。在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看來,“技術可復制性”[5]改變了藝術與大眾的關系,傳統藝術的靈韻正在消失。人工智能作為一門技術性科學,其數據技術與信息交互成為智能輸出的信息載體。如消弭了藝術邊界的裝置藝術,是通過聽覺、視覺與觸覺等多層視角探知人類與科技之間最舒適的可能性,來呈現其數字信息的當代性。智能所引發的技術革新為不同美學的有機對話與深層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從視覺審美到觀點表達,智能信息交互讓藝術產生不同程度的化學效應。例如人工智能通過圖像識別的普及,公共場合人臉識別和屏幕終端的人像采集等。它一方面消減了人類的工作壓力,另一方面也重新定義了人類的工作方式。
(二)媒介工具與多元美學的共生
人工智能作為一種科技媒介,它的介入使當下藝術形成理性的審美判斷。康德認為:“鑒賞判斷并不是認識判斷,因而不是邏輯上的,而是感性的(審美的),我們把這種判斷理解為其規定根據只能是主觀的。”[6]康德式的感性判斷一時間使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感性審美成為大家的關注點。因為,從任何方面看,人工智能都不具備康德式感性因素,基于經驗的、主觀的審美判斷更無從談起。然而當代藝術的審美已不再局限于“美的精神”或“什么是美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后現代繆斯的娛樂文化已滲透到百姓的生活之中,正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每個人的審美認知。今天,我們的吃穿住行多是在科技媒介的虛擬空間中實現,屏幕式的虛擬終端更是多元美學的充分顯現。
技術之于藝術,媒介工具成為促進藝術的主體[7],并非取代人類藝術創作。人工智能正不可逆轉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轉移并保存了當下價值觀,同時也改變了藝術創作的方式,在催生新藝術現象的同時,也生發出具有雙重互動的不確定性美學。[8]百年前,德國現代建筑學派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就認為人類審美會隨著科技發展而變化。當時多媒體用于藝術被看作無厘頭,隨著科技對藝術的滲透,多元美學使當時的“不可能”變成現在的“可能”。生活在一個應接不暇的多元時代,人類視覺正不知不覺地被各類屏幕圖式所捆綁。從電影屏幕、電視屏幕,到電腦屏幕、手機屏幕、iPad屏幕直至今天各類公共電子屏幕終端等,這些虛擬終端正以全息方式懸浮于現實空間。實體空間被智能虛擬消弱,不斷出現的物質數字化、環境虛擬化和生活非物質化在這條道路上漸行漸遠。
三、結語
在科技與藝術的融合、求知與審美的融通,以及認識論與文化傳播層面上,我們需認識到其存在的潛在問題,它現處于尚未成熟的研究階段,仍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需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科學與藝術結合的必然性
人工智能對藝術創作的介入,充分反映了科技與藝術之間的發展趨勢。科技與藝術的結合,從文藝復興繪畫采納暗箱技術就已初見端倪,當下人機交互的藝術生產,其本質是一場科技的跨學科行為,也是藝術以智力行為檢測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要考量機器的智能本質及其潛在的“藝術家”身份,機器創造是由人類智能觸發的,兩者互動共生,而這正是人工智能藝術產生的魅力所在。[9]人工智能對藝術的接受是對它的再生。人工智能藝術具有雙重屬性,其隱性話語折射資本與權力的“神話”;而顯性話語則呈現出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以及科技與藝術之間的完美演繹。[10]藝術家以怎樣的身份和姿態代入藝術創作,藝術實踐與藝術教育如何將多元美學與新媒體的現代傳播同步,是擺在眼前的一個重要課題與機遇。
(二)藝術本質的不可復制性
人工智能以理性工具介入藝術創作,對視覺圖像的技術生成,其數據技術對藝術風格的模仿,當前仍未能超越藝術史的范疇。人工智能藝術是在數據庫儲存的圖像信息中“創作”的作品,對藝術作品所蘊含的個人情感和精神因素,它無法像人類那樣對現實生活進行觀察、研究、分析、選擇與提煉來獲取素材和情感體驗。藝術家在探索過程中積淀的藝術感知、觀察力、思考力與表達力,是技藝純熟的臨摹無法比擬的。人類藝術創作的本質是審美,人工智能仍是在人類限定數據程序的技術性學習,其智能媒介所產出的作品并未跳出藝術史的美學規范。在審美上,并非像杜尚、博伊斯與克萊因那樣對藝術形式的顛覆性革命。當下,人工智能的創新理念與傳播途徑,究竟是對藝術創作的技術模仿還是對藝術審美的觀念革新,抑或是智能機器作為新美學觀念的技術載體?仍需期待。
(三)未來科技如何賦予藝術
人工智能介入藝術使各種質疑和警惕接踵而來:人類藝術家會被取代嗎?人工智能藝術會有情感靈魂嗎?……如何把握好這把“雙刃劍”,是科技與藝術在碰撞中需思考的問題。人工智能對藝術的介入,正如19世紀攝影技術誕生對西方繪畫的沖擊。1839年,攝影誕生后出現兩種聲音:一種是攝影作為藝術的潛力被多數人質疑,另一種是很多人預言繪畫會走進末路。科技與藝術之間從來不是對立與取代。相反,科技是藝術求變的動力機制,正如印象主義光色是在攝影氛圍中誕生。一百多年過去, 繪畫并未走進末日,攝影卻成為藝術的分支,二者良性互動,彼此借鑒。只有站在增量角度,我們才能意識到科技在解放了藝術的機械成分的同時,也賦予藝術以哲性思考。未來已至,今天的狀況與當時的情形如此相似,人工智能將越來越多地應用于藝術領域,作為一種新生的傳播媒介,只有以開放的姿態擁抱它,才是迎接未來的正確態度。
參考文獻:
[1]陶鋒.人工智能美學視域中的審美理性[J].文藝爭鳴,2022(11):167.
[2]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M].方爾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177.
[3]吳文瀚.論人工智能的話語實踐與藝術美學反思[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4):105.
[4]HubertL.Dreyfus,How Computers Still Cant Do:A Critique of Artficial Reason[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14.
[5] 沈語冰,張曉劍.20世紀西方藝術批評文選[M].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18:37.
[6]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
[7]陳常燊.AI藝術是否可能?[J].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2(11):6.
[8]馬立新,涂少輝.AI藝術創作機理研究[J].美術研究,2022(6):83.
[9]湯克兵.作為“類人藝術”的人工智能藝術[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5):182.
[10]吳文瀚.論人工智能的話語實踐與藝術美學反思[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4):101.
(作者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博士)
編校:張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