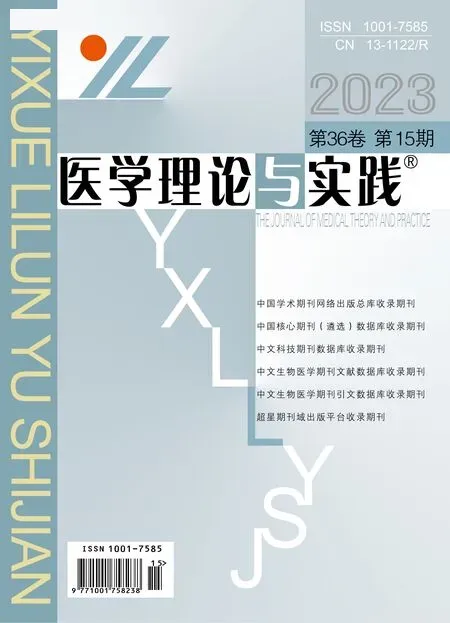Cytochrome C在大鼠SAH后早期腦損傷的表達及意義
楊煌強 魏俊懷 江志賢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泉州市第一醫院神經外科,福建省泉州市 362100
在腦血管意外中,蛛網膜下腔出血(SAH)是一種具有高死亡率和高致殘率的疾病,并且,它的永久性殘疾率和死亡率是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2倍[1]。這些死亡的患者大多數是由于最初的出血和出血后早期腦損傷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療,研究認為這是造成那些幸存者高致死率和高致殘率的主要原因。盡管過去幾十年腦血管痙攣已經被許多藥物研究和治療,但即使腦血管痙攣被逆轉,但患者的預后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2-3]。基于這些原因, 早期腦損傷(EBI)被認為是未來研究的主要目標,也是防治SAH后腦血管痙攣癥狀的主要手段。EBI的病理分子機制包含血腦屏障通透性的改變、神經元和內皮細胞的凋亡及腦腫脹等。這些病理機制對SAH后神經功能的恢復具有重要影響[4]。
SAH后EBI的病理生理改變過程是由多條信號傳導途徑參與的。其中,起關鍵作用的信號通路將成為未來針對SAH后EBI治療的研究熱點,由于細胞凋亡現象在SAH后的腦組織被廣泛發現,故細胞凋亡信號通路被認為是EBI的關鍵通路[5]。近年來研究認為JNK參與的Caspase的信號通路在細胞凋亡中起著主導作用,Cytochrome C是JNK磷酸化后作用的底物之一。所以,我們將Cytochrome C作為細胞凋亡途徑的分子標志物,假設Cytochrome C參與SAH后早期腦損傷的病理生理過程[6]。因此,通過研究Cytochrome C在早期腦損傷的作用進一步證實抗細胞凋亡治療對改善SAH后EBI是一種可行的治療方法。
1 實驗方法
1.1 動物分組 將成年的健康SD大鼠120只(體重300~350g,雄性),隨機分成6組:(1)正常組(n=20),不予任何操作,自由生存,正常飼養;(2)假手術組(n=20),除未注入自體血外,其余步驟均按大鼠枕大池注血法[7]嚴格規范操作進行;(3)SAH組(n=20),大鼠SAH的動物模型是采用枕大池注血法建立的;(4)SAH+DMSO組(n=20),按10mg/kg的劑量標準,采用腹腔內注射法于蛛網膜下腔出血動物模型建立前1h和蛛網膜下腔出血模型建立后6h進行腹腔注射;(5)SAH+SP600125(10mg/kg)組(n=20),SP600125按10mg/kg溶解于DMSO溶液當中,分別在SAH模型建立前1h和模型建立后6h進行腹腔注射;(6)SAH+SP600125(30mg/kg)組(n=20),SP600125按30mg/kg相同的方法溶解于DMSO溶液中,在相同的時間點腹腔注射入實驗動物。其中每組取6只用于TUNEL檢測各組大鼠腦皮層細胞凋亡的情況;每組再取6只用于Western蛋白印跡法檢測腦組織Cytochrome C表達情況。
1.2 各組大鼠生存情況的觀察 各組大鼠的存活數目及神經功能行為:觀察各實驗組模型建立后24h大鼠的存活數目,依據Yamaguchi評分系統[8],分別從觀察對象的進食量、活動力和功能缺損三個方面進行評分,本實驗是在 SAH后24h對存活大鼠進行神經功能評分,評分越高,表明實驗動物的神經功能損傷越重。具體評分標準見表1。

表1 Yamaguchi神經行為功能缺損評分標準
1.3 實驗標本制備 實驗標本的制備方法采取的是“心臟灌注固定法”在實驗后24h分別將各分組動物處死并取材。具體步驟如下:使用10%的水合氯醛(0.3ml/kg)再次對大鼠進行腹腔內注射麻醉,然后,將麻醉后的大鼠取仰臥位固定于潔凈手術臺上,用手術剪暴露大鼠胸腔,于心尖處使用醫用輸液器針頭刺入左心室,然后用顯微剪刀打開大鼠右心房。通過左心室輸注250ml磷酸鹽緩沖液及250ml 0.9%氯化鈉后,斷頭取腦組織備用。每組各隨機選取12只大鼠完整大腦,用于TUNEL法及Western蛋白印跡法檢測腦皮層組織凋亡征象。
1.4 蛛網膜下腔出血嚴重程度分析 蛛網膜下腔出血嚴重程度的評估已經有其他學者報道。簡而言之,基底池被劃分成6個區域:左右額部,左右顳部以及上下腦干。每一部位都評0~3分,每只大鼠評分0~18分。0分:蛛網膜下腔無血分布;1分:少量血液分布于蛛網膜下腔;2分:中等量血塊;3分:大量血凝塊。本實驗中,在24h內處死的大鼠中如果出現硬膜下、硬膜外血腫或者少量下腔出血(評分<12分)的將被排除出實驗。只有嚴重的下腔出血(評分>12分)的大鼠才被納入實驗組,進行進一步研究。每組各取6只大鼠的顳葉腦組織進行Western blot檢測。剩下的每組大鼠經上述同樣方法處理后;再次用4%多聚甲醛250ml灌注后取腦,并用4%多聚甲醛浸泡腦組織固定做TUNEL檢測。
1.5 TUNEL染色法檢測凋亡神經細胞 取下的大鼠腦組織標本于4%多聚甲醛中固定,然后將腦組織用石蠟包埋,行連續切片,每片厚度5μm,裱片后放入60℃烘箱烤片2h。采用TUNEL法(試劑盒購于美國羅氏公司)檢測腦皮層組織中凋亡神經細胞。計算TUNEL陽性反應細胞數:每只大鼠在模型建立后24h、48h隨機選取3張切片,在光學顯微鏡下觀察皮層區 TUNEL陽性反應細胞數,隨機選取2個視野在200倍鏡下對陽性細胞進行計數并記錄,并進行統計學分析。
1.6 Western Blot法檢測Cytochrome C的表達情況 建立大鼠SAH模型后24h時,再次對其進行腹腔內注射麻醉,麻醉滿意后進行開顱,迅速于穿刺側出血塊附近取大小1mm×1mm×1mm大腦皮質組織塊(頸內動脈走行區域),凍存于-80℃冷凍箱中以備用。Cytochrome C表達蛋白的提取:(1)取凍存的腦組織標本100mg,將取到的標本剪碎,同時放入4℃冰水浴中,用超聲將其粉碎,離心機離心20min,轉速設定11 000r/min;留取離心的上清液,室溫下放置30min備用。(2)采用酚試劑法測定蛋白的濃度。(3)蛋白變性。(4)配膠。(5)電泳。(6)轉印。(7)封閉。(8)孵育一抗。(9)孵育二抗。(10)清洗。(11)顯色。(12)Western Blot結果量化分析。利用Image-Pro Plus凝膠成像分析軟件進行分析,對實驗每條蛋白電泳帶的灰度值記錄,定量分析數據并統計圖像。
1.7 統計學方法 利用SPSS20.0統計軟件處理實驗數據,以平均值±標準并表示實驗結果;利用單因素ANOVA檢驗對各組均數之間進行比較, 以P<0.05表示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觀察各實驗組大鼠死亡率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結果 在實驗后24h對各組大鼠參照Yamaguchi評分系統進行死亡數及神經功能評分(見表1)。其中在假手術組和正常組均未見到大鼠死亡,且功能缺損未見明顯異常,兩組評分均為0分。SAH組中,大鼠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3分和4分共有10只,死亡數7只,死亡率為35%, SAH+DMSO組經行為功能缺損評分主要分布在3分和4分,死亡數8只,死亡率40%。SAH+SP600125(10mg/kg)組及SAH+SP600125(30mg/kg)組這兩個實驗組在神經功能缺損評分主要分布在1分和2分,死亡數分別是3只和2只,死亡率分別15%和10%;這暗示NK抑制劑(SP600125)在改善SAH后小鼠的神經功能障礙癥狀有明顯的效果(見表2)。

表2 各組大鼠24h神經行為功能缺損評分及死亡率
2.2 TUNEL檢測凋亡神經細胞結果 本實驗通過TUNEL法染色顯示,各實驗組均可見腦皮層凋亡細胞著色清晰,呈棕黃色,并且在大鼠SAH模型建立后的各個時間節點,呈棕黃色染色的凋亡細胞均明顯多于假手術組。見表3、圖1。

圖1 各組大鼠不同時間點腦皮層細胞凋亡現象(TUNEL 染色;×200)

表3 細胞凋亡檢測結果
2.3 Cytochrome C的表達結果 圖2為Western印跡檢測腦組織中Cytochrome C的變化。在本實驗研究中,由圖3可知在SAH后24h內,Cytochrome C的表達呈上升趨勢;正常對照組內皮細胞中可表達微量的Cytochrome C,而且在各個時間點之間所獲得灰度變化不明顯;但是經JNK抑制劑(SP600125)干預后大鼠腦組織Cytochrome C的掃描條帶灰度逐漸減弱,增加SP600125濃度隨干預時間延長,Cytochrome C的灰度減弱得越明顯。

圖2 West-blot檢測Cytochrome C的表達情況

圖3 Cytochrome C表達情況比較
3 討論
蛛網膜下腔出血是腦卒中最為致命的一類;雖然它僅僅占腦卒中5%,但是因為其在中老年中高致病性、高死亡率以及高致殘率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負擔。在動脈瘤破裂72h內造成的早期腦損傷被認為是治療蛛網膜下腔出血的主要目標;神經細胞凋亡被認為是導致蛛網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腦損傷主要原因[9]。本實驗建立的標準大鼠SAH動物模型是運用枕大池注血法,該方法具有成功率高及操作簡單等優點;通過觀察建立大鼠SAH模型后24h的神經功能評分進一步證實了早期腦損傷存在于蛛網膜下腔出血。同時,我們運用TUNEL法檢測發現實驗動物的大腦皮層凋亡細胞計數增多,Cytochrome C表達上升。SP600125干預后實驗動物神經功能缺損改善,大腦皮層和海馬區凋亡細胞計數增多,Cytochrome C表達上升。據目前研究認為,SAH后產生的血液裂解產物的毒性作用、缺血性腦損傷、急性高顱壓、再灌注損傷和急性腦血管痙攣等可能是造成早期細胞凋亡現象的主要原因。細胞凋亡的過程受多種復雜途徑的調控,但JNK參與的Caspase信號通路在細胞凋亡起主導作用已被證實。
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是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家族成員之一[10]。以往關于JNK在SAH后EBI發生發展中作用的研究表明:JNK信號傳導通路參與EBI中凋亡機制的調節,其抑制劑SP600125是一種強效的ATP競爭性抑制劑,具有可逆性、選擇性及細胞滲透性,在神經元細胞及血管內皮細胞凋亡過程發揮抑制性作用,進而能減輕SAH后早期損傷所造成的腦水腫及血腦屏障的破壞,降低大鼠實驗性SAH后的死亡率[11-12]。過去研究顯示,Cytochrome C能夠促進炎性介質的釋放,且Cytochrome C釋放可使蛋白質在胞質內積累,造成局部滲透壓增高而出現水腫。細胞色素C是一種與線粒體有關的促凋亡因子。在正常的機體生理狀態下,它是一種細胞色素氧化酶,位于線粒體內側外膜。它不僅是線粒體中參與電子傳遞鏈中的蛋白,還參與細胞凋亡過程。大量研究表明,細胞色素C參與缺血性疾病、腫瘤、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患者細胞凋亡的作用受到廣泛關注,并且在那些患者血清中發現其增高[13]。因此,在預測異常凋亡病理過程,血清細胞色素C濃度的變化有相當的臨床意義。
線粒體釋放Cytochrome C入胞質引起細胞凋亡:病理狀態下,Cytochrome C自線粒體中釋放入胞質中,其在胞質中聚集后可誘發細胞凋亡,這一過程是通過Bcl-2家族調節[14]。線粒體中細胞色素C的釋放是由于線粒體外膜通透性增高,其形態學的改變是由于膜的硬化和隔離所致。從線粒體轉移到細胞質后,細胞色素c與Apaf-1結合,從而作為Caspase的協同因子,引發JNK參與的Caspase活化級聯,導致細胞凋亡[15]。在本研究中,SP600125組的Cytochrome C的表達量明顯低于空白組,這提示,Cytochrome C表達與蛛網膜下腔出血后周圍組織細胞凋亡有關,JNK激酶抑制劑可通過抑制JNK信號傳導通路下游Cytc表達而抑制其所產生的級聯反應,進而抑制神經細胞凋亡,保護神經元。
本研究結果表明了Cytochrome C在蛛網膜下腔出血后的表達,并且進一步證實了在SAH后早期腦損傷中細胞凋亡起了重要作用。在 SAH后破壞了血腦屏障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使其通透性發生了改變,促使腦水腫的發生和發展加重,產生腦組織結構破壞及神經元損傷,導致 EBI,而JNK抑制劑 SP600125通過對蛛網膜下腔出血后的早期腦損傷細胞凋亡的產物表達影響,能夠在一定水平上逆轉上述過程,從而實現了其在早期產生的腦損傷起到重要保護作用。因此,在臨床上,我們將對蛛網膜下腔出血后出現的早期腦損傷的診斷和治療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幫助。但本實驗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目前JNK在SAH后EBI中的具體作用機制仍不明確,需要未來繼續深入研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