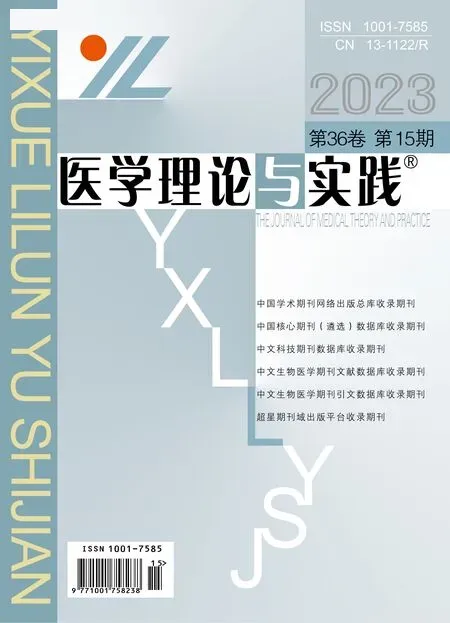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與CRP、UA及PRA的相關性研究
朱洪坤 李小強
1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醫院 510000; 2 南方醫科大學研究生院
原發性高血壓是一種多基因遺傳性疾病,疾病的發生機制尚未明確,目前多認為原發性高血壓的發生與遺傳、生活方式、環境等綜合因素密切相關。原發性高血壓患者患病期間血壓不同程度升高,伴隨有頭暈、失眠、健忘、耳鳴、乏力等基礎癥狀,疾病進展后可促使動脈粥樣硬化發生[1]。動脈粥樣硬化是一種具有進展性的慢性炎癥疾病,該癥狀的出現可直接導致高血壓患者病情進展速度加快,同時還可能誘發其他心血管疾病,進而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危害其預后[2]。研究認為,動脈粥樣硬化進展中最早受累的是頸動脈,因此對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IMT)進行檢測是鑒別動脈粥樣硬化發生與否的重要指標依據[3]。目前臨床對高血壓患者動脈粥樣硬化的診斷多應用血管造影,該方法準確情況較好,但臨床應用復雜程度高,不易推廣。研究提出,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進展中伴隨有C反應蛋白(CRP)、尿酸(UA)及血漿腎素活性(PRA)異常改變[4]。故本文主要考慮分析上述指標在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進程中的表達水平,以期為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的臨床診斷提供數據支持,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擇2020年8月—2022年8月收治的70例頸動脈粥樣硬化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為觀察組,另選擇同期收治的70例正常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納入對照組。觀察組男40例,女30例;年齡42~79歲,平均年齡(57.63±6.10)歲。對照組男38例,女32例;年齡41~82歲,平均年齡(58.02±6.15)歲。兩組基線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有可比性。參考IMT檢測結果,將IMT>0.9mm且<1.2mm的37例頸動脈粥樣硬化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納入內膜增厚組;將IMT≥1.2mm的33例頸動脈粥樣硬化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納入內膜斑塊組。內膜增厚組男22例,女15例;年齡42~78歲,平均年齡(57.94±6.22)歲。內膜斑塊組男18例,女15例;年齡44~79歲,平均年齡(58.21±6.17)歲。內膜增厚組與內膜斑塊組基線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有可比性。參考超聲影像學檢查結果將內膜斑塊組分為內膜斑塊穩定組(n=18)與內膜斑塊不穩定組(n=15)。內膜斑塊穩定組男10例,女8例;年齡44~77歲,平均年齡(58.61±6.25)歲。內膜斑塊不穩定組男8例,女7例;年齡45~79歲,平均年齡(58.54±6.23)歲。內膜斑塊穩定組與不穩定組基線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有可比性。
1.2 選擇標準 (1)納入標準:①符合2020版《國家基層高血壓防治管理指南》[5]中相關診斷標準;②收縮壓≥140mmHg(1mmHg=0.133kPa)或舒張壓≥90mmHg;③既往無嚴重腦部外傷、感染性疾病史;④意識清晰可積極配合研究開展;⑤生命體征無異常改變;⑥知曉研究目的且自愿簽署同意書。(2)排除標準:①因自我意識或其他原因無法完成各項檢測評估者;②多器官功能障礙者;③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者;④合并有其他危急重癥需立即治療者;⑤存在其他急性炎癥疾病者;⑥因轉院或其他原因導致病歷資料統計不全者。
1.3 方法 患者入院后均于晨間空腹狀態下采集肘靜脈血壓3ml,將血液樣本快速置入含乙二胺四乙酸二鈉試管中,后續在3 000r/min條件下進行15min常規離心處理,獲取血清樣本后進行CRP與UA水平檢測。其中CRP水平采用免疫透射比濁法檢測,UA水平采用雙試劑尿素酶法檢測,試劑盒由北京北方生物技術研究所提供,相關檢測操作均參考試劑盒說明書規范執行。將采集的血液離心處理后獲取血漿樣本,并使用放射免疫法檢測PRA水平,試劑盒由北京北方生物技術研究所提供,相關檢測操作均參考試劑盒說明書規范執行。CRP正常水平0.068~8.2mg/L;UA正常水平208~428μmol/L。PRA正常水平0.82~2.0nmol/(L·h)。
1.4 觀察指標 (1)比較觀察組與對照組CRP、UA、PRA表達水平。(2)比較內膜增厚組與內膜斑塊組CRP、UA、PRA表達水平。(3)比較內膜斑塊穩定組與內膜斑塊不穩定組CRP、UA、PRA表達水平。(4)收集所有亞組中CRP、UA、PRA數據資料及其水平變化情況,分析上述指標與內膜增厚及內膜斑塊穩定性的相關性。

2 結果
2.1 觀察組與對照組實驗室指標水平比較 觀察組CRP、UA、PRA表達水平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觀察組與對照組各項實驗室指標水平比較
2.2 內膜增厚組與內膜斑塊組實驗室指標水平比較 內膜斑塊組CRP、UA、PRA表達水平均高于內膜增厚組(P<0.05)。見表2。

表2 內膜增厚組與內膜斑塊組各項實驗室指標水平比較
2.3 內膜斑塊穩定組與內膜斑塊不穩定組實驗室指標水平比較 內膜斑塊不穩定組CRP、UA、PRA表達水平均高于內膜斑塊穩定組(P<0.05)。見表3。

表3 內膜斑塊穩定組與內膜斑塊不穩定組各項實驗室指標水平比較
2.4 頸動脈粥樣硬化與實驗室指標水平的相關性分析 CRP、UA及PRA均與內膜增厚呈正相關(P<0.05);CRP、UA及PRA均與內膜斑塊穩定性呈負相關(P<0.05)。見表4。

表4 相關性分析結果統計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改變,高血壓發病率呈逐年升高趨勢。高血壓患者患病期間通常伴隨有不同程度的動脈粥樣硬化進展,且伴隨動脈粥樣硬化逐漸加重,患者其他心血管并發癥發生風險也相應增加[6]。高血壓患者通常病程較長,長期病理作用下可導致其血管內剪切應力增強,湍流增多,動脈內皮損傷風險增加,正常內皮功能減弱,而后累及頸動脈—主動脈—冠狀動脈,因此對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進行檢測可準確反映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的進展情況[7]。既往研究認為,動脈粥樣硬化屬于一類慢性炎癥反應過程,因此多類型炎性物質均在動脈粥樣硬化進展中有重要作用,此外UA還與動脈血管內膜損傷有密切聯系[3,8],因此對炎性指標及UA進行檢測可為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動脈粥樣硬化的進展評估提供數據參考。
為明確CRP、UA與PRA在高血壓患者動脈粥樣硬化過程中發揮的具體作用,本文中選擇了140例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CRP、UA、PRA表達水平均高于對照組(P<0.05),表明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發生后,其CRP、UA、PRA指標水平均表現出升高趨勢。CRP是臨床常用判斷炎癥疾病產生及進展的檢測指標,其作為一種炎性介質,可促進炎性因子釋放,誘導組織因子與細胞黏附分子表達,積極參與了血管炎癥反應發生與進展,對動脈粥樣硬化的獨立預測價值較好[9]。UA是由細胞代謝、食物中核酸與其他嘌呤類化合物分解的產物,高血壓患者在長期病理狀態下腎小球動脈硬化逐漸加劇,腎小管氧缺乏,乳酸產生量逐漸提升,UA的排泄相應降低,血管壁長期大量堆積UA,導致血管內膜炎癥反應發生,血管內膜也由此不斷損傷,最終促使動脈粥樣硬化發生[10]。既往研究認為,PRA在諸多類型心血管疾病的獨立預測上具有重要價值,其是高血壓患者動脈粥樣硬化與全因死亡的主要危險因素[11]。PRA升高后,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激活,內環境狀態異常,血壓水平持續升高,細胞凋亡逐漸嚴重,血管內皮出現損傷,炎癥反應逐漸加重,動脈粥樣硬化進程加快。
后續研究中筆者參考IMT將觀察組70例患者進行了亞組劃分,并統計了兩組患者CRP、UA、PRA表達水平,結果顯示,內膜斑塊組CRP、UA、PRA表達水平均高于內膜增厚組(P<0.05)。表明CRP、UA、PRA直接參與了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進展,在增加血管內膜厚度、促使內膜斑塊發生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參考超聲影像學檢測結果,將33例內膜斑塊組患者分為內膜斑塊穩定組與內膜斑塊不穩定組,通過開展后續研究發現,內膜斑塊不穩定組CRP、UA、PRA表達水平均高于內膜斑塊穩定組(P<0.05),表明伴隨CRP、UA、PRA表達水平不斷升高,高血壓患者頸動脈內膜斑塊不穩定性逐漸加重,由此肯定了上述指標在鑒別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嚴重程度上的重要意義[12]。研究認為,CRP水平表達與動脈斑塊穩定性有密切聯系,該物質可誘導炎性細胞浸潤,逐漸加劇血管內皮炎癥反應,斑塊穩定性隨之減弱,最終斑塊破裂形成血栓,加重患者疾病風險[13]。UA水平升高則能對動脈血管正常內環境產生破壞作用,通過加重血管內皮炎癥反應,加速脂質積累與血管內膜損傷,破壞動脈血管斑塊穩定性。PRA水平升高在誘導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激活后,血漿腎素分泌量也隨之增加,水鈉潴留嚴重,患者血壓水平升高,動脈粥樣硬化進展加快。患者長期處于血壓升高環境下,微血管逐漸出現損傷,病變組織缺氧程度逐漸加重,動脈血管內皮正常生理功能減弱,血管彈性降低,硬度降低,斑塊物質穩定性也隨之減弱,疾病風險增加[14]。本研究通過對頸動脈粥樣硬化與CRP、UA、PRA表達水平的相關性進行分析發現,CRP、UA及PRA均與內膜增厚呈正相關(P<0.05),說明伴隨研究檢測指標水平升高,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內膜厚度逐漸增加;CRP、UA及PRA均與內膜斑塊穩定性呈負相關(P<0.05),說明伴隨檢測指標水平升高,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內膜斑塊穩定性逐漸減弱,心血管不良事件風險增加。
綜上所述,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發生后,其CRP、UA、PRA指標水平均明顯升高。伴隨CRP、UA、PRA指標水平不斷升高,患者動脈粥樣硬化進展加快,病情風險性逐漸提升。臨床針對上述指標水平進行細致檢測,可為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風險與不良事件的風險預測提供數據參考,保障后續干預治療方案順利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