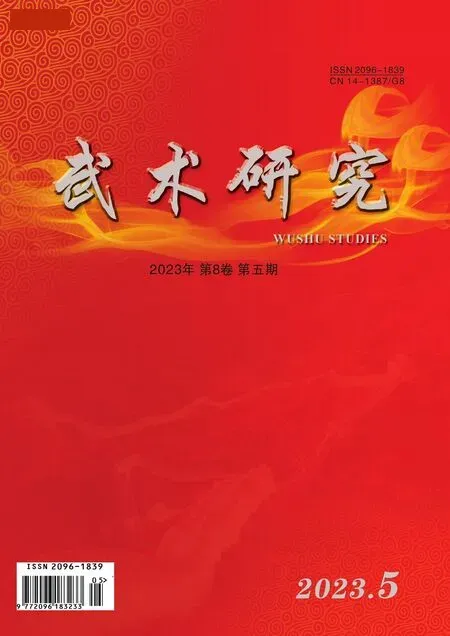少林“武醫文化”技法特點的失落與重生
高啟恒 王 虎 張長念
1.首都體育學院研究生部,北京 100191;
2.北京市正澤學校,北京 100000;
3.首都體育學院武術與表演學院,北京 100191
1 前言
自古武不離醫,醫不離武,“武醫文化”同根同源。武術與中醫的發展在文化上相互貫通,在技法上相互滲透,明確展現出“武醫文化”同根同源的典范。在早期社會,對于武醫的理解主要是能夠為主體提供經絡、骨骼和關節等有關身體的構造認識,避免損傷的惡化,既能為醫治病人提供幫助,又能將身體作為御敵的武器。由于戰事的紛爭和醫療資源的匱乏,促使著少林“武醫一體”的作用成為了王權爭執與抵御戰爭的重要工具,但少林“武醫文化”在君主集權制的影響下,被賦予一定力量時,同樣也面臨生存威脅。當少林武醫被賦予的特殊身份對帝王統治的新皇朝產生威脅以及少林武醫的信念被動搖時,少林“武醫文化”的生存空間、傳承模式和整體觀念都受到了一定的擠壓和冷落,少林“武醫文化”的傳統療法與技法則難以展現。
2 “武醫文化”的歷史源流
在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中,“武”“醫”成為皇室宗族獲取權力的重要力量,同時,也用于滿足戰爭所帶來的傷病與疾病的需要。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漢之際,社會動蕩和變革造就了“武醫文化”的社會基礎。夏商周時代,“武醫”所蘊含的古代哲學理論,促使“武醫一體”雛形形成。魏晉隋唐時期,皇權爭斗“武醫”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了極大提高,尤其是少林寺的創立,也為少林“武醫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而唐代初期,少林武醫成為皇室宗族的重要力量,正如,少林僧人曇宗、惠玚精通醫術的診斷與治療,并且協助李世民平王叛亂,而在近現代史中,鄭懷賢為“武醫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價值和參考意義。[2]由此可見,“武醫一體”的發展貫穿整個歷史,而少林武醫文化不僅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印證了少林武醫對救濟、治病、救人、養生、抵御和防衛集為一體,且具有較強的互通與互融作用。
3 少林“武醫文化”的概述
3.1 少林技法與“武醫結合”的具體體現
3.1.1 少林傷科
古往今來,少林功夫歷經1700 多年的歷史,其中少林僧家弟子曇宗、惠玚更是精通醫術,將醫術與武術用于一體,創立了少林傷科。少林傷科起初是少林僧人配合少林秘方快速治療在習練中所受到內外傷病的少林子弟,后因佛教普度眾生,少林弟子需下山歷練,并將少林醫術用于所到之處廣施善緣,懸壺救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德禪和尚講自己六十載臨床經驗,結合少林武醫所贈藥方,悉數授予弟子,后又整理、撰寫《少林寺秘方集錦》《少林寺傷科秘方》《少林點穴》等書籍,將中國武醫的璀璨明珠公布于世,造福國民。
3.1.2 少林推拿
少林推拿是結合少林武術與中醫的理論基礎用手或者肢體的其他部位,將規范化的動作配合身體受力的強弱,對其特定部位進行治療與防治的一種醫療手段。[3]少林推拿主要是借助于雙手的變化,平衡身體的陰陽,增強人體對抗損傷的能力,其中手法的操作包括:人體上部對應的五指拿法 、掃散法 、推橋弓等;中部對應單手推胸部、 順推胃部 ,橫掃大腸 、雙手刨推肋脅;下肢對應平推大小腿、揉搓大小腿。少林推拿手法是少林弟子通過雙手運用內功功法將阻礙人體內在的渾濁之氣進行疏散,防止“六淫”(中醫指“風、寒、暑、濕、燥、火”)的侵入。而如今,少林推拿逐漸成為中醫治療疾病的一種醫療手段。
3.1.3 少林正骨
少林正骨術歸屬于少林功夫,在武學與醫學中具有少林卸骨術和少林上骨術兩種,是少林僧醫在長期治療跌打損傷的實踐經驗中不斷摸索,探尋能夠快速治療少林弟子在練功時所受到的損傷,防止因小傷的積累造成嚴重后果。少林正骨法主要是以人為主體,以手為主要工具,結合了氣血和經絡學等為決斷傷害程度的主要依據,并以手功復位和點穴治傷等為主要的療法救治傷病。在社會的快速的變遷下,少林正骨術也逐漸日趨完善,成為少林武醫結合的重要標志。至2016 年,少林正骨也正式被納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4]
3.2 少林“武醫文化”的理論依據
少林“武醫文化”是以武醫為主體,以陰陽五行、經絡、藏象、精氣血津等古代哲學為準則,是集預防、治療、康復、防身、強體于一身的綜合性的知識體系。傳統少林武術主修外家拳,講究氣力相隨,氣順則力順,順則通。中醫認為人與自然共為一體,將五臟對應陰陽五行的理念,以形、氣、脈所產生的反應探究人體內部的病理、治療與防治。《素問·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將人體脈穴分為上中下三部,每部對應的是天、地、人三候,因此,可根據三部九候之位也來決斷人的死生,處百病,調虛實,除邪疾。[5]中醫對于養生、治病和藥物毒性的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來搭配,每一品所對應的治療方式不同,所產生的效果自然也不相同;而少林武術則是將身體分為三節,每個三節中又各有三節,通過體悟的練習方式使其主體更加深刻地感受身體對應著梢節、中節、根節三個不同的位置,每三節與主體的各個部位協調配合,進而產生效果。可見,“自古武醫不分家”“武醫一體”道出了以治病、防病、養生、修身為目的的武醫同源的前身,“武”的三節與“醫”的三品分別展現了“武醫一體”的整體觀念,這也為“武醫一體”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3.3 少林“武醫文化”的技法案例
3.3.1 卸骨術與上骨術
少林卸骨術皆屬于《少林七十二絕技》的重要武技之一,主要有:卸肩術、卸肘術、卸腕術、卸膝術、控骨術等武技。經過社會的快速發展,作為社會產物的少林卸骨術也被分成具有懸壺救濟的“醫手”又有擒拿格斗的“死手”,兩手同為一用是將原有的骨關節位置卸除,造成脫臼、滑落、斜歪等狀態,從而使對方喪失局部的功能掌控。[6]卸骨始于技擊,歸于擒拿(擒手),習卸骨者,以傷科為主要依據,精通生理解剖,熟知人體三百六十余塊骨頭結構及形狀。對此,卸骨術用于實戰搏斗中,一推一卸,一捏一揉可迅速使人體關節失去正常生理機能,痛疼難忍,可見卸骨術是作為擒拿格斗中一招制敵的重要技術。少林上骨術與卸骨術同為一體,亦稱正骨術。[7]習練上骨術必精通卸骨,否者則精中不足,留存后患。上骨術與卸骨術相同,都是需要手法內勁雄厚,并且精通人體關節的構造,運用手中巧勁,對敵手的關節進行復位或者控制,方可在實戰中把握良機,克敵制勝。
3.3.2 點穴法
少林點穴法作為《少林七十二絕技》的重要武技,點穴法以經絡學說為依據。少林點穴法是少林武僧在經絡學的基礎上,在長期的習練中,利用雅咀、鶴咀、雞咀、金針指等拳掌法,擊打人體穴位,并根據擊打的輕重判定其所起的救治與治病的作用。根據唐豪《人生穴位并治療法》的介紹中得知,“擊打人體長強穴,可使人屎出脾泄,重擊華蓋穴,可使人立刻昏迷”等皆是穴位遭受重創后的癥狀。[8]在社會環境影響下,點穴法在中醫理論的基礎上產生了戳、點、錘、踢、撞等擊打關鍵穴位的方式,進而對其損傷部位進行救治。少林點穴法通過與中醫的融合,還可借助針灸搭配上合理的實踐,用于臨床的實踐治療。
4 少林“武醫文化”技法特點的困境
4.1 “武醫文化”的生存危機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西方思想的匯入,導致根植于我國本土的武醫文化的生存地位遭受嚴峻考驗和排擠。在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熱潮的介入后,具有古代哲學陰陽五行、藏象等學說的“武”“醫”被世人掛上了“玄學”“神論”等標簽,武醫的技法、拳理和傳統治療術更是被棄而遠之。[9]西醫與競技體育的出現,代替了人們對于傳統“武醫”生活內容的現實需要,“武醫文化”的價值觀念在中西并用中出現了錯亂,少林武醫迫于社會環境的需要,強行做出了革變,造成人們在繼承“武醫文化”的內容上出現了偏差,從而嚴重威脅了“武醫”的社會地位和生存方式。在受到社會變遷和西方科學的影響后,崇尚西方理論為之科學,棄傳統的拳理、技法以及治療之法,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人們也從“武醫”周期性調理、診斷、預防等方面逐漸向西方的高效和快速的治療轉變。最終社會環境的演變,傳統特色的的缺失,西方科學的擠壓進一步加深少林“武醫文化”社會地位與生存空間的縮減和沒落程度。
4.2 “武醫文化”的傳承受阻
在處于自然經濟的中國傳統社會中,“武醫文化”的傳承方式主要來源于兩方面:一是家族傳承;二是師徒傳承。兩種傳承方式承載了“武醫”延綿千年的結果。家族傳承通過以家庭為單位實施子承父業的生產方式,即子孫繼承祖先的成就;師徒傳承則是根據師父或徒弟的主觀性而采取的一種非血緣關系的傳承模式。師父根據當時社會現狀以及經濟基礎決定是否收徒,從而將其自身的技藝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授給徒弟,而徒弟背負著傳承該門派技藝的責任。然而,隨著社會生態的失衡與自然經濟解體“武醫文化”師徒制傳承和家族傳承在古代社會中過于單一。面對土地分配不公平,大量人口開始流失,有的人為求溫飽,選擇拜師尋求庇護,這也導致師父在收徒時,需讓徒弟填寫契書,并且契書上規定學徒年限以及學徒期間生死不保等條例,這足以見得“武醫”對師徒制傳承的苛刻條件。另外,以家庭為單位的“武醫文化”傳承,由于所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在傳承方面缺乏靈活性,常常有“子承父業”“傳男不傳女”等方面的限制,認為只有子孫才能將祖先發揚光大。家族傳承在傳統社會中顯然割裂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這也正是造成“武醫文化”傳承方式在社會進步出現斷層和失傳重要原因之一。
4.3 “武醫文化”的整體分離
自古以來,“武醫”講求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和諧統一。少林“武醫文化”的整體觀念,是將人體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通過對人體具身化的了解和掌握,從而達到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和諧交流。中醫的整體觀體現在五臟、形神與精氣神三個方面,而各方面中有包含人體結構的聯系和統一;少林武術在體悟的過程中將人體部位的梢節、中節和根節對應全身,每個三節中依舊包含著另外的三節,體現著人體的功能結構都是具有整體聯系的。這種觀念也使眾多“武醫”的前輩在診斷病情時,一致認為部分位置產生的疾病是因為機體內部的失衡所導致的。而西方哲學觀念的產生,打破了“武醫文化”千百年來的思維理念,西醫與競技體育的到來使人們能夠認識到將主體結構拆分成及其細致的“零件”,具有快速解決復雜物質的難題,同時還有益于技術能力的提高,[10]而這正好與“武醫一體”的整體觀念相悖。然而,在現代化環境的影響下,西方哲學觀念的思維理念逐漸在我國本土中得到認可,反觀“武醫文化”為了迎合社會環境的變化與發展,平衡、和諧、適中“武醫一體”的整體理念被消磨。
5 少林“武醫文化”技法特點的重生
5.1 立足傳統,建構“武醫文化”的當代特色
少林“武醫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歷經千年的磨難和洗禮,其自身所擁有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記憶更是“武醫文化”的立足之本。在社會變遷的今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11]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保存的越好,那么,它也越容易被世界銘記。“武醫”也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縮影,不僅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千年歷史,同時少林“武醫文化”存在的信仰、思維方式以及樸素自然的哲學基礎更是成為了文化的典范。此外,“武醫文化”立足傳統并非是對傳統的照搬照舊,而是將傳統正骨、卸骨、點穴、推拿以及傷科結合現代化的需要推陳出新,致使我國優良的文化成果能夠得以傳承和發展。在治理人體技能和治療疾病時,二者在知識技能的運用上各有千秋,要想擺脫少林“武醫文化”模糊的面紗,需要以心為主宰,以五臟為中心,使經絡連接肢節能夠積極、主動地體悟自然,適應自然和社會的互動,并在“具身”中探索人體生命活動的規律,改善五臟六腑的疾病,讓其整體事物的內在聯系協調有序,以此構建當下屬于少林“武醫”防治一體的身體健康規律理論。
5.2 融會貫通,完善“武醫文化”的傳承模式
在當前社會,“武醫文化”的傳承仍面臨著斷層的嚴峻形勢,單一的“武醫”傳承已然跟不上社會的變遷,只有在借助傳統的家族、師徒傳承的基礎上,與現代化的社會融合,突破單一領域的傳承方式,構建在縱向上保持“武醫一體”的傳統家族與師徒制傳承;在橫向上采納跨界融合、確有專長的傳承方式,以此促進“武醫一體”單一的發展和傳承路徑。確有專長是作為中醫的一類傳承方式,且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正是這種合法性促使中醫在傳承方面給予了民間醫者更多的渠道。反觀武醫的師徒制傳承,限制的內容造成了武醫結合寸步難行,但將確有專長運用到“武醫文化”的傳承方式上,通過兩者非血緣師徒制的傳、幫、帶與口傳心授,規定在傳承過程中學習武醫所需要的學時,最后根據考試獲得該領域的認可后授予畢業證書,這樣有益于促進現代社會“武醫一體”的融合,同時也為武醫在傳承路徑提供多元渠道。
5.3 防治并重,提倡“武醫文化”的技理融合
少林武醫在理論上追求臟腑、經絡對應五行與陰陽的對立制約,在技術上講求“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的共生共進。換言之,傳統的少林武術以遵循中醫理論的準則下,尋求氣、血、津液、經絡等在人體各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并借鑒在少林武術的傳統技法與拳理中,增強習練時對體悟的感受,這也使習武者深刻認識到中醫對人體構造的重要性,有利于提升先、后天的整體體質,達到“預防”的共通效果。[2]而中醫則是將武術技法用于傳統治療中,通過對學習武術掌握武術發力的控制和身體習練得出的體悟經驗,讓推拿、正骨和點穴等醫療手段具備更加精準和穿透的治療效果,從而產生“治未病”的作用。正如,《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點穴法,正是借助了中醫的經絡學說為基礎,通過擊打人體的穴位,使人體的氣血或停止、或流暢地運行,都會對人體的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產生不同的效果。[12]鄭懷賢更是對武醫的融合發展躬身踐履,并根據正骨理筋手法與武功技法的密切關系,將中醫理論與武術技法中的擒拿、點穴、正骨理筋集于一體的整體觀念,并標新出今日的“十三手法”“經穴按摩”“正骨推拿”和“推拿練功法”等鄭氏傷科按摩技法。[13]由此可見,傳統少林武術與中醫二者在“防”與“治”的技理中并行兼顧、相互融合,同時少林技法與中醫的健康思想促進了少林武術在推拿、正骨、點穴等醫療手段的提高,這為“武醫”在“治未病”中的協同融合奠定了基礎。
6 結語
在經歷了不同階段社會環境變遷的洗禮后,作為人類文明成果表現形式的少林“武醫文化”,其“武醫一體”的關系貫穿于整個武醫的歷史進程。隨著社會文化的動態轉變與西方文化的沖擊,少林“武醫文化”迎來了一系列變革,而眾多極具實踐價值的少林“武醫文化”技法、傳統醫療術的生存地位、傳承模式、整體觀念逐漸在社會進程中被淡化和摒棄,阻礙了“武醫文化”的發展。然而,少林“武醫文化”只有以傳統為根,借鑒西方文化促進少林武醫的發展,展現自身具備的當代特色;開拓少林“武醫文化”確有專長的傳承模式,完善傳統技法、治療術融匯貫通的渠道;強化“武醫一體”對技法理念的整體觀念,發揮少林武醫技法對人類“防”“治”健康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