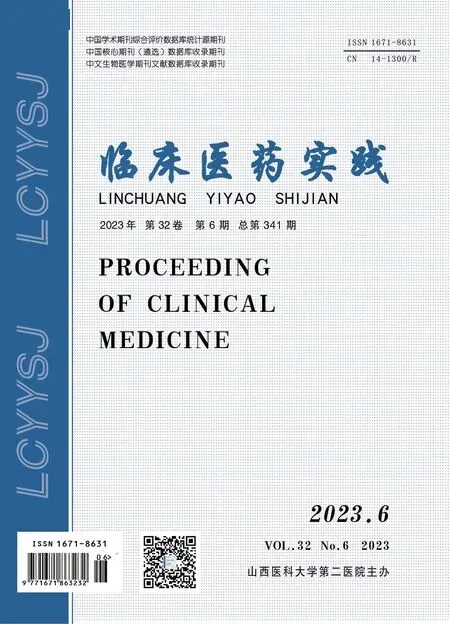淺析頭針治療腦卒中后運動性失語及影像學應用
趙彬凱,毛立亞,毛忠南,王文超
(1.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2.甘肅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甘肅 蘭州 730000)
運動性失語(Broca失語)是腦卒中后最常見的失語癥類型之一,以語言表達障礙為主要臨床表現,對患者的日常交流、生活及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傳統認為Broca區是卒中后造成運動性失語的關鍵,然而隨著現代醫學影像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灌注成像和擴散成像重新定義了運動性失語的發病原因主要是Broca區及其相關腦組織局部血流動力學的改變,進而引發的腦組織結構形態的微觀變化。語言功能的恢復是臨床與基礎研究關注的問題,頭針是治療腦卒中后運動性失語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對近些年不同影像學技術在治療運動性失語中的應用研究進行綜述,分析各影像學技術的優勢,探討其在運動性失語頭針治療中的應用,以期為患者在卒中后語言康復方面運用頭針治療提供參考。
1 定義及流行病學
運動性失語又稱為表達性失語,是腦卒中后常見的諸多后遺癥之一,主要以語言表達障礙最為突出,患者表現為自主理解能力及思維能力正常,但說話呈非流利型、電報式語言,同時可伴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復述、命名、閱讀和書寫等功能障礙。據數據調查顯示[1-2],卒中后發生失語的概率為18%~68%,其中運動性失語約占卒中后失語的67%,且卒中后伴語言功能障礙患者的并發癥及病死率明顯高于無語言功能障礙的卒中患者。
2 運動性失語的發病機制
一般而言,腦部單一語言功能區的損害會導致相應的失語癥類型,但臨床上Broca區的損害不僅會影響語言的組織和表達,同時還會影響理解、命名等功能,這可能與Broca區相關弓狀纖維束以及皮質下等結構的損傷存在密切的聯系有關[3-4]。語言功能區域的神經纖維呈網絡樣覆蓋,在各組織間穿梭走行,十分復雜,并與其他部位的皮質及皮質下結構有廣泛聯系[5]。可見語言功能是一個由非模塊化、高度整合的神經系統處理,其涵蓋的區域遠遠超出了傳統語言功能區的范圍。故經典語言功能區的損傷與失語癥的分類并不完全對應[6]。王金言等[7]采用3D-pCASL成像技術發現病灶側損傷部位CPF值(每100 g腦組織在單位時間內通過的血流量)明顯低于對側鏡像區,腦組織缺血缺氧隨后引發的失代償機制造成持續性低灌注,低灌注后的腦組織無法維持正常的能量代謝,繼而以彌散的形式影響與之相關的細胞代謝。這與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
綜上所述,腦卒中后造成運動性失語是基于Broca區以及與Broca區相關的弓狀纖維束、皮質下等局部腦組織和血流動力學的改變。而且有相關研究證明運動性失語的嚴重程度與Broca區血流灌注量成正相關[8]。
3 運動性失語的頭針治療
在中醫方面,素有“頭為諸陽之會”“腦為元神之府”之說,另在經絡學中有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手足三陽皆上于頭面部相交接;所有陰經的經別并入與之相表里的陽經后均上行至頭面部;督脈并于脊里,上至風府,入屬于腦;任脈至咽部,上頤,循面,入目;沖脈上出于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入腦乃別陰蹺、陽蹺,陰陽相交;陽維起于諸陽之會。以上諸經縱橫交錯,溝通內外,聯系上下,將精氣血津液與腦緊密相連。故頭部是運動性失語患者治療的關鍵部位[9]。
樓喜強等[10]和李雪青等[11]選用雙側頂顳前斜線下2/5和顳前線進行頭針治療卒中后運動性失語的患者,治療后采用紅外腦功能成像儀實時測定治療前后局部大腦皮層氧合血紅蛋白、脫氧血紅蛋白和總血紅蛋白,發現頭針的有效刺激量可以激活腦電活動,增高皮質興奮性,改善血流灌注及血管的再通率,提高病灶組織周圍氧的供給和利用,加速了腦細胞的代謝和腦組織的修復,從而促進患側神經軸突連接、語言功能重組和健側代償,共同促進語言功能的恢復。
4 運動性失語的影像學表現
傳統的計算機斷層掃描(CT)與常規磁共振成像(MRI)檢查雖在反映病灶形態結構方面均具有優勢,但卒中后失語并不只依賴于局部結構的改變,更重要的是腦卒中后局部血流動力學的變化,顯然這兩者在功能損害方面尚有欠缺[12]。
4.1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是以測量大腦神經元活動引發的血流動力及血氧飽和度的改變,反映受外界刺激時的活動變化區域、大腦激活模式以及不同層次的相關腦區活動與任務刺激的相關性,進而描述不同腦區之間的功能整合。此外,fMRI對分析優勢側半球病變區域與對側鏡像病變區域的聯系以及對臨床康復的相關性都尤為突出[13-15]。王鑫等[16]通過對同一基線水平的運動性失語患者進行1 個月的語言康復訓練后,采用fMRI檢查,發現右利手失語癥患者Broca區對側的鏡像區被過多激活,反而抑制語言功能的恢復,證明語言功能的恢復具有明顯的左側偏側性,右側半球過分激活并不利于語言功能的恢復。同時相關研究通過以較大的感興趣區域為指標,多次測量的激活區域及強度重復率高達85%,證明fMRI數據具有可重復性,并不會因為治療結果或測量方式而導致較大的誤差[17-18]。
4.2 灌注成像
磁共振灌注成像(PWI)作用機制是在一個強的預備脈沖后施加一系列快速振蕩的梯度脈沖鏈,并同時進行信號采集,從而直觀地觀察腦組織的血流灌注動態變化過程,通過收集信號的高低反映血流灌注情況,因此,該檢查可反映卒中后失語患者病變區組織微血管分布及血流動力學改變[19]。周芯羽等[20]采用PWI分析60 例腦梗死后失語癥患者,通過對失語癥患者語言功能區血流量變化的分析,得出PWI技術能夠直觀反映腦組織血流量的相對變化,同時PWI具有多層掃描、組織覆蓋體積大的優勢,能夠完成掃描組織內血流流經過程、組織供血動脈的流入過程以及靜脈血液流出過程,且整個過程中只包含了微循環對比劑進入血管后影響組織信號的情況,基本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因此,該技術所反映的情況是相對客觀的。
CT灌注成像通過追蹤靜脈團注對比劑,對感興趣區域層面進行連續CT掃描,獲得感興趣區時間—密度曲線,并根據曲線通過不同的數據模型,計算出各種灌注參數值,能更有效且量化反映局部組織血流灌注的狀態,全面評價腦缺血的嚴重程度,準確地顯示低灌注后所致的半暗帶。張世魁等[21]對67 例發病24 h內的急性腦梗死患者進行CT灌注成像,結果顯示56 例發現腦內灌注異常,診斷敏感度高達83.58%,證明CT灌注可在患病早期發現病灶,并根據灌注參數和圖像分析病情及預后。根據腦損傷后血流動力學的改變,發病后由低灌注最先引發功能異常,其后才出現形態學的改變,所以盡早干預低灌注區域可能對腦組織結構改變起到積極的影響[22]。
PWI與CT灌注成像的原理基本相同,均能對卒中后腦組織低灌注進行動態掃描,但兩者同樣存在著許多缺點和不足,如對比劑需要快速的團注,腎功能不全或對碘過敏患者禁用。兩者比較,PWI的空間分辨率不及CT灌注成像,且信號強度與團注對比劑后的血漿濃度無線性相關性。CT灌注成像具有較高的放射性輻射量,掃描的灌注范圍也比較局限。隨著對CT設備的改進,已經可以實現在不影響圖像分辨率的前提下,做到對全腦的灌注掃描,并盡量降低輻射量[23]。此外,CT灌注成像相較于其他影像學檢查具有性價比高、與常規掃描易于結合、圖像空間分辨率高、成像時間短等自身獨特的優勢[24]。
4.3 磁共振擴散成像
研究發現[25]腦組織損傷后尚不能立即建立吻合有效的側支循環,導致腦血流量減少,引發小動脈急慢性缺血,繼而可能造成白質纖維束結構完整性的改變;臨床腦卒中恢復期的評價有賴于腦組織皮質下等結構的體現。目前磁共振擴散張量成像(DTI)及磁共振擴散峰度成像(DKI)均是通過分析生物組織中水分子擴散的程度,顯示白質纖維束的形態、結構、數量、走行等微觀信息[26]。葉彥池等[27]利用DKI技術分別對20 例腦卒中后引起的運動性失語患者及健康志愿者進行頭顱掃描,直接在纖維束圖中顯示出腦白質的受損和破壞情況,并通過對兩組DKI數據的處理分析,提示患者腦組織受損區域神經纖維束較對側明顯稀疏。同時郝清等[28]從腦卒中患者急性期DTI檢查中篩選出累及單側基底節區的患者16 例,發現梗死灶纖維束較健側直徑變細、位置移動、纖維數量減少甚至部分斷裂。由于兩者水分子運動的差別,DTI雖對皮質下的白質結構十分敏感,但由于灰質的擴散分布主要是各向同性的,對其不敏感。腦卒中的病理反應具有不確定性,然而DKI的峰度參數較DTI的擴散參數更能敏感地反映組織微結構變化,且可通過動態追蹤神經纖維束的變化過程,生成大腦纖維束圖,顯示白質通路的連接情況,更重要的是其對腦皮質和腦髓質具有同樣的敏感性[27-29]。相較于DTI圖像分辨率低的不足,DKI有更精確、更敏感顯示腦組織微觀結構的異質性優勢,為頭針干預治療再灌注和白質纖維束的數量及連接情況提供有效的臨床依據。相關研究顯示[27,30-31],DTI對皮質下的白質結構十分敏感,但灰質的擴散分布主要是各向同性的,對其不敏感,腦卒中的病理反應具有不確定性,故DTI并不適用于初期的病位診斷;而DKI無論是灰質、白質,均具有較好的敏感性,可彌補DTI之不足,且較DTI能更精確、詳盡地顯示微結構的變化信息。
5 小 結
腦卒中后最先表現為血流低灌注,其次由低灌注先后引發功能異常和形態學的改變,所以盡早干預低灌注區域可能對神經功能及腦組織結構改變起到積極作用。灌注成像對腦卒中初期血流低灌注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可在腦卒中發生后準確定位低灌注區域,為頭針治療提供精準的施針部位。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可較好地顯示受外界刺激時活動變化的區域、大腦激活的模式以及不同層次的相關腦區活動與任務刺激的相關性,可作為頭針治療腦卒中后運動性失語的客觀評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顯示語言功能的恢復具有明顯的左側偏側性,也為臨床使用頭針提供了治療思路。DKI與DTI具有顯示白質纖維束形態、結構、數量及連接情況的優勢,均可以預測腦卒中語言結局、頭針治療后監測治療效果,同時還可以致力于以后研究神經重塑與語言功能恢復的相關性。但因DTI對腦卒中的病理反應具有不確定性,若存在灰質和白質的共同損傷,則其并不適用于初期病位診斷。
綜上所述,影像學技術既可早期定位血流低灌注區域,也可動態持續觀察恢復期間的血流灌注及相關病變組織恢復情況,為臨床診斷、早期干預治療、改善低灌注、保護尚未病變組織及實時動態觀察恢復情況提供依據,為卒中后運動性失語的頭針靶向針刺治療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