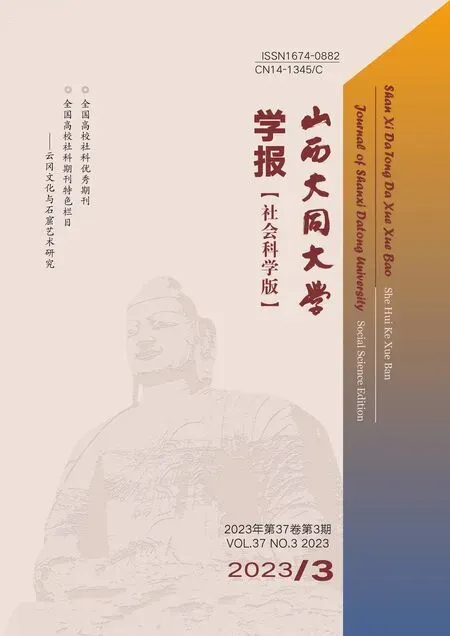論平城時代“大一統”意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
張公達,孫玉梅
(1.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2.山西大同大學云岡學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0)
十九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時代命題,而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研究不能缺少歷史維度。自春秋戰國時代起中國就孕育產生了以“大一統”思想為代表的價值理念,不少學者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淵源上溯至“大一統”理念,或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圍繞“大一統”思想擁有“自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理論探索與歷史研究正方興未艾。
一般認為,“大一統”意識誕生于農耕文明,在中原文化中較為典型,是中華文明極具代表性的一種思想。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大地出現了首個由少數民族統治的穩固政權——北魏。它不僅在疆域上統一了北方,結束了五胡十六國130余年紛爭的局面,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民族大融合,打破了華夷之辨,減少了民族對立;同時在經歷了激烈而痛苦的碰撞之后,在意識形態上融合了儒道釋三家思想,對中華傳統文化高度認同,極大地豐富發展了“大一統”意識,。
可以說,拓跋鮮卑實現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在“大一統”實踐上的最高成就。因此探究北魏平城時代的“大一統”意識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一、時代變局的召喚
西晉滅亡之后,廣袤的北方大地朝代更迭頻繁,十幾個民族政權陸續登場,進入了五胡十六國時代。登國元年(386 年)正月,拓跋珪建立代國,四月改制稱魏。在定都平城之初,北魏政權仍需與后梁、后秦、后燕等國相較量,同時基本以秦嶺-淮河為界與東晉、南朝對立,分別統治中國的北部、南部區域。在與諸多政權爭霸的過程中,少數族裔統治多數民族,自然會面臨正統身份構建與正統地位的話語權爭奪問題。而這既是“大一統”意識產生的原因,也是其有機組成部分。
平城時代的“大一統”實踐,也是北魏統治者解決民族矛盾的需要。在入主中原之初,拓跋鮮卑成功地施行了胡漢分制,緩減了鮮卑與漢族的矛盾,使得北魏新興王朝在北方站住了腳。同時起用漢族官員,形成了由拓跋貴族和漢族共同執政的局面;胡漢雜居的區域不斷擴展,胡風漢俗相互雜糅,在北魏王朝廣泛存在。然而,拓跋珪死后,民族矛盾慢慢變得尖銳起來,拓跋鮮卑作為征服者,對中原地區的欺壓和掠取屢見不鮮,導致民族矛盾不斷加劇,僅建國后的幾十年時間內農民起義先后達80 余次,北魏的統治者勢必要扭轉這一政治局面。
在地緣與民族的影響下,北魏王朝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北魏積極經營西域,使來自西方的藝術、文化、科學技術進入中原,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融合,并不斷創新,成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為隋唐多元統一國家的形成奠定基礎,也為世界文明發展畫卷中增添了靚麗的一筆。
二、平城時代“大一統”的意識與實踐
中國古代“大一統”意識主要涵括疆域上的“天下一統”、政治上的“王權一統”、文化上的“儒家一統”以及在族群上主張“華夷一統”等。[2]
(一)一統天下的期望 在疆域上,北魏歷代君主無不崇尚“大一統”的局面,尤以“平城時代”的六位君主武功最盛。拓跋珪曾說:“《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吳楚僭號,久加誅絕,君子賤其偽名,比之塵垢。”[3](P37)在北魏進取中原,定都平城之后,繼任的君主依然不減武功,渴望實現天下統一。拓跋嗣多次北伐柔然,穩定北魏北部邊疆。泰常七年(422 年),拓跋嗣親征東晉,奪取南燕故地青州、兗州、豫州、司州等。拓跋燾是一位既有統一之志,又有軍事才能的雄主,先后擊敗柔然,滅亡大夏,擴地千里,并在北地設置了六座邊鎮,屯將駐兵,稱雄漠北,使得北部邊疆獲得長時間的安定。從431 年始,至439 年,胡夏、西秦、北燕、北涼等政權先后被北魏滅掉,北方五胡十六國130余年政權紛爭的混亂局面結束,之后北魏又將柔然、土谷渾以外的北方少數民族統一在自己麾下,最終結束了北方分裂局面,統一了中國北方。隨后又向西域用兵,設立西戎校尉府,并抵御南朝北伐,攻至長江北岸。《魏書》稱拓跋燾“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3](P109)《通典》云:“自太武以后,漸更強盛,東征西伐,克定中原。”[4](P4451)孝文帝拓跋宏也志在“南蕩吳越,復禮萬國”,即使在馮太后掌朝期間,也于太和元年(477 年)10 月收復淮北地區。北魏疆域北至沙漠、河套,南至江淮,東至海,西至流沙,并將西域諸國、東北諸國,北方的柔然納入到北魏的統治體系之中,為民族的大融合和統一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民族認同的構建 隨著疆域的擴大,作為京畿的平城地區也迎來了人口的大量遷入。在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前后,曾向平城進行大規模移民。據李憑教授統計,這次大移民時間集中、數量巨大、成分復雜,約有150 萬人口從四面八方被遷入雁北地區。除官方向京畿地區充實人口外,還有不少部落、部族內遷、內附。在平城定都之初就已經形成擁有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了。在龐大的人潮之中,既有來自河北平原上的漢族百姓,也有社會發展程度尚落后的游牧民族。隨后道武帝拓跋珪采取諸多措施,使得平城地區農牧業、交通、貿易、都市建設均得到了迅速發展,“在開發京畿的共同勞動中,漢族與北方各游牧部族人民通過生存經驗與技術的交流而增進了民族感情,推動了民族交往,使當時的雁北不僅是容納大量移民勞動和生活的場所,而且成為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爐。”[5](P283)《魏書》卷六〇曾記載當時的場景:“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3](P1341)
在北魏政權統治了以漢族為主體的眾多人口之后,統治者積極構建民族認同,首先尋求與華夏同根同源的理論依據:“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后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3](P1)拓跋鮮卑源自黃帝一系,是其論證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的需要,也是在消除與占主體的漢族之間的隔閡。其次通過寬松的民族政策積極推動民族融合。面對周邊諸多少數民族政權以及西域諸國,一方面武力統一,另一方面采取招撫、和親等措施,努力實現“大一統”。前期主要以武力征伐為主,招懷為輔,而中后期主要以懷柔為主,征討為次要手段。在北魏皇室中,皇后慕容氏、姚氏、赫連氏、郁久閭氏、馮氏,來自于不同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之初,迎娶后燕慕容寶之女,并立為皇后;拓跋嗣與后秦和親,迎娶西平公主,是為太武帝拓跋燾之母;太武帝在攻下大夏統萬城后,將赫連勃勃的兩女兒納入后宮,其中一個被封為皇后;文成帝的生母郁久閭氏,本是柔然王族人;獻文帝生母文成元皇后李氏,是從南朝來到北魏。北魏的和親政策,一方面促進了政權間的友好交往,另一方面促進了各民族的血脈交融,客觀上實現了以北魏為宗主的“天下一家”的目的,以和親的方式將各民族納入北魏大家庭之中。來自上層的聯姻勢必會影響民眾,孝文帝還針對鮮卑族人推行同姓不婚,迫使鮮卑與其他民族尤其是與漢族聯姻,推動鮮卑族的漢化過程。
(三)文化、宗教的并蓄 北魏統治者在實行寬松的民族政策同時,也主動接納、認同和吸收中原文化。拓跋鮮卑復國之時,先前進入中原的各族已經走上封建化和漢化的道路,北魏政權要想發展,就必須推行漢化改革。北魏效仿魏晉以來的官僚體制,陸續吸收漢族士人進入北魏政權,任用了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珪時許多制度均出自漢族士大夫之手,如上谷張袞、清河崔玄伯“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拓跋燾曾一次征請數百名漢族士人參政,又如三朝老臣崔浩,文成帝拓跋濬至馮太后掌朝時大臣高允,孝文帝拓跋宏時輔國將軍李沖等。任用漢族士大夫參與國家治理,穩定、擴大了統治的社會基礎,緩和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促進了民族間的溝通與交融。
中原的典章制度與禮樂文化也得到了北魏統治者的重視和學習。北魏立國之初,就逐步建立起各種祭祀制度,呈現出胡漢雜祀的特點。道武帝稱帝后,天興元年(398)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3](P33)“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于西郊”,[3](P2734)并修建太廟,效仿中原王朝建立國家祭祀制度。孝文帝時,“確立了‘同堂異室’的七廟制、宗廟締祭、孟月時祭和皇帝親祭等內容,促使宗廟祭祀制度不斷完善。”[6](P303-314)直到太和十五年(491),道武帝拓跋珪的神主被供奉在太廟正中,“這樣把君臨中夏的北魏第一位皇帝奉為太祖,加強了北魏君臨中夏的特殊政治意義,孝文帝便為自己作為華夏文化的繼承者,找到了根據。”[7](P547)
在尊孔崇儒的思想氛圍中,北魏平城時代的帝王雖然信奉佛教,但都以儒學為正統思想。從道武帝拓跋珪開國起,就于平城設立太學,把祭孔作為皇家禮儀的一種常制,由此確立儒學在國家政治當中的地位。在拓跋珪遷都平城的第二年,即“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3](P35)后又“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余字,號曰《眾文經》。”[3](P39)文明太后執政和孝文帝時期達到高潮,據殷憲先生《北魏平城營建孔廟本事考》:“拓跋代平城百年,志在融己于中華文明之中,于孔廟建立、宣尼祭祀,自是其中之義。”“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復于太學之外另立孔子廟,這是中國古代于曲阜之外的中國國土上所建的第一座孔廟。”[8]這一系列措施都加速了鮮卑族的漢化。
平城時代民眾間的融合還可以從佛教信仰中窺見一斑。在孝文帝漢化改革之前,云岡石窟供養人造像由主要穿著胡服,逐漸出現了胡、漢服混雜的現象,反映了胡漢之間民族關系逐步融洽。而在更廣大的山西、河北、山東、陜西地區,“無論是改革前還是改革后,服飾上都是既有胡服供養人,也有漢服供養人,從姓氏上看也是如此,既有漢姓供養人,也有胡姓供養人”,[9](P241)說明胡漢各族民眾沒有太大的民族區隔,在生活上密切聯系。“基于共同的信仰,不同姓族的信徒可以逾越民族畛域,組成社邑共同從事造像供養活動。在這種共同活動的影響下,民族界限與差異自然會逐漸弱化,逐漸走上相互融合之路。”[10](P273)在從事佛教活動的過程中,社邑切實加強了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們的聯系,同時構成了共同社會精神生活,增強了凝聚力。
只要有利于大一統,無論儒、道、佛哪種思想,北魏平城時代的帝王們都呈現出兼容并包的姿態。即便是太武帝滅佛,也有樹立正統的因素在其中,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國,帶有鮮明的外族印記,早期出家為僧者大多為胡人,信仰佛教也成為“夷狄之俗”。太武帝曾下詔:“昔后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3](P3034)站在中原文化正統繼承者的立場上,稱佛教為“邪偽”“鬼道”之說。通過打擊佛教來消弭作為外來族群的鮮卑與漢民族的隔閡,借以達到趨同華夏,樹立正統的目的。
無論是疆域上的統一,還是寬容的民族政策,抑或是文化上的兼容并取,都是“大一統”的題中之意,北魏政權從而不斷實現,并最終完成“脫夷入華”。經過平城時代近一百年的磨合,北方的民族融合取得了極大的發展,又與內遷各族的統一觀念以及中原傳統文化的繼承相聯系。同時,民族的不斷融合又將帶來新的統一,為隋唐兩朝疆域的擴大、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與文化藝術的豐富多彩創造了前提。
三、平城時代“大一統”的歷史意義與啟發
平城時代的“大一統”意識及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先是北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結束了北方的分裂與動蕩,有利于北方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了各民族的交融交往。其次是民族認同的構建,使得拓跋鮮卑等少數民族不斷融于中華民族大家庭,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壯大。再次北魏平城時代在文化上一系列改革舉措,為傳承、發展中華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基于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是在我國多民族交融的歷史長河中逐漸生成并鑄牢的。”[11]平城時代的民族融合是中華民族形成的重要環節,這一時期民族大融合進程中形成的“大一統”意識與實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史中至關重要的部分,也具有典型示范意義。
首先,從思想傳承上說,北魏平城政權繼承了秦漢以來的“大一統”思想,在拓跋燾時提出“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將“四夷”作為天下這個大家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拓跋弘提出:“天下民一也,可敕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3](P129)“天下一家”、“天下民一也”的思想即是古代命運共同體、民族共同體的表達。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的漢化改革,也是平城時代“大一統”意識的延續。其次,從民族認同上說,拓跋鮮卑通過一系列改革,廣泛吸納各族人才,推動政治與文化轉型,最終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族中,也為中華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再次證明文化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紐帶。最后,從歷史影響上說,平城時代有混亂、有分裂,但這一時期為后來的隋唐統一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使得中華民族無論歷經千辛萬難,都有一種民族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在國家統一時起著維護統一、防止分裂的作用;在國家分裂時,又能促進統一,結束分裂局面。
在北魏各民族實踐“大一統”的推動下,“中華”不再是“漢人”的代名詞,而是各民族共有之“中華”,為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源。通過考察平城時代“大一統”觀念下的民族融合,可以看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能忽略文化維度,只有不斷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增強文化自信,推進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對話、和諧共生,開放包容、交流互鑒,才能使各民族群眾了解中華優秀文化的歷史發展脈絡,共筑精神之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