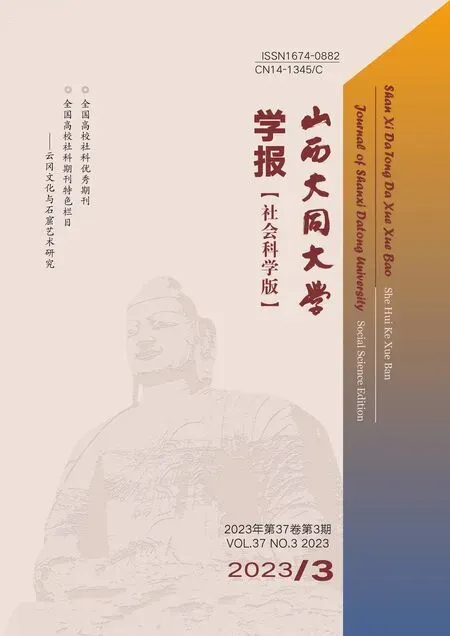戴季陶的禮制思想淺析
張雯歡
(山西大同大學(xué)云岡學(xué)學(xué)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張灝曾指出:傳統(tǒng)中國的價值取向存在著“以仁為基礎(chǔ)的德性倫理”這個形而上的層面和“以禮為基礎(chǔ)的規(guī)范倫理”這個形而下的層面,“禮”的規(guī)范是“仁”的價值在從廟堂的國之大事到百姓的日用尋常間的具體展開,而這種規(guī)范的核心便是“三綱五常”之說。近代以來在西潮的沖擊之下,綱常及其背后的禮制成為傳統(tǒng)負(fù)面化之后被集中攻擊的箭垛,[1](P114-115)并產(chǎn)生了不斷激進(jìn)化的浪潮。在孫中山去世后,長期跟隨孫中山的戴季陶一改其在民初的激進(jìn)面貌,先后寫就《孫文主義之哲學(xué)的基礎(chǔ)》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從儒家價值和中國固有文化出發(fā),將三民主義的民族嫁接于傳統(tǒng)道德之上,把孫中山定位于從堯舜到孔孟的道統(tǒng)繼承人,以保守主義的態(tài)度將政治與文化統(tǒng)攝在內(nèi),并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此后的戴季陶以道自任,力圖用傳統(tǒng)儒家的價值態(tài)度收拾人心、消弭社會中不斷高漲的革命意識。但戴季陶及南京國民政府對民族固有道德的宣揚始終面臨著這些價值本身缺乏“禮制”這樣規(guī)范性的展開形式,因此非但不足以凝聚人心,更使得三民主義與民族固有道德淪為被新青年嘲諷的口號。1937 年全面抗戰(zhàn)展開,國民政府在整合全國資源運用于抗戰(zhàn)之時,也力圖將抗戰(zhàn)與建國化為一體。戰(zhàn)時的巨大損失讓物力維艱,慘痛傷亡更加重了人心的灰暗,中日之間物質(zhì)層面的差距使得中國的精神倫理動員成為一種必要。“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以必起”,[2](P86)抗戰(zhàn)何以堅持到底,勝利之后要建設(shè)的理想國又是什么樣貌?作為國民政府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gòu)者,戴季陶將目光從三民主義投向在歷史上影響更為深遠(yuǎn)的禮制。
到了1942 年,中國在反法西斯同盟中四強之一的地位確認(rèn),近代以來的不平等條約在形式上被廢除,抗戰(zhàn)的前途漸趨于明朗,如何“不失時機借外交成就”“改造民眾心理,轉(zhuǎn)移社會風(fēng)氣,革除政治習(xí)性”以重新凝聚國民政府搖搖欲墜的權(quán)威,消弭群眾普遍的革命心理便成為國民政府抗戰(zhàn)建國事業(yè)的當(dāng)務(wù)之急,“移風(fēng)易俗,莫善于樂,治上安民,莫善于禮”,[3](P343)戴季陶的想法得到了蔣介石的認(rèn)可,于是在蔣的授意下,戴出面主持民國禮制的討論與議定,受命以來戴季陶對三禮“朝夕誦讀”,[4](P322)進(jìn)而研習(xí)四史、通志、通考等,“三延其期、六易其稿”做《學(xué)禮錄》一書,在這本書及同期的書信文章中,戴季陶表達(dá)了他仿周之制度為民國制禮作樂、建國育民的禮制思想。已有關(guān)于戴季陶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其早年思想的轉(zhuǎn)變、重新解釋孫中山思想的“戴季陶主義”和戴季陶與日本關(guān)系的研究,缺乏對其晚年思想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力圖通過戴季陶晚年留下的“制禮”文獻(xiàn),分析其晚年的禮制思想。
一、戴季陶對禮的基本認(rèn)識
在《中華民國禮制之基本觀念》中,戴季陶寫了他對“禮”的基本認(rèn)識:“禮者,人群共同生活之倫紀(jì),行為之準(zhǔn)則,性情之節(jié)制也”。[5](P355)禮的核心,在戴季陶的定義中為公共秩序、良善風(fēng)俗,與現(xiàn)代所稱的民法類似,但其邊界又遠(yuǎn)遠(yuǎn)溢出法“權(quán)利——義務(wù)”的邊界。禮與法又是“僅一線之隔”,都是對秩序的框定、對人心的約束,比起政令刑罰的冷酷森嚴(yán)、高壓強制,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理念認(rèn)為禮樂德治會帶來井然有序且脈脈溫情的社會、有恥且格的國民,由此提升華夏文明的境界。因此,戴季陶對禮的定義有四:體也;理也;履也;宜也,但其對于禮制思想的闡述更注重的是從建國治民的“禮者體也、禮者理也”[5](P356)角度,對此《周禮》給了這個角度最好的借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設(shè)官分職、以為民極。”[6](P2)傳說中的文王武王周公制禮作樂的功業(yè)造就了儒家典籍中所載的“理想國”——孔子曾形容為“郁郁乎文哉”,因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戴季陶論周之禮樂政教“上承堯舜,下啟漢唐,享國之久,逾兩千年,其文化郁郁為后世立法者,蓋所自來者遠(yuǎn),而所積者厚,取經(jīng)多而用物弘也。”[5](P359)“文教之降,超邁前古,漢唐以來,更莫及焉。”[7](P282)周制煌煌,而所以綱紀(jì)天下立范后世,在于其“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tuán)體”,[8](P302-303)禮樂制度經(jīng)孔子之手變?yōu)槿陙碇袊紊鐣睦硐牒陥D。自清末至民國,近代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傳統(tǒng)的帝國于辛亥年崩解,新的民國始終綱紀(jì)不立,從北洋到南京,革命的聲浪此起彼伏,建國立制的宏愿與消弭革命的立場縈繞在戴季陶的心中,并隨著抗戰(zhàn)所要求的全民動員體制而更加迫在眉睫。觀今鑒古,戴季陶認(rèn)為唯有周制既可共克時艱,又能為萬世開太平。因而建國“以學(xué)周為上”。[5](P85)
從文王、武王、周公的年代到抗戰(zhàn)期間的民國,時間的跨度已有3000 余年,外延寬廣的禮制從來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其內(nèi)容、結(jié)構(gòu)及使用范圍因王朝興廢、社會變遷而屢次發(fā)生變化,但同時,禮的基本義理與社會功能則在數(shù)千年間未發(fā)生過根本變化,禮是道德于行為上的展現(xiàn),儀式行為的內(nèi)容可以隨時代而變,但引領(lǐng)其間的禮義則自古貫之。因此戴季陶在認(rèn)為“禮者,宜也”的同時也認(rèn)為“禮者,體也”、“禮者,理也”。[5](P355)具體而言以“學(xué)周為上”,戴所致力的是將周禮的“體”“理”注入到民國的國民、社會乃至領(lǐng)袖之中。
周禮在文獻(xiàn)中展現(xiàn)的是一個完善的國家典制,從個人到社會、國家都盡然有序,富有哲理和道德,“政教一體,文武一體,安危禍福,上下共之”,[7](P281)整個國家社會是以禮樂政教結(jié)成的文化體,這個理想國為數(shù)千年來的儒者所深信不疑,戴季陶亦是如此。因此以周禮為藍(lán)圖,戴季陶力圖從道德秩序、社會秩序、政治秩序提出對民國禮制提綱挈領(lǐng)的規(guī)劃。
二、道德秩序:節(jié)制中和、文武并舉的建設(shè)之德
在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中,物我合一、天人合一,,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與宇宙的和諧運行之間存在著銅山崩而洛鐘應(yīng)的關(guān)系,天有問題,不完美,矯正的責(zé)任在人,矯正的力量在人心。[9](P39)近代中國天道隱去、國道彰顯,天人關(guān)系被國人關(guān)系所取代,但從道德人心出發(fā)挽救國運的信念卻一以貫之下來,存在于從孫中山到戴季陶等人心中。
孫中山在《建國方略》曾說過:“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xiàn)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10](P4)從此出發(fā),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與重新解釋者,戴季陶更是堅定認(rèn)為欲挽回世運首在于挽回人心。從五四之時開始,在討論盛衰興亡之際,對于當(dāng)時甚囂塵上的“經(jīng)濟(jì)原因”,戴氏在文章之中堅稱:“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不過是歷代興亡的一部分道理,而最大的關(guān)系,是在人的關(guān)系,從歷代人心的振興與墮落上,可以決定歷代的興亡”,[5](P1007)故“救國之道,首重人心”。[5](P1383)
在戴季陶看來,當(dāng)日人心最大的危機在于欲望與虛無,失去了節(jié)制中和的約束。一者是以欲望為主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說的毒害,一者是以自由為主的權(quán)利學(xué)說的放縱。“不重個人修為,拋卻民族道德”,“人與人不知立身之本,故土地荒蕪,事業(yè)衰敗,不知立國之本,故百事頹廢,內(nèi)亂時做,外辱趁之。”因而“我輩負(fù)建國責(zé)任者,自有端趨向而正人心之責(zé)。”[5](P21)
所以在戴季陶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將“崇道德以振人心”列為第一條,并在之后補充“厥有四端”:
“一曰:切實闡揚總理遺教
二曰:確立與國家社會家族個人現(xiàn)代生活相應(yīng),繁簡適中,文質(zhì)合度之禮制
三曰:制定與國家社會公共生活相應(yīng)、莊敬正大剛健和平之樂章,陶育民族道德,潤澤國民奕世不衰之生命
四曰:在社會實際之生活上,提倡服務(wù)互助、整潔有序之習(xí)慣,俾養(yǎng)成普通自然之風(fēng)尚,以立克己合群之始端。”[5](P1047-1058)
可見,在戴季陶的思想里,文質(zhì)合度、莊敬平和的道德是禮樂的主旨,也是他制禮作樂的目的,比起繁縟的禮節(jié)所呈現(xiàn)出來的文明氣象,禮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籠罩和道德自律中的意義更為戴季陶所期待。與中華民國禮制所匹配的道德,戴季陶定位為孫中山承自《中庸》所提出的“智仁勇”三達(dá)德,并引申為“智以知仁,勇以行和。而所以行之者三,存之以誠,行之以敬,致之以公耳,誠者意也,公者道也,而敬者,其行也”。[5](P355)在戴季陶所看重的道德中,仁與敬占有特殊的地位,這兩者所代表的謙卑克制的心態(tài),被戴季陶認(rèn)為是建設(shè)之德。[5](P550)
傳統(tǒng)儒家自孔子開始便以人為本位,因而戴季陶進(jìn)言,人類有別于動物的特點,“推其德本,首在仁愛。施之于國家,則為忠孝,施之于社會人類,則為信義和平,皆無不以仁愛為徹始徹終之至善。”[5](P534)與要求自我節(jié)制的“仁”相匹配的是要求自我審慎的“敬”。“禮主于敬,曰毋不敬,慎者,敬之興也。”[5](P258)
周的禮制除了“節(jié)人類之性情”之外,還有一點讓戴季陶頗為神往,那就是“文武合一”:“周制文武合一,無無業(yè)失教不能戰(zhàn)之民,亦無不能率兵做戰(zhàn)之官,故其所謂大學(xué)者,文武兼修,德術(shù)并重。”[7](P277)“政教一致,文武一體,安危禍福,上下共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有戎事,即已征召及于全民,則六官之長,亦必全體服戎,蓋全國無一不知禮樂之民,無一不能射御之官。周之文明者此也。”[7](P281)
自清末“軍國民教育”傳入,普魯士和日本那樣的國民普遍的軍事訓(xùn)練和強力的國防動員成為一種教育理念,但戴季陶卻將這種教育理念賦予中國傳統(tǒng)色彩,并嵌入到周代的禮樂制度中。
“國家之成,賴于武力,源于武教,修于武德”,[5](P738)何為武德?即同為“智仁勇三達(dá)德”,武德的最高價值在于“止戈”之意,“能扶天下之危者,則具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樂者,則獲天下之福,止戈為武之義,于此可以大明。”[5](P1425)禮節(jié)制而慎重的思想道德亦籠罩于“武德”之上,在敬慎仁愛之間,文武最終達(dá)為一體,成為戴季陶所理想的國民風(fēng)尚。
但文武之道終究不出心性之學(xué),“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傳統(tǒng)道學(xué)教育如何不流于空疏并進(jìn)而應(yīng)付日益專業(yè)化的現(xiàn)代社會和內(nèi)憂外患的嚴(yán)酷環(huán)境?戴季陶在其所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在崇道德以正人心的第一條之后,將“興實學(xué)以奠國本”[5](P1049)列為第二條,但戴季陶對科學(xué)技術(shù)終不脫“器用”的認(rèn)知,在他的觀念里,現(xiàn)代炫目的科技與“有虞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5](P538)并沒有本質(zhì)性的區(qū)別,不認(rèn)為科學(xué)技術(shù)在價值上有一套不可否定、不可截斷的技術(shù)理性,“而倫理修身教育是精神教育,是教育的根本”,[5](P507)“常德習(xí)教,重于克己,習(xí)于器用”是戴季陶看來理想的本立致用之道。總的來說,戴季陶對禮制之下理想國民的暢想強調(diào)文武并重、節(jié)制中和,終究是以德行為本,并未太遠(yuǎn)離半個世紀(jì)之前張之洞的“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框架。
三、社會秩序:全能政府、賢人政治的周制復(fù)歸
孫中山多次以“一盤散沙”形容中國社會的現(xiàn)狀,認(rèn)為國人由于沒有組織、缺乏紀(jì)律、缺失共同信仰而導(dǎo)致自由散漫、民風(fēng)萎靡。[11](P722-723)戴季陶對中國社會的判斷繼承了孫中山,“國人幾千年來一直有如一盤散沙,社會缺乏組織”,[5](P13)在這樣的語境之下,戴季陶診斷中國社會的病相在于缺乏組織而濫于自由,荒于教化且缺少信仰。
二十年代初,國民黨“以俄為師”的改造讓戴季陶等看到了嚴(yán)絲合縫的組織性、上下一體的動員力,在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所面對的嚴(yán)酷的民族戰(zhàn)爭中,這種組織性與動員力儼然是現(xiàn)代國家生死存亡的標(biāo)志,“要在現(xiàn)代世界中生存,必須變成高度國防國家不可。高度國防國家特征,在政治上看,一切國家機關(guān),各個行政部門,一切社會機構(gòu),各級社會組織,整個的構(gòu)成國防設(shè)備之一,在一個動力使用之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能夠動,能夠自動,很有力量的動,這叫做高度的國防。換句話說,一切科學(xué)化。”[5](P195)“革命之道,使全國民眾成為一有機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12](P104)高度的組織化與動員力是戴季陶所認(rèn)為的現(xiàn)代國家的標(biāo)志,也是革命的目標(biāo),但其“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充斥著工具理性化的科層制并不符合戴氏這樣心懷傳統(tǒng)的人心中“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中庸之道,在他看來,上古《周禮》中對周制的描述既符合了對國家社會高度組織化的要求,又充盈著脈脈溫情,顯示著和諧高尚。
戴季陶認(rèn)為周禮將整個國家以王官為軸,結(jié)成了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周禮六官分職而聯(lián)事,其組織之嚴(yán)密,漢以后無能及者,尤人之身體然,五官四肢,各有其用,而皆相聯(lián)屬,未有手動而足不相關(guān),耳動而目不相屬,唯主之者不同耳。”[7](P284)周通過禮樂政教、王官鄉(xiāng)紳家國同構(gòu)、組織成一個嚴(yán)密的政治文明體,在這樣的政治體中,既有傳統(tǒng)社會“養(yǎng)生送死,敬老慈幼”的脈脈溫情,又能“國有戎事,即征召于全體國民,則六官之長,亦必全體服戎”,[7](P281)禮樂政教合為一體,“國與民為一體,軍與民為一致,德行道藝為一途”,[7](P283)體現(xiàn)在每一個國民身上,“蓋全國無一不知禮樂之民,無一不能射御之官,周之文明者此也。”[7](P281)
故戴季陶總結(jié)道:“周之政治,為最優(yōu)良之特點,其古今列代所不及者,曰計劃政治萬能政府而已”。[7](P290)但戴季陶又認(rèn)為這樣的“計劃政治萬能政府”與現(xiàn)代國家行政官僚機構(gòu)的工具理性邏輯和科層制運作不同,政治運行的靈魂不是出于機械的律令程序,而是出于“賢人德業(yè)”、“禮樂教化”。“政府所以成其萬能,政治所以成為最切實際之計劃者,蓋政出于賢,賢興于教,教周于民,民遂其生,下無失教失養(yǎng)之民,上無違法亂紀(jì)之官,無失時失度之政。”[7](P290)“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戴季陶經(jīng)常引用孟子這句話表達(dá)在公共政治中人治和法制并興的重要性。對于通常所認(rèn)為的傳統(tǒng)政治偏重人治輕視法制,戴季陶則言:“中國古代并不是人治,而是以人事制度為中心的法治國家。歐洲行政重法,用法來防止個人能力的發(fā)展,中國是重視行政,重視人員的拔取與淘汰。”[5](P195)“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孔子在《中庸》中對于政治的認(rèn)識,以此為標(biāo)準(zhǔn),戴季陶認(rèn)為“中國今日之所以離亂至于是者,其原因在于政治不良,而政治所以不良者,人事不臧,為其大端。”[5](P132)比起現(xiàn)代西方政治理念中所強調(diào)的權(quán)力歸屬和程序正義,戴季陶更看重儒家所推崇的道德責(zé)任,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戴氏的“全能政府”“并不強調(diào)國家權(quán)力的歸屬問題,將國家政治職能的承擔(dān)和社會職能的發(fā)揮視作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13](P171)
在論述完“國”之后,戴季陶進(jìn)而提出自己的“全民政治”觀,以使傳統(tǒng)周制與現(xiàn)代政治理念相對接:周之所謂外朝之政者,大有類于近代之所謂全民政治。最要者,在人民直接表示其意向而不假諸代言人。蓋當(dāng)時之卿、大夫、士,皆受教育庠序與國學(xué),德行道藝皆有成就,然后得選舉以升于朝,故卿大夫士為人民之代表。士不世官,官事不攝,其本即在選賢興能,出長入治。茍以現(xiàn)代間接民權(quán)制度例之,卿大夫士已無一非間接行使民權(quán)之人,而外朝之政,其義不若是也。[7](P291)
由上文可見,戴氏強調(diào)人民之中的賢者比人民的多數(shù)更能代表民意。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戴季陶曾給出這樣的解釋:
“在昔為政在人,人也者,指圣人賢人而言,有圣賢即有善政,無圣賢即生惡政。何為善政,即人人足衣足食,無鰥寡孤獨之存在,如政治上有一人不得其所,則圣賢引為己罪,圣賢不啻社會之天平。今天平已轉(zhuǎn)為多數(shù)人之手,若社會上有一人不得其所,則多數(shù)人不能辭其咎。”[5](P13)
在這段文字中,戴氏將往昔圣賢所擔(dān)負(fù)的天道轉(zhuǎn)化為今者大眾抽象的公意,而同時又將平等從權(quán)利轉(zhuǎn)化為道德責(zé)任,用其另一段文字解,這樣的“平等觀”是因為“天之生人,雖然有聰明財力的不平等,但是人心必欲使之平等,這是道德上的最高目的——努力利人”。[5](P13)因此戴季陶所認(rèn)為的選舉權(quán)依舊為“選賢與能”:“選杰出之人物,拔諸群眾之上,使當(dāng)政治之任,是為選舉權(quán)。”[12](P102)
戴季陶所矚目的“計劃政治萬能政府”模板無疑出自蘇聯(lián),但是賦予其的政治倫理與制度安排卻又不離傳統(tǒng)政治道德為先、賢人為任、教化為責(zé)的框架。在這樣的框架下,中央之于地方的動員力度如何?是否能達(dá)成戴季陶所觀察的如蘇聯(lián)那樣嚴(yán)絲合縫、如臂使指的國家機器呢?
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對地方的安排是以縣為基礎(chǔ)的自治,而戴季陶將這種縣的自治賦予了“禮樂道德”與“賢人政治”的暢想。戴季陶嘗言:“中國之社會,基礎(chǔ)何在?吾人細(xì)心推求之,則知其每一鄉(xiāng)村,至少必有會受高等教育服務(wù)于鄉(xiāng)村這三人,其一人為醫(yī)師,一人為牧師,一人為小學(xué)校長,此三人者,實為全村之領(lǐng)袖,一切公私生活,均有此三人指揮之協(xié)助之,故能日進(jìn)文明,民安物豐。”[5](P9)從這段話看,戴所強調(diào)的并非國家權(quán)力在鄉(xiāng)村的滲透與組織,而是透著地方本位的“民安物豐,可以看做是傳統(tǒng)鄉(xiāng)紳政治的現(xiàn)代延續(xù),而不是對鄉(xiāng)村原有組織的打破和固有權(quán)威的顛覆。在傳統(tǒng)基層社會中,與紳權(quán)同樣重要的是家族,面對當(dāng)時有人提出農(nóng)村中家族的存在有礙于國家權(quán)力向下深入,戴季陶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近年來各處多有欲促進(jìn)國家統(tǒng)一而反對同鄉(xiāng)團(tuán)結(jié),甚而至于不許有宗族家族之存在,此種運動,似乎太過,不近人情,其弊與太過重視家族宗族而忘國家之統(tǒng)一者,同為不合乎中道,不近乎人情之偏見。”[5](P597)中道,即中庸,被戴季陶認(rèn)為是“人間極純正的道德準(zhǔn)則”,[5](P468)亦是他想象中地方社會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間的操作原則,除了對紳權(quán)與家族這類小共同體要求中道而行之外,戴季陶對地方公共權(quán)力的運作考量也秉持著傳統(tǒng)禮樂教化的模式,他欣賞雍正皇帝教國之六訓(xùn):“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āng)里,教訓(xùn)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5](P555-559)這是一種指向地方與家族本位倫理要求,而非指向一個大的國家認(rèn)同的公民道德。他理想中的基層權(quán)力運作模式是“父以教子,師以教弟,長官以教僚屬,將帥以教士兵”,以達(dá)到“共信共行,互切互磋,親愛精誠,始終無間”[4](P221)的理想狀態(tài)。。
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在戴季陶的理想國里禮制覆蓋下的社會秩序都是充滿著賢人和德性的考量,他認(rèn)為這樣的社會一方面具有現(xiàn)代國家的組織與動員能力,另一方面亦保留了傳統(tǒng)地方的和諧安寧,符合國父孫中山對地方“自治”的規(guī)劃,更重要的是戴季陶認(rèn)為這樣充滿著德性倫理和責(zé)任倫理的社會國家可以規(guī)避掉大眾民主的平庸與自私,保留傳統(tǒng)政治事業(yè)中強調(diào)的高尚道德,在中道而行的信念下,他試圖用經(jīng)典中“周制”的復(fù)歸來整合一個兼容傳統(tǒng)現(xiàn)代、個人社會國家的制度,在個人的道德秩序與社會的德性運作之外,戴季陶還力圖通過領(lǐng)袖示范來,框定禮制下的政治秩序。
四、政治秩序: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作則君師的領(lǐng)袖表率
在由孔子開創(chuàng)的儒家思想里,與禮樂的黃金時代相輔而成的是由上古圣君構(gòu)成的先王世界。正是由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其德行為民立極,才使得典籍中所記述的黃金時代有了出現(xiàn)的可能。
1924 年孫中山答采訪者問其思想來源之時,說:“中國有一個正統(tǒng)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tǒng)思想,來發(fā)揚光大。”[14](P203-207)孫中山死后,戴季陶作《孫文主義之哲學(xué)的基礎(chǔ)》,根據(jù)這句話及孫中山晚年復(fù)歸傳統(tǒng)的思想取向,將孫中山及其思想全部搬入道統(tǒng)之中,“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于中國正統(tǒng)思想的中庸之道”,[15](P343)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孔子以來繼往開來的大圣”。[15](P427)而在其所著《學(xué)禮錄》的開篇,則模仿《尚書》對先王的贊譽來極言孫中山承接道統(tǒng)、繼往開來:“國父敬天法祖,覆載無私,光照四方,惠澤百世。立承先啟后救國救民之大志,創(chuàng)三民主義五權(quán)憲法之宏規(guī)。領(lǐng)導(dǎo)國民革命,興中華,建民國。于今全國國民共遵遺教,眾志齊一,德業(yè)日新。政府敬承休命,夙夜匪懈。”[7](P267)力圖將孫中山以國父之尊立于儒家經(jīng)典里需要頂禮膜拜的先王圣殿。
先王之道,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立范定制,堯、舜、禹、成湯、文、武、周公無一不是集道統(tǒng)治統(tǒng)于一身,開創(chuàng)了立范千載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倫理原則。因此戴季陶建構(gòu)孫中山的政治合法性,一方面強調(diào)孫為民國創(chuàng)制三民主義五權(quán)憲法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更要意圖突出孫在政治秩序外對民國道德秩序的示范:“復(fù)殷殷垂訓(xùn),教人以智仁勇之三達(dá)德,而歸之于至誠至敬至公”,[7](P267)在這兩方面之下,戴季陶認(rèn)為國父孫中山的形象就同經(jīng)典中的古圣先賢一樣,身兼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其思想是民國政治超越性的權(quán)威所在,承接傳統(tǒng),合于現(xiàn)實,是立國之基,萬世不易之法。
但是在建構(gòu)了孫中山“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的形象之后,戴季陶又強調(diào)“周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未聞即以文王為上帝。”[5](P352)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乃至孫中山在政道與治道的權(quán)威來自其對“上帝”所代表的至德要道的領(lǐng)悟和踐履,而非其自身是上帝。具體到孫中山而言,在極言孫中山“敬天法祖,覆載無私”之后,但卻在孔子紀(jì)念日上明確反對將孫中山的遺像供于上而將孔子的遺像供于下的狀況,“試想當(dāng)國父生前,若如此辦,國父肯乎?必不肯也。”[7](P296)
與孫中山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的國父形象建構(gòu)一同進(jìn)行的,是戴季陶對孫中山思想去革命化的重新解釋,在戴季陶禮制的理想國里,孫中山的思想被呈現(xiàn)成與德性倫理、賢人政治一致的尊德尚賢的模式:
遺訓(xùn)曰: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jìn)大同。公也。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忠必信。敬也。一心一意,貫徹始終。誠也。……仁者仁也,親親為大,三民主義之本,在于民族,親親之義也。而其實踐也,以民生為首要,博愛之義也。民權(quán)主義者,治國之法,尊賢尚功之義也。合而言之,仁而已矣。[7](P271)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將中國傳統(tǒng)的領(lǐng)袖歸為“卡里斯馬”類領(lǐng)袖,認(rèn)為中國的領(lǐng)袖往往由德行而被認(rèn)為具有正當(dāng)性,并且由德行具有神圣性或表率性。[16](P64)在戰(zhàn)爭之中,卡里斯馬被稱贊與追隨并不由于其具有英雄精神,而是因為其具有“道德上的正義”和個人的高尚德行,即“卡里斯馬美德”。[16](P166)戴季陶將這種道德上的正義不僅強調(diào)于經(jīng)他之手重新解釋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里,,還投射到抗戰(zhàn)時期蔣介石形象的建構(gòu)中。戴季陶與蔣介石相交于微時,見證了蔣從“無名之輩”到攬黨、政、軍權(quán)于一身的國民黨總裁、孫中山接班人,但是他不論在公開的演講還是私人的書信中,對于蔣介石領(lǐng)袖能力的稱贊與領(lǐng)袖地位的認(rèn)可無一不是從道德品行出發(fā),而非其在政治軍事上的能力或功績,其中不乏“至誠忠孝”[5](P563)“以德從政”[5](P569)“真實不欺”[5](P1362)這類力圖將蔣介石包裝為傳統(tǒng)儒家士大夫的詞匯。
儒家政治以教化自任,以德性為感召,以政治盡宗教之職能。錢穆在點評中國古今政治家時,將其稱為“政治之風(fēng)度”,風(fēng)指“風(fēng)力”,度指“格度”,“風(fēng)力者,如風(fēng)之遇物,披拂感動,當(dāng)者皆靡,格度則如寸矩尺規(guī),萬物不齊,得之為檢校而自歸為齊。”“因此一政治家之風(fēng)度,其潛力所及,每成為一時政治之風(fēng)度。”[17](P233)
禮制作為親親尊尊的等級秩序,其權(quán)威重在道德表率,通過建構(gòu)孫中山和蔣介石“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作則君師”的形象,戴季陶終歸希望能夠以道德去扭轉(zhuǎn)“軍紀(jì)、吏治、士習(xí)、民風(fēng)之日趨墮落,殺人放火掠奪之肆行無忌”[5](P949)的時代,通過領(lǐng)袖的道德表率,可以讓社會令行教化、有序和諧,因此民國的禮治秩序在戴季陶的想象里是:“務(wù)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長官以教屬僚,將帥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親愛精誠,始終無間。人人能成為頂天立地之人,斯中華民國能成為富強康樂之國。”[7](P268)
結(jié)語
余英時曾指出:與西方思想史上經(jīng)典的激進(jìn)與保守不同,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激進(jìn)與保守之間沒有一個可供作為基點的穩(wěn)定的秩序,“沒有一個共同的坐標(biāo)”。換句話說,近代中國不論激進(jìn)者還是保守者,都是對現(xiàn)實的國家社會乃至思想文化秩序不甚滿意的,認(rèn)為“政治退化”了。[18](P191-193)但在這種不滿的基點上,與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對進(jìn)步價值的確認(rèn)不同,戴季陶所代表的這類保守主義者卻力圖從歷史傳統(tǒng)中尋求已經(jīng)消亡的社會或子虛烏有的烏托邦,來作為對現(xiàn)實困境的克服和理想國的想象,從孫中山死后用儒家思想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到抗戰(zhàn)中在受命制禮的契機下對其禮制思想的闡述,中年豹變后的戴季陶一直致力于讓背誦著“革命尚未成功”的國民政府變成古代傳統(tǒng)合法繼承人,《學(xué)禮錄》中對道德秩序、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三者結(jié)合復(fù)歸周制的想象是是他保守主義者理想的理念型建構(gòu)(ideal type),韋伯形容這種理念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的作用時說:“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zhì)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創(chuàng)造出的世界圖像,常如軌道上的轉(zhuǎn)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著人類行為。”[16](P15)戴季陶及其苦心造詣的禮樂理想及其之后“北泉議禮”的盛會同民國這個時代之間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他所向往、所描繪的禮樂周制的理想國與當(dāng)日民國大多數(shù)深受西方學(xué)說與時代氛圍影響的青年學(xué)生、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不是一個理念籠罩下的世界圖像,就像兩條不同的鐵軌,相交于內(nèi)憂外患、眾聲喧嘩的當(dāng)日民國現(xiàn)實這一點,卻終究是通往不同的方向,這也注定了戴季陶所主張的禮樂周制的建國理想應(yīng)者寥寥,更何況對于良知、責(zé)任倫理和表率的強調(diào)在民國政府官員觸目驚心的腐敗對照之下,讓當(dāng)時哪怕傾向文化保守的人也頗感如《大學(xué)》所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19](P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