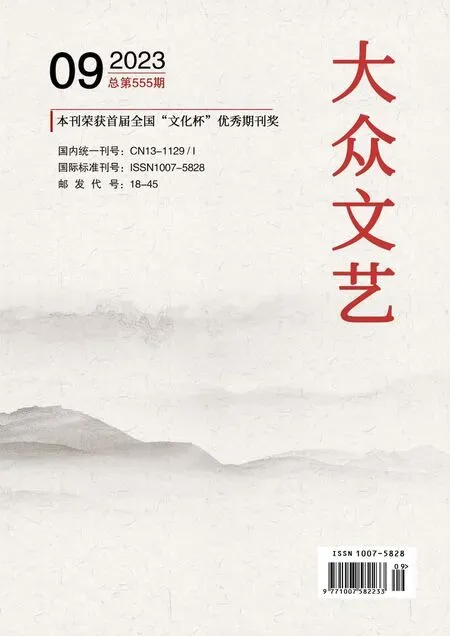T.S.艾略特與卞之琳三十年代創(chuàng)作中對(duì)古典詩傳統(tǒng)的回望
孫思宇
(鄭州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河南鄭州 450001)
卞之琳是現(xiàn)代中國著名詩人和翻譯家,他在漫長(zhǎng)的文學(xué)生涯中不僅留有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而且還撰寫了數(shù)量可觀的文字以集中闡釋他對(duì)新詩寫作的理論認(rèn)識(shí),極大推動(dòng)了中國新詩的發(fā)展。在1979年出版的《雕蟲紀(jì)歷》所寫自序中,卞之琳將其詩歌創(chuàng)作分為三個(gè)階段。其中的戰(zhàn)前詩作集中體現(xiàn)了卞之琳詩歌的獨(dú)特風(fēng)格。這一時(shí)期他開始接受現(xiàn)代西方詩學(xué)理論,創(chuàng)作日益走向成熟,從波德萊爾、魏爾倫、馬拉美到瓦雷里、里爾克和艾略特,卞之琳不斷汲取外來養(yǎng)分并結(jié)合既有經(jīng)驗(yàn),逐漸形成自己的詩歌氣象。而在諸多西方詩人中,卞之琳對(duì)艾略特較為推崇,并多次論及艾略特與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首先,卞之琳在譯介艾略特的詩文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xiàn):艾略特的著名論文《傳統(tǒng)與個(gè)人才能》正是在卞之琳的翻譯下才得以首次為中國民眾所知,而且《卞之琳譯文集》中也收錄了他對(duì)艾略特的評(píng)價(jià):“艾略特……最初一起干的是所謂‘拆臺(tái)’工作……他們?cè)诰裆蠠o出路當(dāng)中產(chǎn)生的消極作品里,也多少可以起揭露現(xiàn)時(shí)的積極作用。”①[1]從中可以看到卞之琳對(duì)艾略特創(chuàng)作的肯定態(tài)度。此外,他還回憶到:“對(duì)于西方文學(xué)……從1932年翻譯魏爾倫和象征主義的文章轉(zhuǎn)到1934年譯T.S.艾略特論傳統(tǒng)的文章,也可見其中的變化。”②[2]更提及“寫《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對(duì)于我前期中間階段的寫法不無關(guān)系。”③[3]不難發(fā)現(xiàn),艾略特對(duì)卞之琳來說具有相當(dāng)重要意義。
1934年5月1日出版的《學(xué)文》雜志上刊登了卞之琳受老師葉公超囑托翻譯的《傳統(tǒng)與個(gè)人才能》,這也是它在中國刊物上的首次發(fā)表。卞之琳自稱此文“大致對(duì)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較能經(jīng)得起時(shí)間考驗(yàn)的新詩篇的產(chǎn)生起過一定作用。”④[4]艾略特這篇論文主要由兩方面組成:首先,艾略特介紹了自己對(duì)于歷史意識(shí)、歷史現(xiàn)存性等問題的看法:“傳統(tǒng)的意義實(shí)在要廣大得多……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存在性……現(xiàn)存的藝術(shù)經(jīng)典本身就構(gòu)成一個(gè)理想的秩序,這個(gè)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紹進(jìn)來而發(fā)生變化。這個(gè)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現(xiàn)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樣以后要繼續(xù)保持完整,整個(gè)的秩序就必須改變一下。”⑤因此作家和作品始終都處于歷史和傳統(tǒng)之中,他們被傳統(tǒng)制約的同時(shí)最終也會(huì)加入傳統(tǒng)并推動(dòng)現(xiàn)存的體系發(fā)生變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傳統(tǒng)的價(jià)值和意義得以進(jìn)一步豐富。其次,艾略特具體論述了詩人心靈在具體創(chuàng)作中的催化功能,進(jìn)而旗幟鮮明地指出詩歌價(jià)值主要體現(xiàn)在其藝術(shù)過程上而非創(chuàng)作主體本身情感的強(qiáng)烈波動(dòng)。雖然《傳統(tǒng)與個(gè)人才能》沒有能用于實(shí)際參考的創(chuàng)作方法,但它肯定了詩人與傳統(tǒng)的密切聯(lián)系,并在此基礎(chǔ)上主張?jiān)娙艘粩喾艞壆?dāng)前的自己,歸附更有價(jià)值的東西。這些理論無疑對(duì)卞之琳產(chǎn)生了影響,促使他在1930年代的創(chuàng)作中更自覺地檢視和利用中國古典詩歌的豐富資源。
作為貫學(xué)中西的詩人和翻譯家,卞之琳在20世紀(jì)30年代初就走上一條既現(xiàn)代又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路徑,而《傳統(tǒng)與個(gè)人才能》亦加深了他對(duì)“傳統(tǒng)”的理解。發(fā)表于抗戰(zhàn)勝利前夕的《新文學(xué)與西洋文學(xué)》一文中卞之琳系統(tǒng)表達(dá)了有關(guān)“傳統(tǒng)”的體會(huì):“那并不是對(duì)舊東西的模仿……我們只有以新的眼光來看舊東西,才會(huì)使舊的還能是活的。”⑥[5]可見卞之琳眼中的傳統(tǒng)并非靜止的實(shí)體性概念,它與現(xiàn)代超越了狹隘的二元對(duì)立,在時(shí)代和歷史中不斷變遷并顯示出強(qiáng)大的整合能力和生命力。這就使置身現(xiàn)代西方詩歌場(chǎng)域中的卞之琳更強(qiáng)烈地意識(shí)到自身傳統(tǒng)的力量,他在1930年代創(chuàng)作的一些作品就從多個(gè)方面對(duì)這種“傳統(tǒng)”觀念進(jìn)行實(shí)踐。
一、有意識(shí)使用中國古典詩歌成規(guī)
卞之琳在詩歌中曾大量運(yùn)用“水”“夢(mèng)”“春草”等古典意象,此前學(xué)者對(duì)此做過專門分析。古典意象的運(yùn)用固然對(duì)詩歌風(fēng)格定型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僅憑這些詞匯只能在表面上渲染典雅氣氛,隱藏于意象背后的結(jié)構(gòu)因素才是關(guān)鍵。中國古體詩詞的中心意象群都與詩歌主題有所關(guān)聯(lián),而所謂古典詩歌成規(guī)的運(yùn)用就是這些元素在現(xiàn)代語境中的重現(xiàn),表現(xiàn)之一便是對(duì)“典故”的使用。眾所周知,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先驅(qū)胡適先生旗幟鮮明地提出“務(wù)去濫調(diào)套語”“不用典”兩條戒律,但卞之琳卻在多首詩中大量用典,還自加注釋闡明其含義。雖然這些并非都是古代詩人常用的典故,可仍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卞之琳的詩歌與古詩的聯(lián)系,同時(shí)也和胡適提倡的“白話”詩分道揚(yáng)鑣。例如《春城》: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fēng)箏
……
真悲哉,小孩子也學(xué)老頭子
別看他人小,垃圾堆上放風(fēng)箏
他也會(huì)“想起了當(dāng)年事……”
悲哉,聽滿城的古木
徒然的大呼
呼啊,呼啊,呼啊
歸去也,歸去也
故都故都奈若何
我是一只斷線的風(fēng)箏
……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fēng)箏
詩題中“春城”意象源于韓翃《寒食》首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直以來,這首詩常被用以諷刺君王獨(dú)寵專權(quán)的宦官和外戚的昏庸之舉。由此可見,詩句背后隱含的典故無形中擴(kuò)大了詩歌的表現(xiàn)范圍,而卞之琳將自己的《春城》視為“諷刺詩”就是將其作為古典詩歌的成規(guī)加以使用。除此之外還有以下幾處:“歸去也,歸去也”化用《詩經(jīng)·邶風(fēng)·式微》蘊(yùn)含的國家衰敗之意;“故都故都奈若何”則改寫了項(xiàng)羽的《垓下歌》;“想起了當(dāng)年事……”似乎只是一般引語,但由于卞之琳熟知戲詞,此處可能截取了《四郎探母》中楊四郎在遼營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喟嘆。在一系列化用和典故中卞之琳表現(xiàn)出“直接對(duì)兵臨城下的故都(包括身在其中的自己)所作的冷嘲熱諷”這種只有具備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shí)的人才會(huì)產(chǎn)生的情感。不僅如此,我們還能看到艾略特《荒原》的影子。首先,《春城》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詩中酒館對(duì)話那部分所表現(xiàn)出的戲劇性表演的抒情方式。作家在該段詩歌中將抒情主體隱藏,單從對(duì)話的戲劇情境中表現(xiàn)批判意味。《春城》第四段的表現(xiàn)方式則與“酒館對(duì)話”如出一轍,作者不對(duì)交談雙方做出說明,也沒有讓抒情主體表達(dá)觀點(diǎn),僅憑對(duì)話傳達(dá)出諷刺意圖。另外,作者還像旁觀者一般觀察著其他的戲劇性場(chǎng)景:如“他也會(huì)‘想起了當(dāng)年事……’”好似稚童唱著滄桑的戲詞,蒼涼感呼之欲出。另一個(gè)技巧則是對(duì)古典成規(guī)的運(yùn)用,該手法在《荒原》中也大量出現(xiàn),艾略特甚至為此加以注解。《春城》中出現(xiàn)的諸多短句正如《荒原》中“請(qǐng)快些,時(shí)間到了”“晚安”的不斷循環(huán),象征著卞之琳對(duì)艾略特傳統(tǒng)觀的實(shí)踐。
從卞之琳的《無題》詩中同樣能體現(xiàn)出他對(duì)古典詩歌成規(guī)的運(yùn)用。學(xué)者們大多將這種以男女情愛作為主要內(nèi)容并有所寄托的“無題詩”體式看作李商隱的首創(chuàng)⑦[6]。卞之琳的《無題》共五首,也有關(guān)于愛情的表達(dá),這是對(duì)李商隱的無題詩最明顯的借用。不過更重要的區(qū)別在于它們體式上的差異。卞之琳五首《無題》的格式皆為“每首八行,四行一段”;可正如張采田所說“此體只能施之七律,方可宛轉(zhuǎn)動(dòng)情”,⑧[7]從古至今李商隱《無題》中最為人稱道的卻還是六首七律詩。對(duì)比卞詩的“每首八行,四行一段”,它自然與近體律詩有相似之處,但實(shí)則兩者并不相同。眾所周知,律詩的每一聯(lián)都需要承擔(dān)固定功能,而且非常注重韻律和節(jié)奏上的起承轉(zhuǎn)合,即使李商隱詩歌具有較強(qiáng)的跳躍性和隱晦性,我們?nèi)匀荒茌^為清晰地看到其中的七律章法。而卞之琳《無題五》中“襟眼是有用的,因?yàn)槭强盏摹焙汀笆澜缡强盏模驗(yàn)槭怯杏玫摹眱啥卧谡Z法上呈現(xiàn)出重復(fù)中變化的樣式,并通過“簪花”“散步”等意象的轉(zhuǎn)變?cè)谕瑯拥倪壿嫿Y(jié)構(gòu)中得出相似的意味。可以說第二段是在第一段基礎(chǔ)上推衍出來的,其中的同構(gòu)邏輯又憑借意象的變化凝聚詩意,這與律詩乃至所有古典詩歌的組織方式都有所不同。再如卞之琳的《無題三》。此處明顯化用了李商隱“夢(mèng)為遠(yuǎn)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一句。通過對(duì)比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李詩主題上所突出的“思遠(yuǎn)”與《無題三》著力表現(xiàn)的相見和分離確有相似之處。但細(xì)讀后我們便會(huì)發(fā)現(xiàn)此詩布局上的巧思:第一段中“我”“你”“門薦”“滲墨紙”“塵土”“字淚”“踩”“掩”之間存在高度對(duì)應(yīng),是邏輯同構(gòu)關(guān)系;第二段第一句接續(xù)上文,而“珊瑚”又理應(yīng)是“海水洗盡人間煙火”后的結(jié)晶,所以第二句顯然與后兩句承接更為密切。全詩雖傳遞出惆悵情緒,但詩人并未直接陳說短暫相逢后又要分離的悲哀,而通過見面時(shí)“我”的慎重到想象對(duì)方的書信再到最后“月臺(tái)送別”等一系列具體場(chǎng)景折射出一絲纏綿的哀傷,這與李商隱《無題》詩中的寄托和寓言手法有所不同。
二、詩歌中自由聯(lián)想的結(jié)構(gòu)方式
當(dāng)深入到結(jié)構(gòu)層面時(shí),卞之琳的詩呈現(xiàn)出另外的特點(diǎn),廢名稱之為“自由表現(xiàn)”和“觀念跳得厲害”,⑨[8]這與卞之琳奉行的“注重暗示性”和“著重含蓄”⑩[9]藝術(shù)追求共同為其詩歌創(chuàng)作賦予類似于李商隱、姜白石詩詞的形跡。造成此形跡的原因除了對(duì)古典詩歌成規(guī)的運(yùn)用,還有就是廢名所說的與古典詩相近的新風(fēng)格。廢名曾將這一特征與溫庭筠的《菩薩蠻》相比較。這首詞從開篇中靜態(tài)的繡鳥聯(lián)想到真實(shí)水鳥激起的波紋,再進(jìn)一步推至池上的花,思緒呈現(xiàn)出跳躍性。下片四句的跳躍更加明顯,廢名說“他描寫了好幾樣事情,讀者讀之而不覺”,(11)但看似不覺實(shí)則整首詞中都暗含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繡衫”句對(duì)應(yīng)“翠翹金縷”,“煙草”句則與“水紋”句的“春池碧”契合。朦朧的煙草正是“池塘生春草”所致,而“青瑣”句的“芳菲”恰是“池上”句的“海棠梨”,進(jìn)一步觸發(fā)“玉關(guān)”一句女子對(duì)心上人的思念。即便全篇沒有邏輯連接詞,表面看只是意象的堆放,其內(nèi)在的邏輯結(jié)構(gòu)卻嚴(yán)絲合縫,使之看似跳躍卻又讓人讀之不覺。由此可見,觀念的跳躍并不隨意,貌似混亂的表面下貫穿內(nèi)在的情感和邏輯線索。
類似的對(duì)位結(jié)構(gòu)在卞之琳詩中也有體現(xiàn)。例如《寂寞》。這首詩結(jié)構(gòu)簡(jiǎn)單,但頗似溫庭筠詞中的意義對(duì)位模式。作者首先通過聲音的相似性將蟈蟈與夜明表聯(lián)系起來,夜明表像鳴叫的蟈蟈在枕邊滴答作響,幫助孩子排遣苦悶。第二段再次提到蟈蟈,不僅字面上呼應(yīng)第一段,而且鳴叫的“動(dòng)”還與荒墓的“靜”形成對(duì)照;詩的最后說“他死了三小時(shí)夜明表還不曾休止”,可見雖然表還在發(fā)聲但人已歸于沉寂,此時(shí)夜明表和死去的孩子之間同樣存在對(duì)照,使夜明表與蟈蟈在“寂寞”的意義上再次產(chǎn)生聯(lián)系。從語言上也能發(fā)現(xiàn)詩中鮮有表示邏輯關(guān)系及表達(dá)情緒的詞匯,意義層次間都只做客觀呈現(xiàn)而沒有進(jìn)行說明和抒情,體現(xiàn)出異于溫庭筠的客觀化特征。
另一種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詩歌中的跳躍結(jié)構(gòu)線索是情感,但由于情感的急遽跳躍往往令讀者難以捉摸,也就造成它們不易用釋義的方法進(jìn)行解讀。因此,情感線索如若真的存在于詩歌中并發(fā)揮功能,對(duì)其解讀也必定要立足文本中的形式功能。如卞之琳的《車站》。這首詩中有多個(gè)“夢(mèng)”字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意象,但主題又是現(xiàn)實(shí)。在夢(mèng)與非夢(mèng)的意象之間出現(xiàn)鋼絲床、小地震、火車的怔忡幾個(gè)跳躍性強(qiáng)同時(shí)又是對(duì)心跳的喻指。從語義上看,被彈響的鋼絲床多出現(xiàn)在輾轉(zhuǎn)反側(cè)或夢(mèng)醒時(shí)分;“小地震”指的是驚心動(dòng)魄的夢(mèng)境;接著以火車的怔忡隱喻火車與鐵軌的撞擊和心率的共振,又象征火車將到來時(shí)主人公內(nèi)心的激動(dòng),暗示“我”對(duì)火車到來已渴望許久,卻唯恐如今的現(xiàn)實(shí)只是一場(chǎng)夢(mèng)的心路歷程。
三、跳躍及非演繹傾向的語言
此外,卞之琳的詩歌還呈現(xiàn)出一種并不常見的技巧,即語言上跳躍和非演繹傾向的特征。前文中通過自由聯(lián)想構(gòu)成的觀念跳躍從語言上就能找到線索,進(jìn)而使讀者產(chǎn)生別樣的審美效果。比如溫庭筠“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一句,塞雁、城烏、鷓鴣雖都是鳥類意象,但卻是不同的動(dòng)物,而隨著字面線索的跳躍,讀者的觀念和視野也隨之變化。再看卞之琳的《候鳥問題》。這首詩的跳躍從白鴿鈴到駱駝鈴開始,再從駱駝到陀螺,它們共同營造的語境由“遠(yuǎn)了”和“挽”形成重合。接著通過“鳥”進(jìn)行的隱喻則構(gòu)成全詩的核心。被風(fēng)箏羈絆的“紙鷹、紙燕、紙雄雞”不僅與歸雁形成對(duì)比,而且和后文的《候鳥問題》一書共同暗示“我”像風(fēng)箏和陀螺一樣不自由的尷尬處境。整首詩的語境彼此斷裂又共同指向?qū)Α拔摇钡碾[喻,將“我”被封鎖在城市中的困境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
由此可見,結(jié)構(gòu)和語言的跳躍是兩個(gè)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葉維廉把它作為中國舊詩語言的重要特征與白話詩的說理性和演繹性相對(duì)比,將之命名為非演繹性表達(dá),并進(jìn)一步概括出:“極少或沒有人稱代詞;極少或沒有時(shí)態(tài)或表示時(shí)間變化的詞;極少使用表示邏輯的連接性、分析性的詞”。(12)[10]等特點(diǎn)。而我們?cè)跍乩钜慌傻膭?chuàng)作中往往能看到這些要素:他們?cè)谠娫~中使用最多的就是名詞和實(shí)詞,其次是動(dòng)詞,而很少使用表示邏輯關(guān)系、時(shí)態(tài)、心理狀態(tài)以及突顯感情色彩的名詞,這就使句子間的轉(zhuǎn)換鮮有情感上的說明。由此,溫李詩歌注重自由表現(xiàn)、跳躍等結(jié)構(gòu)要素實(shí)則都可以視為語言的特點(diǎn)。進(jìn)一步分析卞之琳的詩歌也能發(fā)現(xiàn)這種特征。卞之琳的詩中也多有副詞和虛詞,但它們的使用一般是為了達(dá)到讓句子通順的目的,而在句與句、段與段之間的空白處這些需要邏輯線索的地方卻往往省去連接詞。例如《半島》:
半島是大陸的纖手
遙指海上的三神山
小樓已有了三面水
可看而不可飲的
一脈泉乃涌到庭心
人跡仍描到門前
昨夜里一點(diǎn)寶石
你望見的就是這里
用窗簾藏卻大海吧
怕來客又遙望出帆
全詩沒有表示狀態(tài)或時(shí)態(tài)的副詞,只在“昨夜里一點(diǎn)寶石/你望見的就是這里”中出現(xiàn)了人稱和時(shí)間狀語。那么與其說是強(qiáng)調(diào)時(shí)間,不如說是在突出暗夜與發(fā)光寶石的對(duì)比。所以此時(shí)的“昨夜”就代表了回憶和對(duì)過去的悵惘,像李商隱《無題》中的“昨夜星辰昨夜風(fēng)”一樣不單單發(fā)揮其表示時(shí)間的作用。而且詩中沒有表明分析和邏輯性的關(guān)聯(lián)詞,比如作者并未說明“三神山”“三面水”和“一脈泉”之間的關(guān)系,還有最后兩句也明顯省略了表示因果的連接詞等等。這種非演繹性語言給卞之琳的詩歌帶來古典風(fēng)韻的同時(shí)也加深了其中的晦澀之感。
四、客觀性表達(dá)
艾略特認(rèn)為維護(hù)傳統(tǒng)離不開個(gè)性的犧牲,這是他對(duì)浪漫主義、表現(xiàn)主義等理論的反駁,并且在《玄學(xué)派詩人》《哈姆雷特》等文中進(jìn)一步提出“客觀對(duì)應(yīng)物”“思想與感性的結(jié)合”等創(chuàng)作原則。比如“客觀對(duì)應(yīng)物”原則是指:“用一系列實(shí)物、場(chǎng)景,一連串事件來表現(xiàn)某種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終形式必然是感覺經(jīng)驗(yàn)的外部事實(shí)一旦出現(xiàn),便能立刻喚醒那種情感。”(13)[11]而中國古代的詠物詞中似乎也有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例如姜夔《暗香疏影》中《暗香》一篇:“舊時(shí)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fēng)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zhǎng)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shí)見得。”姜夔并沒有直接抒情,而是將開篇的梅花作為激發(fā)思緒的關(guān)鍵線索,作者以“梅花”展開聯(lián)想,不僅完成了回憶與現(xiàn)實(shí)的場(chǎng)景切換,還表現(xiàn)出追憶往昔的感慨。這就使“自我”消隱在這類詠物詞的結(jié)構(gòu)中,進(jìn)而讓以對(duì)物進(jìn)行觀察的主體視角結(jié)構(gòu)全章的方式替代了既往主體情感占據(jù)中心地位的抒情方式。
卞之琳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同樣運(yùn)用了類似的技巧。比如代表性的詠物詩《圓寶盒》。卞之琳在結(jié)構(gòu)中將自我抒情主體隱藏,開篇點(diǎn)出“幻想”并將圓寶盒作為對(duì)想象力容器的象征,串聯(lián)各種顏色結(jié)構(gòu)全章。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卞之琳曾在《雕蟲紀(jì)歷》中依據(jù)“讓時(shí)間作水吧,睡榻作舟/仰臥艙中隨白云變幻/不知兩岸桃花已遠(yuǎn)”這幾句已經(jīng)作廢的詩做出了一些解釋。他認(rèn)為這兩段具有相似性。對(duì)比來看,它們都存在視點(diǎn)變換,注釋中的詩句在結(jié)尾處隱去“讓時(shí)間作水,睡榻作舟”的主體,淡化人的視角;正文將圓寶盒作為觀察視點(diǎn)同樣隱藏了“人”,使圓寶盒成為融合不同時(shí)空和視角的色相的載體,呈現(xiàn)出客觀化效果。再如收錄于《魚目集》中的《歸》。詩開篇中“聞自己的足音”“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都可看作是客觀化表達(dá),而作者也通過天文家、足音等客觀對(duì)應(yīng)物將抽象的情感外化為具體形象,同樣帶來了含蓄的審美效果。此外,這首詩中還有卞之琳對(duì)艾略特詩歌的化用和吸收。除了此前論者“只不過中國詩人寫得更簡(jiǎn)練,更緊湊,而這是傳統(tǒng)的絕句律詩多年熏陶的結(jié)果”(14)[12]這句對(duì)卞之琳化用艾略特《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以道路比喻心理狀態(tài)的評(píng)價(jià),詩中的客觀對(duì)應(yīng)物同樣是對(duì)艾略特詩學(xué)原則的實(shí)踐。此外,卞之琳將《歸》收入《雕蟲紀(jì)歷》時(shí)對(duì)它做出了一些改動(dòng),修改后的《歸》似乎就像通俗的說理性表達(dá)一般,并且強(qiáng)調(diào)了“脫出軌道”,對(duì)“圈子之外”也不再提及:每句字?jǐn)?shù)不再整齊,將“聞”改為“聽見了”,第三句也變?yōu)椤澳窃谕鈱佣颐摮隽塑壍溃俊盵13]這或許出于作者對(duì)一些可能引發(fā)歧義的詞的擔(dān)憂,不過句中依舊保持著“在外層”的說法,可見作者客觀的態(tài)度并未改變,整首詩的風(fēng)格也沒有較大出入。
結(jié)語
綜上所述,卞之琳在1934-1937年間的創(chuàng)作中大量選取古典詩詞的典故、意象入詩,而且還融合古典詩詞的結(jié)構(gòu)和語言特征,體現(xiàn)出他這一時(shí)期對(duì)傳統(tǒng)的回歸。同時(shí),盡管卞之琳詩歌中存在許多古典詩詞元素,但其詩學(xué)理論基礎(chǔ)和審美視野是現(xiàn)代的,而且毫不掩飾對(duì)西方詩學(xué)技巧的運(yùn)用,表達(dá)的也是現(xiàn)代人所具備的情感。就像他所說的那樣:“由于對(duì)西方詩‘深一層’的認(rèn)識(shí)……進(jìn)一步了解舊詩、舊詞對(duì)于新詩應(yīng)具的繼承價(jià)值,一般新詩寫作有了他所謂‘驚人的發(fā)展……’”(15)因此卞之琳對(duì)中國古典詩歌傳統(tǒng)的回望并非簡(jiǎn)單地用“舊材料”進(jìn)行拼湊,所以沒有造成林庚那樣被嘲笑為“沒有格律的古詩”的結(jié)果。他以現(xiàn)代人的眼光站在現(xiàn)代詩學(xué)的審美立場(chǎng)上去發(fā)現(xiàn)意象、典故等傳統(tǒng)資源在現(xiàn)代語境中的適配性與合理性,這不僅使其創(chuàng)作在新與舊的碰撞中激發(fā)更多可能,而且也推動(dòng)我國古代詩歌傳統(tǒng)在“歷史現(xiàn)存性”的開掘中煥發(fā)生機(jī)與活力。
注釋:
①周伊慧.T.S.艾略特對(duì)卞之琳的影響[J].湖南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社版),2006(04):151.
②卞之琳.卞之琳譯文集(上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5.
③卞之琳.雕蟲紀(jì)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16.
④卞之琳.卞之琳集[M].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9:339.
⑤卞之琳.卞之琳譯文集(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77.
⑥解志熙.靈氣雄心開新面——卞之琳詩論、小說與散文漫論[J].現(xiàn)代中文學(xué)刊,2011(1):78.
⑦劉學(xué)鍇.李商隱傳論[M].合肥: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2002:630-633.
⑧劉學(xué)鍇.李商隱詩歌集解(增訂重排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4:1647.
⑨(11)廢名、朱英誕.新詩講稿[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3,332頁.
⑩卞之琳.人與詩:憶舊說新(增訂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31頁.
(12)葉維廉.中國詩學(xué)[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2:246-252.
(13)王恩衷編譯.艾略特詩學(xué)論集[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13.
(14)王佐良.中國現(xiàn)代詩中的現(xiàn)代主義——一個(gè)回顧[M].文藝研究,1983(04):30.
(15)卞之琳.人與詩:憶舊說新(增訂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