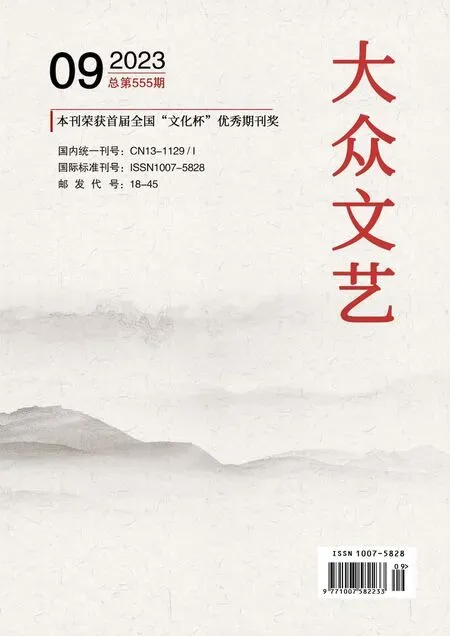論延安時期詩歌大眾化的美學思想
李堅凱
(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陜西延安 716000)
1935年,在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師陜北后,延安文藝的序幕正式被拉開。各種文藝政策陸續推出,文藝活動競相上演,文藝組織紛紛成立。街頭詩、戲劇、歌舞劇等各種各樣的文藝表演送到前線軍民的眼前,尤其是自抗戰全面爆發之后,周揚、丁玲、艾思奇、何其芳等文藝理論家的到來,他們用優秀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來支持著抗戰。在各種文藝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中,關于詩歌創作的理論和作品的出現可以說是一方耀眼的花園。
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稱《講話》)發表之后,描寫勞動大眾生產生活的作品逐漸占據主流位置,具有“人民性”的詩歌作品源源不斷地被創作出來,甚至由此形成了與“九葉詩派”“七月詩派”鼎足而立的詩人群體。按照龍泉明的解釋,這一群體可以稱之為“延安詩派”,即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不斷吸引其他解放區詩人加入這個團體,從而促進工農的密切結合。因此從根本上講,它“不是一個純地域性的詩歌群體,而是一個詩歌流派。”[1]在這一團體下,聚攏了許許多多的詩人,如活躍在陜甘寧邊區的蕭三、賀敬之、艾青等;活躍于晉察冀的魏巍、田間等;活躍于太行山區的阮章競、葉楓等。他們雖然所處地域不同,但是在詩歌創作上,都集中體現了“大眾化”這一美學思想。同時,也正是由于這種地域上的差異,間接使得各個詩人之間的文學思想相互碰撞,從而促進了他們在詩歌美學思想上達成一致。
一、形式的大眾化傳播
1942年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2]857這表明他已經認識到在當時文藝界存在著對工農兵輕視的問題,因此他通過《講話》所要傳達的就是要求文藝工作者要樹立“為工農兵服務”的創作意識。并且鼓勵文藝工作者要親近工農兵,同時引導文藝工作者開始思考“為誰而歌”的問題。針對毛澤東所指出的文藝創作中“人不熟”這一問題,許多詩人進行了反思,于是他們開始逐漸去貼近勞動人民的生活,甚至為了創作出老百姓真正喜聞樂見的作品,自發的去和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艾青創作的《吳滿有》,他為了能夠創作出大眾滿意的作品,便住到了吳滿有的家中,與他朝夕相處、平等交流。在創作出初稿后,又來到吳滿有的家中讀給他們聽,當面聽取吳滿有的意見,不斷修改,直到吳滿有滿意為止。這些行為表現出了“在主流政治文化尤其是毛澤東文藝美學的影響下,延安詩派形成了工農兵詩歌審美思想”,[3]即大眾化的詩歌審美思想。
為了進一步將這一思想落實到底,延安時期的詩人們開始從詩歌創作最基礎的“詩體”入手,各自在自己擅長的詩體上進行創作,古體詩、自由體詩、十四行詩等詩歌越來越多地被創作出來。不過在這一系列的創作探索過程中,自由體詩歌仍是許多群眾最為喜愛的表現形式,而且因為詩人們需要用大眾的情感來反映大眾的心聲,所以他們就必須以人民大眾的思想和習慣去創作作品,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民歌體”詩歌,如戈壁舟創作的《邊區好似八陣圖》:“兩山中間一道川,/兩川中間一架山。/翻過山來又是川,/轉過川來又是山。/邊區好似八陣圖,/敵人進來不得還!”[4]120又如賀敬之的《臨男民兵》《過黃河》《果子香》等作品,這些詩歌都用大眾最為熟悉以及最能接受的形式來教育影響百姓,使其真正成了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
詩歌向民歌“取經”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創造具有民族形式的詩歌和實現詩歌大眾化是當時延安文藝界的要求。蕭三在《論詩歌的民族形式》中就指出中國新詩的創作必須要有中國情感,必須要用具有中國民族的形式來表達。要求詩人們在關注民族形式的同時亦要注意中國百姓的整體情況,即當時中國大眾至少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朗誦出來的詩太洋化了的時候,老百姓一定不會喜歡的,一定不會被接受。”[5]同時,阮章競也發現群眾之所以對他們的“民歌體”詩歌抱有興趣是因為用民歌形式“編寫歌舞、活報劇,群眾都較喜歡看。”[6]而人民群眾的反映令文藝工作者們意識到只有創作出對群眾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才能贏得群眾的歡迎。
此外,形式的大眾化不僅體現在創作形式上的“民歌化”,還體現在傳播方式的多樣性上。1938年邊區文協“戰歌社”發表了《街頭詩歌運動的宣言》,針對印刷和紙張的缺失問題,他們號召人們進行街頭詩運動,其目的不僅在于利用詩歌做抗戰的武器,而且也要使詩歌真正走上大眾化的道路。由此,在詩人們活躍的區域隨處可見“墻頭詩”“巖壁詩”。同年,作為“街頭詩運動”發起人之一的高敏夫將街頭詩的種子帶到了晉察冀邊區,隨后街頭詩便在這里生根發芽,遍地開花。楊朔稱之為:“(詩歌)絕不高坐在繆斯的寶典里……他們走進農村,走進軍隊,使詩與大眾相結合,同時使大眾的生活詩化。”[7]這些詩歌以其準確、生動、凝練而又形象的語言,傳達了極其深刻的思想和極其強烈的感情,使詩歌在鼓舞人心、愉悅性情、催人奮進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真正做到了在實現詩歌大眾化的過程中利用詩歌做抗戰武器。
由此,我們可以從詩歌形式的大眾化中看出,《講話》之后“詩歌要為人民服務”已經印刻在了延安時期詩人們的思想中,他們已然意識到人民群眾才是詩歌服務的主體。這表明在文化領域,文藝真正的主人已經由知識分子開始向人民群眾轉變。
二、語言的大眾化流行
延安文藝工作者對于根據地人民生活情況的了解也是以《講話》作為分界線的。在此之前,他們對于人民生活并不了解,有時為了創作甚至憑空捏造人民生活,這使得他們的詩歌無論是從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還是從語言的使用上都不切實際,以至于創作出來的作品百姓們讀不懂,也就談不上接受。對于這一點,毛澤東就在《講話》中明確提出了文藝工作者們的短處就是由于“語言不懂”,導致他們高高在上,與人民群眾有距離感,所以有時創作的作品中生造了一些與人民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語句。并且指出要想做到文藝“大眾化”,途徑就是“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2]851曾經主張通過詩歌朗誦來實現詩歌大眾化的音樂家呂驥也認為,詩歌朗誦要“接地氣”,這不是為了給文藝工作者畫“牢籠”,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所做出的正確選擇。畢竟當一個地區只有“土語”時,那么“土語”就是通用的語言。
自此,詩人們開始與人民有了初步的結合,少量的農民語言和民間語言開始逐步進入到詩人們的詩歌中,就如艾青在《吳滿有》中對吳滿有的生活描寫,無論是寫吳滿有之前的貧苦生活:“三個孩子擠在炕上,/不是赤著上身,/就是光著屁股,/臟的像豬子,/瘦得像猴子。”[8]54還是寫他現在的幸福生活:“你的臉像一朵向日葵,/在明亮的天空下面,/連影子里都藏著歡喜。”[8]54這些詩歌無不是用人民大眾的語言來表達,并且都飽含真情,真正做到了為民而歌。
自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后,學習人民大眾的語言就成了一股熱潮,廣大文藝工作者們在將陜北方言拿來“學習”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適用于自己作品的表達方式。可以說,相較之前,在語言的大眾化運用上,延安時期的詩人們已經正式的“土”化,如蕭三、田間、李季等,大量的陜北方言出現在他們的口中、作品中。在田間創作的長詩《戎冠秀》中,他就選取了許多群眾的語言作為創作元素,如:“……戎冠秀心發軟,/老鼠跳過她手邊;/頭一回減租,/鬧了個糊糊。”[8]55這些詩歌通過運用群眾的語言,不僅使作品更加符合群眾審美,而且飽含了群眾的情感和智慧。
此外,還有青年詩人賀敬之,他在《講話》發表之后,積極踐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號召,通過深入群眾,學習群眾語言的方式,將詩歌與陜北民歌進行了融合加工,如他創作的《行軍散歌(開差走了)》:“崖下下來了老媽媽,/窯里出來了女娃娃/……把我們圍個不透風,/手拉手兒把話明:‘水有源來樹有根,/見了咱們八路軍親又親’……”[9]376這一句句鮮活口語的運用,描繪出了八路軍與邊區百姓之間的魚水之情,讓人不禁分外感動。這都是延安時期詩人們在語言上接近民眾,踐行文藝大眾化的結果。
縱觀延安時期詩人們創作語言的變化過程,他們不再自視清高,和勞苦大眾保持距離感,而是拜群眾為師,向群眾學習,努力汲取和提煉大眾語言的精華,創作出了許多樸素的、自然的、口語化的、非矯揉造作的、民族的新詩。這也使得他們在實現“小我”和“大我”的有機融合中,讓自己的創作充滿無限生機與活力。并且在推廣傳播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真正地表現出了只有符合大眾的接受習慣和欣賞口味,才能真正贏得大眾的喜愛。
三、內容的大眾化顯現
1943年,蕭三對《講話》之前的各種文藝思想進行過研究和總結,其中“有人認為,通俗、大眾的東西,至多只是文藝的一種——而且是‘低級’的一種,那些主張及實行寫通俗大眾東西的作家,是寫不出來真正‘高級’作品的”[4]60以及“寫些通俗的、大眾化的作品,只是為了抗戰需要,是出于一時的不得已,而其實,那是文藝的降低,甚至那不是文藝”[4]60的觀點可以說是和毛澤東所提倡的文藝大眾化背道而馳。針對這些觀點,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明確且有力的給予了回答:“對于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2]873這就使得延安時期詩歌大眾化的另一表現就是內容的大眾化。因為延安時期詩人們創作的詩歌歸根到底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必定脫離不了人民的生產勞動,所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作為詩歌的素材而出現。可以說,延安時期的詩歌不僅是人民生活的反映史,而且也是時代的記錄史。所以針對當時的人民生活,諸如生產勞作、擁軍支前,還有邊區百姓的民主政治以及全新生活等,詩人們都用自己的詩歌去盡情描寫,塑造了豐富多彩的人民群體形象。
同時,由于延安時期處在戰爭年代,一切圍繞戰爭,一切為了戰爭,是那個時代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詩人們所作的詩歌作品除了描寫戰爭、拼殺和犧牲外,大多數反映的是廣大勞動人民生產建設的場景。如藍曼《勞動的歌》:“我們緊緊地,/追趕著太陽和月亮,/我們把愛情,/全放在镢頭上。/停停镢頭向后望,/身后一片黑色的波浪。/土浪黑,我們汗滴,/正散發著陣陣清香……”[9]533戈壁舟的《燒炭》:“這是原始的森林,/這是無人的荒山,/縱橫浩浩數百里,/知道古老的黃河邊。/突然一支遠征軍,/出沒在這無人的森林。/鳥兒在叫第一聲歌唱,/人們就攀沿著荊棘前進……”[9]78這些詩就生動地表現出了邊區人民生產勞作的真實過程,記錄了廣大勞動人民為了美好生活而不斷奮斗的拼搏畫卷。除此之外,還有陳學昭的《邊區是我們的家》:“法西斯的第五縱隊,特務分子,/勾結敵人要來破壞我們,/惡魔的黑手,/伸向邊區,/試試看!/我們要用明快鋒利的劍,/斬斷那惡魔的黑手!/邊區是我們的家,/我們的生命屬于它,/我們要拿頭顱熱血來保衛它!”[9]304張鐵夫的《選民會》:“范五坐在那里灰溜溜地/低著頭不言語。/老村長制止了騷動起來講話,/他說范五是剛從白區過來的農民。/在國民黨那里他活了半輩子,/甚至沒有聽說過自由和民主,/邊區里人人平等他還沒全解下,/要使他腦筋改轉,/大家要慢慢教育他。”[9]333這兩詩就凸顯了當時身處邊區的老百姓們為了守護邊區,堅決對抗侵略者的堅定勇氣以及邊區農民參與民主政治,在政治領域翻了身的真實狀況。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那就是即使是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人們依然沒有放棄對于美好愛情的向往與追求,許多詩歌中都描寫了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其中傳播范圍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是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這部長詩以貧苦農民王貴與李香香的愛情為主線,描繪了農民與封建地主勢力的尖銳矛盾和激烈斗爭,歌頌了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曲折過程,塑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在我國現代詩歌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
從大眾化的美學思想來看,這種內容大眾化的出現主要是廣大詩歌作者在下鄉入伍的過程中,完成了心理身份轉換,詩人從思想到創作都實現了凈化,能夠主動、自覺地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也就是說,此時的詩人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詩人,而是親眼看到農民勞動甚至親身參加農民勞動的詩人,他們的創作視角聚于工農兵身上,他們作品的內容也就是大眾生活中的所有活動。如張志民的《王九訴苦》《死不著》描寫了農民階級在遭受苦難和壓迫之下的一種成長過程;柯仲平《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生產》一詩,描寫出了勞動人民進行抗戰的巨大決心……
結語
總而言之,從延安時期詩歌創作形式、創作語言以及創作內容“大眾化”的表現中能夠看出,在《講話》之前,詩歌大眾化已經是一個大部分詩人們所共識的觀點,但是就以何種方式去尋求“大眾化”則產生了多種分歧,不過這種分歧在《講話》發表之后便不復存在了。而且在經過這一實踐過程之后,作為精神產品的詩歌已經不再是精英階級的專屬,而是表現出一種文化重心向普通大眾下移的趨勢。并且這一過程也使得詩人們完成了思想上的蛻變,真正站到了大眾的立場上去創作,努力追求作品的“大眾化”成了他們創作的美學基礎。這一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文藝創作來說,依然具有借鑒意義。文藝工作者們應該時刻站在廣大群眾的立場上,將現實生活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有機結合,以文藝特有的方式將之展現;而不是用機械的、古板的或者巧合的一種描繪來想象性的創作文藝作品。所以,文藝家只有真正站在群眾之中,用文藝作品為群眾服務,才能真正體現“大眾化”的美學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