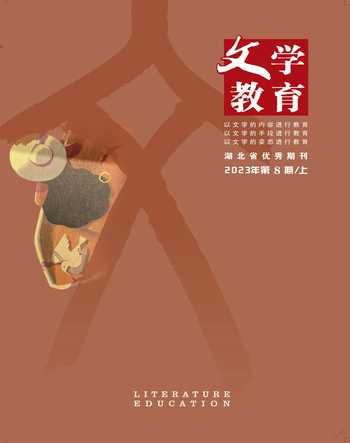遲子建小說集《一壇豬油》里的城市與鄉村
李霏
內容摘要:《一壇豬油》是一部以城市和鄉村為背景的小說集。遲子建以鄉下人的眼光審視城市,既看到了城市經濟的發達,人民生活的富足,又發現了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同時,她以城市人的眼光觀察鄉村,展現景美、人美、情美的鄉土魅力和其存在的不理想面。遲子建的城鄉書寫從最初的“鄉村崇拜”轉為客觀地訴說城鄉現狀,雖然鄉村存在一定的缺憾,但是它仍為人類心靈的安撫地。
關鍵詞:遲子建 《一壇豬油》 城市 鄉村
《一壇豬油》小說集是遲子建小說編年系列(1985-2010)的最后一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2004-2010年遲子建創作的以《一壇豬油》《采漿果的人》《野炊圖》等為代表的12篇小說,《一壇豬油》小說集在遲子建作品集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展現了遲子建創作風格的新轉變,由“童話般”書寫轉向社會現實書寫。在遲子建的筆下,城與鄉是這部小說集的兩大書寫空間,她筆下的城市與鄉村書寫具有雙重性特點。在寫作視角上,她站在鄉村審視城市,站在城市遙望鄉村。在激進的城鎮化進程中,作家沒有把城市和鄉村二元對立起來,而是在城與鄉的比照中,謀求城鄉的健康發展。
一.以鄉下人的眼光審視城市:躁動與生機
《一壇豬油》小說集收錄的作品創作于2004-2010年,當時中國社會正處于動態更新且持續發展的狀態,城鄉一體化快速推進,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時代浪潮下,城市文明以勢不可擋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推動社會轉型,為了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農民進城,城鄉交流進一步加強。1964-1981年遲子建在鄉村生活,后來由于求學和工作等原因一直居住在城市,與生活空間隨之變化的是遲子建寫作態度從早期完全抵觸城市轉為逐漸接受城市。1990年遲子建來到哈爾濱,她說,“最早來到哈爾濱,我沒有自己的屋子,所以工作寫作之余,特別喜歡在街上閑逛。我走到每一個地方,都覺陌生,因為這不是我生活的領地,我感到孤單,雖說哈爾濱是座美麗的城市。”[1]遲子建作為城市的“外來者”,面對陌生的城市她存在一定的抵觸情緒,但是,定居并了解哈爾濱的過程中,她也親身感受著在城市生活的優勢,享受著城市提供給她的更高的發展平臺,“我對哈爾濱,從最初的隔膜到現在就是水乳交融了,你在這座城市當中了解它的歷史、文化、風俗等等一切,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在升溫,對它有了表達的欲望。”[2]遲子建心路歷程的變化使得她與這座城市的關系從最初的有“隔”轉變為水乳交融,對城市的態度由“談不上愛”轉為“親”,并于1998年定居在哈爾濱。融入城市的生活經歷為她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城市自然而然地走進了作家筆下。遲子建筆下的城市可分為“有名”城市和“無名”城市,“有名”城市指有具體名字的城市,如北京、興林和塔里亞等,“無名”城市即沒有具體名字的城市。在《一壇豬油》小說集中,無論是有名城市還是無名城市,作家都消隱城市個性而刻畫城市群像,集中展現城鎮化中城市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客觀說明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里的城市“通病”。當飛速發展的城市與逐漸落后于時代的鄉村發生碰撞時,遲子建多以鄉下人的眼光審視城市,在冷色調的詩意書寫中展現城市的喧囂、墮落與生機。
遲子建以鄉下人的眼光審視城市,這是帶有較強的作家主觀感情色彩甚至是個人偏好的創作。相較于沈從文審視城市的“偏激”視角,遲子建審視城市的目光是溫和的、客觀的,她既寫出城市的問題,也肯定城市的先進之處。一方面,遲子建筆下的城市充溢著喧囂與黯淡。1990年遲子建初到哈爾濱,她既沒有完全屬于自己的生活空間,又要適應完全異于鄉村的生活模式,諸多因素使她喪失了對城市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她當時的內心是游離于城市的,她看到城市喧囂之下的罪惡與沉淪,異變的人類欲望。她從細微之處著筆,由外及內的暴露城市弱點,控訴優美環境的不再,譴責城市人們無休止的欲望。在《蒲草燈》等篇目中,遲子建筆下的城市骯臟逼仄,街巷散布著廢紙片,遺落著果皮、粘痰,空氣里彌漫著魚腥氣、街邊廁所的尿臊味。相較于描繪城市整體環境的光鮮亮麗,遲子建深入刻畫城市隱蔽處,關注生活在城市邊緣人們的生活環境。與環境惡化隨之而來的是城市欲望的泛濫。“20世紀90年代,城市文學開始從審美現代性的視角闡述城市生活,城市成為欲望的符號,城市文化演變成一種“物”的文化。”[3]遲子建筆下的城市欲望滋生,欲望誘導人生悲劇的輪番上演。色欲的引誘下,在《蒲草燈》中警察嫖娼,助長了當地的妓女行業;局長嫖娼,甚至侵犯民女鄒英,導致鄒英不堪恥辱,含恨而死。金錢橫行的城市中,物欲使城市人唯利益至上,行人還需要“付費問路”;《野炊圖》里的馮飚說:“這世道的人只認金元寶,銀錠子!”[4]更是對物欲城市的正面批評。
另一方面,遲子建筆下的城市又充滿了繁榮和生機。遲子建發掘城市閃光點,描繪城市的高樓大廈和一片車水馬龍的繁忙景象,遲子建肯定城市是一個生活富裕的所在,因為它滿足了現代人們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城鎮化進程中,城市作為主體不斷發展前進,城市的地理優勢和政治職能使城市優先享受到國家政策效益,從而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為城市人提供了富足的生活條件,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完整的基礎生活設施,這在遲子建的小說中都有所表現。在關于城市的側面描寫中,城市經濟發展前景更為明朗,城市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百雀林》中的明瓦進城后趕上縣里公路管理站增編,憑老兵復員政策,成為正式工人,明瓦的姐夫二歪離開鄉村到城市開種子店,二歪的外甥到城里學美發,明齋做廚子……不僅如此,城市為人們提供了更好的資源配置。城鄉衛生資源配置不平衡,具體表現在城鄉衛生費用、基礎衛生設施、醫療衛生管理體制和醫療保障體系等方面。《百雀林》里的王瓊閣得了股骨頭壞死,要從小城鎮遠赴到蚌埠、赤峰和丹東等大城市看病,小腰嶺鎮和青峰村無法醫治的病人被轉到城市里的醫院接受治療,由此形成了鄉村到城市看病,小城市到大城市看病的普遍現象。而在遲子建關于城市的正面描寫中,可以看出城市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物質生活。《一壇豬油》小說集中,水果店、百貨商場、飯店、棋牌室、茶館、理發店等場所頻繁出現,高樓、馬路、吉普車、自行車早已普遍,碼頭上的客船和貨船生意繁忙。過年時的火車票價格高昂,但是仍然一票難求,列車上的乘客們愜意地吃燒雞、豬手,喝小酒、嗑瓜子。《五羊嶺的萬花筒》中城市餐館在夏季有熗拌木耳、鹵八角花生米、水晶豬皮凍等新式菜品,飯店一天走三五箱啤酒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二.以城市人的眼光觀察鄉村:感動與反思
遲子建小說編年系列共四卷,包括《北國一片蒼茫》《親親土豆》《花瓣飯》《一壇豬油》。在遲子建小說編年系列前三部作品中,她筆下的鄉村是一片不受塵世凡俗侵擾的理想之境,鄉村人也一直以正面形象出現,而在編年史系列最后一部《一壇豬油》小說集中,遲子建的城市生活經歷使她獲得了一種審視鄉村的全新視角,即以城市人的眼光審視鄉村。作家的創作風格發生變化,她理性看待并接受城市文明,不再采用以往“烏托邦”式鄉村描寫手法去展現完美無暇的鄉村,而是在表現鄉村美的同時,審慎地落筆于鄉村的惡俗之處。從城市反觀鄉村,鄉村并非從前印象里的那般完美,而是善惡并存。《一壇豬油》小說集中作家筆下的鄉村,充滿詩情畫意又含有眾生苦態,她對落后于時代的鄉村人充滿同情,在詩化語言中訴說他們的悲痛命運,使人在凄婉中感動,在溫情中反思。但總的來說,遲子建對待鄉村的態度是親近的,鄉村雖然充滿惡俗但仍是心中的清凈之地,是人類精神的安撫地。
遲子建與沈從文一樣,筆下的鄉村書寫是美麗的,都用詩意的語言表達淡淡的哀傷,氛圍凄婉唯美。《采漿果的人》中白云、青草、土地、野果等意象在作家的筆下可愛動人,又因鄉村遠離城市,既無“三廢”污染,也無噪音騷擾,空氣新鮮,土地肥沃,草木茂盛,這是一片美麗宜居的鄉村。正是在這種似真似幻的鄉村里,塑造了如鄒英(《野炊圖》)、紫云(《花牤子的春天》)、蒼蒼婆(《采漿果的人》)、黑妹(《塔里亞風雪夜》)等農村人物形象,她們有著烏溜溜的大眼睛、漾著笑意的嘴角、秀麗的臉龐。鄉村人不僅長相靚麗,而且精神風貌淳樸自然。《塔里亞風雪夜》中李貴是遲子建筆下理想的鄉下人形象,他為了不弄臟保潔員剛拖完的地面,脫鞋走進銀行;身處消息閉塞的小村莊仍關心民生國事,為汶川大地震捐出自己僅有的一百零五塊錢;他還連夜坐載蜂箱的車趕到城里看奧運開幕式;最后卻在向稅務局檢舉商家不開發票的路上發生車禍。李貴樂觀地直面生活苦難,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鄉村大自然中,作為鄉村養育出的后代,李貴富有同理心,善良真誠地待人,不畏懼世俗的眼光,忠于內心,勇敢熱烈地生活。但是這些農村人物的故事結局大多是充滿悲劇色彩或者具有深沉意味,使人感慨命運無常,又領略到鄉村的牧歌情調。
遲子建不僅以贊美的眼光欣賞鄉村,同時,也以反思的眼光審視鄉村滯后處。周曉揚曾評遲子建“不回避東北那片寒冷土地上的貧困、苦難和丑陋。”[5]原始鄉村環境孕育出了淳樸的鄉村民風,但鄉村也無可避免地存在落后低俗的一面。長期居住在城市的遲子建注意到鄉村的滯后處:存在缺憾的鄉村環境和鄉下人身上的劣根性。缺憾的鄉村盛行封建迷信,這阻礙了鄉下人接受科學文化的意識。在小說《西街魂兒》中,寶敦被炸山采石的聲響嚇到驚厥,以徐隊長、寶敦媽為代表的鄉下人們,他們相信封建迷信,愿意去找巫醫“治病”,認為郵票可以“招魂”,治愈身體的疾病。而從北京下放到農村接受勞動改造的張以菡則痛斥她們:“你們真夠愚昧的,孩子病了不去看醫生,去找巫婆!”[6]——表達了作家對農村愚昧現象的批評。村中的沼氣池因年久失修,在高溫環境爆炸導致張以菡身亡,但是西街鎮的鄉下人們不能客觀地理解并接受科學現象,把張以菡的死歸為是她不貢獻自己郵票,所以寶敦的冤魂藏進糞池,索了張以菡的命。此外,鄉村同城市一樣,存在情欲和色欲泛濫的現象。村民們經常開關于兩性的低俗玩笑,鄉下人口中所談論的大多都是男男女女的事情,女性之間擔心對方勾引自己的丈夫,男性之間擔心妻子與村里其他男人發生不正當關系。《花牤子春天》里的花牤子強行侵犯紫云、小寡婦、陳六嫂,墮落的陳六嫂在鄉村干起了妓女行當,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們在城市嫖娼,染上性病后又帶回鄉村。
三.遲子建筆下城市與鄉村的關系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工業化進程,我國的城鄉關系總體經歷了城鄉分治、二元對立體制局部瓦解、城鄉統籌和城鄉融合四個階段。小說集《一壇豬油》展現了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里,中國城鄉關系發生變化:從二元分治轉向城鄉統籌,這種變化使遲子建看到城鄉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進步與不足。《一壇豬油》小說集里的城鄉書寫以中國進入21世紀后的第一個十年作為社會背景,反映城市版圖不斷擴大,城市人擠占鄉下人生存空間的過程。城鄉關系是不平等的,城市更具有侵略性;但城鄉又絕非是二元對立的。“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 只有二者可持續發展, 才能相互支撐。”[7]城鄉相互支撐,促進彼此成長是作家理想的社會狀態,但是遲子建發現,現實城鄉關系的融合是艱難的。對于如遲子建一般的精英知識分子們來說,這種“難融”是一道較為容易跨過的障礙,即使最初的他們來自鄉村,她們依然可以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對于平凡的小人物來說,他們沒有適應城市生活的能力,城鄉的“融合”是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人類的心靈最終歸依到哪一方?遲子建最終選擇了鄉村,這既是她的“鄉土情結”,也是擁有過幾十年城市生活經歷的鄉下人遲子建最后的家園抉擇。
城與鄉的融合僅停留在表層空間的流動,在遲子建人文主義目光的注視下,其實城鄉深層次的、心靈層面上的融合依然是難以實現的。“新時期以來,城市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并成為現代化進程的導引方向,這個顯著事實直接引發了由鄉入城的現象。”[8]在城市居住多年的遲子建愈發清晰地認識到城鄉難融之處,作為一名精英知識分子,遲子建融入城市的過程是比較成功的,但是對于大多數鄉下人來說,融入城市的過程是對自身內里的“撕裂”,這種“撕裂”帶給他們身體上的疲憊與精神上的混沌,來自底層的鄉下人,經濟能力與觀念轉變都有所欠缺,致使鄉下人無法選擇自己理想中的城市生活,只能被動地等待城市生活的篩選。《雪窗簾》里來自農村的老婦人坐火車不會換臥鋪票,她失去了原本屬于自己的床位,在冰冷的板凳上獨坐整夜;老婦人不會坐火車折疊椅,向列車員求助卻換來不屑的眼神和刻薄的話語,車廂上的城市人用湊熱鬧的心態看完這一場鬧劇卻無人施以援手。城市人傲慢地咄咄逼人,鄉下人畏縮怯弱,鄉下人被城市排擠在城外,這是一堵無形的城,一座隔在城市與鄉下人心里的墻,這座城墻僅僅依靠外部力量是行不通的,只有城鄉從心底接納彼此才能真正地打通這座無形之墻。城與鄉在空間上是流動的,城市人會到鄉村進行勞動改造、走訪調研、收漿果等,對于走入鄉村的城市人來說,他們的心靈世界仍屬于城市,鄉村對于城市人只是出于目的性需要而短暫停留的地方。但是對于進城務工的鄉村人來說,他們的精神世界已然受到城市影響并發生動搖與改變,他們渴望在城市扎根但沒有能力在城市定居,最后又尷尬地重返鄉村。《百雀林》里的農村小孩周明瓦在十一歲時被養父接到城里生活,起初明瓦成家立業,人生順意,甚至他還幫助農村親戚們在城里打工,后來在一系列變故之后,明瓦卻無奈地返回鄉村任職養鳥員,依靠明瓦生存的農村親戚們也陸續失去了城市的工作,被迫返回鄉村。鄉下人進城后很難在城市扎根,他們只是完成了一次從農村到城市,或長或短的空間流動,而非長久的駐足生活。
面對城鄉難融的境況,雖然鄉村充滿缺憾,但是在遲子建筆下它仍為人類救贖之地。遲子建筆下的鄉村是非理想化的,帶著缺陷和傷痛,遲子建認識到城鎮化進程中城市縱情聲色、金錢本位、享樂主義等負面欲望已經成為了城市的一部分,無法根本性的剔除。而鄉村也染有這些不良風氣,遲子建筆下的鄉村也出現色情、重利和虛榮等道德“失范”的問題,但是鄉村的可塑性使這些問題迎刃而解。因為鄉村人正視個人欲望,不逃避犯下的錯誤,及時自省,適時改正。遲子建基于自己的生活習慣和生活體驗建立了一個人類精神家園的棲息地,這是承載著人類美好希望與真誠大愛的土地,這片土地就落在鄉村。遲子建把鄉村構想為生長真愛之地,真誠的愛可拯救人精神的墮落。小說《一壇豬油》中,“我”和丈夫老潘是地道的農村人,即使長時間分居異地,仍夫妻恩愛,感情堅定。“我”的兒子螞蟻也從小成長于農村,偶然機會認識了來自林場河對岸的蘇聯女孩并一見鐘情,他勇敢地游向河對岸的蘇聯,只為追尋真愛。鄉村能夠孕育并生長出真正的愛情,這種真愛救贖人們的精神。與之相反,城市無法生長真正的愛情,來自城市的崔大林為了與來自大城市的女教師程英結婚,偷走“我”的戒指,程英也為了一枚昂貴的戒指嫁給自己不愛的人,這是一對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脆弱的婚姻關系,絕非愛情。遲子建構想的這片真愛生長之地,更是自我救贖之地。《蒲草燈》中在城市犯罪的“我”逃回鄉村后,重獲心靈的歸屬感和熟悉感,相較于城市陰暗潮濕的環境,鄉村充滿陽光,有大片的草原、金紅的晚霞、米黃色的麥子和絢麗耀眼的葵花,較之對城市冷色調書寫的不同,作家選用大量暖色調事物打造放松的鄉村環境,使“我”恍然意識到自己的罪責,最終“我”擎著象征愛與希望的蒲草燈去自首。“我”在城市自首的念頭是出于對法律懲罰的恐懼,這是被動的救贖,而“我”在鄉村自首的念頭是受到鄉村來自精神上撫慰過后的結果,這是一種真正的、真誠的人心靈上的救贖,但是只有在鄉村,人才能做到心靈上的平靜。
歷史的車輪滾滾而來,城鎮化正處在現代化的宏大進程里,與傳統鄉村道德倫理、生活生產聯系最為密切的村民們,也面臨時代與社會的轉型。如何讓值得珍視的鄉土情感在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以某種新的形態保存下來值得現代人深思。遲子建在《一壇豬油》小說集中向外界傳遞出這樣的信息: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現代性一直都是二者共同追求的目標,一個截然二分的社會狀態是不健康的,遲子建希望城和鄉能夠相互支撐走向美好;但是在很難進行理想融合的當下,人類應當為自己選擇一個可以依靠的心靈港灣,那就是擇鄉村而依。遲子建對鄉村充滿信心,在她看來,鄉村在未來不僅會像城市一樣,是生活舒適自由的所在,鄉村還依然是人心靈的棲居之所,是值得依賴的精神富饒的家園。遲子建對鄉村充滿壯麗豐滿的信心與期待!
參考文獻
[1]董雨陽,陳淥,遲子建.從他鄉到故鄉——遲子建永遠溫情的文學世界[N].黑龍江日報,2013-05-16.
[2]王志艷,遲子建.遲子建長篇新作《煙火漫卷》:獻給哈爾濱的一首長詩[N].新華網,2020-09-10.
[3]于小植.“城市主體”建構及其限度——論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煙火漫卷》[J].文學評論,2021(06).
[4]遲子建:《一壇豬油》[M].第10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5]高平.小小的北極村 世界的北極村——遲子建文學創作的文化人類學簡釋[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
[6]遲子建:《一壇豬油》[M].第8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7]劉彥隨.中國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J].地理學報,2018,73(04):637-650.
[8]范耀華.論新時期以來“由鄉入城”的文學敘述[D].華東師范大學,2007.
[9]楊藝嫄.遲子建小說創作流變論[D].長沙理工大學,2015.
[10]桂璐璐.遲子建城市小說創作論[D].安徽大學,2015.
[11]鄭學鵬.遲子建小說對家園的尋求[D].華南理工大學,2015.
[12]仲秋云.論遲子建小說的苦難書寫[D].江南大學,2019.
[13]李培林.李煒.陳光金.田豐.新成長階段的中國社會建設——2010~2011年中國社會發展形勢分析與預測[R].第14頁,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