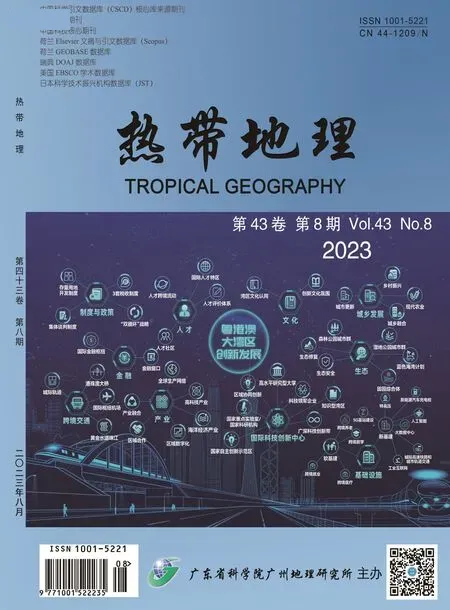基于地緣關系的“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區位優勢度評價
郭建科,馮天琪,秦婭風,劉曉揚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大連 116029;2.遼寧省“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校協同創新中心,大連 116029)
海上運輸作為商品與貨物流通的載體,承擔著全球貨物貿易運輸的主要部分。中國于2013年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后,截至2022年,“絲路海運”命名航線已達94 條,累計開行超過9 000艘次,完成集裝箱吞吐量超過1 000 萬標箱,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較2013 年增長了73%(國家發展改革委 等,2015),顯示“海上絲路”沿線巨大的經濟聯系與增長潛力。港口作為水陸交通最重要的聯系樞紐,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發揮商品與貨物集散、中轉的核心作用。如何對港口區位進行科學評價,成為一項具有現實意義的科學問題。
自1943 年E A Kautz 在《海港區位論》中對港口區位進行了探索后(楊吾揚 等,1997),港口研究的范圍不斷拓展至港口與腹地的發展以及國際貿易、國際關系等方面(Hilling et al., 1984)。港口的研究核心在于對腹地的評價。此后,港口與腹地關系的研究不斷拓展。隨著港口與腹地的緊密聯系,港口表現出對于發揮腹地物流中心功能的依賴性,使得港口聯系網絡的形成受到更多市場和政治要素的影響(Rodrigue et al., 2010)。而國內多從不同視角探討港口與腹地的經濟關聯與影響,揭示了港口與腹地發展的關聯度及其關聯發展效應(梁雙波等,2007)、港口在城市發展不同階段對其影響程度(殷翔宇 等,2022;2023)等。通過梳理港腹關系研究脈絡,可以發現港口區位研究除了考慮空間距離、運輸成本外,愈發重視港口與陸、海向腹地關聯下的區位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港口研究的傳統國別邊界被突破,要素流動對港口腹地城市發展的影響及港口與境外腹地區域合作將成為重點方向(楊陽 等,2016)。港口研究也多從不同尺度腹地屬性的視角展開。在區域化港口群的研究中發現,通過調動區域地緣經濟內在聯系建立協調互補的集裝箱港口群,可促進長三角地區的區域化發展(莊佩君,2009);更小的空間尺度上,通過描繪上海—寧波、深圳—香港之間港口競合關聯演變,不同的港口群動態演變模式得到揭示(Wang et al., 2022);在港口體系形成演化過程中港口的重要性也被劃分成不同階段(曹有揮 等,2003;王成金 等,2011);港口在區域發展中的作用在不同背景港口-腹地關聯視角下得到揭示(梁雙波 等,2009)。需要注意的是,港口關聯能反映港口在現實海運下的經濟、外交、社會等方面的緊密程度,這在港口區位評價中有重要作用,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此外,如地緣聯系等甚至可以對國際經貿往來起關鍵性作用的關聯要素,在港口區位研究中也有待進一步整合。
基于復雜網絡的港口聯系與海運網絡研究正方興未艾。自1998 年真實世界的小世界特性(Watts et al., 1998)和無標度特性(Barabasi et al., 1999)得到驗證,網絡的類型與結構被科學界定后(Newman, 2003),復雜網絡方法在現實對象的應用便具備理論基礎,在交通、城市等研究中被廣泛應用,以海運網絡為表現形式的港口地理研究成為主流(田煒 等,2007;鄧貴仕 等,2008;牟向偉 等,2009)。其中,節點中心性是在港口評價中被廣泛采用的指標(Peng et al., 2018; Wu et al., 2018),如:在腹地經濟、航運機制與政策慣性共同影響下形成的東北亞地區的港口等級格局借助度中心性得以揭示(Ducruet et al., 2010);中國大陸航運網絡的等級結構借助節點度得以展示,港口吞吐量與節點中心性的相關關系也得到揭示(杜超 等,2016)。上述研究展示了基于航線形成的港口關聯格局,但由于對港口關聯采取拓撲化處理,港口及其他交通系統要素自身的地理性差異難以得到有效表達(莫輝輝 等,2008),復雜網絡下的港口關聯,需還原其在現實條件下的地理空間基礎及其社會制度等要素的空間差異性,并考量港口背后所蘊含的地緣關系等綜合性要素。在地緣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秦大河 等,2020)的前提下,結合港口聯系與腹地的制度環境等地理區位要素進行港口區位優勢度綜合評價顯得愈發必要。
因此,本文基于港口的航運關聯、地緣關系、空間集聚與腹地支撐條件,對現實港口間關聯互動中的區位優勢度進行量化,并將其與復雜網絡下的港口評價展開對比,主要探討2個問題:1)融合地理區位要素的港口評價及港口區位關聯在空間上呈現怎樣的空間格局分布特征;2)此空間分布與基于復雜網絡方法的港口評價結果之間有何差異?以期豐富港口評價方法與視角,使港口區位優勢度評價更具現實參考性。
1 評價框架構建
1.1 港口區位中的地緣因素
區位既指事物的位置,也表示該事物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與各種經濟、社會因素的空間聯系(顧朝林,2012)。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的制度、文化轉向,影響經濟活動的制度、文化因素便成為研究的重點(李小建 等,2004)。港口作為水陸交通最重要的聯系樞紐,不單純是地理現象,更是綜合的區位現象(董潔霜 等,2003)。港口間的聯系不僅取決于地理位置、航線開通情況,還受到港口腹地間地緣關系等因素影響。港口間的地緣環境差異,會在不同程度阻礙港口間關聯互動的產生,成為影響港口聯系的距離摩擦因素。距離摩擦反映移動過程中,時間和費用的預期消耗對行為動機的消極影響,此現象廣泛存在于商品流通中,可用于解釋交通區位與對外聯系的關系(顧朝林,2012)。因此,將地緣關系作為因素納入港口區位評價十分必要。現實中,來自港口間地緣關系的距離摩擦會作用到具體海運活動中,并且受到地理上的距離影響,以航線關聯為具體表達。因此,本文從港口間的地緣關系、空間集聚、航運功能3個方面入手,并結合港口航次加權度所表示的腹地支撐,對港口區位進行綜合評價(圖1)。

圖1 港口的區位優勢度構成Fig.1 Consist of port's location advantages
需要說明的是,相當一部分研究中,空間距離一般采用CEPII 中Geo_distance 數據(吳群鋒 等,2019;邸玉娜 等,2018)或Google Map 計算坐標間直線距離(王豐龍 等,2019),該數據具有獲取的便利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達港口間的空間鄰近性,但卻無法表達在現實海運活動中港口關聯的空間距離衰減;而海上航線距離則反映在海上航行中船舶要克服的真實空間距離,能更好地表達兩港口之間的空間關系。因此,本文選取港口間海上航線距離,作為空間距離摩擦的表達形式。作為地緣關系的主要構成,貿易國之間的制度距離和差異是雙邊貿易的阻力因素(潘鎮,2006),制度距離與雙邊貿易之間存在的相鄰效應,會抑制雙邊的進出口往來(許家云 等,2017)。制度距離被廣泛應用在企業對外并購投資、雙邊貿易等研究中。港口作為雙邊貿易最主要的實現媒介,貿易國的制度差異通過影響經貿往來的成本,進而對港口間的航線聯系產生影響。因此,引入制度距離表達港口間的地緣關系,與空間距離共同表達在不同國家港口間的距離摩擦。
選取4 項因素進行港口區位評價(表1):1)航運功能表達港口的航線承接能力,采用港口的航線重合度表達。不同港口存在共同的航線聯系區域,在特定市場區域內港口間存在競爭關系,航線重合度越高,港口間的航運關聯越緊密,港口區位的重要性越高。2)空間集聚體現港口的空間距離對港口間的關聯互動起空間約束作用,采用港口間海上航線距離表達。港口間的海上航線距離越遠,相互的關聯越弱,港口的區位重要性越低。3)地緣關系體現港口間制度距離,采用全球治理指標(WGI)與恐怖主義統計(GTD)表達,以說明地緣關系對港口區位的影響。港口間腹地的制度差異越大,港口間關聯互動的阻力越大,港口在國際經貿往來區位選擇中優先級越靠后,區位優勢度越低。4)腹地支撐體現港口對外聯系強度,采用航次加權度表達。航次加權度越大,腹地的航運需求強度越高,區位優勢度相應越大;航次加權度通過班輪航線數據統計而來,在跨國研究中有效地規避了港口城市尺度下諸如吞吐量、GDP、外貿額等統計指標的獲取障礙,指標說明詳見表1。

表1 港口區位優勢度測算指標與數據來源Table 1 Indicators of port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data sources
1.2 指標及數據說明
1)地緣關系——港口間制度距離Z。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對制度的定量研究愈發受到關注,“治理”成為重點方向(臧雷振,2012)。世界銀行開發的世界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即是對“治理”抽象概念的量化測度。由于世界治理指標的全面性、延續性、公開性,其已被公認為最具影響力的綜合指標之一,并成為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的重要參考。該指標由世界銀行1996年創建,目前已經涵蓋了全球215個國家和地區,其包含6項分指標,分別是話語權與問責(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穩定(Political Stability)、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監管質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程度(Rule of Law)、腐敗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雖然WGI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論框架,但其作為綜合性全球范圍的評價指標,在社會科學定量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謝宜澤,2018)。例如,諸多研究揭示了WGI 不同指標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的作用差異(王永欽 等,2014;蔣冠宏,2015;張羽,2017)。港口作為重要基礎設施,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主要對象,將WGI指數應用到港口重要性評價也存在其可行性與合理性。此外,事件分析方法也被應用于雙邊關系的定量研究中(潘鎮等,2015),本文選取對營商環境影響更為直接的恐怖主義事件作為對WGI的補充。參照現有的制度距離測算方法(Kogut et al., 1988;許家云 等,2017;吳小節 等,2022),基于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標(WGI)與馬里蘭大學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①https://www.start.umd.edu/gtd/(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對海上絲路沿線港口所屬腹地間制度距離進行測算。計算公式為:
式中:zij為港口間制度距離;Igi、Igj分別表示存在航線聯系兩港口所在國家的第g項指標;Vg表示第g項指標的方差;N表示指標個數,本文N為7。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港口間空間距離與制度距離二者量綱不同,因此,采取分級賦權方法。受制于可供參考的研究有限,權重的確定結合現實通航情景,由多次計算、比較確定。計算公式為:
式中:α為港口i、j所屬國家間制度距離權重系數,若兩國制度距離zij<0.5,賦權1,制度距離zij∈[0.5,)1,賦權0.75,制度距離zij∈[0.75,)2 ,賦權0.5,制度距離zij∈[2,)3 ,賦權0.25,制度距離zij>3,賦權0.01。β為不同國家陸上鄰接關系判斷系數,若兩國存在共同陸上邊界,則β賦值為0.5,若兩國不存在陸上相鄰關系,則β賦值為0。原因在于,考慮到跨國航線的影響因素更為復雜,港口間的聯系暢通程度難以與同一國家內交流相比,因此在不同國家制度距離基礎上,對其陸上鄰接關系再作判定,以此修正制度距離。
2)空間集聚水平——港口間空間距離D,將其按照航行時間賦予權重,其具體操作為:
式中:θ為航程權重系數;Dij為兩港口間的海運航線距離,按照大型集裝箱船舶平均航速20節計算航程,航行時間6 h 內賦權1,6~12 h 賦權0.75,12~24 h 賦權0.5,24~36 h 賦權0.25,超過36 h 賦權0.01。
3)航線聯系——航線重合度F。港口間航線聯系程度越高,兩港口相互承接航線的能力越強,功能聯系越強。計算公式為:
式中:Lt為當年與港口i、j均有聯系的港口間的航線頻次;Li、Lj分別為港口i、j當年開通總共的航線頻次,也即為航次加權度。
最后,參考港口區位優勢度與交通優勢度的計算方法(金鳳君 等,2008),對上述港口間區位關聯的相關要素進行集成,表達港口在國際經貿網絡中區位的重要程度,計算公式為:
式中:(Dij+Zij)作為港口空間與制度距離摩擦權重,替代區位優勢度與交通優勢度計算Fij所對應的權重值。
從廣義的角度看,“海上絲綢之路”沿線集裝箱航運網絡涉及亞、歐、非三大洲,沿岸港口遍布亞洲太平洋、北印度洋、地中海與歐洲大西洋沿岸,本文截取2008和2018年《中國航務周刊》(陳宏兵 等,2008;2018)由中國至亞、歐、非各國港口的集裝箱船期數據,經按照“一市一港”原則對多港區合并后,共包含沿線港口233 個。其中,2個年份均出現的港口124個,僅在2008和2018年出現港口分別有54和55個(表2)。
2 港口區位優勢度評價結果
現有研究已揭示航運等交通運輸網絡表現出無標度特征的網絡層級性,即少數擁有更多連接數量港口在網絡中的重要性更高,大多數港口因連接數量較少而重要性一般(田煒 等,2007;牟向偉 等,2009;杜超 等,2016),但這忽視了航運網絡的地理空間屬性對港口重要性的作用(莫輝輝 等,2008)。而以地緣關系的港口區位優勢度作為體現港口在航運網絡中重要性評價標準,是否也表現出復雜網絡評價下無標度特征,決定著從地緣關系與地理空間視角評價港口區位優勢度是否必要。
2.1 港口區位優勢度表現出無標度特征
通過繪制累積分布概率曲線揭示港口區位優勢度是否符合無標度特征(圖2)。可以發現,在港口的復雜網絡度與航次加權度累積概率分布下,航運網絡均表現出高度的無標度特征,指數函數擬合R2均超過0.96;而港口區位優勢度的累積分布曲線盡管表現出無標度特征,但其指數函數擬合R2未超過0.88,無標度特征弱于復雜網絡指標。結合分布概率看,港口區位優勢度頭部港口占總體概率降低,無標度特征趨于弱化,表現出不同于復雜網絡評價指標的趨勢。這意味著從地緣關系的港口區位優勢度與復雜網絡對港口的評價均具備無標度特征,但港口區位優勢度的程度較低且有減弱趨勢;說明盡管復雜網絡指標可以基本刻畫國際航線中港口的地位差異,但在地緣關系日益復雜背景下,頭部港口的絕對影響力已逐漸分散到各等級港口中,該趨勢僅在港口區位優勢度中得到展現。

圖2 2008(a、b、c)、2018(d、e、f)區位優勢度與復雜網絡指標累積概率分布曲線Fig.2 Curve of cumulative-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location advantage and complex network index in 2008(a、b、c)、2018(d、e、f)
2.2 港口區位優勢度空間格局分析
通過ArcGIS 自然斷點法對港口區位優勢度進行分類,將其劃分為高、次高、次低、低4個等級,以展示其等級結構與空間分布。從不同等級的港口數量上看,港口區位優勢度呈由高等級向低等級的“金字塔型”,由低等級構成區位優勢度的主體等級結構。由高到低4個等級數量分別為2008年7、12、37、124 個,2018 年5、13、26、136 個,其中高、次低等級港口數量減少,次高、低等級港口數量增加,區位優勢度等級整體重心下移,與上文頭部港口的影響力減弱趨勢相吻合。高等級港口中,歐洲港口數量大幅減少,中國港口由2 個增加到3 個,在“海上絲路”沿線航運中居于主導地位;其中,胡志明港作為越南最大港口,依托東盟地區的經濟增長動力,由次高等級上升至高級港口。次高等級港口數量變化最少,次低等級減少幅度近30%,主要是非洲港口在2018年均為低等級港口。低等級港口多集中分布在亞洲,構成“海上絲路”沿線港口的主體等級結構。總體上,區位優勢度等級整體偏低,低等級港口數量占據絕對優勢,超過其他3類等級數量之和,符合上文揭示的無標度特征所體現的層級性特征。
從空間分布(圖3)上看,地緣關系下的港口區位優勢度基本以低等級港口為沿線港口的主體框架,隨著等級的升高,空間集聚性也愈發突出。高等級港口由2008 年的7 個減少至2018 年的5 個,2018年除上海、漢堡外,其余3個均由次高等級升級而來,其空間分布重心在2008—2018年由西歐變遷至中國,反映以經濟水平為表現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變遷,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在“海上絲路”航運中的重要性顯著提升;次高等級港口除在西歐大西洋沿岸與東亞太平洋沿岸外,還分布于北印度洋海域,顯示該海域對于“海上絲路”沿線航運的重要程度;次低、低等級港口廣泛分布于“海上絲路”沿岸,構成區位優勢度等級結構的主體。

圖3 “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區位優勢度等級空間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rts' location advantages
綜上可知,港口區位優勢度的變遷與港口腹地發展息息相關。如歐洲港口整體等級隨著原有一體化格局面臨的挑戰而出現不同程度的等級降低;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強勁增長,使得所屬港口等級整體上升。這說明港口腹地的地理區位條件對航運活動的正常運行發揮著顯著作用,港口除發揮航運功能外,還深受地緣關系、全球經濟發展等的深度影響。而本文所構建的基于地緣關系的港口區位評價指標,對港口的地理位置和與其開通航線港口間的地緣關系進行量化表達,得出沿線少數港口在本國參與“海上絲路”經濟帶經貿往來中發揮重要作用,具備較高等級;而低、次低等級港口一方面由其腹地經濟與社會條件所決定,另外,腹地交通運輸結構差異也對港口功能產生影響,如日本盡管擁有強勁的腹地經濟發展水平,其作為海岸線綿長的島國,國際航線在其國內也有多次掛靠,稀釋了其國際航線對外關聯的作用程度,造成其更低的區位優勢度等級。
2.3 港口區位關聯空間格局分析
通過ArcGIS10.4對港口兩兩之間的區位聯系與網絡聯系進行空間表達,從圖4可以看出,港口間的區位聯系呈現弱關聯為主的等級結構。區位弱關聯在2008 和2018 年中均廣泛存在于遠距離兩港口之間,次弱及更高等級的區位關聯存在明顯的空間分布重心:2008年僅漢堡—勒阿弗爾兩港之間為強區位關聯,2018年還有上海—頭頓之間也形成強區位聯系;次強關聯則始終集中在亞洲,次弱關聯除2008年存在于圣彼得堡與中國港口間的區位關聯之外,則基本與次強聯系呈現類似的分布特征,形成亞洲港口內部的關聯格局。亞洲港口間的區位聯系明顯強于歐洲港口以及洲際港口間區位聯系,形成圍繞中國港口的對外聯系格局:其中,孟買、卡拉奇在2008 和2018 年均為與中國港口區位關聯最強的印度港口;越南港口在兩個年份中也始終與中國港口保持較為顯著的區位關聯。2018年港口區位聯系重心向亞洲轉移,據此可認為地緣關系下的港口區位聯系與港口腹地息息相關,隨著亞洲諸多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以亞洲內部為主導的港口區位聯系格局逐漸形成,這與地理位置的相鄰、地緣的相近、經濟的互動存在關聯。

圖4 “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區位聯系等級空間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ank of port location relationship along Maritime Silk Road
港口間更高等級的區位聯系以同一國家港口為主要關聯構成,港口間的區位聯系強度基本遵循距離衰減,即距離越近且處于同一國家間的港口區位聯系越強,距離越遠則區位聯系越弱,該格局可基本視作是空間距離影響下的距離摩擦因素所主導,港口間的區位聯系仍未能突破地理空間限制而形成普遍的跨區域聯系。
3 港口區位優勢度與網絡指標的差異對比
3.1 相關性分析
為進一步展示港口區位優勢度與復雜網絡指標之間的差異程度,選取復雜網絡中廣泛使用的節點評價指標——節點中心性(度中心性、介中心性、鄰近中心性)與節點的航次加權度,與港口區位優勢度進行相關性分析。首先,通過峰度、偏度對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發現原始狀態與經過取對數處理后的港口區位優勢度與復雜網絡指標仍不能滿足正態分布,不適用于Pearson相關性檢驗,因此,采用非參數相關檢驗。其次,基于各港口區位優勢度與復雜網絡各指標在2008 和2018 年各自對應排名,進行Spearman秩相關性檢驗。結果(表3)顯示,港口區位優勢度與復雜網絡指標雖多數通過相關性檢驗,但相關關系始終較弱,相關系數最高僅為0.507;而復雜網絡下的航次加權度與各節點中心性指標均在99%置信區間下表現出較高水平的相關性,相關系數為0.722~0.962。

表3 “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區位優勢度與復雜網絡指標相關性檢驗Table 3 Correlation test of location advantage and complex index of ports along Maritime Silk Road
綜上,港口區位優勢度通過表達地緣關系、空間集聚、功能聯系與腹地功能等地理空間屬性,與復雜網絡指標所指代的港口重要性具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構建港口區位優勢度指標來評價港口重要性十分必要。港口區位優勢度旨在刻畫港口間航線聯系構建過程中,由其空間分布差異賦予其各自不同的重要程度,如分布在航道關鍵位置、島嶼型國家的港口在國際貿易網絡中其區位具有更高的重要性;而復雜網絡指標則與航司航線規劃與運力配置等因素高度相關,航線背后所體現的經濟要素則是其表達的主要內涵。
3.2 空間格局對比分析
考慮到復雜網絡指標之間高度的相關性,選取航次加權度及與其相關性最低的介中心性作為復雜網絡評價指標的代表,以更全面揭示2類不同港口重要性評價指標的空間格局分異。
3.2.1 港口等級空間格局分析 從不同重要性等級的港口數量上看,在復雜網絡下,沿線重要性等級整體偏低,低等級港口數量占據絕對優勢,超過其他3類等級數量之和,符合復雜網絡揭示的無標度特征所體現的層級性,這與港口區位優勢度的等級格局類似。
從空間分布上看(圖5),復雜網絡下航次加權度與介中心性的高等級港口明顯以東亞地區為分布重心。航次加權度與介中心性均由較低等級港口構成沿線基礎框架,二者的高等級港口僅在中國華東、華南地區,航次加權度次高等級2008年分布于中國、馬六甲海峽、地中海與北大西洋區域,至2018年僅在亞洲分布,地中海、大西洋沿岸則均為次低與低等級港口;而介中心性次高與高等級港口均位于中國,次低等級港口除馬六甲海峽處新加坡、巴生2 港口外,其余次低等級港口也均位于中國。

圖5 “海上絲路”沿線復雜網絡指標等級空間分布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lex network index of ports along Maritime Silk Road
基于復雜網絡中航次加權度與介中心性的港口評價結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難以表達港口腹地經濟發展等現實地緣環境變遷。現實中的聯系網絡經復雜網絡方法的拓撲化處理后,其背后的社會、經濟等現實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如自2008—2018年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帶給其在國際經貿與航運網絡中的相對地位改善未能得到充分體現。而本文所構建基于地緣關系的港口區位評價指標,對港口的地理位置和與其開通航線港口間的地緣關系進行量化表達,將港口區位優勢度等級變化與其腹地變遷深度融合。
3.2.2 港口關聯空間格局分析 通過ArcGIS10.4對港口兩兩之間的區位聯系與網絡聯系進行空間表達,從圖6可以看出,港口間的網絡聯系與區位聯系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關聯類型差異。不同于港口間的區位聯系強度基本由空間距離影響下的距離摩擦因素所主導,網絡聯系表現出明顯的跨空間關聯特征,形成以上海、鹿特丹、漢堡為核心節點的國際航運網絡結構,更高程度網絡關聯廣泛出現在跨國跨洲際的海運活動中,港口間關聯的構建擺脫了地理空間分布的制約,具有“流空間”的表現特征。流空間網絡作為一種高級一體化的網絡結構(孫中偉 等,2005),其節點(nodes)之間具有某種相互作用功能的聯系(章錦河 等,2005)。航運流的跨區域流動性,便使港口節點之間因航運流的連接與耦合而成網絡。

圖6 “海上絲路”沿線網絡聯系強度空間分布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twork relationship of ports along Maritime Silk Road
綜上,港口作為連接水路交通系統的樞紐,航線的網絡聯系作為其主要的功能表現形式,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背景下區域聯系空間尺度的不斷拓展,被其所承載的貨物、資源流動塑造成“流”的空間關聯形式。節點在“流空間”中作用與影響的范圍明顯不同,不同節點之間存在層次與等級結構的分異成為必然(董超,2012)。這體現航線聯系背后所體現的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與生產分工,以關鍵港口為支配節點,形成一個具備多層級的交通運輸組織網絡,以關鍵節點為樞紐實現物流在全球范圍內的周轉流通。而港口的區位聯系,因根植于港口間的地理空間關聯,約束著其間航線轉移替代的空間距離與制度距離,難以因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而改變其空間表現形式,由此形成全球化背景下港口本地化(localization)關聯的表現形式。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1)港口區位優勢度作為一種評價港口在國際經貿網絡中重要程度的綜合評價標準,與現有復雜網絡指標存在一定差異。累積概率分布曲線擬合顯示,港口區位優勢度表現出類似于復雜網絡指標所具備的無標度特征,港口等級有明顯的層級性,但無標度特征在減弱;2 類指標間相關系數最高僅為0.507,而復雜網絡各項指標相關系數最高達0.962。這充分說明構建體現地緣關系的港口區位評價指標的必要性。港口區位優勢度在刻畫港口間現實的關聯互動過程中,由其空間分布差異賦予其各自不同的重要程度;而航次加權度則與港口的腹地經濟發展、航司運力配置等因素高度相關,腹地經濟則是其所表達的本質要素。
2)港口區位優勢度彌補了復雜網絡指標對于港口地理內涵挖掘的不足,對港口的地理位置和與其開通航線港口間的地緣關系進行量化表達。總體上,在“海上絲路”經濟帶沿線,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港口普遍呈現較高水平的區位優勢度。而在以航次加權度與介中心性為代表的復雜網絡指標的評估中,因僅從系統的結構著手,忽略交通運輸網絡根植的地理空間屬性,其所劃分的港口等級及其變遷未能充分體現腹地經濟相對地位的變化。
3)港口之間的區位聯系與航線聯系展現出不同的空間表現特征。港口間的區位聯系仍表現為場所空間的形式,關聯強度基本遵循距離衰減定律,即處在同一國家且距離越近的港口間區位聯系越明顯,距離越遠或處在不同國家則區位聯系越弱,基本由空間距離所主導,是全球化背景下港口聯系的“地方化”的展現形式;港口關聯網絡形成以圍繞亞洲新興經濟體港口的區位聯系重心,反映過去一段時期亞洲新興經濟體在東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區域組織與協定下,互聯互通與經濟文化往來大幅增加。而港口間的航線關聯則表現出明顯的“流空間”特征,地理空間分布在港口建立航線聯系中的制約作用微弱,港口間更高等級航線關聯存在于跨國跨洲際的海運活動中,其所承載的貨物、資源流動構成全球化的核心。
4.2 討論
基于本文結果,對中國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的海上運輸提幾點建議:1)發揮國內港口群的合力優勢,著力優化港口群內部的協同分工、發展規劃與資源配置,將港口優勢整合為區域競爭力,鞏固提升中國國家尺度在“海上絲路”交通網絡中的重要地位。2)建立港口制度風險的監測預警機制,針對“海上絲路”沿線國家間制度距離摩擦動態風險,建立風險預警與評估機制,積極化解潛在風險因素。3)充分運用作為“海上絲路”經濟帶的倡議方優勢,與沿線國家開展密切的經濟往來,深化外交合作與政策互信,加強航線聯系密集港口間的區位聯系,減少聯系形式的空間錯配,避免港口雙邊往來由單一的航運業務主導,保障海上運輸安全。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1)在研究區域與樣本選擇上,受制于數據來源,所用航線均由中國始發,數據最新年份為2018年,計算結果對現實海運活動表達存在一定誤差,不過作為對評價框架的驗證仍具有參考性;2)在指標構建上,僅考慮地緣關聯相關因素及基礎的海運距離,不同國家間的雙邊關系、貿易協定以及不同港口的市場份額、經營范圍均未被納入,在表達港口間社會與地緣因素的綜合性上有待完善;3)對地緣關系區位與主流的復雜網絡間對話不夠充分,在于地緣要素的綜合指標與復雜網絡的單一指標指代的港口關聯形式,分別表現為場所空間與“流空間”,其二者間疊合匹配與耦合協調關系未得到揭示,有待進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