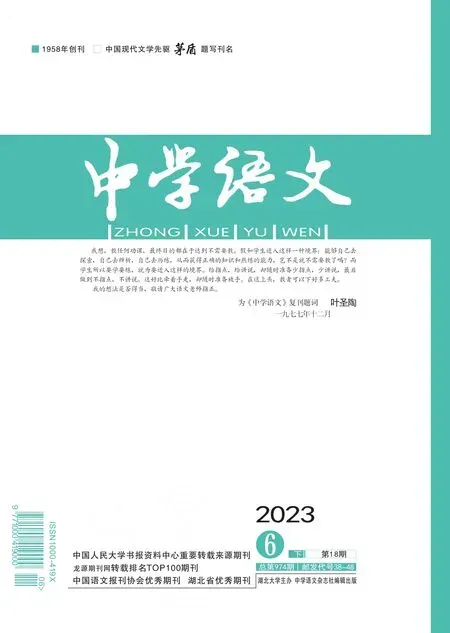《雁門太守行》文本解讀
崔麗媛
《雁門太守行》是唐代詩人李賀的代表作。李賀素有“詩鬼”之稱,其詩歌作品風(fēng)格詭譎,善于錘詞煉句、大膽想象,從而營造出一種綺麗奇特的意境。但是,李賀詩歌的詭譎綺麗,也往往成為學(xué)生解讀其作品的難點(diǎn)。圍繞詩歌的語言文字、背景信息等展開多元化的分析,既可以幫助學(xué)生突破難點(diǎn),還有助于讓他們感受到其中的色彩美、意境美。
一、關(guān)注色彩,描摹意境
李賀之所以被稱為“詩鬼”,是因為其詩風(fēng)奇特、意境詭譎綺麗,而色彩詞的廣泛運(yùn)用,是李賀營造意境的重要方式。在解讀詩歌文本時,我們一定要關(guān)注文本中的色彩詞,利用色彩詞描摹詩歌的意境,體會其作品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審美特質(zhì)。
詩歌的首聯(lián)“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體現(xiàn)了作者奇妙的構(gòu)思和卓越的想象力。從作者的視角來看,眼前兇猛來襲的敵軍,就像天空中翻滾的黑云,帶給人一種強(qiáng)烈的壓迫感。解讀此句時,學(xué)生不免會產(chǎn)生疑惑,作者為何要將激烈的戰(zhàn)事描繪為“黑云”?教師可以聯(lián)系生活經(jīng)驗,讓學(xué)生想象,在暴風(fēng)雨到來之前,原本光彩艷麗的天空,會瞬間暗淡下來,一大片烏黑的云籠罩天空,這與敵軍來犯時萬馬奔騰、煙霧蔽日的氛圍十分相似,都給人一種緊張之感。在這里,作者以“黑色”為主色調(diào),描摹出一種壓迫感極強(qiáng)的意境。而“壓”和“摧”兩個動詞,更凸顯了情勢的危急和緊張。下句,作者以“甲光”起勢,意為守城戰(zhàn)士身上的鎧甲映照著最后一抹陽光,這一抹陽光猶如閃閃發(fā)光的金色鱗片,在黑色背景下顯得尤為耀眼。借助這一強(qiáng)烈的色彩對比,表現(xiàn)了作者戰(zhàn)勝敵軍的決心,也描繪了我軍將士嚴(yán)陣以待的場面,通過黑、金兩種顏色的對比,營造了十分緊張的戰(zhàn)前氛圍,給人一種強(qiáng)烈的震撼。
詩歌的頷聯(lián)“角聲滿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作者從視覺、聽覺兩個角度,將兩軍激烈交戰(zhàn)后悲壯的意境描摹得十分形象。學(xué)生可從“秋色”一詞中了解到,此時正值深秋時節(jié),結(jié)合邊塞地區(qū)的自然風(fēng)貌可知,深秋時節(jié)的天氣寒冷、氣氛陰森,戰(zhàn)爭的號角聲不斷響起,給人一種凝重、沉郁和陰森可怖的感受。戰(zhàn)爭過后,作者以“塞上燕脂凝夜紫”一句,將鮮血浸染后的土地比喻為女子用的胭脂。學(xué)生可能會認(rèn)為作者用詞不當(dāng),因為這些浴血奮戰(zhàn)的將士用他們的生命保家衛(wèi)國,詩人卻將他們的鮮血比喻為胭脂,不否顯得有些輕浮呢?而事實并非如此,作者以卓越的想象力,將被血液浸染的土地比喻為紫色的胭脂,是有事實依據(jù)的。經(jīng)過一個深秋的夜晚,原本鮮紅的血液,經(jīng)過冷風(fēng)的吹打、沙土的覆蓋,已經(jīng)成為一種悲壯的“紫色”,這既是對戰(zhàn)爭的寫實描寫,也是用藝術(shù)化的手法營造了一種悲傷、濃郁的戰(zhàn)場意境。
詩歌的頸聯(lián)“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到了此聯(lián),詩歌的色彩稍顯暗淡。在解讀此句時,為了讓學(xué)生領(lǐng)會詩詞的含義,最關(guān)鍵是讓他們了解“易水”這一歷史典故,教師可以結(jié)合“荊軻刺秦王”的典故,引入“風(fēng)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fù)還”的詩文內(nèi)容,借此展開詩詞解讀。雖然學(xué)生并未看到色彩詞,但是他們也能體會到一種暗淡、蕭瑟的色調(diào),并深刻地感受到悲壯的情感基調(diào)。
詩歌的尾聯(lián)“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與前三聯(lián)有所不同,此句的色彩濃烈、艷麗。在文本解讀的過程中,學(xué)生應(yīng)先解讀“黃金臺”這一典故,明確其歷史源流,理解詩人引用此典故的目的,即“報效祖國的決心”。從色彩上看,“黃金”一詞凸顯了暖色調(diào)的特征,相比于前三聯(lián),作者以閃閃發(fā)光的金色為主,將自身以及守國將士的樂觀心態(tài)表現(xiàn)出來,凸顯了他們?yōu)閲鲬?zhàn)沙場的決心,這種情懷讓人深受感動。
從全詩的內(nèi)容出發(fā),作者以其卓越的想象力、觀察力和文學(xué)表達(dá)力,描摹了一幅色彩斑斕、濃郁的畫面,將戰(zhàn)爭的場景以極富藝術(shù)氣息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改變了以往邊塞詩沉悶、蕭瑟和荒涼的色調(diào),融入了一抹詭譎、綺麗的色彩,而通過色彩的轉(zhuǎn)換,詩人也將自身的情感變化寄寓其中,體現(xiàn)了他從沉悶緊張、凝重壓抑到高亢激昂的情感轉(zhuǎn)變,展現(xiàn)出了李賀高超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
二、勾連群文,強(qiáng)化體驗
文本解讀不僅僅局限于“這一篇”,還要從“這一篇”過渡到“這一類”,通過這樣的過渡和轉(zhuǎn)換,學(xué)生便能熟練且扎實地掌握文本解讀的方法,也能夠不斷強(qiáng)化自身的閱讀體驗。統(tǒng)編版初中語文教材中編選了體裁、題材豐富的古詩詞,在文本解讀教學(xué)中,我們要由《雁門太守行》這一篇古詩詞,關(guān)聯(lián)與之具有相似性特征的多篇古詩詞,讓學(xué)生在勾連群文的過程中,歸納和概括這一類古詩詞的共同特征、藝術(shù)風(fēng)格,使他們在對比閱讀的過程中,強(qiáng)化自身的審美鑒賞、文化感知體驗。在此基礎(chǔ)上,學(xué)生不僅能理解此篇古詩詞的內(nèi)容和主題,還能在拓展化的群文閱讀活動中,積累豐富的文學(xué)常識和歷史知識。
從色彩渲染的角度勾連群文。前文中我們提到,李賀之所以被稱為“詩鬼”,與其善用色彩息息相關(guān),在其創(chuàng)作的詩歌中,不乏色彩濃艷的作品,如《殘絲曲》中的“綠鬢年少金釵客,縹粉壺中沉琥珀”,《感諷》中的“秋涼經(jīng)漢殿,班子泣衰紅”等。教師可以將這些色彩濃艷的詩歌,作為群文閱讀的資源,構(gòu)建起“李賀詩歌中的色彩意象”的群文閱讀體系,讓學(xué)生從色彩詞的運(yùn)用效果、象征意義等不同的角度,展開項目化、深層次的解讀和品鑒活動,于對比中體會李賀在色彩運(yùn)用上的獨(dú)到之處,由此達(dá)到勾連群文、強(qiáng)化體驗的目的。
從衰亡意象的角度勾連群文。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李賀在描寫衰亡的意象上獨(dú)具造詣。經(jīng)人統(tǒng)計和歸納,李賀的詩歌中,出現(xiàn)最多的一個字是“老”,其次為“寒”“斷”“愁”“死”等,從這可以看出,李賀不僅是一個善于描寫衰亡意象的詩人,他還對寫“死亡”有著特殊的偏好。基于這一共同特征,我們可以指導(dǎo)學(xué)生將《雁門太守行》《塞下曲》《客游》《過華清宮》等古詩詞串聯(lián)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群文體系,讓學(xué)生總結(jié)和概括李賀在寫“死亡”時的特征,引導(dǎo)他們展開對比解讀,從詩歌的意象、視線變化等不同的角度,明確其語言特色、藝術(shù)手法、文本主題等。在對比群文時,學(xué)生能收獲不同的閱讀體驗,其文本解讀的深度也能不斷加強(qiáng)。
在文體意識和單元意識的驅(qū)動下,我們圍繞著關(guān)注色彩和勾連群文等不同方面,指引學(xué)生描摹古詩詞的意境、探究詩人的情感,強(qiáng)化其閱讀體驗,讓他們明確同類詩詞的異同點(diǎn),推動他們從“這一篇”的文本解讀活動中積累經(jīng)驗、總結(jié)方法,并于“這一類”的文本閱讀中體會和感受文本背后隱藏的審美、歷史和文化價值,明確其間的關(guān)聯(lián)。經(jīng)過這一拓展式的文本解讀活動,可使學(xué)生的閱讀廣度、閱讀深度大大增強(qi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