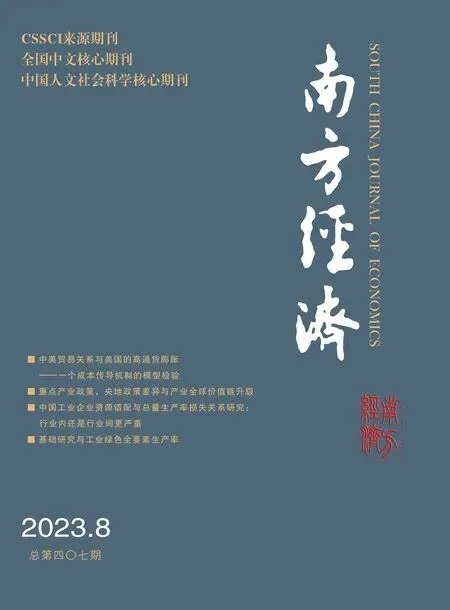中美貿易關系與美國的高通貨膨脹
——一個成本傳導機制的模型檢驗
韋 森 蘇映雪 張嘉誠
一、研究背景
2022 年下半年以來,美國、英國及歐盟各國的高通貨膨脹率成為世界各國所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問題。如圖1 所示,2022 年6 月,美國通脹水平最高達到8.93%,打破40 年來美國通脹水平的記錄。自80年代以來,美國都一直處于低通脹、低增長的“大緩和”時代。即便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美聯儲通過貨幣超級“大放水”救市后,美國通脹水平依然維持低位,甚至通脹不達美聯儲設定的2%的目標。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美國政府重新采取了一系列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應對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從2022年開始,美國、歐盟各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突然急速攀升,各國的通貨膨脹率創多年來的新高,部分國家甚至達到兩位數的物價增長。為應對破歷史記錄的高通脹水平,2022 年美聯儲、英格蘭銀行以及歐洲央行已經進行了多輪加息和其他貨幣緊縮政策企求遏制通貨膨脹。但美國和歐洲各國央行多次激進的加息舉措也引發了世界各國對經濟衰退、債務風險等問題的擔憂。綜上,對通脹成因的分析以及前景走勢的判斷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各界討論的熱門話題。

圖1 美國通脹水平創多年來新高
關于美國此輪高通脹的成因,既有研究的主要觀點總體上分為需求側推動和供給側推動兩類。需求側因素中,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實施的擴張性財政刺激政策(楊航,2022;吳秀波,2022),如以現金補貼居民家庭,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消費需求,進而拉動物價上漲。疫情造成的隔離管控提高了在家工作的人數,刺激了住房市場的需求和住房價格的上升(李迅雷、陳興,2022;張靜靜,2022)。同期美國快速進行疫苗接種、恢復產業工人就業,生產部門迅速度過疫情沖擊后,居民消費需求得以恢復,從而推升了價格水平。供給側因素中,俄烏戰爭和全球原材料供應緊張引起供應鏈矛盾,提升了產品生產平均成本,全球能源價格(尤其是原油價格)顯著上升,這推高了美國和西方各國通脹水平(肖立晟、吳立元,2022;益言,2022;張偉,2022;紀敏,2022;賀洋等,2022)。然而,在這兩類廣為人知的通脹成因之外,本文認為美國此輪通脹高企的供給側原因要進一步追溯到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這一因素同時將為2008年后美國通脹處于低位作出一致解釋。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美兩個大國的貿易和國際關系互動在某種程度上主導著世界貿易的全球格局。中國通過積極參加國際貿易拓展海外市場,在東南沿海地區形成了加工貿易出口聚集區。中國長期對美國形成貿易順差,而從其貿易品組分看,中國往往是出口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工業產成品,相比之下美國向中國出口產品主要是農業產品、原材料,以及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技術性產品。我們認為在以上貿易格局下美國長期攫取對華貿易的價格福利,用外部低價產品匹配美國國內旺盛內需,這構成了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大規模貨幣寬松但通脹處于低位的原因。
2018 年前后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悍然開啟貿易戰。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三輪加征關稅和貿易制裁政策,為2022 年美國的高通脹埋下了伏筆。全球化時代,貿易格局對大國經濟、價格與貨幣政策具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疫情重創全球供應鏈后,貿易關系成為經濟以及發展戰略決策的重要參考因素,既有研究關注了中美貿易沖突危及經濟全球化(黎峰,2019),但是鮮有文獻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對美國經濟自身的不利影響予以足夠重視。認識到這一點,將有助于中美兩國更加全面和理性評估當前的政策走向,以求恢復和增進合作,共同應對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
二、理論悖論、特征事實與研究假設的提出
(一)貨幣數量論分析的迷思:為何美聯儲多年來貨幣寬松并未引發高通脹
弗里德曼(Friedman,1970)曾認為:“通脹無時無刻不是一個貨幣因素,它是,且僅源自于貨幣(超過產出)的增長。”然而,回顧美國二十一世紀的通脹和貨幣供應關系,我們很難觀察到顯著的相關趨勢。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滯漲發生后,美聯儲貨幣政策工具從調控貨幣供應變成了設定政策利率(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FFR),并將通脹設定在了2%的穩定目標。央行貨幣政策重點不再是直接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速,而是調節貨幣供應以實現其設定的通脹目標和期望就業水平。
仔細考察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宏觀經濟的一些現象,可以發現通脹問題很難再被認為是純粹的“貨幣問題”。從貨幣工具和通脹的運動關系看,二者之間的聯系已經非常微弱,尤其是政策利率已經接近或觸及零下界時,央行無法進一步設定負利率刺激經濟。因此,在金融危機后傳統貨幣工具“似乎”完全失去用武之地。面對金融危機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美聯儲啟動了量化寬松和流動性支持工具等“非傳統貨幣政策”,直接向市場投入流動性——這似乎又回到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供應量工具。然而,盡管投放了大量流動性,美國的通貨膨脹卻并未大幅上升,且較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還略低。2014年,盡管美聯儲貨幣寬松政策延續,但是美國的物價水平卻仍然向下“跳水”,一度出現通脹“不達標”的問題,如圖2。因此,將2021 年以來的高通脹完全歸因于貨幣寬松政策或將是有偏的,還需要對此輪高通脹進行深入剖析,以發現更為重要的因素。

圖2 美國貨幣寬松與通脹水平趨勢并不一致
(二)中美貿易與美國通脹的特征性事實
1.2021年美國的國際貿易運輸成本上升、貿易條件惡化
2021 年下半年,美國通脹連月高升引發市場與政策層高度關注,正值疫情對美國供應鏈形成沖擊,國內外財經媒體特別強調供應鏈瓶頸導致美國的高通脹問題,但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一點是美國進口產品的運輸成本呈現飆升之勢,如集裝箱的價格高企。疫情期間,中國仍是美國的最大進口伙伴國。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是交通運輸產品、機械化工產品、日用紡織品及玩具等,同時美國的鋼鐵等產品供應也主要依賴對中進口。2020年新冠爆發初期,美國從中國進口成品鋼同比增速驟減50%。2020 夏季,隨著德爾塔病毒在東南亞肆虐,美國從中國進口成品鋼又陡然上升。直到2022年1月,美國從中國進口成品鋼同比增速仍高達207.7%。
在新冠疫情爆發后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數量增長,同時進口成本也在上升。中美海運中的集裝箱價格在2020—2022年期間上漲超過六成。運輸成本和運輸數量的同步上升加劇了美國進口產品的價格上漲,構成了輸入性通脹壓力。
疫情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金額飆升,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大幅上漲,美國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上漲。2021年12月美國通脹再上新臺階。當月美國的GDP增長數據表明,當月美國經濟主要依賴進口拉動,而進口拉動的因素不是來源于進口量的增長,而是來源于價格的上漲。由于進口價格的提升,美國的對中貿易赤字也快速上漲,如圖3。

圖3 美國貿易赤字主要國家貢獻
美國對中國的進口需求的增加和進口商品價格飆升,還反映在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2021年11月開始,美聯儲貨幣緊縮轉向,在不斷高漲的加息預期下,美元走勢上揚,但并沒有壓制人民幣匯率。相反,人民幣走勢出現一波獨立行情。
2.美國從中國進口貿易在疫情期間顯著增加
新冠疫情以來,因為有政府財政補貼,美國食品以及居家耐用消費品,包括家具、電腦等消費需求大增,這些消費品也是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的范圍,而美國此輪通脹漲幅較為顯著的即是食品價格。從圖4可以看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食品、汽車零部件和其他消費品、資本貨物金額在2018年貿易沖突后均下降明顯,但在疫情期間大幅回升。中美兩大經濟體主導世界經濟格局、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深化的情形下,中國對于全球供應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盡管因為政治和外交層面原因,美國在對華政策方面采取制裁、孤立的取向,但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當前結構意味著這種逆全球化的潮流將對世界經濟、對美國自身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圖4 美國從中國進口金額品類構成
3.美國從中美貿易中獲取的福利與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動機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加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到2008 年,中國已成為美國的最大進口來源國,如圖5。盡管中國貿易量迅速上漲,但在價值鏈分工中,中國仍主要是依靠勞動力紅利生產廉價和低附加值商品,其中部分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國,成為美國居民家庭常見的日常消費品。美國進口的大量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構成了其在金融危機后釋放通脹壓力的缺口,盡管消費需求回升,但消費品價格仍能通過進口保持低位,因此美國通脹在這一時期維持低位是不無原因的。然而,在中國的工業化結構轉型、調整升級過程中,中國出口產品產業鏈延長、附加值上升,國家戰略也由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并在多個行業領域建立起產業優勢和定價力量。美國在同中國貿易中所能享受的“低價”福利逐漸收窄,這也是美國尋求對中國進口替代、在全球找尋新的產品生產基地的原因。從圖5 中可看到,美國從東南亞地區的進口份額逐年上升,這背后是美國擺脫對華貿易依賴、尋求其他廉價商品供應鏈的企圖。

圖5 各主要國家出口占美國進口的份額
中美貿易沖突始自2018 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出“美國優先”的口號,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大幅提高對全球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稅,而中國又是美國鋼材進口的第一大貿易國,主要的加征情況如表1。2019年,美國又開始第二階段的對華貿易制裁,對華加征關稅的商品范圍、關稅力度都大幅提高。拜登執政期間,對華貿易沖突政策并未發生轉變,實質上延續了特朗普時期以來的思路。

表1 中美貿易戰中涉及到的關稅加征
2018年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大幅提高了指定品類的關稅稅率。這直接影響了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成本。其背后的“替代思想”也反映在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份額占比開始迅速下降。如這一貿易戰持續影響,美國將逐漸削弱對中國產品的依賴,在東南亞、中南美等地區建立海外產品生產基地,利用當地的低成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而擠出中國出口在全世界產品市場的份額。然而,美國這一戰略還未完全實施便受到了新冠疫情爆發的影響。
4.2020年疫情大爆發后美國進口再次依賴中國
2020 年疫情突襲,美國從中國進口額恢復增長。全球經濟整體受到疫情沖擊產能受阻、產量下降,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明顯。中國的積極防疫政策和良好的防疫結果使得中國成為疫情爆發之初生產受影響最小的國家,美國國內生產受阻,其戰略中中國進口產品的替代國家(如東南亞、墨西哥等)也受疫情影響嚴重。這直接擾亂了美國的進口市場布局,沖擊了美國的產品供應鏈。中美貿易戰背后,美國政府企圖將產業鏈從中國轉出到東南亞市場的戰略受阻。因此,疫情以來,美國不得不再次依賴從中國進口所需產品。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增長對美國消費和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影響。如圖6所示,美國居民消費的增速與從中國進口增速趨勢高度相關。自2021年下半年以來,由于疫情期間補助退出,美國個人消費支出開始下降。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高企,疊加中國疫情零星爆發以及封控措施,2022 年第一季度起,美國從中國進口也開始下降。進口下降、價格上升再加上支出下降,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美國經濟增速下行。可見,美中貿易沖突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甚巨,中美貿易沖突是一個雙輸的游戲。
(三)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的提出
以下用一個簡單模型刻畫美國通脹和中美貿易的關系。設美國消費者商品籃子包含中國進口商品Ccn、其他國進口商品Cot和美國生產商品Cus,其價格分別為Pcn,Pot,以及Pus。設這三類商品以常替代彈性(CES)方式加總為消費指數
家庭部門總是以支出最小化方式選擇每一類商品的消費量
其中ε為產品間的替代彈性。對該問題求解可以得到三類商品的需求函數
以及美國物價指數
設美國從中國進口時,中國在岸價格為Pcn,0,運輸成本τcn占總價格比例
則美國物價指數可表達為
兩邊取全微分并整理得到
因此,上式給出了美國物價通脹與從中國進口產品價格增速d(logPcn,0)、運輸成本dτcn的關系,其系數都為正,意味著中美貿易中更高的進口價格增速、更高的運輸成本都將提高美國物價通脹。
基于上述特征事實和模型,本文提出以下核心研究假設:中美貿易價格和運輸成本的提高將推動美國通脹上升。如果假設成立,那么支持了美國通脹的成本傳導機制,并為中國外貿轉型、中美貿易關系影響美國經濟提供實證支持。此外,本文將在回歸方程中加入貨幣政策的變量以探究傳統的貨幣政策-通脹理論。
三、實證檢驗
基于上述理論悖論與特征事實,本文擬采用實證方法探究美國通脹與貨幣政策、中美貿易的聯系。本文首先對美國通脹數據的時間序列進行建模,其次選取了美國貨幣政策和中美貿易價格、成本的相關時間序列進行了時間序列回歸分析。
(一)數據獲取和描述性統計
為探究美國高通脹的原因,本文對美國通脹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建模,并且將美國從中國進口價格和費用、美國貨幣政策指標作為自變量,分析上述因素對美國通脹動態的影響。本文的通貨膨脹數據來源于美國勞動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本文選取了2006年1月—2022年12月間美國的城市消費物價指數并取對數差分(Δcpiut= logCPIUt- logCPIUt-1)。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價格指數同樣來自美國勞動統計局,該部門根據北美產業分類系統提供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全商品價格指數,同時提供了制造業三大部門(服裝紡織、化工、金屬機械)的進口品價格指數。同時,為刻畫中美貿易戰爆發后大幅上升的貿易成本,本文選取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SITC)提供的HS-2 位編碼進口品加總數據,提取了98 個品類的進口費用、含進口費用(保險、運費等)的進口價值,以此計算了各品類的進口費用占比。本文根據品類進行了簡單算術平均作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費用指標。
美國貨幣政策方面,本文兼顧了傳統貨幣政策(政策利率)以及非傳統貨幣政策(量化寬松、前瞻指引和流動性支持)。本文采用美國財政部(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USDT)公布的1 月期國債收益率構建了月度的短期利率數據,度量了美聯儲的短期貨幣政策。同時,本文選取了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FED)公布的資產負債表中持有的國債規模,構建了對數國債持有量數據,度量其在量化寬松中采取的非常規性貨幣政策。
表2匯總了本文主要的變量、來源和描述性統計:

表2 描述性統計
從時間序列(圖7)看,美國通脹同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增速顯示出較強的協同關系,本文接下來將通過對上述指標的時間序列建模提供關于這一影響的實證證據。

圖7 美國通脹與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價格增速、進口費用同步運動
(二)對美國通貨膨脹數據的時間序列建模
由于通脹數據等宏觀變量序列往往具有序列相關性,本文首先對美國通貨膨脹相關性進行檢驗,并對其建立時間序列模型。本文采用Eviews 計量軟件檢查了美國通貨膨脹變量Δcpiu 的自相關(ACF)和偏自相關(PACF)函數。表3 結果顯示了美國通脹動態存在一定的自相關性,但ACF 和PACF 迅速收斂到0,參考Enders(2004)不應對該變量再次差分。然而,ACF 和PACF 在第6、12 階滯后出現了小幅上升(ρ6=-0.215,ρ12=0.290)暗示了半年度或年度效應的存在。

表3 美國通貨膨脹數據的自相關性
由于描述性統計中通貨膨脹率并不顯著異于0,因此本文對通脹建模時不考慮常數。根據對模型的AIC 和Schwarz criterion,本文優先考慮了ARMA(1,1)模型,在確認殘差已無自相關后,本文嘗試建立以下模型:
對該模型的殘差進行Q-檢驗,結果如表4,顯示Q(6)=11.617、Q(12)=24.266,顯示通貨膨脹存在一個年度效應。因此我們引入了6階、12階滯后項,回歸顯示6階項不顯著,而加入12階滯后項(表4第7列)可以顯著提高擬合優度。選取ARMA([1,12],1)模型,各系數顯著,且對殘差檢驗結果顯示各階滯后均無顯著自相關、偏自相關關系,因此該模型對美國通貨膨脹月度數據給出了良好的建模:

表4 美國通貨膨脹動態模型選擇
(三)回歸分析及穩定性分析
為分析美國通脹的成因,本文參考Brouwer and Ericsson(1998)、Hendry and Ericsson(1991)以及Davidson et al.(1978),并根據第二章第三節的理論模型建立以下計量方程
其中Δcpiu為前述美國城市消費品物價通脹,Δipi為美國從中國進口全品類商品價格指數,charshare 為美國從中國進口全商品平均費用比例(minmax 歸一化處理,代表運輸成本),tr1m 為美國1 月期國債利率,logtrea 為美聯儲所持有的國債規模(對數,minmax歸一化處理)。
根據本文提出的機制:如果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價格和費用顯著影響美國通脹,應該預期β1>0,β2>0 顯著成立,即進口成本越高,美國通脹越高,支持成本傳導機制;如果美聯儲傳統貨幣政策對美國通脹顯著影響,那么β3<0,即緊縮性貨幣政策(利率上升)降低通脹,支持傳統貨幣政策反饋機制;如果美聯儲的非常規性貨幣政策對美國通脹有顯著影響,那么β4>0,即擴張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增發貨幣刺激通脹的渠道成立。本文采用Eviews 軟件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5。其中第一列為基準回歸,第2 列為不加入解釋變量的前述ARMA([1,12],1)模型,而第3~6 列為僅加入部分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第7列則改變了樣本窗口期間。

表5 計量回歸結果
計量結果顯示,僅能確定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價格和費用占比是影響美國通脹的因素,其中進口價格指數每上升1%,美國月度通脹上升0.3271%(β1>0)。而運費成本同樣對美國通脹有顯著影響(β2>0),這支持了美國通脹的傳入型機制。然而,結果并未支持美國通脹與其傳統貨幣政策的聯系(β3=0),而美聯儲擴張資產負債表對通脹存在正向影響(β4>0),但并不穩健(比較第1 列和第5、6列)。第一列的基準回歸結果如下
為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分時間樣本重新對方程進行回歸。本文縮短樣本時間為2006 年1月—2019年12月,檢驗新冠疫情前美國通脹動態的影響因素,結果報告在表5第(7)列。結果顯示美國從中國進口價格變量前的系數仍然顯著且與全樣本結果水平值可比,但進口費用對美國通脹的影響則較小且不顯著。這一結果意味著中美貿易運價、成本對美國通脹的影響主要發生在2020 年之后,即新冠疫情沖擊后中美貿易的運輸成本上升(根據圖7,疫情前費用成本大致占總進口金額的6%,這一比例在2020年后躍升到10%左右)可能顯著提高了美國的通脹。
(四)實證檢驗結論
上述實證分析對第二章提出的三個研究假設予以檢驗,結果支持了美國通脹的成果傳導機制。其中美國從中國進口產品的價格和運輸成本的上漲是構成美國2021—2022 年高通脹的重要原因。其中運價成本反映了全球供應鏈和運輸體系受到疫情的嚴重沖擊,成本上升,對美國經濟形成成本輸入性通脹壓力。而美國進口中國產品價格上漲對美國通脹有顯著影響,其短期機制在于中國出口產品生產企業也受到成本上漲的影響,而其長期機制則在于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和附加值提高,美國難以進口低價產品,進口福利下降。這一結果意味著中美貿易關系的對抗和美國尋求貿易替代的嘗試對美國經濟也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具有較強政策含義。
實證結果的另一方面拒絕了傳統的利率政策對通脹的影響,這顯示出零利率下界下“流動性陷阱”問題的存在。在僅包含貨幣政策(或僅包含量化寬松)的回歸分析中,央行的資產購買計劃(量化寬松)對通脹動態有顯著正向影響,這支持了貨幣理論中的貨幣供應量影響通脹的基本結論。然而,這一效應在加入成本變量后即不顯著,這意味著在美國近20年中,貨幣政策并不是通脹動態的主要影響因素。
四、余論:全球供應鏈調整下的美國通脹與中美經貿關系的戰略選擇
2001年中國入世以來,從中國進口低價、低附加值商品對沖了美國經濟增長的通脹成本,這是美國長達30 年的“大緩和”的原因之一。新冠疫情短期內加劇了美國供應鏈緊張、供需結構沖突的問題,放大了中美貿易沖突的經濟影響,也凸顯了問題背后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對國際關系和經濟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美國對華貿易戰揭示了美國對抗中國崛起的決心。盡管新冠疫情下美國重新提高了對中國進口商品的依賴,但美國未來對華的經濟打壓和對抗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威脅。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了美國的對抗策略實際上對美國產生了顯著的通脹成本。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曾停止部分關稅政策,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美貿易關系對此輪美國高通脹的影響。
疫情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貿易條件惡化,最終為美國通脹點燃了導火索。隨著疫情影響減弱,全球貿易格局趨于穩定,美國或將仍然維持對于中國的進口需求,中美貿易關系仍將對美國通脹走勢產生影響。若以更長遠視角來看,中國不斷進行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創新發展將對美國的國際地位形成新的沖擊,美國對抗中國和扶持其他國家替代中國的動機依然明顯。
隨著掣肘美國經濟增長以及通脹高企的短期影響緩解,全球價值鏈產業鏈格局面臨重塑,這對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格局中的地位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如果美國能夠找到合適的替代供應國,加上美國政府大力支持和輔助制造業回流,會否反過來對中國出口貿易甚至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嚴峻的挑戰?如若中美在貿易領域難以完全脫鉤,同時,中美貿易沖突持續,則還將產生經濟衰退的風險,這對雙方以及世界經濟都是非常糟糕的結果。實際上,2023 年年初硅谷銀行以及簽名銀行(Signature Bank)的破產引發了美國重新思考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促使美國評估其激進加息對抗通貨膨脹的代價。這些經濟后果或許會促使美國政府反思對中國貿易制裁的深層代價。
對中國現階段的發展而言,中美貿易戰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科技和貿易封鎖,無疑對我國之前靠出口創匯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我國面臨內部產業結構轉型壓力和工資、住房成本的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國際形勢也增加了更多競爭和對抗的元素,這都對我國未來的經濟形成了新的挑戰。因此,不管美國和西方各國對我國采取什么樣的打壓政策,諸如高科技封鎖、外資撤出、制造業回流和產業鏈向其他國家轉移,乃至增加各種關稅和貿易保護措施,我國仍然要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不變;同時也要增加對東南亞地區和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和出口。另外,本文的數據分析和理論模型均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科技封鎖乃至各種貿易保護措施,實際上是一個雙輸的游戲,不但減少了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也給這些國家的國民帶來了不可忽視的福利損失,導致西方各國的通貨膨脹兩三年來持高不下,經濟增速下滑,乃至有可能造成全世界的經濟衰退。因此,隨著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官員的進一步接觸和談判,隨著各國元首的互訪,希望能夠讓對方明白貿易戰和科技封鎖無疑是一個雙輸的游戲,會使各國的國民福利都下降,從而使各國的經貿關系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增加貿易合作,共同應對世界經濟的挑戰,避免新的一次全球經濟衰退。這才是21世紀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