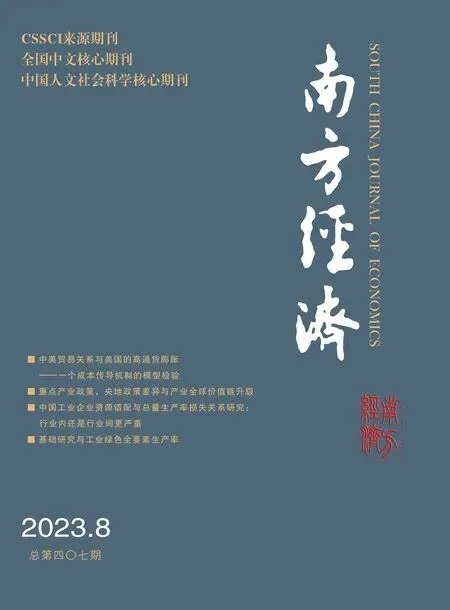是綠色虹吸還是綠色涓滴:低碳試點政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鄰里效應研究
傅芳寧 李勝蘭
一、問題提出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矛盾”的準確定位修正了傳統經濟學單一增長目標的缺陷,揭示了新發展理念對經濟、社會與自然三大系統并重關系和地區均衡公平發展的要求。為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齊頭并進,應對氣候變化給自然界造成的嚴重廣泛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于2010 年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隨后依次于2012 年和2017年擴增試點城市。低碳城市試點工作啟動后,各試點城市均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優勢等出臺了具有當地特色的“低碳城市試點工作實施方案”,且絕大部分方案明確了通過推動技術創新來促進城市低碳發展。綠色技術創新是實現綠色低碳發展模式的關鍵力量,是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鍵因素(Magat,1978),中國在這方面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促進了試點城市內綠色技術創新(徐佳、崔靜波,2020),然而不同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發展不均衡不一致現象逐漸顯現,面對環境治理和綠色轉型問題,各地區不能獨善其身,聯防聯治與區域協同發展是提高我國綠色發展水平的重要著力點(董直慶、王輝,2019;劉金山等,2022)。因此,本文從綠色技術創新視角出發,通過考察低碳試點政策的鄰里效應對我國地區綠色發展不均衡現象進行深入分析,為我國后續完善相關低碳政策與全面協調推進綠色技術創新提供理論依據,為有效緩解社會主要矛盾提出可行建議。
早期對傳統環境政策的研究闡述了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跨區域效應,即環境政策不僅能通過“創新補償效應”及“成本效應”影響當地的綠色技術創新,還會對附近區域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作用(List et al.,2003;Acemoglu et al.,2012;陸銘、馮皓,2014)。當環境政策出臺時,污染產業跨地區轉移造成了環境污染的轉移(Wu et al.,2017;林伯強、鄒楚沅,2014;李勝蘭等,2014;沈坤榮等,2017),從而形成“以鄰為壑”的生產率增長模式(金剛、沈坤榮,2018)。董直慶、王輝(2019)研究發現,在短期內,由于附近地區承接污染產業,當地收入水平提高,鄰地企業有能力增加綠色技術創新投入。但污染產業轉移在長期可能導致鄰地產業向清潔技術方向轉型,從而抑制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由此可見,對不同城市環境政策的非同步激勵會減弱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加強區域之間在環境政策方面的合作機制才能提升“本地-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聯動效應。在制定環境政策時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間存在的技術差距和產業結構差異,采取針對性的效率提升策略,并進行實時監控(沈能、周晶晶,2018)。
對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相關研究,已有文獻主要針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直接實施效果進行了評價,近期研究開始關注試點政策的技術創新效應。絕大部分國外現有文獻認為城市低碳化發展促進了環境污染水平的降低(Wolff,2014;Gehrsitz,2017)。隨著2010 年中國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學術界也越發關注中國城市低碳治理的影響及作用。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龔夢琪等,2019),能夠通過降低城市排污和產業結構升級顯著降低試點城市的空氣污染水平(宋弘等,2019),且通過“鯰魚效應”顯著降低了鄰接非試點城市的碳排放(鄭漢、郭立宏,2022)。技術創新效應方面,低碳試點政策的實施顯著提升了本地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徐佳、崔靜波,2020;Zou et al.,2022),且該促進作用在技術研發階段和成果轉化階段均有體現(胡求光、馬勁韜,2022)。王亞飛、陶文清(2021)研究發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促進了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但這一效應在不同地區呈現出典型異質性。
針對政策實施的鄰里效應問題,目前學術界主要采用空間雙重差分模型(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展開考察。Sunak and Madlener(2016)為考察德國設立風力發電場潛在的財產貶值效應,將建設風力發電場作為準自然實驗,對聯邦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的各風力發電場采用空間雙重差分法進行分析。Qiu and Tong(2021)同樣放寬了雙重差分模型的無溢出效應假設,空間雙重差分模型結果顯示鐵路系統對火車站附近獨立住宅的價值產生了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還波及到處理組外的房產。沈坤榮、金剛(2018)在評估河長制的水污染治理效果時,采用空間雙重差分模型以一百千米為步進距離,考察在不同地理閾值范圍內空間溢出效應的大小。于立宏、金環(2021)分析了雙創示范基地建設的空間溢出效應,空間杜賓效應檢驗顯示雙創示范基地建設促進了本地城市創新創業水平的提升,并對鄰近城市產生了積極作用。
從上述討論可知,現有對低碳試點政策及其溢出效應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和空氣污染等直接政策效果方面,近期文獻開始從技術創新效應角度考察試點政策的進一步實施效果,但忽視了試點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未能對我國不同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發展現狀給予充分有效解釋。基于此,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包括:(1)基于微觀企業層面數據,利用空間雙重差分模型探究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及其傳導機制,并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劃分為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以探究空間層面企業綠色創新行為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真實反應,彌補了當前研究對試點政策鄰里效應討論的不足;(2)從城市綠色發展程度和城市創新能力角度探究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作用的異質性,為試點政策鄰里效應做出了進一步解釋,從綠色創新視角為當前“以鄰為壑”觀點提供了實證證據;(3)對鄰里效應進行分解,以區分試點政策對處理組城市和控制組城市的鄰里效應,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時點和局域范圍的鄰里效應進行異質性分析,完善了鄰里效應計量分析框架,是對我國地區綠色發展不均衡相關研究的重要補充。
余下部分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理論分析及假說提出;第三部分介紹本文的模型、變量與數據;第四部分對基準分析的實證結果進行分析并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五部分為進一步分析,涵蓋異質性分析、機制檢驗和鄰里效應分解;第六部分為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假說提出
為應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氣候變化問題,根據地方申報情況,國家發改委于2010 年7 月確定在五省八市啟動首批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并對試點地區提出了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等五項具體任務;但并未對試點地區設定如重污染行業排放標準、碳排放達峰時間等具體目標,是一項弱約束性的政策。為落實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國家發改委于2012年11月再度將北京、上海、海南等29個城市與省區納入第二批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至此,低碳試點覆蓋了除湖南、寧夏、西藏與青海外的其他大陸省市;低碳試點在我國基本實現全面鋪開。與對第一批試點工作提出的無差異方向性指引相比,國家發改委對第二批試點工作提出了“體現地方特色”的要求,要求地方探索適合本地區的低碳綠色發展模式。為鼓勵更多的城市探索和總結低碳發展經驗,國家發改委于2017 年1 月開展了第三批國家低碳城市試點工作,本次試點包括45 個城市(區、縣),其中不乏轉型壓力較大的西部城市。第三批試點須有一定目標先進性和體制創新性,且須明確設立目標碳排放峰值,可見試點工作更趨成熟。試點政策具有政策組合性特征,各試點地區多措并舉,根據當地稟賦制定包含不同類型環境政策工具的實施方案,具體分為命令控制型工具、市場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三類。此外,試點政府也積極出臺有如專項資金、行業補貼、信貸優惠等各類綠色金融政策,鼓勵企業低碳化發展。
(一)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
環境政策對本地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已基本達成共識。首先,低碳城市試點地區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制定“低碳試點工作實施方案”,絕大部分低碳方案中提出了通過技術創新促進城市低碳發展。試點地區通過建設低碳技術創新平臺并加強低碳技術人才引進等具體手段推進低碳科技創新;該過程伴隨的能源效率提升和生產低碳化會促使本地高能耗產業逐步實現綠色轉型升級,從而又進一步有助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其次,試點政策的低碳約束提高了污染產業的生產成本,倒逼企業升級既有技術開展綠色創新,從而實現“波特假說”。波特假說認為若環境政策設計恰當,企業將有更大的激勵進行環境友好型生產技術的開發,使用新技術會降低生產成本,進而提高經濟效率(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低碳試點城市企業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且面臨政府環境規制、社會責任等多重約束的微觀經濟主體,在充分考慮遵循成本與技術升級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的基礎上,可能通過發展綠色技術創新以實現技術革新,從而降低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排放量,最終滿足試點政策所要求的排放水平。
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存在多種作用途徑。一方面,試點政策可能通過“產業轉移效應”和對資源的“虹吸效應”抑制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根據“污染天堂假說”,環境污染監管政策相對寬松的地區污染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因此自由貿易可能引致環境規制相對寬松地區的生產結構逐步向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最終形成“污染避風港”。污染產業的流入和清潔產業的流出將惡化低碳城市試點地區鄰地產業結構,不利于鄰地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金剛、沈坤榮(2018)研究發現地理位置相鄰城市環境規制執行程度差異的擴大,加劇了污染企業的空間自選擇效應,使得環境規制嚴格執行地區的鄰近城市生產率下降,形成“以鄰為壑”的生產率增長模式。在污染產業就近轉移的同時,試點地區會推行加強資金保障、提升人才支撐等保障措施,并對低碳型產業實施稅收優惠,這就使試點地區成為了政策洼地,對鄰地各方面資源產生“虹吸效應”,不利于鄰近城市的產業建設和人力資本積累,從而對其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試點政策可能通過“效仿效應”和“競爭效應”促進鄰近城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低碳試點城市具有相對明確的減碳目標和較大的政策監督壓力,在低碳實踐過程中積累了獨具地方特色的綠色發展經驗,綠色發展知識和技術的非競爭性會隨著人員的互動往來,并借助網絡信息交流,外溢到鄰近城市(吳玉鳴,2007b)。鄰近地方政府出于環境績效考核的壓力有向先進綠色城市學習、大力發展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從而形成“效仿效應”。此外,隨著政府對綠色環保項目的大力扶持,投資者的綠色偏好日益提升,地方政府為爭取優質資源,吸引資金與人才,可能通過提高環保標準形成“競爭向上”的環境治理競爭態勢(Vogel,2009),有助于發展綠色技術創新。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說1a: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在促進本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同時,通過“產業轉移效應”和“虹吸效應”抑制了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假說1b: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在促進本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同時,通過“效仿效應”和“競爭效應”促進了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二)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與產業結構升級
政府實施環境規制以規范企業的排污行為,污染密集型企業或者通過優化生產流程和生產工藝以減少污染排放;或者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從污染行業退出,轉向清潔型行業,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來減弱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增加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原毅軍、謝榮輝,2014)。同時,環境規制也通過對現有企業的強制性清洗、淘汰來引導產業結構向清潔型方向發展(金碚,2009),企業向清潔型行業的轉型促進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具體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試點城市為實現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的“共贏”,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淘汰一批產能過剩、污染嚴重且效益低下的落后產業,布局具有高端綠色技術、旺盛市場需求和較大增長潛力的現代化高新技術產業,以促進城市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從而引發資本、人力等生產要素從傳統落后產業向效益更好的新型產業流動(王亞飛、陶文清,2021),這種要素在行業間的再配置有助于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而環境規制引致高規制地的污染產業就近轉移將加大鄰地污染產業占比,惡化鄰地產業結構,從而抑制污染承接地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據此,本文提出:
假說2: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可能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促進本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并通過惡化鄰地產業結構抑制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三)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與外商直接投資
以往分析環境規制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的文獻結論存在爭議,存在抑制和促進兩種相反的結論(吳玉鳴,2007a;劉朝等,2014);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與以往以約束排污為主要手段的傳統環境規制不同,主要體現在各試點城市依據本地資源稟賦等條件制定低碳試點工作實施方案,建立相關的森林碳匯補償機制、碳普惠制度體系和低碳扶貧模式,并在資金及科技等方面提供保障(龔夢琪等,2019)。有效的激勵機制將促使試點地區企業實行低碳生產有利可圖,當企業獲利超過環境規制引致的成本增加時,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除相應激勵政策外,試點地區還通過實行自愿型環境政策提高企業節能減排的自主性。部分試點城市通過建立低碳認證制度引導企業參與自愿減排項目,參與自愿減排項目的企業會向外部利益相關者傳達企業環境承諾的信號,從而獲得監管機構、投資者和顧客等利益相關者的支持;當相應支持為企業帶來的間接收益超過企業減排造成的成本上升時,便會促進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為本地帶來了龐大的研發資金,有助于本地開展技術創新活動。而非低碳城市試點地區缺乏相應激勵引導政策,相比之下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據此,本文提出:
假說3: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可能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并通過擠出鄰地外商直接投資抑制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三、模型設定、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本文旨從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視角探究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鄰里效應。檢驗政策實施效應較有效的方法是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由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分三批次逐步開展,本文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評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多期雙重差分法可以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啟動前后,低碳試點地區與非低碳試點地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構建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如式(1):
其中,下標i 和t 分別表示上市公司和年份。GTI 是被解釋變量,表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didct是核心解釋變量,即多期雙重差分變量。多期雙重差分變量didct= 1則表示城市c在年份t屬于低碳試點城市;反之,didct= 0 則表示城市c 在年份t 不屬于低碳試點城市。xit代表一系列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且隨i 和t 變動的控制變量,μjt表示行業與年份的交互效應,δrt表示地區(東、東北、中、西四大區域)與年份的交互效應,λt表示時間效應,εit表示誤差項。
為進一步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本文將空間計量模型與雙重差分模型相結合。空間計量模型中與雙重差分模型結合最多的是自變量空間滯后模型,而自變量空間滯后模型是在普通線性模型等式右端引入所有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即引入外生交互效應,形如式(2):
式中的WX 即為所有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由于等式右端不包括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該模型可以視為普通的線性模型,并使用OLS 方法進行估計。因此,β 衡量的是直接效應的大小,即特定單位中的特定解釋變量的變化對這個單位自身的被解釋變量的影響;θ 測度的是間接效應的大小,即特定單位中的特定解釋變量的變化對其他單位的被解釋變量的影響(Vega and Elhorst,2015)。本文基于上式并借鑒沈坤榮、金剛(2018)評估河長制的水污染治理效果的研究方法采用空間雙重差分模型,等式右邊只包含雙重差分項的空間滯后項,其余解釋變量均以其初始形式作為控制變量,形如式(3):
其中,φ 代表政策的直接效應,即本文所要考察的處理效應,而θ 代表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間接效應或鄰里效應;W 是空間權重矩陣,本文采用285×285 城市層面基于地理距離倒數的行標準化空間權重矩陣,即地理距離越近的地區空間權重矩陣中的權重越大;其他變量與(1)式含義相同。為解決潛在的序列相關和異方差問題,本文將標準誤聚類到行業-年份層面,即假定同一年同一行業之間存在自相關,而不同年或不同行業之間不存在自相關。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本文研究選用了2005—2018 年中國滬深股市A 股上市公司的專利數據及對應的企業層面經濟數據。2009 年11 月國務院確定了到2020 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45%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該行動目標的提出促使各地加大對低碳建設的重視程度,為首批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因此本文研究區間起始時間為2005年。由于中國開展整體監管轉型以優化專利申請結構,2019 年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的專利申請數量24 年來出現首次下降,較2018 年專利申請數量下降10.8%,因此本文研究區間截止到2018 年以剔除監管轉型帶來的影響。此外,對企業樣本做了如下處理:剔除ST、*ST 或PT 上市公司樣本;由于首批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從2010年開始實施,故剔除2010年以后上市的企業;由于綠色技術創新主要集中在污染較高的工業行業,因此本文在行業篩選時剔除了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樣本。上市公司專利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其他企業層面的經濟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和Wind。
1.被解釋變量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綠色專利申請數量,即上市公司本身與子公司綠色專利申請數量之和衡量綠色技術創新,該指標的選取主要考慮到以下兩點:第一,綠色專利數據相較企業研發投入數據具有明確的技術分類,在直觀反映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同時,能夠進一步依據不同技術的創新價值將綠色專利數據進行分類,從而體現創新活動價值貢獻的異質性;第二,專利申請周期長,從專利申請到最終授權通常需要兩年左右的時間,這就導致專利授權數據存在較大的滯后性,考慮到專利技術在申請期間可能就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本文采用綠色專利申請數據更及時地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鄰里效應。
上市企業綠色專利申請數量的數據來源為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綠色專利研究數據庫(Green Patent Research Database,GPRD)。該數據庫是結合中國專利數據以及世界知識產權局公布的綠色專利分類號標準而匹配開發的專業數據庫。參考齊紹洲等(2018)和徐佳、崔靜波(2020)對綠色專利申請指標的構建方法,將該指標分為綠色專利整體申請量(lngrnpat)、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量(lngrninvt)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量(lngrnuty)三種,其中綠色發明專利的創新性高于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對上市企業當年的綠色專利申請數量取對數處理。在穩健性檢驗中,本文采用上市企業綠色專利申請數量占比(grnpatratio),即該企業所申請的綠色專利占其當年申請所有專利的比值,以及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占其當年申請所有發明專利的比值(grninvtratio)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量占其當年申請所有實用新型專利的比值(grnutyratio),來檢驗基準回歸分析的穩健性。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城市是否在當年被確定為低碳試點城市,即多期雙重差分變量did,其表達式為did = Pilot × post,Pilot 表示低碳城市試點地區的虛擬變量,如果該城市或省份是2010 年、2012年或2017年三批政策中某一批政策公布的試點地區,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post為試點政策實施前后的虛擬變量,對應城市低碳試點政策實施期間取值為1,在非試點期間取值為0,如對于第一批低碳城市試點地區,2010年之前取值為0,2010年及之后年份取值為1。
3.控制變量
考慮到企業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產生影響,本文選取了一系列企業經濟特征指標作為控制變量:(1)企業規模(Size),一般認為規模較大的企業具有充足的資金和阻撓潛在進入者的較大動機,從而更具創新性,本文采用企業年末總資本的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規模的大小;(2)企業年齡(FirmAge),已有研究發現成立時間較長的企業通常具有更強的創新意識(張杰等,2015;韓超、桑瑞聰,2018),本文用企業成立時長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年齡;(3)托賓Q 值(TobinQ),Tobin Q 值即企業的市場價值與資本重置成本之比,數值越大表明企業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越強、創新意識越高,其計算公式為(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股份數×每股凈資產+負債賬面值)/總資產;(4)資產負債率(Lev),資產負債率反映了市場對企業信用能力的評價,適度的負債經營為企業進行技術革新提供了資金支持,本文用企業年末總負債除以年末總資產來衡量資產負債率;(5)現金流比率(Cashflow),現金流比率越高表明企業的財務彈性和償債能力越好,本文用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除以總資產來衡量現金流比率;(6)企業業績和治理結構的相關變量:總資產收益率(ROA),用企業凈利潤/總資產平均余額表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T),用機構投資者持股總數除以流通股本表示;賬面市值比(BM),用賬面價值/總市值表示;兩職合一(Dual),即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同一個人為1,否則為0。
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由表1 可見,在2005—2018 年期間,中國上市公司綠色專利申請占比的平均值約為0.0476,可見綠色專利申請相較專利申請總體數量而言還較少,中國綠色技術尚未成熟,未來有巨大的發展創新空間。對比不同類型的綠色專利申請占比,綠色發明專利的專利申請占比為0.0492,高于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占比0.0409,可見在申請的綠色專利中,創新價值更高的綠色發明專利比重更大。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檢驗
按照上述構建的空間雙重差分模型(3),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鄰里效應,估計結果如表2 所示。表2 的第(1)、(3)、(5)列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應,以控制隨時間變化影響所有地區的時間因素,第(2)、(4)、(6)列控制了地區與年份的交互效應,以控制隨地區且隨時間變化的地區時變因素,所有列均匯報了行業-年份層面的聚類標準誤。

表2 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
由表2 可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在促進試點地區本地上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同時,遏制了鄰地上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如果控制年份固定效應,則第(1)列雙重差分項did 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雙重差分空間滯后項Wdid 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在控制了區域與年份交互效應后,第(2)列雙重差分項系數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雙重差分空間滯后項Wdid 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進一步區分不同綠色專利類型,雙重差分項did的系數在第(3)-(6)列中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的did 系數大小差異不大。這與徐佳、崔靜波(2020)的研究結果略有差異,徐佳、崔靜波(2020)研究發現第二批試點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效應主要體現在創新價值更高的綠色發明專利申請上,而對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促進作用較小。造成該結果差異的可能原因是隨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不斷推進,我國專利申請量持續多年保持快速增長,但專利質量難以得到保證,實用新型專利占比較大。雙重差分空間滯后項Wdid的系數在第(3)-(4)列中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在第(5)-(6)列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由此可見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上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遏制作用主要體現在創新價值更高的綠色發明專利申請上,對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無顯著遏制作用。該結果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通過制定體現本地特點的低碳工作實施方案,從供給側淘汰了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產業,這些產業可能遷移至鄰近城市,惡化了鄰地的產業結構;同時試點城市對鄰近城市資本、技術和人力產生“虹吸效應”,不利于鄰近城市的實質性綠色技術創新發展。至此,假說1a 得到驗證。
(二)平行趨勢檢驗與政策動態效應分析
為保證估計量的無偏性,雙重差分模型要求處理組和控制組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平行趨勢假設即在不存在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沖擊時,試點城市和非試點城市企業綠色專利申請情況發展趨勢保持一致,且不隨時間變化而發生系統性差異。本文通過動態效應分析進行平行趨勢檢驗。由于本文放寬了傳統雙重差分模型的無空間溢出效應假設,2010年首批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實施后即產生政策空間效應,因此傳統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對政策實施前n年至政策實施后m年實施效果檢驗的平行趨勢檢驗模式不再適用,本文以2010年作為政策起始年份進行逐年實施效果檢驗。具體地,以首批試點政策實施前一年即2009 年作為對照年份,將政策試點地區與年份的交互項和政策試點地區與年份交互項的空間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以檢驗本地和鄰地平行趨勢假設與政策動態效應。構建模型(4)如下:
其中,postt為研究區間2005—2018年每一年的時間虛擬變量(不包括2009年),Pilot × postt為政策試點地區與年份的交互項,WPilot × postt為政策試點地區與年份交互項的空間滯后項,αt表示每一年本地政策效應的大小,βt表示每一年鄰地政策效應的大小,即每一年政策的鄰里效應,其他設置均與模型(3)相同。
鑒于篇幅限制,本文僅匯報創新價值更高的綠色發明專利申請作為被解釋變量時的情形。圖1繪制了試點政策鄰里效應的估計結果和95%的置信區間,左圖為本地政策動態效應,右圖為政策的鄰地動態效應。對于本地政策動態效應,2010 年前實施政策的虛擬變量系數不顯著,表明在首批試點政策實施之前,試點地區和非試點地區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無顯著差異,支持了平行趨勢假設。2010—2014 年,政策虛擬變量的系數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第一批和第二批試點政策的落地顯著促進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而2015 年的政策虛擬變量系數不顯著,表明試點政策僅在短期內對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促進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效果逐漸減弱。2017 年政策虛擬變量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第三批試點政策的落地顯著促進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對于政策的鄰里效應,試點政策實施前鄰地政策虛擬變量的系數為正,表明試點政策實施前存在一定的“技術擴散效應”;2010 年后鄰地政策虛擬變量的系數由正轉為負,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抑制了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且抑制作用主要表現在第二批和第三批試點政策實施年份之間。

圖1 平行趨勢檢驗與政策動態效應分析
(三)穩健性檢驗
1.剔除同時期其他相關政策的影響
同時期其他低碳政策也可能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產生影響,從而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鄰里效應的識別造成干擾。除了2010 年啟動的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外,2007 年開展的排污權交易試點和2012 年印發的《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均可能影響本地和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為剔除上述政策的干擾,本文對僅覆蓋大氣污染重點控制區的47 個城市和排污權交易試點的11個省份樣本分別進行空間雙重差分檢驗,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可知,僅保留大氣污染重點控制區樣本時,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僅對本地企業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有顯著促進作用,對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未表現出顯著作用。可能原因是大氣污染重點控制區的47個城市與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覆蓋城市重合度高,導致樣本中缺少對照組。僅保留排污權交易試點樣本的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3 考慮同時期相關政策后的回歸結果
2.剔除部分特殊樣本的影響
在低碳試點地區中,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排名前三的城市,這三個城市集中了豐富的經濟、社會資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十二五”時期這三大城市除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外可能還執行了其他嚴格的減排政策,影響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鄰里效應的識別準確性。為排除特殊樣本的干擾,本文剔除北京、上海和深圳樣本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4 第(1)-(3)列所示。從表4 可知,雙重差分項did 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第(1)列雙重差分空間滯后項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第(2)列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第(3)列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剔除北上深樣本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企業綠色發明專利不再體現出遏制作用,這表明對鄰地企業綠色發明專利體現出遏制作用的城市主要為北上深等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

表4 剔除特殊樣本與更換被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
3.其他衡量綠色技術創新的指標
考慮到除了試點政策外的促進企業創新行為的其他不可觀測因素可能影響基準回歸的結論(Popp,2006),本文采用對應的綠色專利申請占總專利申請的比例作為被解釋變量,以排除同時影響專利申請總量和綠色專利申請量的干擾因素,例如創新補貼政策等,回歸結果如表4第(4)-(6)列所示。由表4可知,第(4)-(6)列中雙重差分項di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企業綠色專利申請占比有顯著促進作用;第(4)-(5)列雙重差分空間滯后項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第(6)列雙重差分空間滯后項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上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遏制作用更多體現在綠色發明專利申請占比上,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五、進一步分析
(一)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城市要素稟賦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張華、豐超,2021),本文從城市創新能力和城市綠色發展程度差異性出發,借鑒錢雪松等(2019)的研究方法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的城市異質性。具體地,采用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百強城市CIIC(2020)指標得分排名”表示城市創新能力(ciic),百強城市之外的城市創新指數賦值為0;采用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研究中心等機構發布的“2020 中國綠色城市指數TOP50 報告”中綠色指數數據表示城市綠色發展程度(grnindex),TOP50 之外的城市綠色指數賦值為0。構建模型(5)和模型(6)如下所示。
其中,ciicc為城市創新指數,grnindexc為綠色城市指數,Wciicc和Wgrnindexc分別為其空間滯后項,其他設置均與主模型(3)相同;兩式θ2為判斷城市創新能力和城市綠色發展程度是否影響試點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的關鍵系數,估計結果如表5 所示。從表5 可知,第(1)、(3)、(5)列Wdidct× Wciicc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城市創新能力越強,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綠色技術創新的遏制作用越突出;第(2)、(4)、(6)列Wdidct× Wgrnindexc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城市綠色發展程度越高,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綠色技術創新的遏制作用也越突出。該結果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使創新能力強、綠色發展程度高的城市對鄰地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遏制作用更大,這造成了“以鄰為壑”的不平衡局面。

表5 城市異質性檢驗的回歸結果
(二)機制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的傳導機制,本文采用城市第三產業生產總值與第二產業生產總值之比衡量產業結構升級(Indus32);采用城市外商實際投資額占城市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資(Fdi),由于外商實際投資額的單位為萬美元,因此采用人民幣匯率年均價將美元數據換算為人民幣數據后進行核算。機制變量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機制檢驗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機制檢驗的回歸結果
首先,將產業結構升級和外商直接投資機制變量分別對本地和鄰地試點政策進行回歸,第(1)-(2)列雙重差分項di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雙重差分空間滯后項Wdid 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產業結構升級和外商直接投資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對鄰地機制變量有顯著抑制作用。
其次,將創新價值更高的綠色發明專利申請對本地及鄰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和兩個機制變量分別進行回歸,第(3)列在控制了產業結構升級后,本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綠色發明專利的正向效應較未控制產業結構升級時(0.082)有所降低,對鄰地綠色發明專利不存在顯著作用,并且產業結構升級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本地試點政策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了本地的綠色技術創新,通過抑制鄰地產業結構升級遏制了鄰地綠色技術創新。第(4)列在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資后,本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綠色發明專利的正向效應較未控制外商直接投資時有所降低,對鄰地綠色發明專利的負向效應較未控制外商直接投資時(-0.208)有所降低,并且外商直接投資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本地試點政策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本地的綠色技術創新,通過擠出鄰地外商直接投資遏制了鄰地綠色技術創新。至此,假說2、假說3得到驗證。
(三)鄰里效應分解
1.基準鄰里效應分解
本文(3)式雙重差分空間滯后項的系數衡量的是平均鄰里效應,該系數的大小代表在低碳試點地區實施的試點政策對鄰近所有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平均影響,這忽視了試點政策對處理組和控制組鄰里效應可能存在的異質性。為更精準分析試點政策的鄰里效應,借鑒Chagas et al.(2016)和胡宗義等(2022)的研究方法將試點政策的鄰里效應分解為試點政策對控制組的鄰里效應和試點政策對處理組的鄰里效應,分別構建模型(7)、模型(8)如下:

表7 鄰里效應分解
2.鄰里效應分解時間變化特征
本文在模型(7)、模型(8)基礎上引入鄰里效應分解空間滯后項與首次試點政策實施后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以考察試點政策鄰里效應分解的時間變化特征,圖2 繪制了鄰里效應分解時間變化趨勢的估計結果和95%置信區間,鑒于篇幅限制,本文僅匯報創新價值更高的綠色發明專利申請作為被解釋變量時的情形。左圖為試點政策對鄰近控制組城市的鄰里效應,2011—2017年交互項系數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第一批和第二批試點政策的落地對鄰近控制組城市企業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有顯著抑制作用,其中第二批次試點政策的抑制作用更為突出。右圖為試點政策對鄰近處理組城市的鄰里效應,2010 年首批試點政策的實施促進了處理組地區之間的經驗交流,對鄰近處理組地區綠色發明專利申請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隨著2012年第二批試點政策的啟動,處理組地區之間的綠色技術創新溢出效應減弱,直至2015—2016年溢出效應才再次顯現。

圖2 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鄰里效應分解時間變化特征
3.鄰里效應分解局域特征
考慮到試點政策鄰里效應可能具有局域特征,參考沈坤榮等(2017)的空間權重矩陣設計方法,設定不同的閾值來探究不同距離城市經濟圈的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具體地,在基準回歸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的基礎上,分別以200 千米-900千米、每100千米步進一次為閾值,設定八個局域空間權重矩陣依次代替W1采用模型(7)和模型(8)進行回歸,回歸系數如圖3 所示,圓形標記表示該回歸系數不顯著,三角形標記表示相應回歸系數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從圖3 左圖可知,試點政策對控制組城市的遏制效應隨城市經濟圈的擴大呈現出先增大后平穩的趨勢,平穩起始點在600千米處,且從600 千米開始,試點政策的遏制效應均顯著。從圖3 右圖可知,試點政策對處理組城市的促進作用隨城市經濟圈的擴大而呈不斷上升趨勢,且從500千米開始,試點政策的促進作用均顯著。出現上述結果的可能原因是過于鄰近的地區處于同一省份管轄范圍內,污染產業轉移的獲利空間較小,因此試點政策引致的污染產業就近轉移效應更多地體現在距離試點地區600千米左右的周邊省份;而試點地區之間的正向溢出效應主要由互相交流效仿形成,不存在明顯的經濟圈范圍限制。

圖3 不同閾值下的鄰里效應分解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綠色技術創新是實現綠色低碳發展模式的關鍵力量,本文基于2005—2018 年滬深兩市A 股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采用空間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及其傳導機制,為相關低碳政策的后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對地區綠色技術創新不平衡現象給予了充分闡釋。研究發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對鄰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遏制作用,且遏制作用主要體現在綠色發明專利申請上;此結論在進行了平行趨勢檢驗、剔除同時期其他相關政策的影響、剔除部分特殊樣本的影響、更換衡量綠色技術創新的指標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進一步分析研究發現,城市創新能力越強、綠色發展程度越高,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綠色技術創新的遏制作用越突出,這就造成了“以鄰為壑”的不平衡局面;傳導機制上,本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本地的綠色技術創新,通過抑制鄰地產業結構升級并擠出鄰地外商直接投資遏制了鄰地綠色技術創新;鄰里效應分解結果表明,試點政策對鄰近控制組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遏制作用,其中第二批次試點政策的遏制作用更為突出,遏制作用范圍為600 千米左右的周邊省份,而處理組城市之間具有正向溢出效應。本文的研究結論為有效推進相關低碳政策和促進地區綠色技術創新平衡發展提供了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中央政府需要進一步做好頂層設計,破解環境治理過程中存在的轄區局限性問題,促使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相鄰地方政府就環境治理的目標達成協同規制的共識。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對鄰地上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遏制作用,且遏制作用主要體現在綠色發明專利申請上。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環境政策時應避免負面鄰里效應,發揮試點城市的典范和領頭作用,形成試點城市與周邊城市的合作和協同機制,促進區域共同綠色發展。
第二,小城市積極融入大城市產業發展歷程,同時集中資源和政策大力發展自身明星產業。本文研究結果發現,城市創新能力越強、綠色發展程度越高,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鄰地綠色技術創新的遏制作用就越突出。為應對大城市資源配套、產業和政策等因素引起的虹吸效應,資源相對匱乏的城市應積極融入城市群發展歷程,發展不同城市產業角色分工發展模式,將資源用于集中發展某個或幾個本地特色產業。集中精力發展本地特色、高端、優質產業有利于引進外資留住人才,從而有效緩解大城市虹吸效應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三,拓寬綠色發展經驗交流渠道,通過完善環境信息披露機制激發城市低碳發展動力。本文研究結果發現,試點政策對鄰近控制組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遏制作用,而處理組城市之間具有正向溢出效應。這表明試點政策并不完全是“損他利己”的單邊效應政策,試點城市可以通過分享交流綠色發展經驗等方式形成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從而實現多方共贏。對此,政策制定者應建立綠色發展經驗交流平臺,在完善非試點城市相關信息獲取渠道的同時,通過建立環境信息披露機制激發非試點地區低碳發展動力。
第四,及時對各批試點政策的經驗和教訓進行總結和定期評估,細化不同批次試點城市政策內容,合理安排各批次政策落地時間,深化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效果。本文進一步分析發現,第二批次試點政策對鄰近控制組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抑制作用更為突出,對鄰近處理組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不顯著。可見2012 年發布的第二批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未達到預期效果,試點政策的實施效果未得到逐步深化。對此,政策制定者應根據不同城市發展現狀與前期政策實施情況制定針對性低碳試點政策,合理安排各批次政策落地時間,使試點政策在實施范圍不斷拓寬的同時,實施效果也在政策的動態調整中不斷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