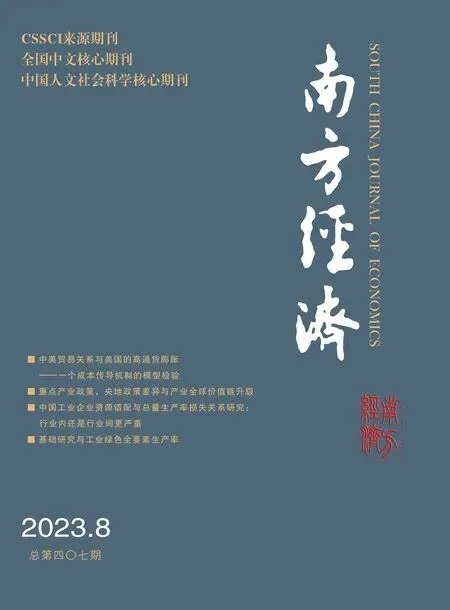重點產業政策,央地政策差異與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
張婕 余壯雄



摘 要:產業規劃為全球價值鏈升級提供重要推力,是政府實現內循環與外循環良性協作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同層級政府的政策實施方向則體現了國家發展戰略與地方比較優勢之間的平衡。文章基于海關數據和重點產業政策數據,利用工具變量法探究央地產業規劃差異對出口企業價值鏈升級的影響和作用渠道。結果表明,中央產業規劃通過提高一般貿易的國內增加值率(DVAR)來推動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而地方產業規劃則通過提高加工貿易的DVAR這一折衷路徑來實現升級效應。此外,還發現升級效應在企業所有制類型和經營規模中存在異質性,而國內要素占比、生產率和創新效率是傳導差異升級效應的重要渠道。文章揭示了不同層級政府在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中的差異化效用,為未來產業規劃政策的實施空間與調整方向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
關鍵詞:產業規劃 全球價值鏈升級 重點產業政策 國內增加值率
DOI:10.19592/j.cnki.scje.401740
JEL分類號:F14,F18,L52?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 6249(2023)08 - 015 - 20
一、引言
2018年以來,在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國際動蕩形勢等多重外生沖擊影響下,中國于2020年提出“雙循環,新格局”的新發展戰略,主張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意圖通過激活國內市場的龐大需求、建立完善的現代產業體系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動力。產業政策也因此頻頻出臺。如何發揮市場優勢、借助產業政策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以更好地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實現內外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已成為當前政府亟需解決的核心問題。現有研究中關于產業政策與產業轉型升級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大多是基于單一的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忽略了產業政策的實施往往伴隨著多種政策工具的組合運用,無法從全局視角綜合評估產業政策的經濟效應。近年來,隨著對各類產業政策效應的討論愈加深入,越來越多的文獻開始轉向使用政府五年規劃中的重點產業政策數據,從全局性角度討論產業政策的效果(宋凌云、王賢彬,2013;趙婷、陳釗,2020)。但是,各省份會在國家五年規劃的基礎上出臺符合本省發展情況的五年規劃。因此,重點產業政策的執行很多時候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目標的權衡。不同層級政府產業政策的差異在實踐中也會帶來不同的效應;張莉等(2017)、余壯雄等(2020)就發現中央與地方重點產業政策對城市工業用地與產業綠色發展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那么,國家“統一方向”的五年規劃與省份“因地制宜”的五年規劃在推動中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中分別扮演怎樣的角色?帶來哪些不同的效果?這些問題都有待深入詳細地探究與分析。
另一方面,有關全球價值鏈的研究始終是國際貿易領域中令人矚目的研究議題,而反映企業產品結構的國內增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作為全球價值鏈地位的量化指標,是相關研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從學術的角度來看,自從Hummels et al.(2001)使用投入產出表來計算垂直專業化程度以來,有關DVAR的研究日見其多。特別是,針對中國產品DVAR的研究已成為近年國際貿易領域研究的熱點之一(Upward et al.,2013;Kee and Tang,2016;毛其淋、許家云,2018;高翔等,2020)。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中國商務部等七個部門于2016年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國際合作提高中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指導意見》中指出,應穩步提升中國單位出口的增加值比重,逐步縮小與發達經濟體差距;可見政府亦認同國內增加值率這一衡量國際貿易中收益分配的指標對于中國制造業實現真正的全球價值鏈攀升的重要意義。而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將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分配問題推向風口浪尖,更是引發了有關產業政策在外貿領域的應用與效應問題的激烈爭論。在此背景下,本文以重點產業政策為切入點,考察其對出口產品DVAR的影響,以探究產業政策對全球價值鏈升級的效果,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從價值鏈地位看,2000—2013年間,中國出口產品的平均DVAR(具體測算方法見下文)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說明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不斷加深。其中,非重點產業的平均DVAR較為穩定的圍繞0.6上下波動,主要的DVAR提升源于國家和省份所支持的重點產業,如圖1所示。受到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后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出現急劇下降的波動趨勢。但從整體來看,無論是國家還是省份的重點產業平均DVAR均呈現出明顯的右上方傾斜趨勢。與之相對應的,由圖2可以發現,國家和省份支持的重點產業出口額也呈現出明顯的右上方傾斜態勢,且波動趨勢同規劃期交接年和金融危機沖擊相吻合。因此,我們猜測,重點產業政策的實施對于提升中國出口產品的DVAR,推動產業實現價值鏈攀升具有積極作用。但由于不同層級政府所支持的重點產業既有重疊又有差異,是誰的政策效應在推動出口產品DVAR提升這一問題仍未可知,需要進一步地深入探討。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1)雖然已有文獻肯定了重點產業政策的出口導向特征(Yu et al.,2020),但關于重點產業政策與國內增加值率之間關系的研究還比較少,而本文為這支文獻進行了有益的補充。(2)本文進一步考察中央與地方政府產業政策的差異化對企業貿易行為的影響,豐富了現有產業規劃差異文獻的研究內容。(3)從重點產業政策的角度出發,系統考察了重點產業政策對中國出口產品DVAR的影響機制,對已有研究進行有益補充的同時,為重點產業政策的未來調整方向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路徑支持。
本文余下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介紹了指標測度、數據與回歸模型設定;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與回歸分析;第五部分是機制檢驗結果;第六部分進行總結。
二、文獻綜述
與本文研究相關的文獻主要有兩塊:一是關于產業政策的政策效應,特別是重點產業政策對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不同層級產業規劃之間關系與作用的異質性;二是關于全球價值鏈升級的影響機制,特別是企業層面的DVAR的測算與影響機制。
(一)產業政策、政策效應與規劃差異
有關產業政策與產業轉型升級之間關系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高新區政策方面,Wang and Wei(2010)指出政府為資助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所提供的政策優惠是中國與發達國家貿易結構重疊程度加深與出口產品國內價值上升的關鍵;出口退稅政策方面,出口退稅率的提升能夠顯著推動出口增長(王孝松、謝申祥,2010),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陳明藝、陳飛,2012);政府補貼政策方面,邢斐等(2016)發現政府補貼是推動出口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且研發補貼與出口補貼政策一齊實施能夠更有效地促進出口轉型升級。但相關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個別具體的政策工具進行分析,無法真實反映多項政策工具組合運用的現實情況,也難以綜合評估產業政策帶來的總體經濟效應。與單個具體的政策工具不同,政府五年規劃中的重點產業政策作為一項全局性的產業政策,在實施中通常配合使用補貼、稅收優惠、利率優惠和貸款支持等多種手段(Yu et al.,2020),能夠更好地捕捉產業政策對特定行業或企業的支持,已經開始被廣泛使用在相關的研究中。從文獻來看,當前基于五年規劃的重點產業政策的實證分析主要集中在資源配置(蔡慶豐、田霖,2019)與生產效率(張莉等,2019;王賢彬、陳春秀,2020)。近年來,學者開始探索重點產業政策對貿易的影響,認為重點產業政策會推動企業出口邊際的擴張(余壯雄等,2020),來實現出口增長(Yu et al.,2020),并誘發企業進行出口業務再分配(余壯雄等,2021)。遺憾的是,雖然已有的研究肯定了重點產業政策對出口擴張的促進作用,但這種出口擴張是否能實現產業全球價值鏈的升級仍然沒有定論,相關的研究嚴重不足,顯然與其重要性不相匹配。
與政策效應相關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關系如何影響政策的效應。梳理研究中央與地方政策差異性的文獻可以發現,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會對各個領域產生影響,僅僅分析國家或省份重點產業政策的經濟效應并不能揭示重點產業政策作用機制的全貌,也解釋不了不同地區與行業在政策實施后的差異化表現。中國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制,中央具有人事任免權,地方則具有區域決策權、自由裁量權(Xu,2011)以及財政上的相對分權(Zhang,2006)。擁有人事任命權的中央政府將GDP增長作為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把地方的經濟發展與當地的官員晉升聯系在一起,在某些時候反而會加大國家與省份發展目標之間的沖突(周黎安,2007)。已有學者注意到中央與地方政府在重點產業政策覆蓋范圍與效用上的差異。在“九五”到“十二五”期間,國家重點產業政策與省份的重點產業政策的差異率約為50%(宋凌云、王賢彬,2013)。從政策效用來看,在環境保護、生產效率、土地配置效率等方面已發現明顯差異。如余壯雄等(2020)發現國家五年規劃著眼于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更傾向于發展低碳排放行業,而地方五年規劃則更關注短期經濟增長,偏向發展高產值的高碳排放行業;宋凌云、王賢彬(2013)驗證了省份特有重點產業政策使重點產業TFP 水平顯著高于非重點產業,而與省份規劃相同的國家重點產業政策對行業TFP 幾乎無顯著影響;楊繼東、羅路寶(2018)認為與國家重點產業政策所覆蓋的產業相比, 省份重點產業政策提及的重點產業對省份內部土地資源的空間配置影響更大。上述研究表明,中央與地方重點產業政策無論是在目標還是在實際執行中都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并帶來差異化表現。由此,從中央與地方政府目標差異角度探討重點產業政策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影響效應就顯得十分重要。
(二)全球價值鏈升級與國內增加值率
全球價值鏈的興起促成了各類官方國際統計機構以增加值為基礎的新貿易統計法則的誕生,也因此掀起以增加值為基礎的全球價值鏈研究熱潮。Balassa(1967)曾指出商品的連續生產過程由于國際分工而被切割成一條垂直貿易鏈,各國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選擇生產環節將其附加值化,并提出了最早的垂直專業化的概念,而后Hummels et al.(2011)提出系統測度垂直專業化的量化指標,用來衡量各國在某一出口品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國內增加值率作為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外在表現(Kee and Tang,2016),其測算方法和拓展研究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在宏觀層面,學者們多使用投入產出表來直接測算行業或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Koopman et al.,2014;徐久香、拓曉瑞,2016),并驗證了價值鏈嵌入位置與宏觀DVAR之間的“微笑曲線”特征(高翔等,2020);與之對應的,微觀層面則是利用企業的產出與進出口數據來測算其DVAR,以此探索企業價值鏈升級的過程與機制(Ma et al.,2015;呂越等,2018)。從影響機制來看,中國加入WTO后,成員之間貿易壁壘的降低使得中國的貿易自由化程度不斷加強,由此帶來的進口品價格下降會降低上游生產中間品的國內廠商的成本,從而使得國內要素替代國外要素成為可能,最終推動DVAR的提高(Kee and Tang,2016),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位置(魏悅羚、張洪勝,2019)。其二,高質量進口產品對企業的自主創新具有溢出效用,通過創新推動加成率上升以及提高出口價格,進而提高DVAR(諸竹君等,2018)。其三,毛其淋、許家云(2018)認為外資進入通過前后向關聯的溢出效應推動了國內增加值率的提高。其四,出口退稅則能夠通過推動加工貿易企業轉型為一般貿易企業而達到提升國內增加值率的目的(劉信恒,2020)。從已有的文獻來看,關于DVAR的影響機制的研究十分豐富,主要機制是通過要素替代、成本加成率、研發創新和出口轉型等作用在DVAR上。與本文研究方向較為類似的有Wu et al.(2021),其以增值稅轉型改革作為政策沖擊來探究對出口企業國內附加值率的影響,但其關注點為單一政策工具——稅收,無法捕捉產業政策支持的整體效應。因此,本文將從綜合性政策工具——重點產業政策,來補充產業政策與對外貿易內在價值的研究。
三、回歸模型與數據說明
(一)回歸模型設定
為了考察重點產業政策對中國出口產品全球價值鏈升級的影響,本文分別測算了度量產品全球價值鏈分工比重的國內增加值率(DVAR)和度量企業產品獲得產業政策支持的比重(rKI),并建立如下的回歸模型,驗證重點產業政策與企業產品全球價值鏈升級之間的關系:
其中,下標i、p和t分別表示企業、省份和年度;DVAR_P和DVAR_O分別對應企業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的DVAR;rKI表示企業獲得政策支持的比重,具體細分為國家政策支持比重(rKI_T)和省份特有政策支持比重(rKI_OnlyP),指標構建和選取原因請見下文;X為控制變量,包括一般貿易占比、出口比重、企業規模、企業年齡、勞均資本、行業市場集中度;[τ]p是省份虛擬變量,t為年度趨勢,[τ]pt即為省份時間趨勢交互項;μi、ρt和εit分別為個體固定效應、年度固定效應和隨機干擾項。此外,所有回歸的協方差計算均聚類到企業層面。
1.企業DVAR的測度
DVAR是指每件出口的最終產品中剔除國外進口的價值部分后國內企業或國內要素所創造的價值比例。考慮中央政府出于經濟長足發展的需要定要支持一般貿易的發展,而地方政府出于對GDP績效的需要很可能會保護本地區加工貿易的發展,那么,不同貿易類型對政策的反應必然存在差異。因此,本文在Upward et al.(2013)的測算方法的基礎上分別計算DVAR:
其中,上標P和O分別表示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M表示進口中間產品的價值;E表示企業的出口額;DS表示企業內銷的銷售額,即銷售總額減去出口額。考慮到使用進口中間品所生產出的最終產品通常不僅僅用于一般貿易出口,可能還會用于國內銷售,MO?EO/(DS+EO)表示企業用于一般貿易出口的最終產品中出口部分所使用的中間品價值1。
本文先匹配工業企業數據庫與海關數據庫,再計算企業的DVAR,樣本期為2000—2013年。詳細的數據處理和計算過程如下。①刪除進口波動較高的石油、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行業,約占工企樣本數的5%。②識別中間產品。對于加工貿易,因為中國海關規定,登記為加工貿易進口的產品只能用于生產加工貿易出口產品,因此,我們將所有進口均定義為中間品進口。對于一般貿易,先利用聯合國公布的BEC(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分類中的BEC代碼來識別中間品2,再利用BEC-HS對照表1識別出海關HS編碼系統中的進口中間品。③用企業名稱將工業企業數據庫與海關數據庫合并后,區分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2,據公式計算出企業層面的DVAR。由于有一小部分樣本存在進口額大于出口額或銷售總額,使得測算得到的DVAR為負值,借鑒Upward et al.(2013)的做法,本文將這類DVAR記為0。
2.政策支持比重指標的測度
五年規劃中有十分詳細的一個章節敘述了未來五年政府將重點扶持和發展的行業,即所謂的重點產業政策。本文借鑒Yu et al.(2020)構建的重點產業政策測算框架,手動收集和整理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五年規劃所提到的重點發展和支持的產業,并將其與2002年的國民經濟行業代碼匹配,形成重點產業政策數據庫,數據涵蓋“九五”至“十二五”4個五年規劃期,全國31個省份以及35個工業2位碼細分行業。具體地,如果一個行業屬于國家或省份重點支持的產業則定義相應的國家或省份重點產業政策變量為1,否則定義為0。
由中國海關數據可知,即使是在二位行業代碼分類下,很多企業的出口產品范圍仍然會覆蓋多個行業;此時,企業出口的產品很可能有一部分屬于產業政策支持的重點行業,另一部分則屬于非重點行業;本文使用重點產業政策數據與中國海關數據匹配,計算出企業出口產品中重點行業的比重,并以此來度量企業獲得政策支持的程度。政策支持比重的測算方法如下:
其中,下標j表示行業;rKI_T(OnlyP)表示基于國家(省份特有)重點產業政策計算的企業獲得的政策支持程度;E代表企業-產品-年度出口額;Sijt為t年i企業在j行業的出口額占t年i企業總出口的比重;KI_T(OnlyP)為國家(省份特有)重點產業政策虛擬變量。
由于在“九五”到“十二五”期間,國家重點產業政策與很多省份的重點產業政策的重疊率都超過了50%(宋凌云、王賢彬,2013)3,張莉等(2017)則建議將各省的重點產業政策同時屬于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的那些行業剝離,計算相應的省份特有重點產業政策,以此來捕捉不同地區產業政策的差異展開分析4。直觀上,中央政府在制定國家重點產業政策時會更多考慮全國宏觀層面的發展目標與方向,而地方政府在制定地區產業政策時通常會在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引入自身發展目標的考慮;那么,將剝離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的干擾后的省份特有重點產業政策(KI_OnlyP)和國家重點產業政策(KI_T)引入模型當中,將更易體現出中央政策與地方政策的差異化影響。
重點產業政策(KI)是政府根據規劃期前的經濟表現以及對未來的經濟預測而制定,并且在規劃期前一年公開披露,屬于前定變量的概念;但是,考慮到在計算政策支持比重(rKI)時所使用的權重為企業當年各行業的出口比重(S),而這一權重通常會隨著政策的不同而變動,是以可能會存在內生的問題。例如,企業為了得到更多的政府補助或政策優惠,會爭相提高政府支持發展的行業的出口比重(余壯雄等,2021);如果產業政策會因行業特征來挑選扶持對象,如國家或省份更傾向挑選具有高附加值率的行業,那么,即使政策是前定的,但這種隨政策而變動的行業出口份額也會受到行業本身的DVAR的影響,這會使得計量模型中的變量rKI存在內生性。同理,企業一方面可能會受到重點產業政策對一般貿易支持的影響而削減加工貿易出口的占比;另一方面,重點產業政策對于企業存在出口導向的作用,會吸引企業進入國際市場(Yu et al.,2020)。因此,回歸方程中所包含的控制變量一般貿易占比(r_ship)和出口比重(r_exp)也可能會存在內生性問題。
本文借鑒Brambilla and Porto(2016)的方法1,利用WTO框架下的MFN關稅2來構建工具變量以解決行業份額(Sijt)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具體構建工具變量的思路如下。首先,根據式(6),使用企業層面年度-行業-國家的出口比重(Sijct)對年度-行業-國家維度的MFN關稅(Tariffjct)進行回歸,回歸中加入了企業虛擬變量υi捕捉隨企業特質,行業年度虛擬變量ωjt捕捉隨著時變的行業特質,國家年度虛擬變量γct捕捉出口目的國的時變特征。然后,根據回歸的結果預測企業-年度-行業-國家的出口比例(?ijct)。最后,根據式(7)將預測得到的企業出口份額與當期的重點產業政策虛擬變量(KIjt)相乘,匯總得到企業年度的政策支持比重的預測(IV_rKIit),作為政策支持比重(rKIit)的工具變量。類似地,本文還使用企業-年度-行業-國家的r_ship與r_exp替換式(6)的Sijct,重新進行回歸預測,估算一般貿易占比和出口比重的工具變量(IV_r_ship和IV_r_exp)。
3.控制變量
參考既有文獻,本文在回歸方程中加入了一些常規的控制變量以控制企業與行業層面的特征差異所帶來的影響:①加入一般貿易占比(r_ship)以控制企業貿易類型偏好;②加入出口比重(r_exp)以控制企業的目標市場特征,即企業的出口額除以銷售總額;③企業規模(ln Size),使用企業每個規劃期首年的實際總資產并取對數得到;④企業年齡(ln Age);⑤資本勞動比(ln KL),使用實際固定資產除以雇員總數后對數化得到,以此控制企業的要素密集類型帶來的影響;⑥行業市場集中度(HHI),用銷售總額作為基礎測算,用來捕捉行業競爭程度。另外,為了消除樣本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均進行了雙側0.5%的縮尾處理。
(二)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了三方面的數據:手動收集的中央與各省的重點產業政策數據庫、工業企業數據與海關貿易數據。數據預處理過程如下:工業企業數據庫方面,首先,將各年的行業代碼統一調整為2002年國民經濟行業代碼版本的兩位數行業代碼;其次,刪除個別與貿易關系不大或產品比較特殊的行業,包括采礦業、能源行業、工藝品制造業、煙草行業、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石油與金屬制造業;最后,刪除工業銷售額、銷售總額、中間投入品價值為空值或者負值,職工人數少于8人或者為空值的樣本。海關貿易數據庫方面,刪除了無關的服務貿易數據;刪除了企業出口額占銷售額比例小于0.001%的樣本以及出口額在5萬美元以下的樣本,以降低極端值影響;剔除中間貿易商1。最終,基于企業名稱將海關貿易數據與工業企業數據進行匹配,再根據行業代碼匹配重點產業政策數據,最終共得到501621個觀測樣本。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四、實證結果與回歸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報告了加工貿易出口的回歸結果,因變量為企業加工貿易DVAR(DVAR_P),自變量為國家政策支持比重(rKI_T)和省份特有政策支持比重(rKI_OnlyP),以對比中央和地方產業政策對加工貿易發展的差異化影響。表中所有的回歸均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估計;IV有效性檢驗均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零假說,且通過了弱工具檢驗,表明IV估計的結果是可信的。列(1)~(2)為僅包含內生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而列(3)~(4)為加入所有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如表2,無論是否加入其他控制變量,關注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高度顯著且符號方向相同。從列(3)-(4)的回歸結果來看,rKI_T對DVAR_P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企業出口的產品劃入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加工貿易DVAR下降0.0285個百分點;與之相反,rKI_OnlyP對DVAR_P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企業出口的產品劃入本省重點產業政策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加工貿易DVAR上升0.0246個百分點。這說明,兩類重點產業政策對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國家重點產業政策對加工貿易DVAR呈現抑制的作用,而省份重點產業政策對加工貿易DVAR呈現促進的作用。
表3報告了一般貿易出口的回歸結果,表格結構與表2類似,但因變量為企業一般貿易DVAR。如表3所示,不同控制變量設定下,rKI_T和rKI_OnlyP的回歸系數方向保持一致且均顯著性高;從系數的方向來看,rKI_T對DVAR_O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rKI_OnlyP對DVAR_O的回歸系數則顯著為負。由此可看出,兩類重點產業政策對企業的一般貿易出口同樣存在迥然不同的政策效應:國家重點產業政策推動了一般貿易DVAR的提升,而省份重點產業政策則會抑制一般貿易DVAR的提升。
綜合表2和表3的基準回歸可知,在推動全球價值鏈升級方面,國家重點產業政策和省份重點產業政策的激勵方向明顯不同:國家重點產業政策主要通過提高一般貿易DVAR的方式,借助一般貿易的升級來推動中國出口產品全球價值鏈的升級;與之相對,省份重點產業政策則主要通過升級加工貿易的方式來實現產業全球價值鏈的升級。作為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與分工的主要方式,加工貿易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確實帶來了很大的助力,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這種產業鏈兩端都被國外控制的低端加工模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當前的發展階段。相比而言,一般貿易的可控性及其與國內要素的聯動性方面都更為強勁,是中國發展“雙循環,新格局”這一長期目標的主要載體。因此,國家政策致力于支持一般貿易的發展與升級是與中國的長遠利益相符的。在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的支持下,企業的一般貿易產品不斷自主成長,持續提升其國內替代能力,體現為推動一般貿易DVAR提升;企業的加工貿易產品則是得益于升級成為一般貿易產品的政策鼓勵,采取升級優質加工產品而留下了競爭能力較弱的加工產品,進而體現出國家重點產業政策作用下企業加工貿易DVAR下降趨勢。從地區層面來看,加工貿易是部分省份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其吸收當地勞動力的成效卓然,全面放棄加工貿易對地區的經濟發展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因此,地方政府會傾向于采用升級加工貿易的折衷方式,來達到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與維持地區經濟增長的平衡。于是,在省份重點產業政策支持下,企業的一般貿易產品可能會利用政策資源進口更多高質量中間品來實現產品優化升級,體現為抑制一般貿易DVAR上升;企業的加工貿易產品則更可能通過搶占高附加值鏈區以延伸產業鏈的方式來實現價值鏈攀升,體現為加工貿易DVAR穩健提升。
(二)穩健性檢驗
本文的樣本期跨越了四個“五年規劃”,但樣本期內包含的“九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時期并不完整。鑒于各個規劃期的目標各不相同,不同規劃期的重點扶持行業差異較大,不完整的規劃期樣本可能會對回歸結果造成扭曲。故此,我們保存完整的“十五規劃”和“十一五規劃”的樣本重新進行回歸,以驗證基準結果的穩健性。表4說明,國家政策支持對加工貿易DVAR有負向影響,對一般貿易DVAR有正向影響;而省份特有政策支持則對加工貿易DVAR為正向作用,對一般貿易DVAR為負向作用;與基準結果一致。
此外,為了檢驗解釋變量的穩定性并放松對工具變量的依賴,我們使用前定的重點產業政策虛擬變量替代基準回歸中的連續型政策支持比重進行回歸。首先,構建企業不同貿易類型下主營行業是否獲得重點產業政策支持的虛擬變量。如果規劃期內企業的加工(一般)貿易主營行業屬于國家重點產業則定義KI_T_P(KI_T_O)為1,否則為0;同樣地,如果規劃期內企業的加工(一般)貿易主營行業屬于省份特有重點產業則定義KI_OnlyP_P(KI_OnlyP_O)為1,否則為0。然后,使用不同貿易類型的DVAR重新對相應的重點產業政策虛擬變量進行LS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兩類重點產業政策指標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與基準結果仍然保持高度一致,即表明本文基礎結論穩健。
(三)異質性分析
1.外資參與
毛其淋、許家云(2018)曾發現,外資進入利于中國企業的出口國內增加值率的提升。由此,我們猜想重點產業政策對DVAR的影響可能在不同所有制企業內存在差異,而外資企業更可能成為產業政策發揮效應的主體。于是,本小節將樣本按照企業的外資參與情況劃分為外資企業1和本土企業再回歸。分樣本的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Panel A為外資企業的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相比,系數符號保持一致。而Panel B的本土企業的回歸結果表示,只有省份特有政策支持比重對一般貿易DVAR的回歸結果顯著為負,其余均不顯著。這表明,對于較為注重內銷、自主性強、全球分工模式利用率較低的本土企業而言,重點產業政策不能有效推動企業實現全球價值鏈的升級,僅在省份重點產業政策支持下會利用政策資源進口高質中間品用于提升其產品質量與競爭力。綜合以上結果可以發現,與全球產業分工聯系更密切的外資企業對于推動全球價值鏈升級的重點產業政策會更加敏感。
2.企業規模
中國當前的經濟模式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級政府借助產業政策等多種手段對整體經濟的發展施加了強大的影響。一方面,產業政策往往更偏向于大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企業1);為了獲得政策支持,大企業會主動調整自身的業務以配合國家發展;相反,小企業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更多是考慮自身的短期利益,從而可能偏離國家的長期發展目標。另一方面,具體到各個地區政策的實施過程,由于業務重置成本較低,靈活性高,無需兼顧社會責任目標,小企業對于地方政策的調整會表現出更強的敏感性。鑒于此,我們猜測重點產業政策升級效應在不同規模的企業中存在差異。不失一般性,以各省份各年企業的實際銷售總額中位數作為分界點,將樣本分為大企業和小企業;當企業i在t年的實際銷售總額超過其所在省份當年所有企業的實際銷售總額的中位數時,定義其為大企業,其余則為小企業。分樣本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rKI_T對大企業的一般貿易DVAR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對小企業的一般貿易DVAR則不顯著;相反,rKI_OnlyP對小企業的加工貿易DVAR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對大企業的加工貿易DVAR的作用顯著度低。這說明了大企業會傾向于保持與中央政策相近的發展方向,推動一般貿易產品的價值鏈升級;小企業則對地方政策的變化更加敏感,側重于加工貿易產品的價值鏈升級。
五、機制檢驗與分析
由企業出口DVAR的表達式(Kee and Tang,2016)1可知,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和企業加成率是影響企業DVAR的兩個直接渠道,故而產業政策在推動企業國內增加值率提升時也主要通過這兩個渠道發揮作用。首先,政府通過產業政策提供低價要素(土地、資金、勞動力等),降低了國內要素相對價格;同時為了扶持本土企業的發展以及區域內企業的聯動,通常也會鼓勵企業使用更多的國內或本地投入品,并給予較大力度的補貼、減稅等優惠措施;為了獲得政策紅利,此時企業選擇更多低價國內要素替代國外進口要素的行為是符合其成本最小化目標的。其次,重點產業政策基于行政手段將資源在重點行業與非重點行業間進行重置也會導致企業過度投資與投資效率降低,抑制政策支持行業內企業的TFP(張莉等,2019),進一步降低企業加成率(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而后影響到出口產品的國內增加值率。最后,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對要素市場的干預行為會誘發企業削弱高風險創新活動而選擇通過主動尋租以獲得超額利潤或收益(張杰等,2011),創新行為的主動削弱會進一步降低市場份額和提升產品需求彈性進而降低企業的成本加成率(劉啟仁、黃建忠,2016),最終影響出口產品的國內增加值率。
鑒于此,本文認為不同層級政府的重點產業政策會通過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生產率和研發創新來傳導其對不同貿易類型國內增加值率的差異化作用并以此來實現全球價值鏈的升級。
(一)國內要素占比
本文參考高翔等(2018)的方法,使用工業企業數據庫的中間投入品減去海關數據庫的進口中間品再除以企業銷售收入計算企業所使用國內要素占比(r_dom),以衡量國內外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這一指標暗含的意義是,當國內要素價格降低時,國內要素占比會升高。在回歸模型設定的式(1)和式(2)中加入國內要素占比(r_dom)及其與政策支持比重的交乘項(rKI系列×r_dom),重新進行回歸估計,結果如表8所示。
如表所示,r_dom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與Kee and Tang(2016)的結論一致,說明國內要素相對價格的降低有利于企業出口國內增加值率的提升。從列(2)~(3)的回歸結果來看,rKI系列×r_dom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顯著為正,意味著國內要素占比越高,兩類重點產業政策對不同貿易類型DVAR的正向作用越強;具體地,對于加工貿易,隨著國內要素價格下降,省份重點產業政策對DVAR的促進作用在不斷增強;而對于一般貿易,隨著國內要素價格下降,國家重點產業政策推動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的政策效應也在不斷增強。由此可見,兩類重點產業政策都會通過影響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從而強化其對出口產品DVAR的推動作用。
(二)全要素生產率
為了檢驗重點產業政策通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作用于產品價值鏈升級的渠道,本文采用OP法(Olley and Pakes,1996)估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并在回歸方程中加入全要素生產率(TFP)及其與政策支持比重的交乘項(rKI系列×TFP),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TFP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隨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DVAR會相應提升。從列(1)~(2)的回歸結果來看,rKI系列×TFP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說明TFP并不是重點產業政策影響加工貿易國內增加值率的作用渠道。列(3)~(4)的回歸結果則顯示,rKI_T ×TFP和rKI_OnlyP ×TFP的回歸系數分別顯著為負和顯著為正,說明中央和地方產業政策會通過影響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對一般貿易的價值鏈升級產生差異化影響。重點產業政策引起的投資低效率會降低企業的整體TFP(張莉等,2019),隨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國家重點產業政策對一般貿易DVAR的正向作用不斷增強,而省份重點產業政策對一般貿易DVAR的抑制作用也逐漸加重。這就說明,政策引致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調整是國家或省份重點產業政策發揮其對一般貿易DVAR的促進或抑制作用的一個重要渠道。
(三)創新效率
本文選取海關數據庫中的企業新出口產品的出口值占其當年總出口的比重作為衡量出口企業創新效率1的指標。具體而言,本文以海關HS前四位碼識別產品類別,并根據企業存續期的出口產品情況識別新出口產品,再使用新產品出口額除以當年出口總額計算每個企業每年的新出口產品比重(r_new)2,最后在回歸方程中加入新出口產品比重及其與兩類政策支持比重的交乘項(rKI系列×r_new),重新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10。
由列(1)~(2)的結果可知,rKI系列×r_new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表明企業的創新效率并不是重點產業政策影響加工貿易國內增加值率的渠道。相反,由列(3)~(4)的結果可知,rKI_T × r_new和rKI_OnlyP × r_new的回歸系數則分別顯著為負和顯著為正,表明重點產業政策對一般貿易DVAR的差異效用會通過企業的創新渠道來反向調節。首先,企業會為了獲得政策支持選擇主動尋租而削弱高風險創新活動以獲得超額利潤或收益,進而表現為產業政策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效率(張杰等,2011);其次,由于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重點產業政策的扶持更多是推動策略性創新而降低了企業的實質性創新(孟慶璽等,2016)。因此,在企業創新效率較低時,國家重點產業政策對一般貿易DVAR的正向作用會得到強化,而省份重點產業政策對一般貿易DVAR的抑制作用則進一步加深。總的來看,與全要素生產率渠道一樣,兩類重點產業政策只有在一般貿易業務中可以通過創新效率渠道來實現其對DVAR的作用。
綜上,兩類重點產業政策會通過影響企業的國內要素占比、全要素生產率和創新效率三個渠道實現其對不同貿易類型DVAR的強化作用。省份重點產業政策會通過提高企業使用國內要素的占比強化其對出口產品DVAR的促進作用。國家重點產業政策不僅會通過提高企業使用國內要素的占比強化其對出口產品DVAR的促進效應,當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創新效率強度處于比較低的水平時,國家重點產業政策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更強。
六、總結性評述
隨著“逆全球化”思潮興起,國際形勢越發復雜,中美貿易戰和全球新冠疫情的雙重沖擊給中國的出口與產業發展帶來嚴峻的考驗。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提出“雙循環,新格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在應對復雜的國際形勢的同時,指引著中國向世界經濟強國的目標前行。這就要求政府要創造有利的條件,支持出口企業加快轉型升級步伐,以承載“雙循環,新格局”的歷史重擔。重點產業政策作為產業規劃的重要階段性措施,是中國政府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工具,為中國企業的壯大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助力。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國海關數據庫、工業企業數據庫以及重點產業政策數據庫,考察了國家和省份重點產業政策與中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之間的關系。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國家“統一方向”的政策與省份“因地制宜”的政策在推動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過程中存在明顯的效應對比;國家重點產業政策對加工貿易DVAR呈現抑制作用,對一般貿易DVAR呈現促進作用;而省份重點產業政策則對加工貿易DVAR呈現促進作用,對一般貿易DVAR呈現抑制作用。異質性顯示,國家與省份重點產業政策的差異化作用主要作用于與全球產業分工更加密切的外資企業,而非本土企業;并且分別通過大企業和小企業發揮升級效應。進一步的機制檢驗發現,國家重點產業政策會通過改變企業的國內要素占比、全要素生產率和創新效率三個渠道來提升一般貿易DVAR,而省份重點產業政策則只通過提高企業國內要素占比實現其推動加工貿易DVAR提升的效應。
本文的研究肯定了重點產業政策在實現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方面的作用,展現了其實現機制,支持了有為政府的觀點。但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目標差異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重點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在產業選擇方面,中央政府在各個階段決定重點產業時更應當注重從全國各區域挑選具有前瞻性、安全性、未來性和亟需自主性的產業,引導具有一定優勢(如人才、環境、產業基礎)的區域承擔該階段的未來產業發展重擔,并需要給予地方政府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地方政府不可盲目跟隨國家的發展方向,引起前瞻性產業過度分散布局。過度競爭可能會導致國內企業更依賴進口技術。地方應當充分考慮自身比較優勢產業,幫助優勢產業通過過渡期實現貿易結構轉型升級。在政策執行方面,對于不同貿易類型的企業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比如,對于國家重點產業政策重合的重點產業,地方政府落實政策時需更關注一般貿易企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困境,采用與加工貿易、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同的差異性政策工具,如提高出口退稅范圍等。用好重點產業政策的差異化效果,可以更好地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可控和安全穩定,使得不同層級的重點產業政策發揮合力共同推動產業全球價值鏈的攀升,促進高質量“雙循環,新格局”的形成。
參考文獻
蔡慶豐、田霖,2019,“產業政策與企業跨行業并購:市場導向還是政策套利”,《中國工業經濟》,第1期,第81-99頁。
陳明藝、陳飛,2012,“我國紡織服裝業出口退稅政策實證檢驗”,《國際經貿探索》,第3期,第15-25頁。
高翔、劉啟仁、黃建忠,2018,“要素市場扭曲與中國企業出口國內附加值率:事實與機制”,《世界經濟》,第10期,第26-50頁。
高翔、黃建忠、袁凱華,2020,“中國制造業存在產業‘微笑曲線嗎?”,《統計研究》,第7期,第15-29頁。
劉啟仁、黃建忠,2016,“產品創新如何影響企業加成率”,《世界經濟》,第11期,第28-53頁。
劉信恒,2020,“出口退稅與出口國內附加值率:事實與機制”,《國際貿易問題》,第1期,第17-31頁。
呂越、盛斌、呂云龍,2018,“中國的市場分割會導致企業出口國內附加值率下降嗎”,《中國工業經濟》,第5期,第5-23頁。
毛其淋、許家云,2018,“外資進入如何影響了本土企業出口國內附加值?”,《經濟學(季刊)》,第4期,第1453-1488頁。
孟慶璽、尹興強、白俊,2016,“產業政策扶持激勵了企業創新嗎?——基于‘五年規劃變更的自然實驗”,《南方經濟》,第12期,第1-25頁。
宋凌云、王賢彬,2013,“重點產業政策、資源重置與產業生產率”,《管理世界》,第12期,第63-77頁。
王賢彬、陳春秀,2020,“中國產業政策對產能過剩的治理效應及機制研究”,《南方經濟》,第8期,第17-32頁。
王孝松、謝申祥,2010,“中國出口退稅政策的決策和形成機制——基于產品層面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經濟研究》,第10期,第101-114頁。
魏悅羚、張洪勝,2019,“進口自由化會提升中國出口國內增加值率嗎——基于總出口核算框架的重新估計”,《中國工業經濟》,第3期,第24-42頁。
邢斐、王書穎、何歡浪,2016,“從出口擴張到對外貿易‘換擋:基于貿易結構轉型的貿易與研發政策選擇”,《經濟研究》,第4期,第89-101頁。
徐久香、拓曉瑞,2016,“中國僅僅是制造大國嗎——基于出口增加值測算角度”,《南方經濟》,第6期,第51-65頁。
余壯雄、陳婕、董潔妙,2020,“通往低碳經濟之路:產業規劃的視角”,《經濟研究》,第5期,第116-132頁。
余壯雄、丁文靜、董潔妙,2021,“重點產業政策對出口再分配的影響”,《統計研究》,第1期,第92-104頁。
余壯雄、董潔妙,2020,“企業出口行業邊際的擴張與收縮”,《世界經濟》,第2期,第167-192頁。
楊繼東、羅路寶,2018,“產業政策、地區競爭與資源空間配置扭曲”,《中國工業經濟》,第12期,第5-22頁。
周黎安,2007,“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第7期,第36-50頁。
趙婷、陳釗,2020,“比較優勢與產業政策效果:區域差異及制度成因”,《經濟學(季刊)》,第3期,第777-796頁。
諸竹君、黃先海、余驍,2018,“進口中間品質量、自主創新與企業出口國內增加值率”,《中國工業經濟》,第8期,第116-134頁。
張莉、朱光順、李夏洋、王賢彬,2017,“重點產業政策與地方政府的資源配置”,《中國工業經濟》,第8期,第63-80頁。
張莉、朱光順、李世剛、李夏洋,2019,“市場環境、重點產業政策與企業生產率差異”,《管理世界》,第3期,第114-126頁。
張杰、周曉艷、李勇,2011,“要素市場扭曲抑制了中國企業R&D?”,《經濟研究》,第8期,第78-91頁。
Balassa, B., 1967, “Trade Liberalization among Industrial Countries: Objectives and Alternatives”, New York: McGrawHill.
Brambilla, I. and G.G. Porto, 2016, “High-Income Export Destinations, Quality and Wa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8: 21-35.
Hummels, D., J. Ishii and K.M. Yi,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1): 75-96.
Kee, H.L. and H. Tang, 2016,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6): 1402-1436.
Koopman, R., Z. Wang and S.J. Wei, 2014,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 459-494.
Melitz, M.J. and G.I.P. Ottaviano, 2008,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5(1): 295-316.
Ma, H., Z. Wang and K. Zhu, 2015, “Domestic Content in Chinas Exports and Its Distribution by Firm Ownership”,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3(1): 3-18.
Olley, G.S. and A. Pakes, 1996,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Econometrica, 64(6): 1263-1297.
Upward, R., Z. Wang and J. Zheng, 2013, “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 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2): 527-543.
Wu, S.B., Y. Lu and X.F. Lv, 2021, “Does Value‐added Tax Reform Boost Firms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9(5): 1275-1299.
Wang, Z. and S.J. Wei, 2010, “What Accounts for the Rising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Xu, C.,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1076-1151.
Yu, Z., J. Dong and Y. Feng, 2020, “The Impacts of the Government Industrial Plans on Chinas Exports and Trade Bal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9(121): 141-158.
Zhang, X., 2006,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nd Inequal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4(4): 713-726.
Key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
Zhang Jie Yu Zhuangxiong
Abstract: Industrial planning provides an important boost for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realiz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circ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ircle.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rec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s reflects the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Utilizing Chinas customs data, Chinese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al firms and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data from 2000 to 2013,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he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of expor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provincial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in terms of policy objectives and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The central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promote the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DVAR) of ordinary trade, but restrain to the DVAR of processing trade. On the contrary, the provincial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promote the DVAR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restrain the DVAR of ordinary trad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GVC are significant only for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the central and provincial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GVC through big firms and small firm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reveal that central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will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domestic factors, reduc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VAR of ordinary trade, while provincial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raise the DVAR of processing trade mainly b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omestic factors.
Our study not only make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s, but also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 support for the future adjustment direction of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which is meaningful for policy maker.
This paper supports “positive government”, and affirm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GVC. However, the goal difference of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 will offset the effect of two kinds of key industrial polic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when formulating industrial pla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make overall plans, whil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should not blindly follow.
Keywords: Industrial Plans;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Key Industrial Policy; DVAR
(責任編輯:徐久香)
* 張婕,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廣東省發展和改革研究院,Email:zhangjiejoey@126.com,通訊地址:廣州市越秀區應元路5號,郵編:510030;余壯雄(通訊作者),暨南大學產業經濟研究院、暨南大學產業大數據應用與經濟決策研究實驗室,Email:yuzx-4@163.com。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作者文責自負。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市場設計研究”(21JZD02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基于監督機器學習的Rubin因果范式研究:模型構建與設定檢驗”(72073039);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RCEP框架下的區域產業合作與價值鏈攀升”(2023A15150104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19JNKY04)。
1 這里假設一般貿易企業用于內銷和出口的產品結構一致。
2 詳情參見Upward et al.(2013)。
1 對照表參見聯合國統計司官網:https://unstats.un.org/unsd/trade/classifications/correspondence-tables.asp。
2 加工貿易定義為海關登記貿易類型為“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其余定義為“一般貿易”。
3 本文也同樣統計過國家與各個省份的重點產業政策的重疊率,與之一致。因篇幅有限,備索。
4 張莉等(2017)發現央地的重點產業政策對城市工業用地出讓的影響程度存在顯著性差異,相對于省份五年規劃內提及的重點產業而言,中央未提及-地方提及的重點產業政策對土地資源的影響最大,即省份特有重點產業政策的影響最大。
1 Brambilla and Porto(2016)使用的是雙邊匯率進行工具變量構建,但其與本文最大的不同在于研究維度。本文需要構建的是企業-行業-年度-國家層面的工具變量,故選擇符合這一特性的關稅來構造工具變量并參考了其模型構建方法。
2 關稅是與重點產業政策無關且無法由企業個體行為所決定的,但切實與企業出口行為相關,影響到企業在各個行業-國家的出口比重。這滿足了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與相關性的要求。
1 借鑒Ahn et al.(2011)鑒別中間貿易商的方法,即將企業名稱中含有“進出口”、“經貿”、“貿易”、“科貿”、“外經”的企業定義為中間貿易商。
1 這里的外資企業包括中外合作經營、中外合資經營和外商獨資企業,根據海關企業編碼的第六位來定義分別是2、3、4。
1 就本文的樣本而言,約78%的國有企業的企業年觀測值被劃分為大企業樣本。
1 文獻中常用新產品產值作為企業創新的指標,但2008年后這一指標缺失情況嚴重(缺失的年份有2004、2008、2011、2012、2013),無法衡量2008年后的企業創新效率,故而舍棄。
2 本文認為只有一般貿易的研發創新能夠明顯影響到一般貿易DVAR,同理,加工貿易也是如此。因此,這里將根據被解釋變量的貿易類型加入同貿易類型的新產品比重進行機制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