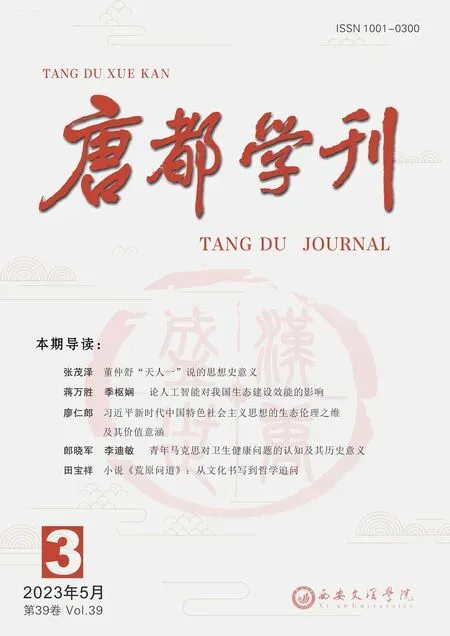董仲舒“天人一”說的思想史意義
張茂澤
(西北大學 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安 710127)
董仲舒提出“天人一”[1]卷12《陰陽義》命題,并進一步表述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1]卷10《深察名號》。可以看出,在董仲舒那里,“天人合一”命題已經呼之欲出了。“天人一”可謂儒家“天人合一”觀念首次明晰的表述,意味著西漢時儒家學者已能比較全面地認識和把握自然與人類社會統一的關系。“天人一”說既是董仲舒思想體系的理論基礎,也是漢代儒學為儒家人性修養和文明教化提供的理論依據。我們應該將“天人一”說視為董仲舒對儒學史的重大貢獻。
董仲舒具體考察了大千世界各類要素及其相互間的聯系,包括天人關系。他發現,世間有十大要素,即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及人[1]卷17《天地陰陽》。這十大要素可分為天地、陰陽、五行、人四類,天地人可謂世界萬物生成的主體要素,因為萬事萬物大都“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地人“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1]卷6《立元神》。天地人怎么“合以成體”?他揭示說:“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1]卷13《五行相生》天地人借助陰陽五行合而為一。陰陽五行,本屬于氣,是氣的表現;氣則是天地人合一的中介,也是天地人合一而生成萬物的載體或材料。可見,董仲舒言“天人一”,表達了他對天與人辯證統一關系的認識。“天人一”,既指天人關系的和諧狀態,也指人們努力修養達到的天人合一理想境界。在他看來,“天人一”不是混一,而是天與人互相作用,有其運動規律;人們對這些規律,可以理性認識和實踐應用。我們今天分析和理解董仲舒“天人一”命題的意義,正可從陰陽五行、由天到人、由人到天、天人合一幾個方面分別看。
一、陰陽五行
《尚書·洪范》早已借箕子之口言及“水火木金土”[2]188五行,認為是大禹治水的首要原則。戰國中后期的《易傳》明確提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3]82,陰陽兩儀再生成八卦以及萬事萬物,這成為我國古代氣宇宙論的典型看法。同時,鄒衍用五行解釋朝代更替,認為黃帝土德,木克土,大禹木德,金克木,商湯金德,火克金,周主火德。代替周朝的應是主“水德”的朝代。此說在當時意欲爭霸統一的齊、梁、趙、燕諸侯中影響很大,梁惠王“郊迎”,趙“平原君側行撇席”,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筑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司馬遷說,鄒衍所至之處,待遇很高,孔子“菜色陳蔡”,孟子“困于齊梁”[4]卷74《孟子荀卿列傳》,完全不能相比。秦始皇統一中國,即用鄒衍說,以周代秦,水克火,主水德,尚黑色,嚴刑峻法。
西漢初年,尚“土”還是尚“水”,朝廷曾發生爭議。董仲舒繞開這個問題,改造陰陽五行說,形成了以陰陽五行為中介材料的天人感應說。其創見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總結陰陽五行運動規律,認為陰陽不離、統一,且陽尊陰卑,五行關系“比相生而間相勝”[1]卷13《五行相生》,即五行間,相鄰者生,相間者勝;二是將陰陽與五行統一起來,作為天地生萬物以及天人合一創造文化的本原性中介,這個說法成為后來理學開山周敦頤《太極圖說》的張本;三是強調陰陽五行與仁義道德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董仲舒說:“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1]卷17《如天之為》,故天地分陰陽,人也分陰陽,事物有陰陽,人類有陰陽。他還發現,天地有五行,人類社會也有五行。“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情,春秋冬夏之類也。”[1]卷11《為人者天》這里提到的“化”,指陰陽五行的變化,認為人的身體、情感及仁義等“德行”,都借助陰陽五行變化這一中介材料而產生,根本上則本原于“天志”“天理”。董仲舒很慎重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他沒有說陰陽五行直接產生道德,而是說仁義道德借助陰陽五行的運行而產生。氣不能單獨產生仁義道德,這是儒家共識。后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論證仁義道德,在漢唐儒學“氣”論基礎上,另辟蹊徑,從更為抽象的天理、良知入手,提出窮天理、致良知命題。在儒學史上,理學、心學在思想系統性上、在社會歷史影響上都超越氣學,是有其內在理論原因的。
其次,董仲舒認為人們進行修養,認識天道規律,離不開陰陽五行中介。他明確說道:“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辯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1]卷17《天地陰陽》人們見天意、天道,觀“天之志”,必須從觀察陰陽五行變化入手:認識“陽陰入出實虛之處”,就可認識“天志”;認識“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就可認識“天道”。
大體上說,陰陽五行是構成世界萬物的質料,是承載天道、天理的工具,是人們認識天道天理的憑借。董仲舒關于陰陽五行的論說,確立了陰陽五行之氣在儒學本原中的輔助地位。這是董仲舒世界觀“醇儒”性的表現。
二、由天到人
董仲舒說:天是“萬物之祖”[1]卷15《順命》。天就像人的“曾祖父”“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眾多,永永無疆。……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1]卷9《觀德》天是世界的本原,人類、三綱等皆本原于此。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人有四肢,王有四政(慶、賞、罰、刑);天有五行,人有五德(仁、義、禮、智、信),身有五臟,政有“五官”(司農、司馬、司營、司徒、司寇)。這都是天人相應、相類的表現。董仲舒將這種相應相類稱為“相副”。他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這是說天人以類而合。又說,春生夏養,秋殺冬藏,“四者天人同有之”[1]卷12《陰陽義》,是天人性能同有而合。他在《深察名號》中說:“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這是說人類文化順天而合。人效法天,人類社會文化(名號,循名責實,使名實相符是代表)發展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雖然這里只說到氣、情感、名號等,但在董仲舒那里,“天人合一”覆蓋了整個自然和社會。天的自然表現是陰陽五行的變化,天的政治表現是奉天承運、朝代更替,天的文化表現是禮樂、名號。這意味著,每個人的人性,每個人的身體、情感、欲望、認知,由個人組合而成的社會共同體如家庭、民族、國家、天下,大家所傳承和面臨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本于天。在此基礎上,人們尊天、事天,奉天、法天,敬天、祭天,就可以達到“天人一”的境界。他的“天人一”說正是天人關系實際的理論表述。
將禮樂、道德追溯到天地之初,《易傳》(從天地到禮儀說)、荀子(“禮有三本”說)皆如此。董仲舒的獨特處在于,他明確肯定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為三綱,認為三綱可“上求于天”,具有神圣性、永恒性、普遍必然性。君王治國,還要注意“五常之道”。他說:“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5]卷56《董仲舒傳》董仲舒要求人們尊天奉天,其目的是為了神圣化三綱五常制度,令人自覺遵行。為什么這么說呢?
第一,人體天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所以人“上類于天”[1]卷11《為人者天》。附著于形體的外貌、言語、心思等,即《尚書·洪范》所謂五事,人的貌、言、視、聽、思,皆“人之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1]卷14《五行五事》。每個人的容貌、言語、感覺、心思皆為天生,也要后天修養,容貌要恭敬,言語要可從,視聽要聰明,心思要寬容。
第二,人性天生,人皆“有善善惡惡之性”,這是進行人性修養和文明教化的基礎。他說:“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1]卷10《深察名號》他提出天生人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1]卷1《玉杯》,可以養育而不可改變,可以培育而不可去除。人們修身養性,文明教化,使人為善,即借助此天生人性而加以修養、教化。
第三,人類社會天生就有三綱五常等制度。董仲舒認為,天有陰陽,“陽尊陰卑”“貴陽而賤陰”[1]卷11《陽尊陰卑》,“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1]卷12《基義》,人也有君臣、父子、夫婦,君父夫為陽,尊貴,臣子婦為陰,卑賤。董仲舒說:“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尊卑等級等禮制與三綱五常一樣,是天生的。君主正是這種禮制金字塔的塔尖。“人之得天得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于天子,疆內之民,統于諸侯。”[1]卷9《奉本》。從社會教化、國家治理的制度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天意如此,君王受命如此,禮義名號如此,人人都應遵循,概莫能外。因為“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不若于言者,人絕之”[1]卷15《順命》。人類社會里的三綱等,正是天人合一的制度化表現。“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1]卷12《基義》有了三綱等制度,不同的人可以團結如一,確保社會和諧穩定,從而實現天人合一理想。董仲舒斷定人類社會先天就有尊卑制度,論據牽強,不符合史實。但天子受命觀念,卻古已有之。《尚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2]180國君、老師都是上天為教化民眾而生的。董仲舒硬說尊卑天定,其動機恐在于令人敬畏,導之以德,提高人們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自覺性。蓋天生人以德、禮,作君、師,人自應修德、循禮,忠君尊師,這是人們奉天、尊天的表現。歷史上的圣王可謂尊天奉天的表率。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董仲舒發現,三代不尊天地不能王,春秋時期不尊天子“不能霸”[1]卷9《奉本》。
第四,人類社會天生就有禮義廉恥等道德價值觀。董仲舒認為,人高于萬物的價值地位也本原于天。因為人本于天,所以人“上類于天”,“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1]卷11《為人者天》,人類社會的仁義道德也本于天。而且他發現,“人之受命天之尊,(有)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廣大有而博,唯人道為可以參天。”[1]卷11《王道通》人是天命的產物,人性中,人身上本就具備道德天賦,這些道德天賦使人具有超越萬物的尊貴地位。比如,只有人才可能進行道德修養、文明教化,只有人才有可能“參天”。天對人獨厚,“天生五谷以養人”“天之常意在于利人”[1]卷16《止雨》。上天尤其“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仁愛君王,制止國家動亂,對待朝廷,總是“盡欲扶持而全安之”[5]卷56《董仲舒傳》。
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也本原于天。他提出:“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天地是名號的大義所在。天地—名號—逆順—是非—言行—事物,人們言行活動、為人處世、應事接物、衡量評判的是非善惡等價值標準皆源于天地,因為“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圣人所發天意”。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為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以君臣父子等名義進行教化,導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使各人皆合其人之名,是為名教。概言之,人們的修養和教化努力,目的就在于讓“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1]卷10《深察名號》,即做事要符合名義,而名義本原于天。
歷史是復雜的,非科學觀念有時也可發揮積極的歷史作用,其關鍵在于人們是否堅持學習,秉公心,獻愛心,善于化消極為積極,變被動為主動。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比附雖不科學,但在道德修養和文明教化實踐中卻產生過積極影響。如發生天災、瘟疫時,治國者相信天人感應論,就會反思自己的治國政策、道德修養,甚至下罪己詔,反省自責,從而可能撥亂反正。漢明帝永平八年(65)十月,有日食。下詔說:“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群臣上奏,直言得失。明帝看后,深自引咎,乃詔:“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6]卷2《顯宗孝明帝紀》又如,漢安帝永初三年(109)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詔曰:“朕以幼沖,奉承洪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饑荒,更相啖食。……咎在朕躬,非群司之責。”[6]卷5《孝安帝紀》古代治國者下罪己詔,歷史悠久。如創立商朝的商湯就說:“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夫”[2]162。周武王也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2]181的反省自責。但以災異下罪己詔的,漢代尤甚。這些都體現了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的積極作用,應該予以肯定。董仲舒“天人一”的世界觀從根本上、主體上說是理性的、人文的,其社會歷史作用也有積極面,不應一筆抹殺。
三、由人而天
董仲舒認為,人生于天,應該“取化于天”[1]卷11《王道通》,效法天道,學習上天,借助上天賦予,進行人為努力,實現人的意義和價值,這就需要人性修養。在董仲舒看來,人們天生具備“能善之性”,但這只是善的基礎,不能直接就說是善。還需要君王教化之,使其成性成人。他用比喻解釋說:“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又說:“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成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1]卷10《深察名號》為什么不承認人性善?董仲舒專門進行了說明。
其一,董仲舒說:“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他將人性分為“名”(概念的內涵)和“實”(概念的外延)兩部分。他稱“名”為“實”,即本質;又稱“實”為“質”,如質料。關于這種人性材料的性質,他認為是中性的,不能說善惡。“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他比喻說:“米出于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于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謂善。”[1]卷10《實性》米出于粟,但不能說粟就是米;玉出于璞,也不能說璞就是玉;善出于性,當然不能說性就是善。他還比喻說:“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卷10《深察名號》絲善,不能直接說繭善,雛善不能直接說卵善,人教化而善,不能直接說人性原本就善,只能說“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要“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須依靠人后天努力才能完成,“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1]卷10《實性》,不是本來性情就如此,不能直接稱為人性。董仲舒認為,“性者生之質”[5]卷56《董仲舒傳》,人性指生命質料、生命材料,即后來張載所謂的氣質之性,不是指人性本體。
其二,在董仲舒看來,要是承認人性善,那就是說人可以“無教”[1]卷10《實性》而善。但實際上,“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茍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1]卷10《深察名號》既然人性已經善了,那百姓們還需要君王教化嗎?這種人性善說不就取消了君王的職責、責任了嗎?董仲舒的反問有力,但卻將孟子所謂人“性善”理解為現實中所有人已經善而不需要修養、教化,這就不符合孟子的原意。孟子講人性善,也提倡存養擴充、讀書知人的修養,兩者并不矛盾。
其三,董仲舒還就孟子人性善說進行分析,認為孟子說的性善指的是人與禽獸比較,人有善端,知道愛親敬長,有惻隱之心等,這固然是善;但這只是“善于禽獸”,比禽獸稍稍善一點,還不能稱為人性的善。人性的善,董仲舒叫做“人道之善”,乃是“圣人之善”。具體內容有“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1]卷10《深察名號》等。董仲舒人性論的論證有新意,但他對孟子性善說有誤解。孟子所謂性善,不是善于禽獸,不是善于現實的具體的個人,乃是本性的絕對善。此說比較抽象,難以理解,但卻不可或缺。因為人性善說乃是儒學的基礎命題。
關于人性修養的具體內容,在董仲舒看來,首先要養生,能夠生存、發展;其次,人成為人,不只有自然生命,還必須有道德修養。有幾點需要結合起來進行修養:第一,僅僅只是人,還不能完成做人成人的任務,必須不忘本原,尊天敬天。因為“為人者,天也”,只有天才能使人成為人,因為天是人的“曾祖父”[1]卷11《為人者天》。《尚書·泰誓上》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2]180,天地是萬物的父母,人是萬物之靈。這些觀念古已有之,而董仲舒說得更具體。第二,遵循天道以養身。董仲舒說:“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養生則“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1]卷17《循天之道》。第三,僅僅自然生命的維持、成長也不能稱為做人成人,因為“為生不能為人”[1]卷11《為人者天》,還必須道德修養、禮法教化,“不知則問,不能則學”[1]卷16《執贄》。第四,人身上有天的基因、德性,人的修養和教化,也要依據這些基因、德性,故人道修養、教化,要求“道莫明省身之天”[1]卷11《為人者天》,反省明了人身上本于天的基因和德性,以此為基礎進行修養和教化。
討論人的修養,首先要關注君主的修養,因為君主是天子,他們奉天承運,是國家的代表。董仲舒認為,君主治國理政,重在效法天道,與天合一。這是因為“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1]卷12《陰陽義》。君主若只是罪己自責,并不能解決現實問題,還必須加強道德修養,實施德治。他明確說:“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如何“救之以德”?就是實行德治,具體措施有“省徭役,薄賦斂,出倉谷,振困窮”,即輕徭薄賦,賑濟窮困,“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1]卷14《五行變救》,提拔重用有道德修養的人才。這些都有助于察舉賢良孝廉,改進朝廷政策,保障窮人生活,正所謂“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圣人之法也”[1]卷11《王道通》。
由人而天,一般人應該如何“受命應天”[1]卷1《楚莊王》,順天應人?照董仲舒看,無非“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于心志,外見于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1]卷6《二端》,即認識敬畏天意;反省自己,言行謹慎;提高修養,加強禮法意識;明善心,行善行而“反道”。強調遵守神圣的禮法等級制度,嚴格遵守祭祀禮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1]卷4《王道》。如孝敬父母,可謂天經地義。同時,人們應有高遠追求,做“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仁人”[5]卷56《董仲舒傳》。實施仁義道德,對己對人有別,應該以仁愛人、以義正我。
人們進行道德修養,經學學習和研究是重要方面。董仲舒說:“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1]卷1《玉英》從歷史事件的所以然,而見天的幽明。“《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1]卷2《竹林》
四、天人合一
董仲舒“天人一”說的核心是天道和人道統一,人道本原于天道,天道要落實為人道。由天到人,由人到天,天人合一,是世界的本真狀態。在天人合一狀態里,“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1]卷6《立元神》,“天生之,地載之,圣人教之”[1]卷11《為人者天》。天生人成,天生人教,天地生養、承載萬物,人則可以教養完成之。天人間有分工,也有合作。
為什么天人之間有這些區別、聯系呢?因為天道和人道在道德上是統一的,但其側重點卻有區別。董仲舒發現,“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1]卷17《天道施》;或者說“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1]卷13《人副天數》。天地的主要性能是施舍、變化,而人的主要性能則重在道義、正義、公義等真理的認識和實踐,以及禮法制度的構建完善。天德和人德統一,故天生和圣教統一;這是天人感應關系中的理想狀態。老子有道生一二三萬和人效法天道說,孔子有天生德和堯“則”天說。董仲舒則細化了天人關系環節。具體看,董仲舒認為,天人關系有授受(天授人受)、主從(天主人從)、尊卑(陽尊陰卑)等關系。而在天主人從關系中,他又結合漢代君主制度實際情況,提出天主君從、君主民從、父主子從、夫主婦從,以及天尊君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等社會倫常關系。這就使他的“天人一”說落實為綱常尊卑制度,為當時社會制度提供理論說明,體現了強烈的時代色彩。
天人關系實際上是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現在科技發達,簡要說清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依然困難,何況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馬克思討論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吸收了近代科學成果,提出“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兩個命題,勞動群眾的社會實踐就是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的統一,社會生產力就是自然人化的產物等等。兩千多年前的我國古人討論天人關系,難免有猜測、想象,如天圓地方、頭圓腳方之類,有仁義道德的價值賦予、以道為核心的邏輯推論,屬形而上思維。董仲舒探尋天人關系之“天人一”論,構建起了儒學史上第一個比較完整的天人觀,給古人提供了人文理性的安身立命之所,無信仰獨斷、傳教獨尊的“二獨”之弊,推動了儒家精神家園超越以神道為主、以信仰為先的宗教格局,也應肯定。
天子、君主被董仲舒作為天命象征、人的代表、天人感應合一的落實,而加以特別重視。他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庸能當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于仁。”[1]卷11《王道通》天地人貫通便是王。一是說王便是天人合一的標識;二是說真正的王符合天人合一、貫通天地人的修養條件;三是說理想的王,應該實行德治仁政,達到天下為公、天人合一的理想社會。
思考天人合一關系,歷史上大體有兩個方向:從天對人看,最早出現了三個類別、兩個環節。關于三個類別:
第一類是天生人成,如董仲舒說:“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1]卷6《立元神》,這種天人合一指自然和社會統一,思想家們思考天人合一的中介、材料時,主要關注陰陽五行,即后人所謂“盈宇宙皆氣也”,天是氣,即天氣,人也屬于氣聚成形,故天人在氣的基礎上能夠合一。陰陽五行之氣難于理性認識,故這類天人合一不免神秘。
第二類是天命人性,以《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說為代表。孔子罕言的“性與天道”問題,亦即人性與天道、天理統一。孔子“天生德于予”、《易傳》“窮理盡性以至于命”[3]93、程朱理學講的“性即理也”,是對這種天人合一的理論概括。天理與人性統一,統一的實質是仁義道德。張載說:“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治理之謂德”,道德的實質是天下之理,即真理。這類天人合一以真理為基礎,最為理性。
第三類是天意民心,以《尚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2]181說為源頭,以孔子“人能弘道”說、孟子良知“固有”說,以及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說、陽明“致良知”說為代表,其統一的主體是意識、精神,一種道德主體性,人成為真正的、理想的人的主體能動性。
董仲舒的“天人一”論在上述三類天人關系理論中,偏重于第一類,但討論具體內容時,也涉及第二、三類。朱熹、陽明主要是第二、三類,但討論時偶爾也會涉及第一類。儒家思想的核心問題是性與天道統一問題,目的在于以天道為人性做說明,為做人成人提供理論依據,也就是要為仁義道德進行論證。歷史上最能順利完成這一任務的是程朱理學,其次是陸王心學,“氣”學一系的論證說明就牽強一些。因為如果氣無理,則不能為仁義道德做論證;如氣有理,則理已經為仁義道德論證了,氣的作用自然下降。董仲舒“天人一”說也要為仁義道德進行論證,因他于天理良知缺乏體會,只能糾結于陰陽五行,反而分散了仁義道德的論證力。所以顯得支離繁瑣,令人難懂。漢唐氣論大體皆如此,不足為怪。
如果撇開“天人一”說討論的陰陽五行問題,將問題集中到思考天人在道德上合一的問題,則天命與道德的關系、人性與道德的關系、國家治理與道德的關系等等論題,在儒學史上就前有淵源而且后有來者,構成了儒學發展主線。重視研究天命與道德的關系,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時間上至少自周公始。《尚書·湯誥》“天道福善禍淫”[2]162說,《易傳》道德修養能夠改變命運說,都是董仲舒“天人一”說的思想源泉。區別在于,董仲舒將道德基礎上的天人合一關系講成一個系統,極大地推動了儒家世界觀的歷史進展。
“天人合一”是我國古代儒道共同的世界觀,但“天人合一”成為命題,卻晚至北宋張載。張載言“一天人”,更明言“天人合一”。他說:“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人。”[7]張載“一天人”說,是董仲舒“天人一”說的動態化表述,可謂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