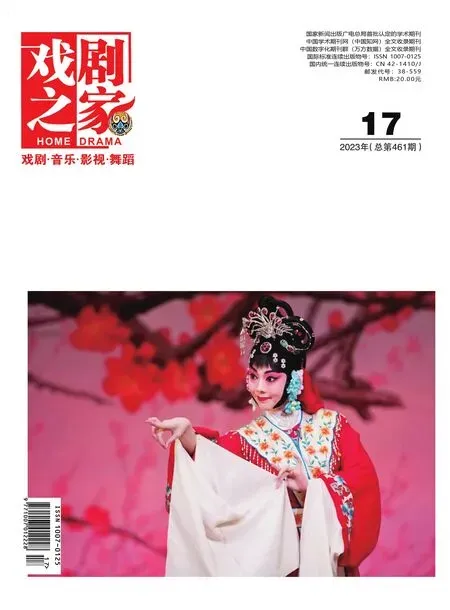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的民族化發(fā)展探究
李若琳
(鄭州工商學(xué)院 河南 鄭州 451400)
鋼琴于十九世紀(jì)自歐洲傳入中國(guó),并逐漸被中國(guó)人所接受,同時(shí),在與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的碰撞中開(kāi)啟了民族化的發(fā)展歷程。萌芽階段的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主要是對(duì)西方經(jīng)典作品進(jìn)行簡(jiǎn)單的復(fù)刻與模仿。新中國(guó)成立后,由于對(duì)外交流日趨頻繁,我國(guó)音樂(lè)教育快速發(fā)展,鋼琴更成為國(guó)民爭(zhēng)先恐后學(xué)習(xí)的西洋樂(lè)器之一。隨著音樂(lè)文化的推廣和普及,我國(guó)音樂(lè)家也開(kāi)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將西方鋼琴音樂(lè)與我國(guó)民族音樂(lè)有機(jī)結(jié)合,并在演奏和創(chuàng)作具有民族特色的鋼琴作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西方鋼琴音樂(lè)與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元素相互碰撞、融合,音樂(lè)作品的調(diào)式、和聲、節(jié)奏、織體等方面逐漸呈現(xiàn)出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特色,這推動(dòng)了鋼琴音樂(lè)的民族化發(fā)展。如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不斷吸收融合民族元素,音樂(lè)體系不斷走向成熟。通過(guò)對(duì)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民族化過(guò)程進(jìn)行研究,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本土音樂(lè)語(yǔ)言,促進(jìn)民族音樂(lè)文化的發(fā)展,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一、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的民族化發(fā)展歷程
(一)萌芽時(shí)期
據(jù)記載,鋼琴最早于公元1601 年傳入中國(guó),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拜見(jiàn)明朝皇帝時(shí)進(jìn)獻(xiàn)了一臺(tái)擊弦古鋼琴。十九世紀(jì)的鴉片戰(zhàn)爭(zhēng)打開(kāi)了中國(guó)的國(guó)門(mén),現(xiàn)代鋼琴也隨著西方國(guó)家的其他商品一起被傳到中國(guó)。而鋼琴真正在中國(guó)取得社會(huì)性地位是在二十世紀(jì)初的“學(xué)堂樂(lè)歌”運(yùn)動(dòng)中。幾代音樂(lè)家前赴后繼,艱難探尋,用音符記載中國(guó)社會(huì)與政治生活的曲折歷程,在樂(lè)聲中展現(xiàn)西式潮流與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二十世紀(jì)初,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大量中國(guó)留學(xué)生在學(xué)成歸來(lái)之后傳播西方文化,其中的一些音樂(lè)家開(kāi)始傳播鋼琴文化,并開(kāi)啟了鋼琴音樂(lè)民族化創(chuàng)作的步伐[1]。例如,趙元任創(chuàng)作的《花八板與湘江浪》《和平進(jìn)行曲》就運(yùn)用了民族音樂(lè)的曲調(diào)結(jié)合西方鋼琴?gòu)椬嗉记桑醪綄⒅形鞣戒撉偎囆g(shù)融為一體。從此以后,現(xiàn)代鋼琴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開(kāi)始產(chǎn)生更多的交織融合,鋼琴藝術(shù)也逐漸在中國(guó)生根發(fā)芽。“五四運(yùn)動(dòng)”后,一批青年人運(yùn)用西方作曲技法創(chuàng)作出帶有民族音調(diào)的旋律,邁出了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教育的第一步。例如,1921 年李榮壽創(chuàng)作的《鋸大缸》和1923 年蕭友梅創(chuàng)作的《新霓裳羽衣舞》都采用了中國(guó)傳統(tǒng)調(diào)式,體現(xiàn)了這一時(shí)期音樂(lè)文化的統(tǒng)一與融合。1934 年賀綠汀創(chuàng)作的鋼琴曲《牧童短笛》具有濃郁的民族音樂(lè)風(fēng)格和鄉(xiāng)土氣息,成為標(biāo)志性的中國(guó)風(fēng)格作品,這部作品被公認(rèn)為是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進(jìn)入成熟期的起點(diǎn),對(duì)其后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和其他多聲音樂(lè)創(chuàng)作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從此以后的幾十年,以《牧童短笛》為代表,中國(guó)鋼琴作品形成了自己的個(gè)性風(fēng)格,即具有明朗熱情、抒情浪漫的民族音樂(lè)特色,這為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民族化注入了動(dòng)力。進(jìn)入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后,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幾乎停滯,鋼琴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也陷入困境,這一時(shí)期問(wèn)世的鋼琴作品雖然不多,但體裁種類(lèi)逐漸豐富,舞曲、序曲、奏鳴曲、敘事曲、重奏等不斷出現(xiàn),不僅延續(xù)了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民族化的路徑,也為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的發(fā)展積蓄了力量。
(二)發(fā)展時(shí)期
新中國(guó)成立初期,我國(guó)鋼琴音樂(lè)迎來(lái)了嶄新的發(fā)展機(jī)遇。20 世紀(jì)50 年代至60 年代初期,中國(guó)鋼琴作品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短暫的繁榮,涌現(xiàn)出一大批格調(diào)清新,形式、體裁多樣的作品。例如,丁善德創(chuàng)作的《兒童組曲》,這一作品堪稱(chēng)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鋼琴作品的“代表作”[2]。《兒童組曲》以?xún)和粘5拇螋[嬉戲和生活趣事為靈感,比如兒童去郊外游玩的情景,撲蝴蝶、跳繩、捉迷藏的游戲場(chǎng)景,將童年歡樂(lè)用曲調(diào)和旋律呈現(xiàn)出來(lái)。在創(chuàng)作中,丁善德將西方傳統(tǒng)音樂(lè)創(chuàng)作技法與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元素相融合,運(yùn)用新穎的表現(xiàn)手法打磨出富有中國(guó)風(fēng)味的鋼琴作品,呈現(xiàn)出活潑鮮明的音樂(lè)形象,展現(xiàn)了濃郁的民族音樂(lè)情懷,同時(shí)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寶庫(kù),推動(dòng)了鋼琴音樂(lè)的民族化發(fā)展。
20 世紀(jì)60 年代中后期到70 年代,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在曲折中艱難發(fā)展,而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出現(xiàn)為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鋼琴藝術(shù)奠定了良好的發(fā)展基礎(chǔ)。鋼琴伴唱《紅燈記》是殷承宗受到“樣板戲”的影響而創(chuàng)作的。《紅燈記》是我國(guó)歷史上第一部與鋼琴合作的京劇,劇目的成功也讓正在被“邊緣化”的鋼琴重新獲得了關(guān)注。在《紅燈記》大獲成功的基礎(chǔ)上,殷承宗組成了“黃河創(chuàng)作組”,1970 年5 月,鋼琴協(xié)奏曲《黃河》問(wèn)世,并在西方樂(lè)器與民族音樂(lè)的碰撞中展現(xiàn)出非凡的藝術(shù)魅力。
雖然我國(guó)的鋼琴事業(yè)發(fā)展比較曲折,但音樂(lè)家們?nèi)匀粍?chuàng)作了一批具有影響力的鋼琴改編曲,其中比較經(jīng)典的有《梅花三弄》《百鳥(niǎo)朝鳳》《平湖秋月》《夕陽(yáng)簫鼓》等。這些作品的問(wèn)世使中國(guó)鋼琴藝術(shù)更加豐富多彩,也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民族化的進(jìn)程。
(三)繁榮時(shí)期
改革開(kāi)放以后,中國(guó)與世界各國(guó)的文化交往日益頻繁,這為中國(guó)音樂(lè)事業(yè)帶來(lái)了新的生機(jī)。在這一階段,中國(guó)音樂(lè)家有機(jī)會(huì)走出國(guó)門(mén),更好地了解學(xué)習(xí)世界鋼琴藝術(shù),世界上許多優(yōu)秀的鋼琴家也來(lái)到中國(guó)進(jìn)行學(xué)術(shù)交流,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文化事業(yè)空前活躍,涌現(xiàn)出一批采用新技法創(chuàng)作的新作品,同時(shí),鋼琴音樂(lè)的民族化也逐漸走向成熟[3]。
“多元化”是這一時(shí)期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作品的特點(diǎn),也是其民族化發(fā)展的重要體現(xiàn)。音樂(lè)家的作品在題材體裁上是多元的,在形式風(fēng)格上是多元的,在審美趣味上是多元的,在技術(shù)技巧上也是多元的。這一時(shí)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汪立三的鋼琴套曲《他山集》。這部作品取意于《詩(shī)經(jīng)·小雅》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shí)巧妙運(yùn)用色彩斑斕的音響形態(tài)對(duì)民族樂(lè)器的發(fā)聲效果以及自然中的聲響進(jìn)行模仿,塑造出鮮明的民族氣質(zhì)和民間風(fēng)格的藝術(shù)形象。這首作品是由五首序曲與賦格組成的復(fù)調(diào)性音畫(huà)套曲,采用宮、商、角、徵、羽五種五聲調(diào)式為基礎(chǔ),選擇了從F 到A 之間的五個(gè)音作為各調(diào)的主音,構(gòu)成了五套序曲與賦格,具有民族音樂(lè)的特征,而作曲手法采用西方現(xiàn)代作曲技法,因此,作品凸顯了現(xiàn)代技法與民族文化的融合。《他山集》這套作品借鑒了國(guó)畫(huà)中題款的做法,在每套曲前都有一段題詞,別具一格的融合賦予了音樂(lè)以意境美,表達(dá)了作曲者希望通過(guò)文學(xué)語(yǔ)言詮釋作品含義的人文情感,也表現(xiàn)出作曲家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向往與熱愛(ài)。作品傳承并發(fā)揚(yáng)了傳統(tǒng)文人墨客在繪畫(huà)上賦詩(shī)作詞的繪畫(huà)藝術(shù)形式,作曲者以樂(lè)譜為畫(huà),以賦詩(shī)詞為意,將現(xiàn)代琴韻和傳統(tǒng)書(shū)畫(huà)藝術(shù)相結(jié)合,體現(xiàn)了多元化的創(chuàng)作理念。
此外,還有許多音樂(lè)家融合西方樂(lè)器的技巧與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文化元素創(chuàng)作出了具有時(shí)代特色的作品,這些現(xiàn)代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推動(dòng)了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的成熟,為我國(guó)音樂(lè)文化事業(yè)的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二、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的民族化發(fā)展表現(xiàn)
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的藝術(shù)魅力和文化價(jià)值在于,“中國(guó)風(fēng)格”通過(guò)鋼琴音色得到了充分展現(xiàn),其神韻在于與音階、調(diào)式、旋法、曲式、和聲、伴奏織體、節(jié)奏節(jié)拍、演奏法等要素的融匯而形成的美學(xué)意境。通過(guò)演奏讓鋼琴發(fā)出中國(guó)文化語(yǔ)境下的特有音響是展現(xiàn)中國(guó)鋼琴文化的良好開(kāi)端。在民族化的發(fā)展道路上,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體現(xiàn)出的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的精神、氣質(zhì)、審美等能讓聽(tīng)者更容易融入中國(guó)文化的主流中去審視民族特色的鋼琴作品,在欣賞中體味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藝術(shù)內(nèi)涵和魅力[4]。縱觀歷史,中國(guó)音樂(lè)家對(duì)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的民族化發(fā)展的探索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一)音樂(lè)調(diào)式的民族化
調(diào)式是按照音程關(guān)系把不同音高組織在一起的若干個(gè)樂(lè)音。在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中,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中的每一個(gè)音都可以作為主音構(gòu)成五聲調(diào)式。在民族風(fēng)味的鋼琴作品中,許多音樂(lè)家都借鑒了五聲音階及相關(guān)理論。例如,《彩云追月》是王建中根據(jù)民族管弦樂(lè)曲改編而成的,作者把西方音樂(lè)技法與中國(guó)五聲音階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了獨(dú)特的韻味,其旋律簡(jiǎn)單質(zhì)樸,線條流暢,抒情優(yōu)美婉轉(zhuǎn),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ài)。此外,鋼琴曲《山丹丹開(kāi)花紅艷艷》采用的是復(fù)三部曲式,運(yùn)用民族商調(diào)式寫(xiě)成,樂(lè)曲開(kāi)頭的引子部分節(jié)奏比較自由,速度變化多。A 部分采用了民族商調(diào)式,旋律較為明亮熱情,在聽(tīng)覺(jué)上給人以深遠(yuǎn)、悠長(zhǎng)之感。B 部分熱情似火,以變奏曲的形式展開(kāi)。結(jié)尾處的A’部分把音樂(lè)推向高潮。樂(lè)曲的三個(gè)部分都帶有變奏曲式的特征,以B 部分為例,作者巧妙融合了傳統(tǒng)的三度疊置和弦同變異性五聲式和弦,讓整個(gè)高潮部分不僅情感激蕩,且細(xì)膩綿長(zhǎng),突出了鋼琴的獨(dú)特音色,也展現(xiàn)了民族音樂(lè)調(diào)式的特點(diǎn)。
(二)曲式結(jié)構(gòu)的民族化
曲式就是樂(lè)曲的結(jié)構(gòu)形式。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不同作曲家在曲式結(jié)構(gòu)的設(shè)計(jì)上也有差異,如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側(cè)重抒情,西方音樂(lè)更注重邏輯性。基于此,在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中,音樂(lè)家們基于傳統(tǒng)文化特點(diǎn)對(duì)曲式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了設(shè)計(jì)。例如,取材于抗日救亡歌曲《黃河大合唱》的鋼琴協(xié)奏曲《黃河》運(yùn)用了西洋古典鋼琴協(xié)奏曲的表現(xiàn)手法,在曲式結(jié)構(gòu)上又融入了船夫號(hào)子等中國(guó)民間傳統(tǒng)音樂(lè)元素,呈現(xiàn)出史詩(shī)般的結(jié)構(gòu)、華麗的技巧、豐富的層次和壯闊的意境。這首音樂(lè)不僅在國(guó)內(nèi)廣為流傳,更享有國(guó)際聲譽(yù),展示了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發(fā)展的成就。再如,《夕陽(yáng)簫鼓》是古代漢族琵琶曲代表作品之一,音樂(lè)家黎英海于1972 年將這首經(jīng)典作品改編成鋼琴獨(dú)奏曲,展現(xiàn)出獨(dú)特的曲式結(jié)構(gòu)。獨(dú)奏曲《夕陽(yáng)簫鼓》中散—慢—快—散的結(jié)構(gòu)形式,中間各段時(shí)空節(jié)奏變量自然遞增,表現(xiàn)了中國(guó)神韻和意境,符合東方的音樂(lè)審美,也巧妙體現(xiàn)了西方音樂(lè)的邏輯思維。這樣的作品充分展現(xiàn)了鋼琴的特色,將西洋樂(lè)器與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元素相融合,是鋼琴藝術(shù)民族化的典范[5]。此外,音樂(lè)家張朝創(chuàng)作的鋼琴獨(dú)奏曲《皮黃》將京劇音樂(lè)元素和現(xiàn)代專(zhuān)業(yè)作曲手法相結(jié)合,在旋律、調(diào)式、節(jié)奏等方面繼承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比較鮮明地融入了“西皮”“二黃”的腔調(diào),采用傳統(tǒng)戲曲音樂(lè)中“板式變化體”這一結(jié)構(gòu)形式和西方復(fù)合調(diào)性、非三度疊置和弦等技法,使整首作品具有濃濃的戲曲韻味,也獨(dú)具民族特色。
(三)和聲語(yǔ)言的民族化
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多是以線性旋律為主的單聲部音樂(lè),其和聲語(yǔ)言比較單一。在鋼琴音樂(lè)民族化的過(guò)程中,中國(guó)音樂(lè)家積極吸收西方和聲語(yǔ)言,融合傳統(tǒng)音樂(lè)調(diào)式,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和聲風(fēng)格。例如,音樂(lè)家江文也根據(jù)古琴曲譜《漁舟唱晚》改編的《綺想曲》在和聲上放棄了對(duì)西方和聲的追求,探求與中國(guó)傳統(tǒng)調(diào)式相一致的和聲風(fēng)格,同時(shí)吸收民族音樂(lè)要素,形成了獨(dú)特的風(fēng)格。此外,音樂(lè)家王建中在改編古曲《梅花三弄》的過(guò)程中,對(duì)不同聲部之間的配合進(jìn)行設(shè)計(jì),突出了和聲上的優(yōu)勢(shì)。作品的第一段呈現(xiàn)出中低音區(qū)的和弦音響,在鋼琴獨(dú)特的音色下,仿佛一股寒冬冷風(fēng)撲面而來(lái),營(yíng)造了一種肅殺的氛圍;此外,作者在結(jié)尾部分利用高音區(qū)呈現(xiàn)出“一唱三嘆”的效果,通過(guò)和聲語(yǔ)言呈現(xiàn)回聲的效果,突出《梅花三弄》的主題,形成余音繞梁的意境。這樣的創(chuàng)作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bǔ)了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的不足,讓鋼琴音樂(lè)的發(fā)展更加豐富、多元。
(四)音樂(lè)理念的民族化
中國(guó)東方音樂(lè)體系作為獨(dú)立于世界藝術(shù)之林的完整的藝術(shù)體系,其主要特點(diǎn)在于其鮮明的價(jià)值理念。中國(guó)鋼琴作品歷經(jīng)百年發(fā)展,已經(jīng)與我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相融合,并在作品中展現(xiàn)出深厚的人文底蘊(yùn)以及獨(dú)特的音樂(lè)理念。例如,《梅花三弄》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融合了西方的音樂(lè)技巧以及中國(guó)的審美理念,展現(xiàn)出濃厚的民族風(fēng)韻、清雅幽遠(yuǎn)的意境、古樸雅致的曲意,充分體現(xiàn)了琴曲“高、潔、清、虛、淡”的審美取向。這樣的創(chuàng)作展現(xiàn)出中國(guó)文化的生命力,也激勵(lì)我們?cè)谖幕瘋鞒械幕A(chǔ)上不斷發(fā)展中國(guó)鋼琴藝術(shù)。
三、結(jié)語(yǔ)
回顧百年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發(fā)展史,中國(guó)鋼琴音樂(lè)藝術(shù)家從最初的學(xué)習(xí)、借鑒,到進(jìn)行民族化的創(chuàng)新,這一歷程見(jiàn)證并述說(shuō)了百年來(lái)中國(guó)的世事更迭、民族情感,反映了中西音樂(lè)文化交融發(fā)展的過(guò)程。當(dāng)前,沒(méi)有哪一種樂(lè)器像鋼琴一樣對(duì)中國(guó)人的音樂(lè)生活產(chǎn)生如此廣泛而深遠(yuǎn)的影響,鋼琴音樂(lè)已經(jīng)成為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此,在當(dāng)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我們應(yīng)繼承傳統(tǒng),努力推動(dòng)鋼琴音樂(lè)民族化,創(chuàng)作具有民族特色的音樂(lè)作品,將獨(dú)具特色的鋼琴藝術(shù)呈現(xiàn)給世界,用鋼琴演繹出動(dòng)人的東方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