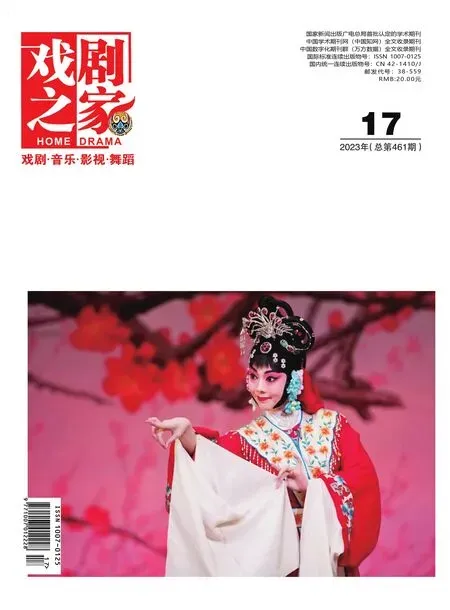李清照兩首古詩詞藝術歌曲的音樂分析及演唱技巧對比
——以《蝶戀花》和《聲聲慢》為例
馮笑倓
(黃河科技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3)
近年來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古詩詞藝術歌曲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中,受到了廣大群眾的青睞,同樣,古詩詞藝術歌曲作為古風音樂流派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對于聲樂藝術而言,古詩詞藝術歌曲有著獨特的藝術特征;在演唱技巧的使用中,相較于古典音樂、民族音樂等其他派系,古詩詞藝術歌曲又有著較為獨立的演唱技巧體系。換言之,即使同是古詩詞藝術歌曲,但因時代、作者、風格以及情感的不同,使用的歌唱技巧也存在著較大差異。
(4)建立與海事處聯動機制:臺風來臨前惠州海事局指揮中心要加強與相關海事處的聯動,加大電子巡航和現場巡航的能動作用,有效控制非本港船舶進港避風,特別是那些提前量很大的船舶堅決不允許進港,在臺風來臨前要求海巡船到現場巡航和驅離,嚴格控制本港避臺船舶的數量,以免由于避風船舶數量太多使錨地擁擠而造成更多船舶險情。
《蝶戀花》和《聲聲慢》是宋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兩支代表作品,它們經過后人改編而成兩首膾炙人口的藝術歌曲。研究同作者的不同作品,更容易發現作品中微小的細節,從而可以更加從容地應對不同風格的古詩詞藝術歌曲。如何更準確地把握這兩首歌曲的演唱方法?本文將從氣息、咬字、情感三個方面展開對比,詳細分析樂段、樂句中的重點細節處理方法。
一、《蝶戀花》和《聲聲慢》的創作特征
(一)古詩詞本體的創作背景
《蝶戀花》和《聲聲慢》是由宋代詞人李清照所創作的兩首宋詞,它們的完整曲名為《蝶戀花·上巳召親族》與《聲聲慢·尋尋覓覓》(以下簡稱《蝶戀花》《聲聲慢》)。眾所周知,李清照的創作風格屬于宋代的婉約派,其作品風格偏向于憂傷、暗淡,情感方面則十分細膩。本文所分析的兩首作品均蘊含著豐富的情感,風格上也較為相似。但正是因為這兩個作品風格相似而內容不同,演唱者在演唱時極容易犯下原則性的錯誤。所以,在演唱這樣風格類似的作品前,了解創作背景就變得尤為重要。
首先,李清照除了借《蝶戀花》表達對故國的懷念之外,還同親族說家常話,表現出親切之感,用清秀的方式表達失落之情,給人以深情但不泛濫的非常適中的情感體驗。其次,《聲聲慢》相比于《蝶戀花》則更加深情,這首作品雖然同屬于李清照的后期作品,但情感運用顯得更加精準和成熟。與此同時,作品表現了在經歷戰亂遷都之后,李清照對于國破家亡的憂傷,以及自己因喪夫、流浪所產生的內心孤獨。這首詞也是李清照作品中情感流露得最為濃烈的作品之一。所以,對于兩首在視聽中風格相近的作品,需要先從所展現的內容和情感方面進行區別,然后使用不同的演唱技巧進行詮釋。
(二)藝術歌曲的創作特征
(2)冷凝式鍋爐并非只是普通增設冷凝式換熱器就可以完成的,需通過系統設計,從整體上進行把關,綜合了燃料燃燒的控制力度、冷凝式換熱器防腐、煙氣分析、供熱模式轉化等多個技術領域。
另一方面,《聲聲慢》與《蝶戀花》在呼吸的節奏上存在差異。《聲聲慢》的旋律多為短時值且較為密集,所以需要保持好換氣的節奏,尤其在樂句中有短時值休止符的地方,不能夠偷換氣息。有些演唱者容易在休止之后找不到音高或歌唱的狀態,正是因為此前終止了演唱狀態。所以,在句中休止符后同樣需要尋找適度對抗的力量,以保證歌唱的狀態。
二、《蝶戀花》和《聲聲慢》的音樂分析
(一)《蝶戀花》音樂分析
一方面,《蝶戀花》與《聲聲慢》同為抒情藝術歌曲,故而演唱時需要使用一些相同的技巧。在氣息方面,《蝶戀花》是一首極為考驗單次呼吸后氣息保持的作品,作品的大部分旋律走向為由低向高,只有到了作品的尾聲才出現旋律的回落。尤其在B 樂段的高潮部分更是出現了長時值的高音樂句。對于演唱此類樂句或樂段時的氣息運用,很多演唱者存在一定的誤區,認為越是高音或越多長時值的樂段就越需要吸入大量的氣息,以備堅持到樂句結束。其實,在演唱之前過多儲存氣息并不利于演唱時的發揮,過量的氣息反而會成為演唱的負擔,帶來緊張、音準突高等失誤。正所謂“飽吹餓唱”,在演唱時,不論音的高低,均需要吸入適量的氣息,如果實際情況中音域過高或需要長時間保持高音,則需要腹部的支撐以及逐漸打開腔體來完成演唱。所以,演唱高音時更考驗綜合技巧的運用,而并非完全依賴于氣息。如作品的第13—16 小節,在這4 個小節中,作者共用了兩個漸強和一個減弱記號,演唱者需要在樂句開始時吸入適量氣息,在旋律逐漸向上的同時下沉肺部下方的橫膈膜,直至最高音處停止并保持橫膈膜的位置,利用橫膈膜對上升氣息的對抗保持高音的演唱,同時腔體也需要逐漸張開至最大,這樣才能保證高音的音準與音色。同理,這樣的方法適用于《聲聲慢》的高音演唱。
(二)《聲聲慢》音樂分析
藝術歌曲《聲聲慢》全曲共67 個小節。首先,在音樂結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原古曲采用了二段體的曲式結構,即A 樂段加B 樂段的形式,而徐沛東版本的《聲聲慢》則加入了再現樂段,對B 樂段進行了再現,可以說是對作品情感的延續,而再現前樂段并加入適當變化可以有效地增加作品的藝術性。其次,在調式方面,徐沛東對古曲原有的調式進行了優化,選擇了更適合女高音演唱的E 羽七聲清樂調式。眾所周知,民族調式中E 為羽音時,G 則為宮音。結合作品旋律可以看出,全曲最高音為小字二組的G,對于女高音來說,作品的音域并不算高,而正好可以將更多的精力用于抒情,當然,適中的音域同樣適合中音、次高選唱。再次,在作品的細節方面,A 樂段旋律中加入了大量的句中短時值休止,以此來表現詞作者“尋尋覓覓”過程中的忐忑,而B 樂段及再現段的旋律逐漸舒展開來,使作品的情感發展呈現出層次性的規律。
古詩詞藝術歌曲的咬字要難于聲樂演唱藝術中的其他類型作品,這是因為古詩詞屬于古代文學題材作品,它不同于只需母音清晰的意大利古典作品,也不同于需要使用方言的民族聲樂作品。古詩詞藝術歌曲咬字的難點在于需遵循古詩詞的韻律。眾所周知,《蝶戀花》與《聲聲慢》是宋詞的曲牌名,而每個曲牌均有著獨特的格律,而作者進行宋詞的創作時也需要按照原有曲牌的格律填詞。《蝶戀花》與《聲聲慢》分別為四仄韻和五仄韻,所以,聲調的清晰在古詩詞藝術歌曲中尤為重要,這需要演唱者在演唱作品前反復朗誦詩詞,然后逐漸加入旋律,最好采用以樂句為單位的校準方式。《聲聲慢》中有許多前后相同的聯合類成語歌詞,如“尋尋覓覓”“凄凄慘慘戚戚”等,在這些歌詞的咬字中很容易將后面的同字咬輕或狀態不一,而對于這類歌詞需要運用到唇部或舌部的力量對兩個相同的字保持同一咬字狀態。與此同時,在歸韻方面需要盡量將后字演唱,這樣就能營造出古色古韻的視聽效果。最后,相較于《聲聲慢》,《蝶戀花》中并沒有前后字相同的歌詞,全篇則多為抒情性的歌詞,在這首作品的咬字中,需要結合作品的旋律,做好長時值音符所對應字的歸韻。如《蝶戀花》第63—64 小節中“了得”中的“得”,因為“得”字聲調為二聲,即現代普通話中的“陽平”,而在古語中被稱為聲調中的“入聲”,在演唱時,很容易因時值較長在歸韻上出現聲調隨著氣息的流動而逐漸提高或不平穩的情況。所以,在對此類歌詞進行歸韻時,除了需要逐漸弱化以外,還需要逐漸收緊腔體,將“得”字中的“e”逐漸過渡到鼻腔,這樣就能保證咬字與歸韻的平穩,并穩當地保持到樂句結束。
三、演唱技巧對比
(一)氣息使用的共性與特性
古詩詞藝術歌曲《蝶戀花》全曲共54 小節,作品在13 小節處進行重復并在49—50 小節處結束第一段的尾聲,全曲的尾聲位于51—54 小節,屬于第一段尾聲的延續。在音樂結構方面,作品采用了有再現的二段體(A+B+A1)曲式結構。之所以選擇A 樂段而非情感更加濃厚的B 樂段進行再現,是因為作者有意為作品建立起完善的情感體系。仔細觀察樂譜可以發現,作者將作品開篇的演唱情感標記為“眷戀的”,而經過兩次“深情”后,在再現部分情感標記變為了“悔恨惋惜的”。情感標記的變化可以顯示創作者對李清照內心的解讀,如果僅僅為了藝術效果而選擇再現B 樂段,這顯然有悖于原作的情感。在調式方面,《蝶戀花》運用了E 羽七聲雅樂調式,眾所周知,雅樂中的變徵和變宮更能夠準確地抒發悲傷、悲壯的情感。最后,作品的節奏以四四拍子貫穿全曲,四四拍的強弱特點可以使情感、情緒得以延伸,從而更加有利于抒情;而旋律方面的創作則迎合了原詞的情感,情緒波動較大的地方會選擇用四度、五度的跳進來表現,音程跨度越大,音與音之間的空隙越大,在演唱中能夠發揮的空間就越多,如作品35 小節處,該處類似于平常做的間奏,演唱則是用“em”音進行抒情,而此處的情感標記為“飄渺回憶的”,樂句開始時的五度跳進以開門見山的方式給人以若有所思的感覺。
《蝶戀花》和《聲聲慢》兩首詞雖然均由李清照所作,但根據其改編而成的藝術歌曲卻由兩位不同的作曲家創作。
眾所周知,宋詞本身就含有音樂藝術的韻律,而其中的經典作品更有歷代音樂家爭相譜曲。《蝶戀花》和《聲聲慢》兩首宋詞也經歷了多個時代、多位音樂家的演繹,而本次要分析的作品正是當下流傳度較高的版本。其中,藝術歌曲《蝶戀花》由我國當代知名音樂人孫靜雯譜曲,屬于較為年輕的作品,但作品優美的旋律與豐富的藝術特征得到了聲樂藝術從業者的認可,近年來該作品被廣泛應用于國內外的各大聲樂賽事;藝術歌曲《聲聲慢》則由我國著名作曲家徐沛東作曲,該作品自問世之后便得到較大的反響,更被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演唱,作品流傳至今仍擁有著龐大的欣賞群體。從創作風格來看,這兩首歌曲均依照宋詞韻律的特點,在古曲的基礎上進行了結構、細節上的優化。如《聲聲慢》古曲最初記載于清朝的《碎金詞譜》之中,經過徐沛東的創作,作品由原來的D 羽七聲雅樂轉為了更加適合人聲演唱和符合當代人審美取向的E 羽七聲清樂,在結構、演唱速度與力度等方面徐沛東也根據原詞的內容、情感進行了相應調整。所以,在保證原汁原味古曲的基礎上,適當進行修改,賦予歌曲時代性,才能使“古詞新曲”成為典范之作。
(二)咬字吐字的方法與特點
由式(1)至式(16)可解得T1,T2,T3,T4,T5,T6,T7,T8,T9,T10,T11,T12和T14,并由此可得循環的量綱-功率
(三)情感運用的區別與細節
從創作特征的闡述中可以看出,《蝶戀花》與《聲聲慢》雖然同屬李清照的晚年作品,但作者在創作兩首作品時因為環境的不同也有著不同的情感。而這種不同則體現在程度、種類等多個方面。通常來講,很多演唱者在拿到這兩首作品時,因為李清照的作詞風格以及歌詞所表現的內容,會很自然地把這兩首作品歸為同類作品,但這會影響演唱效果。所以,演唱者在演唱這兩首作品前需要分析作品情感的細節,運用不同程度的情感詮釋作品。
第一步:川芎、黨參、黃芪、當歸各10克放進砂鍋,加入兩碗清水,放進一個生雞蛋,中火煮10分鐘。第二步:將剛剛煮熟的雞蛋剝皮后,再放進砂鍋內,加入三分之一塊阿膠(約10克),中火繼續煮5~10分鐘左右,然后喝藥湯,把雞蛋吃掉。吃法:一周服用兩次,睡前或清晨起床后服用,吸收效果更好。
首先,作品上的情感標記對于整首作品的情感發展以及演唱時情感的運用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如《蝶戀花》中,樂譜在每個重點的樂句上添加了情感標記,作品整體的情感標記為“悠遠、飄渺的”,而速度則為行板,所以,在演唱時雖然要營造出李清照作品特有的憂傷氛圍,但也需要對情感、情緒有所控制,使之保持在悠遠抒情的范圍內,不能出現過大的波動以及超出作品情感標記的濃烈情感。與此同時,在作品的第5、13、21、35、42 小節處均有不同的情感標記,在細節方面,35、42 小節處情感變化幅度較大,從“飄渺回憶的”轉變為“悔恨惋惜的”,所以,這幾個樂句要表現出情感變化的戲劇性,使情感變化更加突出。其次,《聲聲慢》中并沒有過多的情感標記,只是在作品開始將情感定義為哀婉、動情的。所以,在演唱《聲聲慢》時要比《蝶戀花》更加深情,細節方面則需要注意到作品的開始樂句,即“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此樂句為作品的開篇,同時也是這首詞的核心。演唱者需要在引子時就將情感醞釀到高潮,然后深情、絕望地唱出,從而給整曲營造出悲涼的氣氛。
四、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從宋朝詞人李清照的兩首古詩詞藝術歌曲《蝶戀花》和《聲聲慢》的創作特征出發,深入分析了作品的結構、曲調、情感等,并在演唱實踐的基礎上分析了兩首作品所需要使用的不同演唱技巧。古詩詞是我國文學、藝術史上的瑰寶,所以在演唱古詩詞藝術歌曲時不應該用共性思維去詮釋,而應該仔細分析作品、區別對待,才能將古詩詞中豐富的藝術性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