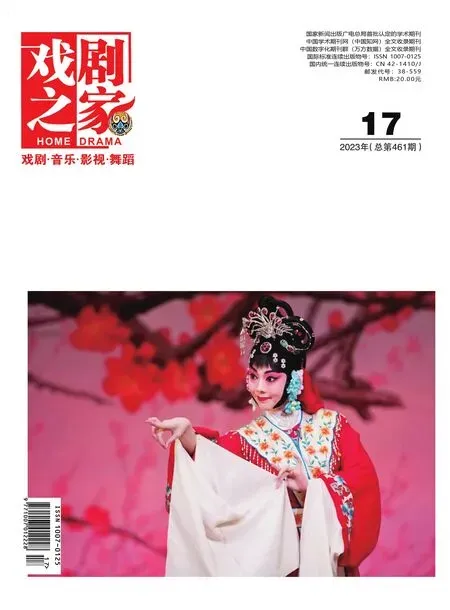新世紀我國神話題材動畫電影中的生態敘事
孫嘉謠
(吉林大學 文學院暨新聞與傳播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5)
神話起源于人類在認識世界之初作為有意識的認識主體對自然中未知事物的講述,這些講述形成了神話故事。在這一認識過程中,人類與自然的主體間性決定了神話故事中存在大量的生態敘事。如果說,神話與神話思維是文藝啟蒙的象征,那么,神話故事可以說是民族發展的縮影,其中的生態敘事則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民族寫照。在中華民族綿延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出現了許多具有中華民族整體性與共同性特點的中國神話故事,這些故事因蘊藏著獨特的生態文明中的中國智慧成了再現中國生態敘事的民族素材。生態文明是指人類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認識并遵循自然-人-社會復合生態系統運行的客觀規律建立起來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和諧協調的良性運行態勢以及和諧協調、持續全面發展的社會文明形態[1]。在生態文明的形成過程與神話故事的演進中,共存著作為基礎性前提的人與自然復合關系,也共有著作為決定性要素的人類主觀能動性,二者在產生的必然性、時空的廣泛性、內容的綜合性等方面形成了多種契合。當下,借助動畫電影的“造夢”力量所講述的神話故事重述了先民對萬物共生的美好愿望,成了當下人們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重要途徑,也成了生態文明智慧的最佳載體之一,以熒屏講述的中國神話故事也如文化基因一般為觀者帶來巨大共鳴。
可以用“故事世界”來形容以動畫影像為載體的神話故事的敘事狀態,這一概念是敘事學家戴維·赫爾曼提出的,并被美國學者伊琳·詹姆斯作為核心概念引入生態敘事學之中。“生態”在與敘事的結合中成為一種整體性的狀態,用以形容一種從內容到形式的新型閱讀習慣,而敘事又從敘事解讀的空間傾向與敘事理解中重建事件、狀態和行為的序列以及敘事的世界制造能力這三種方式闡釋生態,從而使讀者理解不同時空的人在其生態家園生活的狀況[2]。神話題材動畫電影帶領觀眾從現實世界進入神話的“故事世界”,使觀眾沉浸式地同神話人物一同加入敘事進程,在生態敘事學的情境中,觀眾最大限度地閉合了歸屬于自然母系統的本性身份與處于社會子系統的現實狀態之間的分裂,真正地轉向對生態環境的思索。
一、解構與重構:建立虛擬生態環境的敘事時空
電影中,時間與空間的組合決定了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動畫敘事時間的基本形態可分為故事時間、敘事時間和放映時間;與電影不同的是,動畫電影的敘事空間是制作者創造的虛擬空間,是故事中角色的存在空間[3]。以神話為題材的動畫電影表現出在故事時間上的主觀真實、敘事時間上的客觀順時與空間建構上的多維假定,這與生態文明智慧廣泛的跨時空特性不謀而合。因而,在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神話題材動畫電影能夠靈活地將時空進行組合,以建立虛擬的影像生態環境,并在敘事主體態度的轉變中不斷解構與重構,以提示當下的生態問題,其在敘事時空上呈現如下三點特性:
(一)同心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核心作用
原始人類在生產過程中從事著幼稚的思維活動,即將外界的生物或無生命物體都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由這種思維產生的首批傳說和故事叫作神話[4]。神話產生于人類與自然雙主體的互動中,這意味著,神話中的核心問題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問題。這種自然界生態的整體性在敘事時空中表現為多個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同一核心的虛擬生態環境的時空建構。第一類虛擬生態環境建構在神話故事內,被作為故事發生前提的生態環境背景,第二類虛擬生態環境建構在動畫電影的“故事世界”中。新時代的神話題材動畫電影在題材改編上的一個顯著特征便是將神話故事置于一個全新的時空,如《白蛇2:青蛇劫起》的故事發生地修羅城與現代時間線,背景時間的改變優化了神話故事的敘事,這意味著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核心的關系出現并適用于任何一個文明階段,并在當下的生態文明時代被充分重視。時間線的改變也使觀眾在進入神話“故事世界”時忽略傳統的以時序為主導的觀影習慣,轉而關注影像建構的時間。與時間的現實改編不同,空間的變化大多脫離現實走向異化,創作者大多選擇構建一個嶄新的空間,以滿足神話中異于客觀現實的準則。
(二)關聯性:天人合一思想的紐帶作用
神話故事與神話題材動畫電影都有極為廣泛的時空跨度,不同的時空構建出既有個性又有共性的虛擬生態環境,這也是鋪墊且推動電影中情節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探究神話題材動畫電影中敘事時空關聯性的文化之源,可以發現其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命題有密切關系。天人合一本身便強調一種互相關聯的生態整體觀,它強調人是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與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處于平等的位置,不能用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看待自然界,也不能用主客二分的角度認識自然。電影中以人和自然為不同主體構建的虛擬生態時空中時間和空間相互關聯,異化的影像時間由空間彌合,而異化的影像空間又由故事世界的時間線相連,將人與自然雙主體緊密聯系在一起,闡釋“天人合一”思想下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的協調、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一致[5]。《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關押哪吒的結界、山河社稷圖里的世界等都是把神話故事與電影融合創造出的虛擬生態時空,其用異化的神話時空線索與哪吒故事世界中的現實時空相關聯,產生了主人公哪吒人神雙重身份的特有故事軌跡,二者的組合營造出天與人合的時空敘事效果。
(三)對立性: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創新作用
《系辭》曰:“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也就是說,自然界有自己的發展規律,但人能在規律面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達到自己的目的[6]。神話題材動畫電影中呈對立狀態的虛擬生態時空是人在發揮主觀能動性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偏移,即以人與自然關系為核心的虛擬時空隨著敘事的進程發展出現人類中心主義或是生態中心主義的偏移,但其最終又回歸和諧的狀態。在《大魚海棠》中,人類生存的生態時空與神仙生存的生態時空因逆規律性而出現對立,神仙可以看作自然的人格化表現,人類男孩在救化身為紅色海豚的椿時為自然作了犧牲,人類失去了生命;反之,椿執意要送鯤回家時是人類利益大于自然利益,出現了神仙家園的天崩地裂、海水倒灌。這種對立性的影視化表現警示人類在作為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時進行創新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人類中心主義中的人類作為主體存在的客觀現實是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必然前提,完全脫離人類中心主義走向自然中心主義是漂浮的空中樓閣,因此,應該尊重人類的主體地位,更應該從人類主體出發尊重自然的主體地位,而非將人或自然單獨放置在中心位置。
二、整合與平衡:協調多層循環沖突的敘事模式
多層循環的敘事模式是被廣泛運用在影像敘事中的一種手法,《電影敘事學:理論與實例》一書將這種以多層敘述為動力的結構模式歸納總結為回環式套層結構,是指事件本身的進程在影片中退居次要地位,而對事件的不同“講述”則成為結構的重心[7]。對于神話題材的電影敘事來說,觀眾是帶著對故事本身的知識甚至理解進行觀影的,而這種知識背景會給觀眾帶來對這個題材更高的期盼。由此,神話題材動畫電影大多選擇在創作中將原本屬于神話故事中心的矛盾轉移到多層次、多角度、多回環的敘述上去,以整合多個影像本體的沖突,平衡題材與表現之間的核心沖突,協調成為一種多層循環沖突的敘事模式。生態文明的本質特征是人自身的心態和諧、人與社會的關系和諧、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以其為背景,從沖突的主體出發也可將神話題材動畫電影的敘事模式分成多層次的三種類型。
(一)從困擾到突破的循環:人與自我的沖突
自我沖突是制造情節的源動力。熱奈特的理論將故事內外劃分為三個向度,即故事外敘述層次、故事內敘述層次和元故事人物敘述層次[8],自我沖突能夠帶領觀眾從“故事外”進入“故事內”,并在內外視角切換中實現主體的擴延,從社會中的人擴延為范圍更廣的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命主體,進而認識到人在自然中所處的能動性位置,將自己放置在更廣闊的生態中進行認識。觀眾與主人公一同打破內心的自我認識壁壘走向個人的突破,這種困擾與突破又在每一個環節中循環,使觀眾在共鳴中思考現實自我與所處環境的關系,并在電影中因主題走向對人與自然的生態環境進行思考。在電影《姜子牙》中,天尊與狐族之間的生死恩怨被設定為驅使狐妖為禍人間的原因,這可以看作狐類中心視角下的一種生態破壞,也是姜子牙一直以來找尋的真相。
(二)從獨立到融合的循環:人與他人的沖突
將神話中先民在無意識狀態下產生的生態思想雛形與當下系統性、科學性的生態文明進行對比可以發現,社會作為一個主體早已進入生態關系的討論范疇。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便倡導人性與天道之間的貫通,人的概念包含天人關系或人倫關系的內涵[9]。在幾千年的思想演化下,多重的人倫關系又構成了人類的社會系統,形成了生態文明建設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緊密的內在聯系。人與他人之間的沖突來自人的差異性,差異性又來源于多樣性。不論在自然生態中還是在社會發展中,多樣性都是一種智慧,多樣性的物種穩定了自然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文化豐富了人類社會。電影中,因角色之間存在差異而引發沖突是神話題材動畫電影中多樣性的顯著表現形式之一,并且,大多呈現出從獨立到與他人融合的循環敘事模式。《大圣歸來》中孫悟空在面對小和尚江流兒的時候呈現了從厭煩到并肩作戰的過程;《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與村民之間的沖突更是劇情發展的原始推動力。
(三)從阻礙到歸屬的循環:人與自然的沖突
人與自然的沖突是神話動畫電影中的核心沖突。在人類走過了工業文明的灰色時期到意識到綠水青山的重要性后,人類才意識到協調人與自然沖突的必要與緊迫,中國古代是農業大國,中國人在農耕文明中保存下許多可貴的生態智慧,神話題材動畫電影正是當下表現生態智慧與再現人與自然沖突的最佳載體之一。中國神話故事的起源總是以強烈的人與自然沖突開始,例如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其中包含著大量先民征服自然的欲望,又都以回歸自然為終。隨著生態智慧在敘事進程中的作用,神話故事在敘事模式上呈現出從人與自然相互阻礙到人最終歸屬于自然的平衡狀態。無論是先民創造的神話還是電影的劇本改編都遵循了這一沖突模式,這來源于中國生態智慧傳承與影響下的民族共識。從影像表達的角度看,以動畫電影為表現方式的神話故事在改編后加入大量的現代元素,如高樓林立的修羅城、擁有現代機車的再世哪吒等。這些元素以藝術化手段表現生態文明建設中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狀態。可以說,人與自然的沖突在神話題材動畫電影中作為核心沖突成為中國自古以來人與自然關系的縮影,并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從阻礙到歸屬的敘事模式,這不僅是一種對既往的重述,也是一種規律的顯現,模式之下是人與自然之間必然要遵守的生態規律。作為藝術作品的神話題材動畫電影能夠引領觀眾來到以生態文明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故事世界,在審美中主動自覺地汲取神話故事中的生態文明與中國智慧,在古今的交融中完成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度思考。
三、共生與互助:內隱傳統生態智慧的敘事主題
當先民開始編織神話或發明“圖畫文字”來描述事件、傳遞信息時,就已經表明了敘事活動的誕生[10]。時間來到現在,現代科技締造的動畫電影與作為文化濫觴的神話結合,呈現出燦爛的文化景觀,其中,作為重要部分的敘事主題在文化融合中不斷生發。在以神話為背景、生態敘事為視角的故事講述中,作為主體的人與自然表現為共生與互助的狀態,這種狀態來源于神話題材中內隱的生態文明智慧,可將其與電影創作進行結合提煉出如下敘事主題。
(一)遵道——順應自然的發展規律
電影《大魚海棠》講述了《莊子·逍遙游》中“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的故事。故事中的神仙小女孩椿為報人類男孩救命之恩,用自己一半的壽命換了新輪回中還是一條魚的人類男孩,他的名字為“鯤”。這種情節在客觀自然界中不會出現,但神話最終會回到人身上,其作用是強調人的精神狀態,即道家思想中強調的“道”。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說:道以自然為歸,道的本性就是自然[11]。這里提到的“遵道”便可理解為“遵守自然的規律”,即人要遵守自然界之中的規律,還要遵循天性的原則,最終走向精神與萬物的協調融合。遵道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表現為人類子系統與人類社會子系統的發展必須遵循地球生態母系統運行的規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應順應三者的規律,不可越界逆規。在《白蛇2:青蛇劫起》中,有深深執念的人會來到修羅城經歷風、水、火、氣等劫數,劇中將自然之劫物化為會飛的惡鬼,被其撕咬的人會失去生命。其中的執念是逆規律的一種象征,劫起則是自然的一種懲罰,告誡人類要遵守各系統的規律,否則必然要受到自然之母的懲罰。
(二)生長——匯于同一的和合文化
人類自身、人類社會與自然三者的協作發展是和合文化出現的現代因素之一,也是和合文化所倡導的生態文明的重要走向,在神話題材動畫電影中主要表現在敘事主題上的多元素、要素沖突且融合與敘事主題影視化表達上的新方式上,二者共同成為“生長”的生態審美智慧[12]。“生長”在字面意義上指的是生物鏈中的生物是相互依存的,這也符合劇中神話人物的成長狀態,情節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前一個情節的結果常常成為后一個情節的源頭,情節中人物的心理也有著生物鏈一樣的緊密聯系,這種生物鏈式的敘事方式表現了人類與自然世界的同一屬性,即人類作為自然中一員的心理認同感。人類生存于自然界之中,人類又與自然界中的成員們存在緊密的聯系,人類的生長依賴于自然界鏈條中的每一環,人類不能將自己獨立于自然界之外。
(三)尋根——作為動力的家園意識
“尋根”在本文的含義取自文學中的“尋根文化”一言中的含義,用來描述創作者把眼光投向自然,把自然看作一種被人賦予意義的文化現象,使人與自然在交感中獲得新的生命意義[13]。中國文化非常重視以“家”為單位的概念,以人類為主體出發,“家”的概念指的便是自然家園。在本文中,“尋根”被定義為人類回歸自然家園的過程,包含身體上的融入與心靈上的融合。曾繁仁教授曾指出,“家園意識”在淺層次上有維護人類生存家園、保護環境之意;從深層次上看,其意味著人的本真存在的回歸與解放[14]。“尋根”主題也可以從兩種層次分析,從淺層上看,表現為神話故事中主人公尋找并渴望歸“家”的狀態,在這里,“家”是一種狹義上的家庭或家人,例如小青對姐姐小白的尋找;從深層上看,每個神話故事都存在一個目的地,它是神話故事世界中人物的一種心理狀態,主人公在淺層尋根的現實過程中到達這種深層的心理狀態。由于神的形象產生于人對自然以及自然力的人格化描述中,也可以說,神話人物是自然人格化的形象,故觀眾在被帶入主人公的故事世界后會進入這種具有深層家園意識的心理狀態,這可以提醒觀眾走向以自然為家園的簡單、本真的棲身狀態,找尋一片屬于自己的澄澈的心靈歸屬。
事實上,電影敘事是一個在傳統力量、作者個性、觀眾期待視野以及時代社會影響合力作用下形成的綜合體[15]。神話題材動畫電影的敘事因具有故事本身的綜合體屬性與影像表達的敘事屬性,成為許多文化的理論闡釋載體,生態文明智慧便是其中一員,而以生態文明智慧孕育的神話題材動畫電影將不斷書寫蘊含神話精神與生態文明的中國文化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