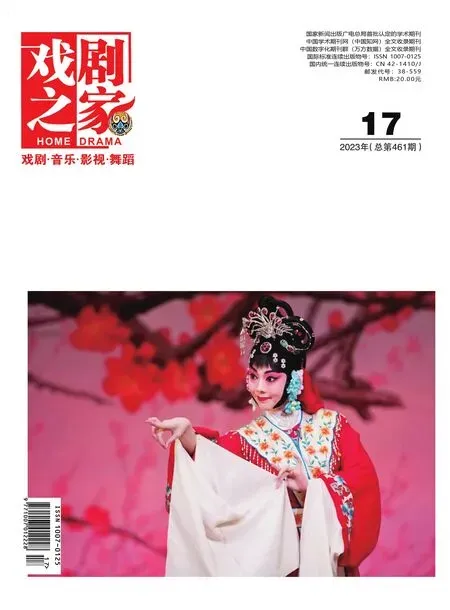韓國影視劇中惡女形象的文化審視
張欣怡
(山西藝術(shù)職業(yè)學(xué)院 山西 太原 030000)
韓國影視劇作品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受到社會思潮的更迭、文化觀念的變革以及女性意識覺醒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韓國影視劇中出現(xiàn)了許多極具“魅力”的女性形象,此類形象與東亞文化中傳統(tǒng)的道德規(guī)范大相徑庭,人們將其稱為“惡女”。在過去的影視劇中,“惡女”常以反派角色出現(xiàn),以“惡女”之“惡”反襯女主人公“真、善、美”。但近年來出現(xiàn)了一系列以“惡女”為敘事核心的韓國影視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或沉溺于個體欲望,或為保護自我走上復(fù)仇之路。這類女性不同于絕對意義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但從這類非常態(tài)的女性形象身上我們更能夠看到女性身上復(fù)雜多樣的欲望與生存動機,這類形象將被固化了的女性還原為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從古至今,“惡女”一詞的詞義發(fā)生了流變,《史記·外戚世家》中“惡女之仇”中的“惡女”指容貌丑陋之女。根據(jù)“惡女研究所”網(wǎng)站調(diào)研,當(dāng)今社會將“惡女”一詞的定義變更為:極富個人魅力,懂得運用一切條件滿足個體欲望,達成自我目標(biāo)的女性。本文研究對象是指,在現(xiàn)代文化語境下,因主客觀雙重原因所造就的性格、心理以及行為具有反叛性、極端性和異化傾向的多元化女性形象的綜合體。[1]在文本上選擇“個性鮮明,借助一切力量達到個人目標(biāo)”的女性形象。
一、個體欲望的內(nèi)在驅(qū)使
黑格爾認為,當(dāng)理性與道德對峙,權(quán)利與想象沖突,必將導(dǎo)致人類思考邏輯產(chǎn)生混亂。如果人類思維中“欲望”占據(jù)主導(dǎo),其結(jié)果必然是道德的錯位。韓國大量影視劇聚焦于社會階層的對立,“惡女”對金錢、地位的追求成為人物敘事的主要動機。此類“惡女”形象具象化表現(xiàn)了貧富社會階層的差異,并將人物走向毀滅的原因歸結(jié)于對金錢與權(quán)力一類的“人類欲望”的追求。
韓國電影《寄生蟲》在第92 屆奧斯卡電影節(jié)上大放異彩,影片架構(gòu)在社會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用符號化的人物構(gòu)建出二元對立的階級表征。為了使整個家庭獲得進入富人家庭工作的機會,妹妹金基婷發(fā)揮著主導(dǎo)作用。從影片的主線故事開始,她就為哥哥成為家庭教師做假證,手法熟練,從容不迫;到應(yīng)聘藝術(shù)治療教師,通過網(wǎng)絡(luò)自編一套心理治療方法,成功騙取女主人的信任;假借“內(nèi)衣事件”使司機深陷信任危機,又捏造高級家庭服務(wù)公司幫助父親成為雇主家的新司機;再設(shè)計趕走女管家,讓母親獲得工作機會。妹妹是整個家庭成員寄生在雇主一家的策劃者,她空有藝術(shù)天賦卻無法深造,她雖然“手段低劣”,卻使整個家庭獲得了體面的工作。雇主一家出游后,她自然、優(yōu)雅、愜意地享受富豪家庭的一切,當(dāng)父親表達出愧疚和不安時,妹妹卻提醒大家“我們才是最值得可憐的人。”妹妹的心智、思想有著遠超年齡的成熟,她手段狠辣,相較于哥哥沉溺在與富家女戀愛的幻想中,妹妹更能夠直擊現(xiàn)實本質(zhì)。憑借妹妹的謀劃,一家人擁有了寄生的宿主,但“地下室事件”爆發(fā)后,失去妻子的吳勤勢意外殺死妹妹,使得寄生關(guān)系徹底破裂,一家人也走向分崩離析,階級的對立、個人的欲望最終導(dǎo)致了妹妹這一角色的死亡。
2022 年熱播的韓國電視劇《安娜》同樣塑造了一位美麗、聰慧、內(nèi)心虛榮的女性形象。由美是個普通人家的孩子,但她優(yōu)秀又渴望成為中心,求學(xué)階段的短暫失利讓她來到富人家庭給富人的女兒安娜做女傭。不愿屈居人下的由美偷走了女雇主的身份、學(xué)歷、名字后,成為耶魯回國的藝術(shù)高才生——安娜,進入大學(xué)教課,成為市長夫人。憑借一個又一個謊言,安娜步入上流階層。她足夠聰慧,高中學(xué)歷卻能夠講授大學(xué)課程;她同樣善良,丈夫殺死真安娜,她痛苦且愧疚,但觀眾無法評價其為一個“好人”,她有欲望也有野心,本質(zhì)上貪圖享受,不滿底層生活,步步為營進入上流社會。相比于很多華麗的如同假人的韓劇女主,由美身上善與惡共存、卑微與自負同在,更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無論是電影《寄生蟲》塑造的妹妹還是電視劇《安娜》塑造的由美,她們所呈現(xiàn)的“惡”都表現(xiàn)了社會階級間的貧富矛盾和不甘屈居人下的個體欲望。人物所呈現(xiàn)的“道德錯位”是個人描述角色自己和他人行為的名稱,觀眾也能借此反思人性的貪婪。[2]哲學(xué)家康德認為:在人的本性中存在一種向善的原初稟賦。[3]兩位女性角色都經(jīng)歷殺戮,《寄生蟲》中的妹妹被殺,《安娜》的由美殺死丈夫,這都是貧富撕裂后的人性表現(xiàn),成為人物關(guān)于反抗的瘋狂抉擇。人物在善與惡的搖擺中構(gòu)建出豐滿的個人形象,整個影視劇的審美內(nèi)涵、社會意義得以深化。
二、復(fù)仇之路的非我表達
復(fù)仇主題是古今中外文人墨客一直癡迷的創(chuàng)作母題,而“恨”文化卻是根植于韓國文化深處的文化傷疤。個體思想源于時代文化,而時代文化源于社會歷史。近代韓國社會先遭遇外國侵略,再經(jīng)歷戰(zhàn)爭,殘酷的政治環(huán)境下,財閥壟斷式地控制著國內(nèi)經(jīng)濟,不斷積累的社會矛盾持續(xù)壓迫著民眾的神經(jīng),形成韓國電影中獨特的壓抑、失序、破碎的“恨”文化。由“恨”文化衍生而來的就是復(fù)仇母題的不斷選用和創(chuàng)作。作為社會文化的表征形式,電影不可避免地會觸及時代的鏡像,觸及時代環(huán)境下人的迷茫與錯亂。[4]樸贊郁作為作者電影的踐行者,其鏡頭中暴力與恐怖美學(xué)交織,他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與波德萊爾筆下的“惡之花”異曲同工。樸氏電影風(fēng)格通過《我要復(fù)仇》《老男孩》《親切的金子》“復(fù)仇三部曲”得到了系列化、具象化的表現(xiàn)。與前兩部不同,在終結(jié)篇《親切的金子》中,復(fù)仇的行為主體變成了女性——金子。在傳統(tǒng)觀念中,男性的復(fù)仇行為被道德和輿論默許,在武俠小說的快意恩仇里,能夠成功復(fù)仇是男性完成家族使命、表現(xiàn)英雄氣概的行為。而女性則不同,普遍意義上女性與孩子被視為弱者,當(dāng)女性不得不奮起反抗、投身復(fù)仇的時候,人物形象就變得更有戲劇張力。金子就是這樣的女性,她是善與惡的共同體,是脆弱與殘忍相互滲透的整體。她被稱為“親切的金子”,在獄中她無私照顧他人,甚至捐出自己的腎臟;但她同樣是惡魔,忍辱蟄伏十三年只為手刃仇人,展開血腥的復(fù)仇,與眾受害者審判、處決白老師后將他的血做成蛋糕分而食之。金子的形象是如此的古怪妖冶,她表情冰冷,化著紅色的眼影,時常露出神經(jīng)質(zhì)的笑,冷傲的紅色高跟鞋帶著極致的誘惑,傳遞出曖昧的感覺。她不屬于傳統(tǒng)女性,她是慈母,與女兒在一起時的她充滿著母性的光輝;她也是蕩婦,她戲弄面包店的小工,索取男人的愛。金子的形象就像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一樣充滿魅力又陰鷙可怖。最終金子回歸了自我,她擦去紅色的眼影,站在雪里與女兒依偎,說“我要雪白地活著。”樸贊郁的復(fù)仇三部曲的終結(jié)篇表現(xiàn)了復(fù)仇的終極意義——復(fù)仇不指向殺戮而是救贖。
自《親切的金子》后,樸氏電影中的復(fù)仇不僅指向痛苦與絕望的仇恨情結(jié),更多指向自我救贖。電影《小姐》同樣塑造了在天使與魔鬼中游走的惡女形象。其以陰郁的畫風(fēng)將小姐受到的性與精神的虐待以冷峻的視角展示出來,豐富的長鏡頭語言為觀眾刻畫了小姐秀子與女仆淑姬兩個女性精彩的復(fù)仇故事。小姐秀子父母雙亡,巨額遺產(chǎn)被姨夫侵占,姨夫每日訓(xùn)練秀子為上流人士閱讀黃色小說,對秀子進行徹底的物化與剝奪。秀子飽受暴力威脅,在凌辱虐待下成長,在臥室中,小姐常常懷抱著洋娃娃思念母親。在第一段女仆的敘事中,小姐似乎是不諳世事的孩子,但事實并非如此。反觀女仆淑姬,她出身小偷世家,由于偷盜手段高超被選在小姐身邊,以侵占小姐財產(chǎn)。兩位女性帶著各自的陰謀接近彼此,妄圖自救,直到兩人相互產(chǎn)生愛慕,她們才開始聯(lián)手展開對男性的復(fù)仇。她們并非傳統(tǒng)電影的中“圣女”角色,而是帶著陰狠、違反道德的污點出現(xiàn),但又真誠可愛。女仆打碎姨夫書房中的蛇頭,帶著小姐逃離囚禁她的牢籠,人物身上的“惡”的一面更好地反襯了女性形象中人性的光輝,成為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表征,影片最后,囚禁她們的男性角色自相殘殺,而小姐與女仆獲得自由與尊嚴(yán),完成復(fù)仇。《小姐》作為一部女性主義電影,塑造了在男權(quán)社會中承受重壓的兩位女性角色,她們有著自身的善良與邪惡,天真與狠辣。她們通過復(fù)仇完成女性對身份認同、實現(xiàn)欲望和自由的渴望。相較于單純的復(fù)仇之后的自我心理救贖,秀子與淑姬“惡女”復(fù)仇更是從“他者”到“主體”的女性自我身份的確認。
電視劇《夏娃》也同樣塑造了一位為復(fù)仇而生的女性形象李艾羅,父母被殺的仇恨成為她所有行動的內(nèi)在動力,她以引誘、破壞他人家庭的方式接近復(fù)仇目標(biāo),復(fù)仇的過程帶著欺騙與計謀。艾羅看似狠絕,但又有不徹底性,她總是被自己親手殺人的噩夢驚醒,會擔(dān)心仇人的處境,其本性的善良柔弱和行為的殘忍形成了戲劇張力。
《親切的金子》《小姐》《夏娃》這類影視劇中的“惡女”形象在“善”與“惡”間游走,在善與惡的兩極融合、滲透中成為一個飽滿而豐富的整體。“惡”由仇恨所滋生,“恨”掩蓋了她們本性的善良,在善與惡的對壘中凸顯人性的復(fù)雜。
三、“惡女”形象的文化審視
影視作品的意義在于它是審美的、藝術(shù)的。“惡女”形象的美學(xué)意義不僅在于其表現(xiàn)了特殊的審美形態(tài),更表現(xiàn)了對社會文化的映照,對人性的深刻詮釋以及文化觀念的影響。
“惡女”形象有著民族集體記憶的印記,民族命運的脈絡(luò)被嵌入人物命運的發(fā)展走向中。朝鮮半島長期的附屬國地位以及近代以來受到日美殖民的歷史成為烙印在大韓民族集體記憶中的傷痛,大量韓國影視劇對這一歷史有所影射。《小姐》故事的背景就是日本殖民朝鮮時期,姨夫本是朝鮮人,娶了日本妻子后堅持說日語、穿和服游走在上流社會。《安娜》中教會假安娜謊言和欺騙的是美據(jù)時期大兵的妻子。經(jīng)歷殖民、戰(zhàn)爭的韓國一度是世界上GDP 總量最低的國家之一,但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發(fā)展,韓國創(chuàng)造了奇跡,成為發(fā)達國家,躋身亞洲四小龍。“惡女”命運走向與韓國國家發(fā)展相吻合,經(jīng)歷了低谷——爆發(fā)的過程。《親切的金子》中出獄歸來的金子、《夏娃》中蟄伏十三年的艾羅、《安娜》中四處打工的假安娜、《小姐》中一直隱忍的秀子小姐,這些“惡女”的命運與民族歷史構(gòu)成了想象性同步。
韓國影視劇中呈現(xiàn)的“惡女”形象表現(xiàn)了導(dǎo)演對個體精神屬性的關(guān)注。從超現(xiàn)實主義的《一條安達魯狗》到法國新浪潮電影《廣島之戀》,這些電影不斷關(guān)注人的生存狀態(tài)與存在本質(zhì),對人的關(guān)注也逐漸從電影轉(zhuǎn)移到電視劇中。惡女形象的出現(xiàn)對人性的復(fù)雜性、多面性有了更多展示。絕對對立的善惡兩極在真實的人的身上會變得混沌不明。在《親切的金子》中,金子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暴力與謊言讓她鋃鐺入獄,當(dāng)她歸來后又以同樣血腥的方式對待曾經(jīng)的施暴者。《安娜》中的假安娜貪慕虛榮、不擇手段,步步為營企圖躋身上流社會,她同樣善良,丈夫殺死真安娜,她痛苦且愧疚。在為人物進行的善與惡的敘事鋪墊中,人物的反差所帶來的戲劇張力更能夠帶給觀眾真實的情緒體驗,這也是“惡女”形象頻繁出現(xiàn)在影視劇中的原因之一。善與惡會雜糅形成人物屬性,這樣的人物塑造更帶有東方哲學(xué)的中庸色彩。超越了二元對立的個體形象更能讓觀眾體會到角色的真實與豐滿。
“惡女”形象的出現(xiàn)也受到文化思潮的影響。韓國男權(quán)社會傳統(tǒng)影響深遠,早期韓國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分為“家庭中的母親”和“滿足欲望的邪惡女人”兩類。但隨著女性主義、性別平等運動的發(fā)展,韓國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變得豐富多樣,女性形象不再是男性角色的附庸,成為影視劇中獨立的、主體性的敘事存在。對女性的審美也變得豐富多樣,韓國影視劇觀眾開始能夠欣賞作為叛逆者、反抗者的“惡女形象”。
四、結(jié)語
“惡女”形象所呈現(xiàn)的反叛與異化,是對女性形象的別樣審美觀照。通過“惡女”形象,人們能感受到人性的復(fù)雜與深刻。在善與惡的交融中,戲劇性的張力與沖突得以凸顯,悲劇性的審美體驗與藝術(shù)表現(xiàn)激蕩人心。“惡女”的形象以獨特的美學(xué)魅力帶給人震撼心靈的體驗,給予人深層次的審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