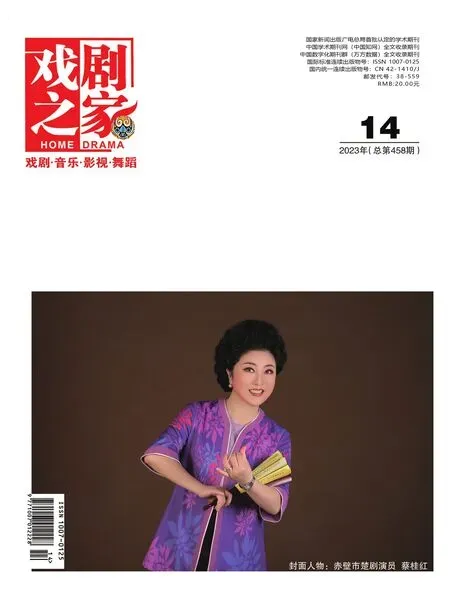再現莫高:淺析敦煌的影視化傳播
竇佳琪,王 睿
(1.內蒙古科技大學包頭師范學院 內蒙古 包頭 014030;2.吉林大學 吉林長春 130012)
一、莫高之源:敦煌莫高窟的開發價值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這里南接青海,西連新疆,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后,作為西陲重鎮的敦煌成了溝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沿線的商業中心,以及各種民族文化交匯的場域。敦煌莫高窟的開鑿上至十六國下至元代,延續了大概一千年,是中國石窟藝術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在世界文化遺產中也具有崇高地位。
1899 年,敦煌千佛洞石室內發現了一批唐代、五代的珍藏書卷,其中,說唱文學故事的底本被稱為“變文”。這一時期的敦煌變文大體分為兩類,一類講述佛經故事、宣揚佛教教義;另一類講述歷史傳說或者民間故事。其中記錄的廣為人知的人物有孟姜女、秋胡妻、伍子胥、董永等。與史書記載不同,脫胎于民間傳說的敦煌變文中記錄的人物更加鮮活,展現了不同視角下人物的多面性。
敦煌壁畫所采用的“石粉彩繪技藝”是甘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它作為最古老的畫種早在漢晉時期就已經遍布敦煌以及周邊地區。石粉彩繪以含有各種礦物質的礦石和礦土作為主要原料,通過粉碎、過濾、晾曬后制成顏料進行創作。這些礦石顏料本身結構較為穩定,不易變色,又因為石窟窟壁土層不平整,創作的過程中要在礫巖崖壁上刷好幾層不同的泥層才能作畫。這些都是古代畫工畫匠的寶貴經驗和有益創新,也是敦煌壁畫經歷這么多年很少脫落的原因。
莫高窟的文獻和絹畫不僅是研究當時日常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參考,也為我國歷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文物證明。《國家寶藏第三季》中有一件名為《歸義軍衙府酒破歷》的敦煌文物,它應該是當年歸義軍衙府宴設司在各種公務接待場合的用酒臺賬。它的一面記錄著各種民俗場合所需要的公務用酒,另一面還記錄著《金剛經注疏》。經過專家的解讀,確認了《金剛經注疏》的年代應為晚唐時期,把這件文物的年代往前推了將近一百年,這也是我國文物研究的重大發現。
敦煌莫高窟是中華文明的絢麗瑰寶,具有非常高的文化開發價值。
二、莫高之遇:敦煌文化影視化傳播的機遇與挑戰
敦煌文化保護和傳播的道路上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敦煌文化具有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受自然環境等諸多因素影響,現階段的傳播開發并不充分。傳播的意義不僅在于讓人知道敦煌和認識敦煌,更要讓人們喜歡敦煌、愛上敦煌,能夠為延續敦煌文明、堅守莫高窟儲備人才;另一方面,在傳播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保護和開發之間的關系?在現代流行時尚的裹挾下,敦煌文化的開發如何堅守自身?這些都是我們亟待思考的問題。
(一)保護與傳播的矛盾
受敦煌的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影響,莫高窟正在以一種緩慢的速度逐漸消失。文物保護專家、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李最雄說:“除了雨水等自然因素之外,人類活動的增多正在越來越嚴重地影響著莫高窟的洞窟環境。”可是,無論是游客進入莫高窟洞窟參觀還是以數字媒介的形式將敦煌素材記錄、加工、傳播,這些都與人類活動分不開。“保護、研究、弘揚”是敦煌研究院的六字方針。保護是物質方面的延續和雋永,弘揚是精神方面的復活和再現,保護和弘揚同樣重要。如何在傳承的過程中兼顧保護和弘揚,如何利用科學技術的手段解決人類活動給石窟壁畫帶來的損傷,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二)堅持文化自信,敦煌有廣闊深厚的資源等待開發
敦煌莫高窟的建造持續了近一千年,擁有非常深厚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九色鹿》根據敦煌壁畫《鹿王本生圖》的故事進行改編,是由中國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1981 年出品的動畫電影。該片采用敦煌壁畫的形式,用中國古代佛教繪畫的風格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九色鹿經常幫助遇到困難的人,在幫助弄蛇人后,弄蛇人向國王告密,出賣九色鹿,九色鹿用神力化險,弄蛇人最終得到報應。《九色鹿》的創作團隊到敦煌實地考察,在敦煌的千佛洞待了將近一個月,完成了動畫片中所有的場景設計。當時的條件艱苦,劇組的創作人員靠著手繪將九色鹿的形象真實生動地送到觀眾面前。《九色鹿》雖只有24 分鐘,但工作人員為此創作設計了200 余幅場景。電影一經推出就獲得了國內國際很多獎項,將九色鹿的形象作為敦煌名片推到國內外觀眾的面前。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遠沒有現在發達,但是我們能依靠豐富且深厚的莫高窟文化資源取得顯著的文化輸出成就,這和我們的文化自信是密不可分的。主創團隊相信來自莫高窟的形象能夠感染觀眾,就是充分相信莫高窟的文化資源能夠感染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這種文化自信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三)不被裹挾,堅守本心
進入新媒體時代,網絡的普遍應用給社會帶來了實時性、流動性、非線性、碎片化等后現代特征,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熱衷追逐流量和熱點都為文化的傳播和弘揚帶來了挑戰。中國的IP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迅猛,產品內容涵蓋了各個細分的文化產業領域,形成了完整的IP 產業鏈條,產業的發展也逐漸受到資本和媒體的關注。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恰恰就是文化IP 產業的最大資源庫。
近年來,故宮憑借文創開發、紀錄片、綜藝節目、跨界合作和各種展覽在互聯網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一躍成為中國的頂級IP,但顯然與其同為世界遺產的敦煌莫高窟在這方面的步調更加緩慢謹慎。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是原敦煌研究院院長,他曾表示,莫高窟的價值和故宮的價值不一樣,故宮的成功不能復制到敦煌來。在接受采訪時,原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先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故宮與敦煌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事關皇家世俗生活,與普通民眾有較近的心理距離,而敦煌以佛教文化為主,因此,在開發利用時還需重視對宗教的尊重與敬畏。他還講到在一次研討會上的經歷:“有一次我在北京參加敦煌服飾研討會,看到有的服裝設計圖采用了敦煌元素,把菩薩像畫在了裙子上。專家看到后就批評說,菩薩是信徒頂禮膜拜的,不可以穿在身上,用一些敦煌的裝飾圖案來設計沒有問題,但使用佛像菩薩像要考慮到宗教信仰,尊重文化傳統。”由此可見,文化符號IP 化進程并不是將文物和圖樣簡單地轉移和復制,而要處理好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關系,尊重文化的原本內涵。
現在,觀眾對于承載歷史名片的作品產出要求越來越嚴格,電視劇《夢華錄》脫胎于元朝關漢卿的雜劇,但現代流行元素的生硬融入和傳統偶像劇套路以及對于原著的魔改使得它的評價喜憂參半。這證明觀眾已經不再接受盲目追求社會熱點實則改變精神內核的作品嫁接。敦煌元素如何乘時代之東風,保住文化自身的根源同時又能夠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呢?綜藝《登場了!敦煌》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莫高之探:根據《登場了!敦煌》探索莫高窟影視化傳播新可能
《登場了!敦煌》是2020年上線的由愛奇藝出品,敦煌研究院指導的聚焦敦煌的原創全景式人文探索節目。節目結合紀實與真人秀拍攝手段,通過音樂、美食、色彩、飛天、匠心、運動、潮流、風俗、英雄、文書這十個維度,全面探索并致敬敦煌。為了更好地保護壁畫和文物,節目組嚴格遵守文物保護相關規定,嚴格控制進窟人數,并且燈光與攝像設備不進入洞窟拍攝,節目中所有的洞窟內影像均為復制窟內拍攝或數字掃描資料。無論是嚴格控制進窟人數還是創新拍攝手法,節目組的良苦用心都可見一斑。除此之外,節目中紀錄片式的呈現手法、多樣化的敘事手法以及注意線上線下超強的聯動性都致力于讓觀眾沉浸式地感受敦煌本身的模樣。
(一)紀錄片式的呈現手法
紀錄片的演繹形式主要強調節目中節目制作者對真實的人物事件與場景的記錄與呈現,也包括對已有的歷史影像資料的采集與還原。紀錄片式紀實的表達方式和真實的敘事手段是《登場了!敦煌》節目中始終貫穿的獨特呈現方式。每期節目的開頭會有一段敘述性強,氣勢磅礴的旁白來為整期的節目揭露主題、奠定基調,輔以紀錄片式的拍攝鏡頭,在理性和客觀的基礎上添加符合敦煌氣質的藝術色彩,使得開頭顯得蕩氣回腸。比如第一期節目中說道:“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上溯萬年,是中原王朝的戰略要塞,也是商貿交融的必經重鎮,鳴沙山東麓,洞窟里藏著絢麗盛大的理想凈土,千年的生活畫卷,石窟里的博物館,吸引著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遠道跋涉而來。”這個時候呈現的畫面是敦煌整體風貌的俯拍和具有代表性景點的航拍鏡頭,以及關于莫高窟壁畫的特寫鏡頭和當年絲綢之路上商旅茶客場景的復刻。這樣的鏡頭語言不僅再現了當時的歷史情境,也使得觀眾身臨其境,增強了節目代入感。
《登場了!敦煌》中紀錄片式的演繹模式的另外一個方面主要體現在邀請與敦煌莫高窟相關的專家學者進行引導和訪談。第一集中,節目組邀請了敦煌研究院藝術研究部部長婁婕來給大家講解,她帶大家去了守護人墓地——莫高窟九層樓對面,宕泉河邊安葬著包括常書鴻、段文杰先生在內的27 位堅守敦煌的莫高人。探索團團長汪涵和敦煌有緣人孟鶴堂還拜訪了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復專家、中國石窟修復第一人李云鶴老先生,聽李老先生講解了壁畫修復的一系列過程。在最后的致敬環節,五人聽了被人稱作“敦煌守護神”的常書鴻先生的書信。節目將已經逝去的扎根在敦煌、熱愛敦煌的前輩們和現在依然堅守在保護莫高窟第一線的大國工匠們的真情講述串聯起來,組成一幅有血有肉的敦煌奉獻圖。所有講解都來源于真人真事,來源于真實的歷史背景和文獻記載,具有較強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同時,向大家展現了老一輩敦煌人播撒熱愛、終生只為敦煌的感人情懷。
(二)敘事特點真實和富有趣味性
節目主要是以敦煌壁畫中所呈現的故事作為行為線索來展開整個節目的敘述。但普通觀眾可能無法一下子就讀懂敦煌壁畫的深層含義,為了有更好的播出效果,讓觀眾能設身處地了解敦煌文化內涵,節目組根據每一期不同的主題邀請不同研究領域的專家、講解員來對莫高窟壁畫內容進行全方位講解和分析。正是有了這些專家的參與,在保證節目質量的同時,也增強了嚴謹性和專業化,使節目的敘事邏輯更加清晰、敘述表達更為完整。
因為敦煌壁畫具有特殊性,所以節目中所有的洞窟內影像都是復制窟內拍攝或數字掃描資料。因此,在《登場了!敦煌》中涉及一些壁畫場景展示的時候是以“動畫”的形式展現的。這種方式促進了敘事的完整性和形象化,起到了補充視覺、輔助理解的作用。新媒體技術讓壁畫中的人物動起來,一顰一笑在壁畫中變得鮮活,不僅增強了畫面的靈動性,也打破了以往文化類綜藝節目座談式的晦澀乏味,增強了節目的趣味性。
(三)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再現敦煌
2020 年11 月28 日,節目推出的“0937—來自敦煌的Push 沉浸式進窟體驗”線下公益展在北京798藝術區正式拉開帷幕。活動現場將線上多樣化的內容進行線下還原,還把第三期“游藝”篇中的投壺項目也搬到現場,使敦煌文化更易被看見與被感受。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傳播方式減輕了僅線上播放節目的文化割裂感,線下展覽讓大家知道敦煌的文化不僅是承載厚重歷史的文化符號,更是實實在在深入日常生活點點滴滴的娛樂項目、運動項目甚至是廣場舞活動。由此也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能夠關注敦煌文化,甚至成為敦煌的守護者和傳播者。
四、結語
敦煌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是文化傳承的必由之路,影視化是傳播途徑中傳播范圍廣、接受者基數大、影響深遠的傳播方式之一。但是,在影視化傳播的過程中有機遇也有挑戰。我們試圖從優秀的節目中總結出適合敦煌文化傳播的影視化道路,力圖擴大傳播范圍,將敦煌精神、敦煌元素送入每個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