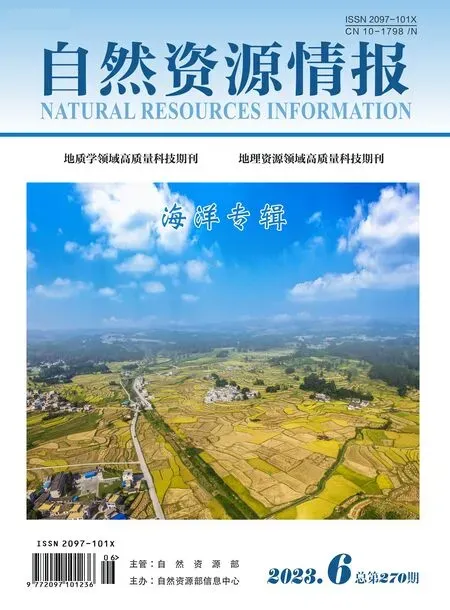海上光伏的立體分層用海模式研究
程永鑫,楊 瀟,李國權
(國家海洋信息中心,天津 300171)
海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來源和保障。隨著海洋開發利用水平的逐漸提高,一方面海洋經濟產業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空間資源日益稀缺,不同用海活動之間的空間矛盾也愈發激烈。在此情況下,對海洋空間由平面開發轉向立體利用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近年來,海上光伏作為新型用海方式發展迅速,但受限于空間資源和產業特性,推動海上光伏與其他行業立體分層布局成為實踐趨勢。從中央到地方在迫切的需求引導下出臺了一系列推動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布局的政策,“風光漁”“漁光互補”等新型復合利用方式相繼出現。
學術界對于立體分層用海及兼容性的研究已比較普遍。其中,在海洋功能的兼容性上,王淼等從立體功能區劃的劃分原則和依據出發,嘗試構建了基于疊置分析的海域空間兼容性利用立體功能區劃模型[1]。趙琪等嘗試選取海域使用情況、海域自然契合度、海域需求空間等相關指標構建了基于兼容性用海的評估指標體系,論證了兼容性用海的評估方法[2]。岳奇等通過對海洋功能區劃的兼容性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認為兼容性判定時應遵循區劃目標優先、管理要求優先、維護基本功能優先和保證基本功能開發優先等四項原則[3]。在海洋空間的立體性上,李彥平等通過對海洋空間進行立體分層處理,并按照用海需求類型的不同將用海空間分為不同層次,而后基于“排他性”原則對分層用海的可行性進行了判別和分析[4]。翟偉康等通過分析我國海域空間資源的自然分層立體特性,以及空間資源開發由單一到多層次的開發過程,最后對我國海域空間資源開發利用所產生的權限界定問題進行探討[5]。崔旺來等刻畫了立體分層使用指引體系,并通過分階段劃定、分步驟化解,以及法律聯動彈性機制實現對空間權屬的精細化管理[6]。關于光伏與其他產業立體利用領域,學者們的研究多集中于“漁光互補”的產業模式及效益評估上。江富平從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選取指標,構建了“漁光互補型”光伏發電的效益評價體系[7];曹玲以SWOT 分析法對主要的“漁光互補”模式進行分析,并對“漁光互補”模式進一步發展提出建議[8];張家華等介紹了“漁光互補”的概念特點和價值,并針對性提出發展建議[9];徐洪鋼通過建立“漁光互補”項目的環境資源效益評價體系,提出改進項目環境資源效益評價的建議措施[10];湯俊超等通過對光伏農業中“光伏+種植業”“光伏+畜牧業”“光伏+漁業”的業態進行分析,提出發展建議[11]。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于立體分層用海及兼容性的概念及實踐研究已較為豐富,對于光伏與其他產業尤其是漁業兼容發展的綜合效益評估及環境影響等研究較為全面,但關于海上光伏的用海立體分層利用模式研究尚少見,關于海上光伏與其他行業立體分層布局管控的研究也較少。因此,本文從海上光伏用海的立體布局實踐出發,研究其立體分層特性,厘清海上光伏能與哪些用海活動在同一海域立體分層布局,為明確海上光伏的布局管控政策和完善海洋空間布局管控體系提供參考。
1 管理實踐及需求
1.1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利用的需求背景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利用主要有兩方面的需求。一方面,近岸海域空間節約集約利用的需求。原海洋功能區劃和海島保護規劃絕大多數停留于平面層次和單一用途,在部分空間利用需求集中區域仍有較大的綜合利用潛力。探索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利用,實質上就是擺脫原有對海洋功能分區單一主導功能的開發利用,由原有二維平面的面上利用擴展至海洋三維空間綜合開發,由粗放型用海轉向集約化利用,能夠極大地促進海洋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12]。另一方面,由于海上光伏發展時間較短,原海洋功能區劃編制時較少考慮到其發展空間需求,劃定的光伏用海空間較少。當下布局發展海上光伏,在已無過多光伏專用空間的情況下,與其他用海活動共享同一海域,立體分層利用是必經之路。在此背景下,亟待厘清海上光伏能與哪些用海活動在立體空間共享海域,研究其立體分層用海的主要模式,為其立體利用和進一步的立體確權提供支撐。
1.2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利用的管理實踐
在光伏產業向海發展需求的驅使下,各級管理機構對于海上光伏復合開發、立體利用管控的相關政策和文件不斷出臺。在中央層面,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委出臺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明確鼓勵“漁光互補”;《關于促進新時代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方案》進一步提出鼓勵“風光漁”融合發展。在地方層面,遼寧、山東、浙江等沿海省份相繼發布文件,推動海上光伏與圍海養殖、鹽田、電廠溫排水區的立體綜合利用,并提出海上光伏項目布局、立體確權的管控要求。由此可見,從中央到沿海地方均對海上光伏布局的需求不斷增大、管理實踐日益豐富,同時從政策角度對于光伏立體分層利用的引導和推動不斷增強。但是由于缺乏系統研究,政策指引僅做方向性引導,多強調的是“要去做”,而距離落地實施的“如何做”尚有距離。在此情況下進行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利用的模式研究,確有必要性。
2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用海的現實基礎
2.1 海洋空間的立體性
海洋空間的立體性是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布局的前提和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簡稱《海域法》),明確提出對于海域的定義,是指我國所屬的內水、領海的水面、水體、海床和底土。據此,在海洋空間研究中一些學者將海洋空間在縱向層面分為水面、水體、海床和底土四個部分[13]。還有一些學者立足于實踐,認為水面上方的邊界范圍較難界定,于是將水面上方空間從水面的概念中抽離,將海洋空間在縱向上分為水面上方空間、水面、水體、海床和底土5 個部分[14]。但考慮到契合管理實踐的需要,以及與《海域法》的相關要求保持統一,采用第一種分層方式則更為適宜。由此將海洋定義為4 層空間,即水面、水體、海床和底土。其中,水面指海水表面及上下方一定的空間,水體指水面和海床之間的空間,海床指海底表面及上下方一定的空間,底土指海床以下的空間(圖1)。

圖1 海洋空間立體剖面圖
2.2 海洋資源的立體分布特征
海洋空間在縱向上的多個層次均有不同的資源屬性,從水面、水體、海床到底土均分布有獨特的海洋資源。例如,水面主要分布著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海床和底土則分布著石油、天然氣、海砂等海洋礦產資源(表1)。而通常對于某種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僅需占據立體空間的某一層次或部分層次,而非全部的海洋空間。這也就意味著,某區域在滿足互不影響或互有促進的情況下,可以分層次同時供多種用海活動進行使用。資源的分層安排,也使得開發利用的分層變成現實可能,這也成為海上光伏能夠進行立體分層利用的基本條件。

表1 各層級海洋空間資源分布
3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用海的實施路徑分析
3.1 基本邏輯
海洋空間的立體性和海洋資源分布的分層性,為海上光伏用海的立體分層利用提供了基本條件。基于此,海上光伏的立體分層利用,一方面要立足于海洋空間的立體性,厘清光伏和其他用海活動所占據的空間層次。另一方面,即使在同一空間層次,因同時存在不同的資源,如水面同時分布著空間資源、太陽能資源、風能資源等多種資源,這也表征著即使在同一空間層次也可能容許不同的用海活動,這就需要進一步判斷海上光伏用海與同一空間層次上其余用海活動相互兼容的可行性。綜上所述,從目前的用海需求及管理實踐出發,要厘清海上光伏立體分層用海的具體模式,需要綜合海上光伏在空間上的立體性和在功能上的兼容性,得出進一步的結論。
3.2 用海活動的縱向空間占用特征判別
自然資源部發布的《省級海岸帶綜合保護與利用規劃編制指南(試行)》(以下簡稱《省級指南》),將海洋發展區進一步劃分為漁業用海區、交通運輸用海區、工礦通信用海區、游憩用海區、特殊用海區和海洋預留區6 個二級區,在二級區內劃分了19個三級區。但是由于分區主要是按照用海行業不同進行分類,而非用海空間層次,即使在三級分區內部,不同用海活動之間其所占據的用海空間層次也并非一致,如路橋隧道區(三級分區)內的用海活動,跨海橋梁和海底隧道所占據的用海層次明顯不一致,故以分區為單元進行立體層次劃分并不科學,以分區內的用海活動來進行匹配則更為符合實踐需求。具體的判別方式:一是要剔除因用海性質或特殊要求無法進行立體利用的用海方式,如軍事用海、油氣開采等活動;二是要考慮到用海活動主體所占據的空間層次,同時還需進一步考慮到保障用海活動順利開展的其他空間,即附占空間(指用海活動的非主要占用空間,在該空間需優先保障主要用海活動順利開展)所占據的空間層次。據此,我們對海上光伏所占據的海洋空間進行判定。目前的海上光伏主要有樁基式和漂浮式兩種模式,其用海活動主體主要為光伏陣列和維持陣列的水上平臺及其附屬設施的用海空間,其主要利用的資源類型為太陽能,占據的空間層次主要為水面空間(圖2)。樁基式海上光伏的附占空間主要是樁基所涉及的水體、海床和底土,漂浮式光伏的附占空間主要是固錨裝置所依附的水體、海床和底土。因兩種主流光伏用海占據空間層次幾乎一致,以下不做進一步區別分析。

圖2 海上光伏占據的空間層次分析
明確海上光伏的用海層次主要為水面空間后,需要進一步對其余可進行立體分層利用的用海活動進行分析,篩選出不占據水面空間的用海活動,以進一步與海上光伏進行立體分層用海。結合《省級指南》提出的分區要求和《海域使用分類》(HY/T 123-2009)明確的用海活動,按照上述判定規則,對剩余可進行立體利用的用海活動進行層次分析,得出其中可進行立體分層利用且不占據水面空間的用海活動主要有:漁業用海區中的底播養殖、人工魚礁養殖,交通運輸用海區中的海底隧道用海,工礦通信用海區中的取排水口用海、溫排水用海、海上風電用海和海底電纜管道用海,特殊用海區內的傾倒用海(表2)。

表2 不占據水面的主要用海活動
3.3 海上光伏與其他用海的兼容性判別
僅從空間分層的角度判定某一用海活動能否與光伏分層利用不夠全面。一方面,在同一用海層次可能存在能夠與海上光伏進行立體分層利用的用海活動;另一方面,一些用海活動即使在空間上與海上光伏能夠共存,但是也可能存在功能上互斥,導致無法立體分層利用。因此,需要對海上光伏與可立體利用的用海活動的兼容性進行進一步判別分析。在用海活動兼容性判別上,一些學者從區劃目標、區劃管理要求、基本功能等兼容原則角度進行研究[3],還有一些學者從海域自然契合度、需求空間、使用狀況、承載能力、投資收益等角度對兼容性進行評估[2]。結合相關學者的思路與方法,以及工作的實際需求,提出兼容性的判斷基本原則為:一是要考慮用海行為的性質,需要建立海上固定設施、平臺等的用海活動,由于其對海洋空間的占用具有長期性和不易改變性,往往兼容性差;僅進行小規模利用,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固定設施的用海活動,通常兼容性較好。二是考慮到用海行為生態影響,一般生態影響較大的活動兼容生態影響小的。三是兼容需要考慮主要功能的實現,在兼容海上光伏的同時,不得影響其主要功能的實現。據此原則,將海上光伏與其他用海活動的兼容性劃分為兼容和不兼容兩種情形,具體判斷如表3。

表3 海上光伏用海的兼容性判定
3.4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用海方案的模式設置
對海上光伏的立體性和兼容性進行判定后,綜合上述研究(表2,表3)得出如下結論:海上光伏在漁業用海區-增養殖區中能夠與底播養殖和人工魚礁在空間上分層利用,與網箱養殖雖同時占用水面空間,但通過兼容性判斷得出網箱養殖與海上光伏能夠兼容,因此在漁業用海區的增養殖區內,能夠布設海上光伏。海底隧道用海與海上光伏用海在立體上可分層、功能上可兼容,故交通運輸用海區-路橋隧道區內能夠與海底隧道用海立體分層布設海上光伏。取排水口、溫排水、海上風電、海底電纜和海上光伏在空間、功能上均可共存,鹽田用海在功能上可兼容,因此在工礦通信用海區中的工業用海區、海底電纜管道用海區、鹽田用海區、可再生能源用海區能夠設置海上光伏。特殊用海區中的傾倒用海雖然在空間上和海上光伏能夠共存,但是在功能上不能與海上光伏兼容,因此在傾倒用海區內不允許海上光伏的布設。海上光伏具體的分層用海方案如表4 所示。

表4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用海方案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布局的方案選擇具有多宜性。由于海洋資源分布的立體性,在同一區域內不僅能與一種海洋功能進行立體分層利用,形成兩種功能用海區(圖3,方案1、2),在同一海域可能同時立體分布三個及以上的用海活動(圖3,方案3、4、5),例如,一些地區正在推廣的“風光漁”一體布局,正是在同一海域同時存在風電、光伏和養殖三種用海活動。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在同一立體空間同時布局除海上光伏外兩個及以上的用海活動時,則不僅需要對海上光伏與其他用海活動的空間分層、功能兼容做判斷,還需要對剩余用海活動及項目整體的實施做進一步研究論證。

圖3 海上光伏立體利用示意圖
3.5 海上光伏立體分層利用需考慮的因素
布局應符合分區管控規則。海上光伏立體分層用海應符合《海域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符合國土空間規劃、海洋環境保護規劃確定的分區和對應的用途管制規則、環境準入規則和負面清單,其布局上應考慮到重要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紅線等的分布,控制對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在其他功能區內立體分層布局海上光伏時,應當注意項目用海首先應保證由功能區劃或海岸帶規劃確定的主導功能用海活動的順利實施,保障主導功能用海所占據的用海空間。
項目布局應充分做好研究論證。實施立體分層利用的海上光伏項目,應以現行法律法規和技術導則為準則,綜合考慮所在海域、所在功能分區的實際狀況,充分論證項目布局的經濟性、合理性以及技術上的可行性,同時考慮本空間其余用海項目的使用面積、年限、用海方式合理性,因時因地制宜選擇方案。
做好用海活動間的協調管理。如光伏項目需要在已登記海域使用權的海域布局,要充分與海域現有使用權人進行符合用海的協商,充分處理好權屬關系、使用年限、開發使用時序、進入退出管理、作業安排和補償金額等問題,避免權屬糾紛,并按照用海層次不同分層設置海域使用權。海上光伏項目建設、運行過程中要充分維護現有使用權人的用海權益。
4 結語
本文立足于海洋空間資源的立體性,對海上光伏的立體分層用海分區方案選擇和實施模式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討,以完善海上光伏布局管控的規則,為實踐提供一定的參考,為行業發展提供助力。研究發現,海上光伏主要能夠在漁業用海區、工礦通信用海區、交通用海區內,與養殖、海上風電、海底隧道等用海活動立體兼容布局。但本文主要基于較大尺度的空間視角,未立足具體海域的環境本底特征,提出的方案也更多為原則性的討論,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