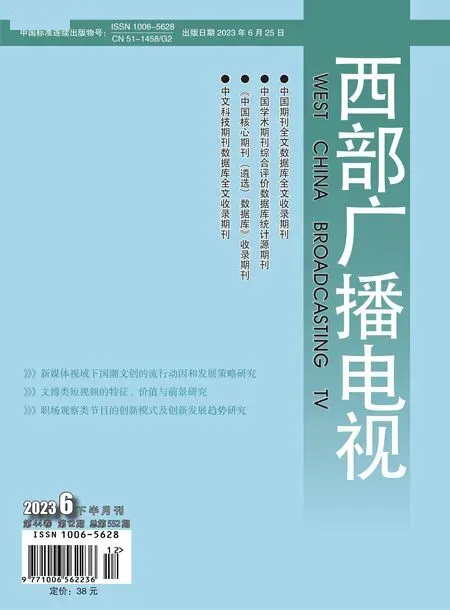嗶哩嗶哩彈幕視頻網站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傳播研究
郭黛的妮
(作者單位:吉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2020—2022 年,B 站跨國家庭中的華人UP 主推出較多以中國美食共享為題材的視頻,視頻內容包括制作中國食物以及邀請自己的跨國家庭成員品嘗并給予評價。此類視頻UP 主的關注量最高達166.2 萬人,近期視頻的播放量超過兩百萬次。對此類視頻內容及傳播現象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此類視頻興起的原因、發揮的作用,并為中國文化的跨文化傳播提供新思路、挖掘新方向。
1 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內容分析
1.1 歷史溯源
此類“與外國人共享中國美食”的視頻在B 站上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UP 主“張逗張花”于2014 年底至2015 年初發布的一系列中國食物共享視頻,此時的分享場景還并非跨國家庭。此后,許多UP 主也嘗試過制作該類視頻,但傳播效果甚微。直到2019 年才有少量跨國家庭華人UP 主對“美食共享”題材有所嘗試,但幾乎都停留于美食制作,很少記錄共享過程,食物也并非中國美食。2020 年是這類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視頻的爆發元年,分享內容以中國食物為主,其中還涉及漢服、旗袍、漢字以及中國科技、中國電視節目等元素。視頻拍攝地點主要在歐洲國家以及美國,視頻時長在30 分鐘以內。目前播放量和點贊量較高的視頻主要由跨國家庭中的華人UP 主制作完成。
1.2 樣本選取
B 站中此類跨國家庭UP 主較多,比較有名的有“混血寶貝EVA”“芳姐和王子”“德國陶淵明”“田納西Jay 和Ari”“北歐冷冰冰”“雨琪在芬蘭”“老少女阿珂”等。本文選取“德國陶淵明”“老少女阿珂”“雨琪在芬蘭”這3 位UP 主的美食共享視頻為研究對象。這3 位UP 主的粉絲數量均在80 萬以上,在B 站此類UP 主中的粉絲人數較高,具有代表性。其中“雨琪在芬蘭”與“老少女阿珂”的粉絲總量在100 萬以上,視頻播放量也大多在100 萬以上。這3 位UP 主B 站平臺使用時間長,此類視頻發展周期較為完整,適合作為樣本。此處對其2022 年及以前的視頻內容元素以及在B站上的播放情況進行分析。相關數據如表1 所示:

表1 B 站3 位UP 主的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統計
“德國陶淵明”的中國美食共享視頻占其各類視頻總量的63.88%;“雨琪在芬蘭”的占比為48.52%;“老少女阿珂”的占比為27.22%。相比于這3 位UP 主其他類型的視頻,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在總視頻數量的占比較高,一經推出就在B 站上獲得超10 萬次的播放量,其中單條視頻的最高累計播放量甚至超過了900 萬次。
1.3 現狀分析與總結
由整理后的數據可知,2020 年為此類視頻的萌芽期,許多跨國家庭的華人UP 主均對此視頻類型進行了嘗試性拍攝,上文提到的許多UP 主的首個中國美食共享視頻皆于2020 年年中到年末在B 站上傳發布。到2021 年,此類視頻初具規模。因為“美食共享”中的品嘗與反應是同時發生的,所以形成了這類特定的“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品嘗反應”類的視頻。2022 年,隨著全球聚集管控政策放松,跨國家庭的華人UP 主的視頻主題逐漸發生了變化,“德國陶淵明”與“雨琪在芬蘭”逐漸以此類視頻為主,后期視頻(統計截至2023年2月)幾乎以中國美食品嘗為主;而“老少女阿珂”的視頻題材逐漸豐富,生活類、美食共享類、分享記錄類視頻均有涉及。
2 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出現的原因
隨著2020 年各國嚴格出入境管理,人口流動速度放緩、人次減少。在“避免感染”心態和各國出入境嚴格管理的雙重影響下,華人減少了回國頻次,在國外停留時間也相應增加。
通過整理B 站上的內容,筆者發現這類視頻的大量出現正是在2020 年。2020 年歐洲多國都對人口聚集有著嚴格的管理措施,這一類華人視頻UP 主處于居家的狀態中。根據UP 主“混血寶貝EVA”的小紅書帖子可知,“混血寶貝EVA”最早于2020 年3 月20 日發布居家烹飪視頻,同年11 月進駐B 站發布這類視頻;UP 主“德國陶淵明”也是在2020 年居家期間將烹飪食物作為自己的視頻素材;UP 主“雨琪在芬蘭”也是在2020 年4 月居家后提高了發布制作中國美食類視頻的頻率。居家烹飪食物成為國內外家庭居家消遣通用方式,烹飪美食在2020 年期間成為華人UP 主制作視頻的熱門素材。
3 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的實際作用
3.1 中國美食共享行為緩解文化休克焦慮感
美食制作除了成為居家期間的熱門素材,還是海外華人度過“挫折期”的有效方式。根據奧博格關于文化休克的觀點,當人們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會失去所熟悉的社會交流符號和標志,這種落差帶來的文化碰撞感會引發強烈的心理焦慮,并且在成人身上尤為明顯。文化休克具體分為4 個時期:蜜月期、挫折期、恢復期和適應期[1]。本文研究的視頻作者大多久居歐洲,在度過了來到異文化世界短暫的“蜜月期”后,會迎來極為痛苦的“挫折期”。人們在“挫折期”中的表現是由遠離母語文化帶來的失落感與疲憊感所導致的,具體表現為難以調和與異國文化成員間的關系、自我認同混亂,無法改變陌生環境的無能為力感等。跨國家庭的華人成員長期停留在國外,與異文化長期相處,加劇了與母語文化的分割感,如果無法回到熟悉的環境,則需要通過必要的方式度過“挫折期”。此時烹飪中國食物就成了度過文化休克“挫折期”的應對方式。
3.1.1 中國美食共享行為能夠助力異文化成員之間互動頻率的提高
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視頻是家庭類和美食類、反應類視頻的融合。家庭類視頻對于關系場景的搭建是現實日常結構的鏡像[2],視頻作者為適應“眼球經濟”時代,需要將家庭中的婆媳、夫妻、姑嫂和親子等家庭關系搬上屏幕,以做到對現實家庭關系結構的鏡像還原。從UP 主“雨琪在芬蘭”視頻內容可知,視頻中呈現的家庭關系也在按照此關系路徑逐漸向外延伸,所以這類美食共享行為能夠在眾多關系中實現。這種在家庭關系間的互動,極大地擴大了跨國家庭中華人的關系圈子,UP 主“德國陶淵明”于2021 年10 月28 日發布的視頻就通過中國美食獲得了與異文化成員間的相互聯系。除此之外,異文化朋友和異文化親戚向UP 主詢問中國美食配方或是UP 主指導異文化成員進行烹飪等,皆能讓UP 主在長期停留海外時產生被認同感,減少對文化差異的排斥。
3.1.2 中國美食文化塑造華人穩定的自我認知
根據一項關于巴基斯坦來華留學生的文化休克的研究,飲食的差異會導致對異國文化難以適應并產生排斥情緒,而制作本國美食是一種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3]。歐洲作為典型的西方飲食地域,其飲食觀念、飲食內容和烹飪方式都與中國有所不同。中國美食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UP 主對中國美食的烹飪可以營造一種母語文化氛圍。UP主的拍攝素材除了中國美食制作與共享,還包含其他中國文化元素,如漢字、漢服和中國科技等。“雨琪在芬蘭”于2022 年6 月4 日關于家人穿漢服體驗中國美食的視頻內容,就是一種對中國文化氛圍的鏡像還原。這對于海外華人來說可以塑造穩定的自我認知以及加深對母語文化的認可。綜上所述,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有助于華人UP 主過渡到文化休克的“恢復期”。
3.2 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促進跨文化傳播
傳播學者伊萊休?卡茨等人于1974 年發表的《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一文中明確指出受眾會在心理因素與社會因素的雙重影響下產生媒介期待,在產生媒介接觸行為的同時使需求得到滿足。雖然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以滿足受眾的媒介使用需求為目的,但被記錄下來的視頻內容實質上還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行為。視頻拍攝實際作用也就演變出兩種方向:滿足受眾需求、進行跨文化傳播。
這類跨國家庭的華人UP 主就在視頻拍攝過程中完成了在社交圈子中的跨文化傳播。根據愛德華·霍爾對于高語境和低語境文化概念的闡釋,中國文化屬于高語境文化,信息傳播高度依賴環境。在這種情況下,美食類、文化體驗類話題則可以通過非語言的方式傳播至低語境文化受眾,直接刺激受眾的感官,如味覺、視覺和嗅覺等,幫助中國文化先在華人UP 主的社交圈子內傳播。這不僅是一種跨文化傳播,還是一種人際傳播,是在線下進行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通過前人的研究可知,人際傳播也具有群體性,人們會花費一定時間參與到群體生活中,并且群體是相互交集的,一個群體的信息會伴隨著成員的流動傳播到另一個群體之中。視頻中的中國文化體驗者也逐漸由跨國家人變成跨國友人,中國文化的跨文化傳播,就這樣發生在親緣關系向社交關系的向外延展之中,美食元素也為后續其他文化元素的傳播搭建了一座橋梁。
4 國內受眾觀看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視頻的原因
4.1 “味覺能指”下的美食欣賞
周鈺棡、楊星宇在《美食類短視頻的“味覺能指”研究》一文中,提到了“味覺能指”的概念,認為美食短視頻的內容傳播在“涵指系統”內存在兩個層級,一是對味覺的指涉、撩撥和滿足為美學旨趣,經由“影像—味覺”的身體動力學過程,短視頻跨越了視覺與味覺的感官壁壘;二是在“味覺能指”的作用下,“影像—味覺—意義”成為一種有效的意義書寫方式和情感表達途徑[4]。簡單來說,“味覺能指”意味著美食類短視頻的影像形態指向的是直接性的味覺滿足,而在“味覺能指”的基礎上融合了多種其他符號和形式,由此構建了更為豐富的意義層。例如,在UP 主“雨琪在芬蘭”的視頻中,以美食烹飪、美食展示與美食品嘗為主,在味覺能指的層面使受眾對視頻中的美食內容產生了統覺,即受眾對美食的理解、記憶和思考相互聯合。家庭成員對食物的滿足對于觀看者來說形成“異質同構”般通感,正如梅洛-龐蒂所言,“我們的知覺指向物體,物體一旦被構成,就顯現為我已經有的或能有的關于物體的所有體驗的原因”。受眾對熟知的中式美食的體驗會在其看到視頻中美食烹飪和美食品嘗的環節時再次出現,在這一機制下,形成視覺向味覺的轉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到味覺神經。
4.2 “凝視”對于文化自信的塑造
趙一凡在《西方文論關鍵詞》一書中認為,凝視是攜帶著權力運作或者欲望糾結的觀看方法[5],“凝視”是除卻感官層次外,理性認識下蘊含了身份背景、文化背景以及權力機制的觀看。對“凝視”的研究自古希臘的視覺至上和理性主義開始,經由薩特、拉康、福柯的發展,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薩特認為在看與被看的關系下自我以及世界的意義才得以存在。拉康則認為看與被看存在著辯證反轉的關系,并且認為“凝視”使欲望在想象中被滿足。
諸如此類美食視頻往往有大量的鏡頭拍攝跨國家庭中外國成員對美食的評價,并且具備一定的敘事結構。例如,在UP 主“雨琪在芬蘭”以“海鮮大餐”為主題的視頻中,開頭的20 秒集中展示了外國家庭成員對中式美食的夸張評價,并且在接下來的視頻中大部分都在展現國外家庭成員對中式美食或積極或震驚的反應,如侄子非常喜歡中式辣椒、侄女對跳跳糖感到震驚等。顯然這類視頻的本質依然是“反應視頻”,帶有明顯的觀點態度輸出。受眾的觀看在這里轉化為了“凝視”,正如耿英華所言,“凝視”是無處不在的,是一種欲望的投射,是一種于想象中獲得欲望滿足的過程[6]。當中國美食被跨國家庭中的國外成員所認可或是贊賞,作為國內的觀賞者,我們也會產生相應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其中渴望自身國家以及民族文化被認可的欲望得到滿足。
綜上所述,國內觀眾對跨國家庭美食視頻的喜愛原因,經由“涵指系統”的兩個層級來解釋:一是由于美食視頻特有的“味覺能指”,實現了視覺向味覺的轉變,指向受眾過往的美食經驗;二是在“味覺能指”的基礎上,受眾在“凝視”中渴望國家民族文化被認可的欲望得到滿足。
5 結語
跨國家庭中國美食共享類視頻在視頻平臺中異軍突起,形成固定的風格并迎來穩定的受眾群體。受眾從觀看中獲得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并通過美食獲得心靈慰藉;傳播者既能夠贏得穩定的流量與關注,又發揮了跨文化傳播的實際作用,為我國在國際中展現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一定的借鑒與參考。但此類視頻如今也面臨著同質化問題,需要視頻制作者及時尋找新方向,為國內受眾提供更加豐富的題材與視覺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