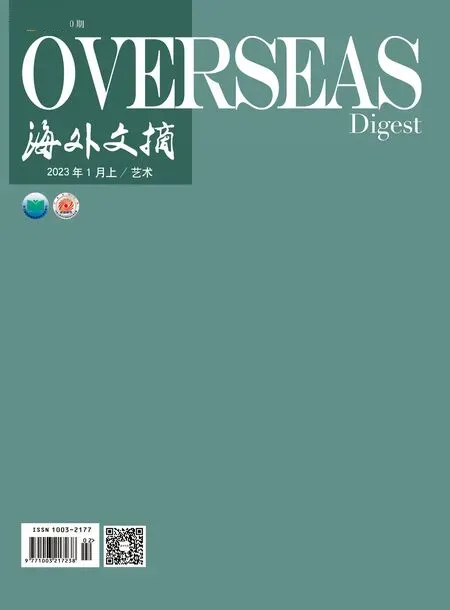莉麗·布里斯庫的女性自我意識
□李應梅/文
弗吉尼亞是英國偉大的現代小說家以及女性主義評論家。她的作品以寫作技巧見長,構思精巧,別具一格,并具有明顯的女性主義思想。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更是20世紀西方文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思想超越了那個特定時代的局限,對于女性主義運動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伍爾夫反對“房中天使”的女性形象,認為這是維多利亞式的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主張女性應該爭取自由,顛覆兩性二元對立框架,實現其自身價值,改變女性被邊緣化、客體化的境地。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思想貫穿于作品始終,《到燈塔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作者通過塑造莉麗·布里斯庫這一另類的女性人物,解構了以男權為中心的霸權主義:莉麗·布里斯庫勇于追求自己熱愛的藝術事業,拒絕傳統女性文化模式。申富英對莉麗追求神圣的繪畫藝術的行為給予肯定,認為莉麗找到了生活的本來面目以及藝術的真諦[1]。本文從“顛覆兩性二元對立”以及“對藝術的不懈追求”兩方面分析莉麗·布里斯庫的女性自我意識,以求以作者化身的莉麗·布里斯庫為窗口,探究作者本人的女性意識及主張。
1 顛覆兩性二元對立
伍爾夫成長于維多利亞時代末期,這是由男性掌控著話語權的時代。英國學者約翰·梅彭對維多利亞時期男性家庭模式進行了概括:“維多利亞式的家庭就是一個龐大的父權制機構……妻子和母親的角色是充當繁重的家庭經濟事務的管理者,她極少有指望過任何別的生活。[2]”加上當時唯有男性才能享受教育的特權,女性只能在家中這種封閉的環境中接受所謂的培養“女性氣質”的教育,“女性氣質”成為英國社會衡量女性品德的標準,因此以男權中心社會的價值標準進行構筑的女性形象——“房中天使”成為當時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主流。她們美麗、善良、順從,對家庭和孩子無私奉獻。伍爾夫在其《女人的職業》中對其描述道:“她相當惹人喜愛,有無窮的魅力,一點也不自私——簡而言之,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從來沒有自己的想法、愿望,別人的見解和意愿她總是更愿意贊同……她純潔無瑕……具有極其優雅的氣質。在那些日子里——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最后幾年——每間房子里都有她的天使。[3]”《到燈塔去》中的拉姆齊夫人是伍爾夫作品中極具代表性的“房中天使”。她悉心照料八個子女,給予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她對丈夫體貼入微,適時地給予安慰與鼓勵;她熱情并樂于助人,使塔斯來先生得以恢復自信,使孤獨的人感到溫暖;她迎送賓客,締造和諧、溫暖的氛圍,讓人們暫時忘卻了分歧與爭執。但伍爾夫寫作她,是為了“殺死她”。伍爾夫揚言:無論在任何時候,只要察覺到她那翅膀的投影或是身上的光輝投射到“我”的稿子上,就會不顧一切地去殺死她。可是這幽靈并不是說殺死就能殺死的。殺死一個幽靈比起殺死一個真實的人來說要困難得多。有時,作者自以為已經處置了她,可是她又照樣會偷偷地溜回到其身邊。伍爾夫認為殺死這位“房中天使”是每位女作家工作的一部分。這樣可以避免其他人甘愿成為“房中天使”,喪失自我意識,成為第二位“拉姆齊”夫人。
因此她在《到燈塔去》中大膽地塑造了莉麗·布里斯庫非“房中天使”的反叛形象,與拉姆齊夫人作為對照,表達她的女性主義主張: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就是要否定男權中心意識對女性形象的建構,就是要顛覆兩性二元對立的傳統。莉麗·布里斯庫,44歲,卻仍然單身。她拒絕走進婚姻的殿堂,在她看來,妻子只是丈夫的附屬品,婚姻只會給她帶來無盡的束縛與女性自我意識的喪失。世上再沒有比它更沉悶、更單調、更殘忍的了。人應當擁有自己的生活,應當獨立地享受人生,而不是去扮演一個傳統的女性角色,那些陳腐過時的 “局限性的陳舊觀念”應該摒除掉。拉姆齊夫人則早早結婚,她是典型的“房中天使”,溫柔善良、端莊優雅、完美無瑕。夫人認為到了一定的年齡,女性是要結婚的。婚姻是女人的歸宿,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已然足夠。她認為莉麗顯然到了男性所不能接受的年齡,除非他是威廉·班克斯那樣的高齡長者。她是這樣評價莉麗的:“到了四十歲,還是莉麗更勝一籌。在莉麗身上,貫穿著某種因素,閃耀著一星火花,這是某種屬于她個人獨特的品質。但是,她恐怕男人不會賞識。[4]”拉姆齊夫人始終熱衷于撮合明塔和保羅的婚姻,然而莉麗卻認為這是一樁失敗的婚姻。明塔和保羅也最終分開了。在文章中,拉姆齊夫人對家庭無私付出,任勞任怨,最后身心疲憊,在倫敦溘然長逝。隨著夫人的離去,一切美好蕩然無存。莉麗對拉姆齊夫人是報以同情的。莉麗對婚姻持否定的態度是作者女性主義思想的體現,作者認為女性要實現其自身價值,就必須獨立自主,殺死“房中天使”,從而喚醒女性自我意識。伍爾夫深信只有顛覆這種傳統的“房中天使”形象對女性內在精神的框定,才能使女性找到真正的自我。而莉麗對繪畫藝術的不懈追求則表達了作者希望女性擺脫傳統的女性角色框架,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自己的價值,最終建立女性主體意識,重構女性身份的想法。
2 對藝術的不懈追求
拉姆齊夫人盡善盡美,關愛、體諒、遷就所有人,猶如天使。莉麗卻完全不一樣,她體現了伍爾夫的新女性主張,即使孑然一身,也要追求自己的夢想。莉麗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但在男權社會,她注定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莉麗受到了來自查爾斯·塔斯來以及拉姆齊夫人的反對與貶低。塔斯來用不屑的口吻說道:“女人不能繪畫,女人不能寫作。[4]”拉姆齊夫人則認為繪畫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消遣,不僅不支持莉麗追求繪畫藝術,還試圖使莉麗回到所謂的現實中,勸說莉麗必須結婚,并極力撮合她和萊斯利先生,即使莉麗并無此意。只不過有一次看到莉麗和班克斯先生走在一起的背影,夫人便說:“沒錯真是他們倆。這不是意味著,將來他們會結合嗎?對,他們倆必須結婚!多好的主意!他們倆必須結婚![4]”如此種種,便是莉麗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所面臨的處境。正如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所言:“女子天賦過人,必然會發瘋,或射殺自己,或離群索居,在村外的草舍中度過殘生,半巫半神,給人畏懼,給人嘲弄。[5]”因此莉麗是有些缺乏自信的。她彷徨迷茫,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堅持自己的繪畫藝術,認為自己不能夠憑借自己的藝術創作得到人們的肯定,因此總是畏首畏尾,不敢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思想,也沒有勇氣向他人主動展示自己的畫作。
但是莉麗有她自己的人生理想,始終不懈追求著藝術,不曾放棄過藝術。經過了十來年的時間,莉麗明白了藝術的永恒:世間沒有永恒不變的事物,除了文字和繪畫的藝術外,一切都在變化之中。她認識到繪畫能夠表達自己的思想,并且永久留存。她將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寄托在藝術的永恒之中。
為了留下這永恒的瞬間,莉麗決心完成擱置十年之久的拉姆齊母子之圖。
在作畫的過程中,莉麗遇到了重重困難。她發現想象的事情很簡單,在實踐中就變得復雜起來。她思緒萬千,卻無從下筆,“從何處落筆?在畫布的哪一點涂上第一道色彩?這可是個問題 。[4]”莉麗想到了拉姆齊夫人,她對夫人的情感是復雜的。她曾對夫人充滿了抱怨與不理解,認為夫人只是充當男性情感宣泄對象的“工具人”。然而現在,她終于真正理解夫人,理解她所做的一切是她完美品德的一部分,理解她身為“房中天使”的不得已的命運。莉麗呼喚著夫人,“帶著一種突如其來的強烈沖動,好像在一剎那間,她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她在畫布的中央添上一筆。畫好啦!大功告成啦。[4]”
完成畫作之時,是拉姆齊夫人及其精神定格為永恒之時,也是莉麗自我人格完善之時。
莉麗面對著維多利亞時代男權社會下男女極其不平等的客觀現實,但她內心覺醒的女性意識不僅沒有被這種殘酷的外部環境所扼殺,還迸發出強大的能量。她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中,深刻體悟到男性對女性的偏見的根深蒂固,但她從不動搖自己追求藝術的決心。她努力地排除困難,忘卻局限自己的種種瑣碎問題與壓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永恒的藝術創作當中。
莉麗熱愛自由,聽從自己的內心,有著自我獨立的精神和敏銳無比的洞察力。伍爾夫以細膩、靈活、富有詩意的筆觸塑造了這一生動鮮活的女性角色,謳歌了她獨立自主的精神,贊美了她對藝術和自由的追求。伍爾夫認識到當時的社會給女性的“無形的約束”,女性自我意識缺失等問題。為了女性成長,伍爾夫提出“改變女性對自我的認知,重塑女性自我形象”的呼吁。而“莉麗”這一角色,正實踐著伍爾夫的呼吁。莉麗身上具有鮮明的女性覺醒色彩,是作者伍爾夫的真實寫照。
3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一位形象飽滿、特色鮮明的女性——莉麗·布里斯庫的形象躍然于紙上。她拒絕依附男性生活,蔑視并逃離傳統婚姻;終其一生,追求著自己的繪畫藝術。伍爾夫借由這個角色,揭示了維多利亞時代女性權利缺失以及教育不平等的客觀現實,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伍爾夫意識到由男性文化孕育的男女二元對立的不平等性別關系廣泛根植于人類歷史和客觀現實中,因此女性需要“成為自己”。所謂“成為自己”,就是建立一種獨立而又開放的女性自我,女性要全面自由地發展自我、實現自身價值。這種樸素的女性思想對后世女權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引用
[1]申富英.評《到燈塔去》中人物精神的奮斗歷程[J].外國文學評論,1999(4):66-71.
[2] John Mepham.Virginia Woolf,A Literary Life.弗吉尼亞·伍爾夫:存在的瞬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 弗吉尼亞·伍爾夫.女人的職業[M].王斌,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4] 弗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M].瞿世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5] 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M].賈輝豐,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