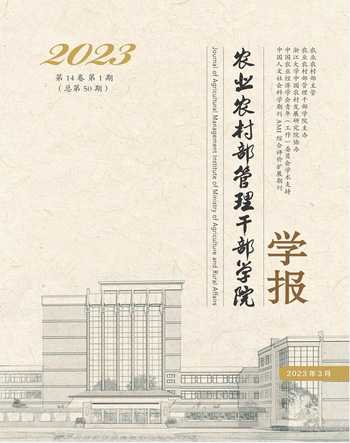數字化進程中鄉村產業轉型升級路徑與對策:發展背景和文獻分析
彭超 李婷婷 齊心 馬九杰 朱鐵輝 陳玨穎 劉合光
摘 要:數字經濟日益融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諸環節、全過程,這種影響也延伸到鄉村產業轉型升級上。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已經成為數字化的重要切入點。文獻分析的結果表明,鄉村產業轉型升級與數字化融合程度更深、賦能范圍更廣、創新驅動更強,亟需對數字化背景下的鄉村產業改造升級路徑、融合發展機制、政策創新創設進行研究,為做強做優做大鄉村數字經濟提供學理支撐和決策參考。現有文獻存在忽視鄉村產業主體異質性、少有考慮產業發展階段性差異、缺乏定量分析等問題。需要從產業主體特質和鄉村產業發展階段特征出發,聚焦于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具體路徑,探究數字化對鄉村產業升級的影響機制。
關鍵詞:數字化;鄉村產業;轉型升級
21世紀10年代以來,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化技術加速創新,智慧農業、智能制造、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等數字化業態快速發展,數字經濟日益融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諸環節、全過程。尤其是,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速度之快、輻射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弱質產業彎道超車、城鄉要素配置優化、國內經濟大循環暢通的關鍵力量。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前提,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環。鄉村產業連接自然資源與內需大市場,產生了海量數據資源,成為新型生產要素的重要來源。數字技術和業態在鄉村產業發展中具有豐富的應用場景,激活了鄉村產業的發展創造活力。數字化開啟了鄉村產業發展的新格局:要素自生激活、技術貫穿滲透、市場互聯互通、主體創業創新、業態跨界融合。可以說,數字化不僅是鄉村產業興旺的新興驅動因素,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鄉村產業的支點。因此,鄉村產業轉型升級與數字化融合程度更深、賦能范圍更廣、創新驅動更強,亟需對數字化背景下的鄉村產業改造升級路徑、融合發展機制、政策創新創設進行研究,為做強做優做大鄉村數字經濟提供學理支撐和決策參考。開展數字化背景下鄉村產業轉型升級路徑與對策研究,不僅可以豐富數字經濟與產業組織的相關理論研究,也能夠為數字化背景下我國城鄉產業發展促進政策改進提供實證依據。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日益深化的今天,廣大亞非拉國家與中國面臨著人口密集、城鄉差距巨大等類似問題,探索數字經濟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驅動機制,將為推動發展中國家數字紅利共享、消弭數字鴻溝貢獻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
一、數字化進程中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
(一)中國正處在數字化的關鍵時期
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世界趨勢。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紛紛出臺國家數字化發展戰略和行動方案。例如,德國出臺《數字化戰略2025》,美國發布《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計劃》,英國實施《產業戰略:人工智能領域行動》,日本發布《人工智能戰略草案》,等等。把握數字化發展態勢,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全方位推動數字化變革,已經成為世界趨勢。
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鄉村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將發展數字經濟上升為國家戰略。《網絡強國戰略實施綱要》《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等一系列戰略規劃的出臺,推動數字經濟在各個領域的快速發展。2019年以來,隨著《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 —2025)》的印發,一系列支持數字鄉村發展的優惠政策也陸續出臺。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形勢良好。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為38.6%,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7.8%①。數字產業化規模持續增長,軟件業務收入和大數據產業規模分別從2016年的4.9萬億元和0.34萬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8.16萬億元和1萬億元以上。產業數字化進程提速升級,我國電子商務交易額由2015年的21.8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37.2萬億元②。總體上,我國的數字產業化規模逐漸壯大,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不斷加快,數字化已經成為驅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的核心力量。
但是也應當看到,中國數字化進程中存在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雖然我國數字經濟體量較大,發展迅猛,但仍受基礎研究薄弱、數字人才短缺、數據孤島問題嚴峻等因素制約,面臨數據安全、網絡安全等一系列重大挑戰。同時,我國的鄉村數字化水平仍與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明顯差距,鄉村數字產業化滯后,數據整合共享不充分、開發利用不足,數字經濟在農業中的占比遠低于工業和服務業,產業主體素質和數字化使用能力弱,成為數字中國建設的突出短板 [1, 2]。
當前,數字化發展面臨著一系列問題與挑戰,嚴重制約著數字化的快速健康發展。解決好數字化建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可以為數字化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補齊鄉村數字化短板,有利于推進我國的數字化進程,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3, 4]。
(二)中國鄉村產業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重要時期
一方面,我國鄉村產業發展迅猛。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農民就業收入水平不斷提升,鄉村產業的迅猛發展,為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提供了有力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通過一系列綜合配套改革推動鄉村產業的快速發展,農業及相關產業產值持續增加,鄉村產業體系不斷完善。2021年,農業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18.44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5%。其中,食用和非食用農林牧漁產品加工與制造超過4.96萬億元,農業生產性服務業、休閑農業、農村電商等服務業營業收入近4萬億元。
另一方面,鄉村產業也面臨重大挑戰。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科技投入不足、市場競爭力不強等因素制約著我國鄉村產業的發展。當前,國內外遭遇新冠疫情的沖擊,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和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我國鄉村產業發展更為艱難。在數字化背景下,鄉村產業發展主要面臨著產業結構失衡、產業要素活力不足、產業基礎設施薄弱、鄉村勞動力欠缺、科技投入不足、數字適應能力不強、數字共享發展不足、數字資本與社會資本不兼容、數字替代壓力巨大等問題[5]。為了推動我國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促進鄉村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鄉村產業的轉型升級至關重要[6]。
(三) 數字化給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數字化帶來新機遇。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化技術為我國鄉村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助力,帶動電子商務等新業態的發展。我國數字鄉村建設加快推進,每年政府都會發布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浙江、江蘇、廣東等省份也相繼出臺數字鄉村發展政策文件,政策體系更加完善,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③。數字鄉村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數字經濟可以通過創新和改造傳統產業,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鄉村產業全面深度融合,不斷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和區域布局,大大推動農業產業系統性轉型,提升農業生產效率,促進鄉村產業全面振興[7, 8]。
數字化帶來挑戰。我國的數字化產業、信息化產業仍處于新興發展階段,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數字技術的區域間差異、數字經濟與產業融合不均衡、專業人才的匱乏等問題依舊突出,這些問題成為數字化時代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制約[2]。
抓住機遇,科學應對挑戰,充分獲取數字紅利,是促進我國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鄉村產業轉型升級要抓住數字紅利,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促進數字化與鄉村產業的融合發展,積極發展新業態、新產品、新模式,解決鄉村產業轉型升級中的問題,實現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9, 10]。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分析
為了厘清國內外關于數字化背景下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進展,本項目主要從數字經濟與數字化轉型、鄉村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三個方面梳理相關文獻。
(一)關于數字經濟與數字化轉型的研究
圍繞數字化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目前學術界主要側重于數字化與數字化轉型、數字化政策兩個方面的研究。
1.數字經濟、數字化與數字化轉型內涵、問題、路徑等相關研究。隨著互聯網的全球化發展、數字技術與網絡技術的不斷融合,數字經濟進入高速增長軌道[11, 12],數字經濟的內涵不斷得以拓展。數字經濟是一場基于因特網的具有豐富創新內涵的技術革命,被認為是一國(地區)經濟增長的新源泉[13]。它由電子商務基礎設施、電子業務和電子商務三部分組成[9],具有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種發展路徑。作為一種繼農業和工業經濟之后的新經濟,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為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以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4]。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不僅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和傳統產業的提質增效[14],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增加產業動能、提升產業效益,而且能夠推動鄉村產業新業態、新產品、新模式的不斷涌現[1]。這對于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現代農業發展和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具有重要意義[15, 16]。
隨著全球數字化進程的加快,數字化正成為數字經濟的核心驅動力,成為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強大動力。就本質而言,數字化是指在企業內部運用數字技術優化業務流程、運營方式和工作方式等,從而實現降本增效,并通過改造、創新、融合等路徑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而數字技術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具有迭代快、擴散快、滲透性強等特點[4],能夠對傳統商業模式、業務模式和管理模式進行創新與重塑,實現企業產品創新、增加生產效益等,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17]。數字化的飛速發展,不僅有利于提升農業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改善物流水平,完善農業服務,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提升鄉村治理水平[18],還能夠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農業生產的數字化,推動鄉村產業、生活和治理的數字化,促進鄉村產業與鄉村各領域的重構與創新[19],進而推動數字農業的快速發展與數字鄉村的建設。在實踐中,數字化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例如數字技術及其質量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性,不同主體數字技術可及性有差異,數字技術使用能力有差異,容易產生“數字鴻溝”,勢必進一步加大城鄉發展差距與貧富差距[20-22]。
數字化轉型是指運用數字技術進行全方位、全鏈條、多角度的改造過程[23, 24],其通過數字技術打造數字化能力,創新變革傳統業務,不僅有利于進一步創新產品與服務、流程和商業模式,而且能夠提升運營效率和組織績效[23, 25]。截至目前,學者們已從主體、技術范疇、轉型領域和轉型效果的視角對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和內涵進行詳細闡述。a)從主體來看,有些學者認為企業是數字化轉型的主體,而有些學者認為國家、市場等應作為數字化轉型的主體。b)從技術范疇方面來看,一種觀點是數字化轉型要使用信息化技術[26, 27],另一種觀點則是數字化轉型要以新一代數字技術為依托[2]。c)在數字化轉型領域方面,現有研究普遍認為數字化轉型集中于業務領域(如改進或重構企業的業務)和組織整體(如組織變革)兩個方面[28-30]。d)從數字化轉型效果來看,諸多研究認為數字化轉型可以推動企業績效、運營效率提升[31-34]、組織架構變革[35],并推動產業結構升級[36]。未來,隨著數字技術發展、用戶需求改變和競爭環境的加劇,針對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中面臨的技術供給不足、人才約束和業務能力低下等現實挑戰,應依托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工具,從企業智能制造、行業平臺賦能和園區生態構建等三條主要路徑,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3]。
2.數字化政策相關研究。數字化是技術進步的結果,也是政府引導的結果。企業是推進實現特定產業數字化的主體,政府則是一國實現數字化的主要推動者[37]。政府的引導體現在政府制定和實施的數字化政策上。目前關于數字化政策的研究以定性文章為主,認為政府的數字化政策主要分為供給型、環境型和需求型三大類[38]。供給型政策主要表現為對數字化發展具有一定推動作用,包括培養技術人才、完善基礎設施、加大技術資金的投入等。環境型政策代表能夠為數字化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的政策,包括目標規劃、產權保護以及法律規范等。需求型政策表示為穩定數字化市場的政策,包括政府采購、用戶補貼和價格指導等[39]。具體而言,在供給型政策中,政府聯合企業、學術界和社會等各領域,在加強對現有勞動力的數字技能培訓的同時儲備未來數字人才,努力緩解數字化過程中的主體異質性問題,增加數字化的人力資本;政府加強財政對基礎設施與技術資金投入兩個方面的傾斜力度,為數字化發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40]。在環境型政策中,政府借助鄉土社會的互助力量和市場力量,通過現有政策資源支持創新以及創新政策執行模式兩種方式為數字化發展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41]。在需求型政策中,政府采購主要包括 R&D采購和創新產品采購[42],能夠長期激勵企業進行創新[43, 44],對于數字化技術的創新有重要意義。
整體來看,已有文獻大多停留在對數字化、數字經濟和數字化轉型概念內涵的闡述層面,部分研究涉及數字化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但是鮮有研究分析數字化在鄉村產業轉型升級中所承擔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有關數字化如何推動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量化研究也較為少見,開展這個方向的研究對于促進數字化與鄉村產業的融合發展、推動我國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二)關于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
早期的鄉村產業主要指農業,現在的鄉村產業內涵較為豐富,既包含農業、林業、牧業、漁業、農產品加工業等傳統產業,也包含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業、電商、物流、田園綜合體等新興產業,是鄉村一二三產業的總稱。當前我國鄉村產業依然存在產業結構失衡、鄉村組織化程度低、產業鏈效益低、專業人才缺乏和資金短缺等現實問題。產業轉型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民經濟構成中,產業結構、產業規模、產業組織、產業技術裝備等發生顯著變動的狀態或過程,具有全方位和多層次特征[45]。而產業升級的實質是產業由低技術水平和低附加值狀態向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狀態的單向演變過程,具體包括企業內部、企業之間、本土或國家內部及國際區域四個層次的升級。顯然,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更復雜的系統工程,并不單單是產業轉型與產業升級的疊加組合。有學者認為,產業轉型升級的主體是企業,其本質是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優化,具體是指以技術創新為動力推動產業結構有序高級化的過程,使產業朝著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發展[46]。產業轉型升級的起點是主導邏輯(企業根本性戰略信念、戰略假設和戰略意圖的表達)改變[47]。
現有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鄉村產業轉型路徑選擇、鄉村產業發展影響因素和鄉村產業發展政策三個方面。
1.關于鄉村產業轉型路徑選擇的研究。學者們從不同理論視角提出不同的路徑。一是基于組織變革視角的分割式適應、整體共演、技術影響和系統變革路徑;二是基于能力視角的協同和重塑路徑[48, 49]。前者通過開發新的數字化實踐并將其與企業原有實踐相融合與協調,后者涉及利用數字技術在企業之間創立共享身份,重塑企業的原有實踐。產業可以通過深化重點產業數字化改造、加快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加強核心技術研發、推進互聯網平臺建設、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加強數字化人才培養等方式實現轉型升級。多數文獻認為,產業轉型升級有助于企業構建持續的競爭力。但在轉型升級過程中,由數字化技術帶來的隱私、社會公平等問題,產業自身存在的產業資源未完全融合、資金短缺和人才缺乏等問題也不容忽視[50, 51]。從發展鏈條與要素組合角度出發,學者提出新的路徑區分方法,認為產業轉型升級的四條路徑分別為產業鏈轉型升級、價值鏈轉型升級、創新鏈轉型升級和生產要素組合轉型升級[52]。從產業主體角度,呂鐵對我國傳統產業轉型路徑進行了分析,認為企業要結合數字化趨勢,加快推進企業智能制造、行業平臺賦能和園區生態構建,通過如上三條路徑積極務實地推動傳統產業的轉型[3]。
2.關于鄉村產業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現有研究認為影響因素眾多,包括社會需求、技術進步、制度影響、資源稟賦、市場化水平、投資供給等[53, 54]。多數學者認為區位條件和要素稟賦因素是影響鄉村產業發展及轉型升級的重要因素[55, 56]。除此之外,還包括市場化水平、技術進步和選擇、技術變遷、空間因素、勞動力供給、產業集聚以及自然條件等因素[57-60]。稟賦結構借助生產要素價格影響技術選擇和創新,進而對鄉村產業結構升級產生重要影響[61]。
3.關于鄉村產業發展政策的研究。已有研究認為,鄉村產業發展政策可概括為基礎性制度安排、政策手段、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四大類[62]。第一,基礎性制度安排主要指為鄉村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所需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包括產業園區、數字基建、教育、交通等基礎設施。如數字教育的推進,可以為鄉村產業轉型培養人才隊伍,能夠有效緩解數字化主體異質性問題。第二,政策手段主要是指綜合運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為鄉村產業轉型發展提供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為其創造穩定的市場環境[63, 64],能夠為鄉村產業平衡供給和需求,推動鄉村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第三,競爭政策包括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鄉村產業產權的保護等方面。競爭政策主要從立法建設、執法公正、監管有效、遵法守法四個角度完善鄉村產業發展的制度體系,制定完善的政策框架[65]。第四,產業政策主要是合理引導調控鄉村產業的發展,為鄉村產業轉型提供科學咨詢與發展信息,積極利用產業政策促進產業技術創新,充分激發企業活力,推動鄉村產業的技術改造與現代化發展[66]。
當前,圍繞鄉村產業政策有效性的爭論一直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于農村地區的產品和要素市場不完善[67, 68],政府需要制定產業政策來推動鄉村產業的快速發展,從而使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達到最好[69, 70, 41]。另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并不能提升經濟效率,也未必能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效果,可能會造成尋租和腐敗行為,進而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71, 72]。而外部影響因素的制約和國際鄉村產業發展的經驗表明,政府是推動產業發展的有為之手,國家需要制定相關產業政策進行干預,為鄉村產業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73]。
綜上分析,盡管現有研究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及其路徑和政策進行了廣泛分析,但在數字化背景下分析鄉村產業如何轉型升級、不同特質鄉村產業主體如何選擇偏好的路徑以推進和影響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較為少見。相應地,在充分考慮鄉村產業主體異質性上研究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進而針對不同主體和地區進行差異化政策設計,對于推進我國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關于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
1.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研究
當前,國內外諸多學者已從數字金融、人工智能、鄉村產業融合等不同角度闡述了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多數學者認為,數字化有利于推動經濟增長[74, 75],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環境可持續性和發展的包容性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76, 77, 18]。
現有文獻關于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發展的正向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有利于優化要素配置,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機遇。數字化基于數據共享性、要素流動重組、知識溢出等優勢,使技術外溢隨著產品交換和資本流入而強化[78],加速了要素、信息、人才等資源要素的流動與優化組合,能夠逐步縮小城鄉數字鴻溝[79, 80],促使區域產業發展更加分散[81],為鄉村產業的發展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82],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8]。
第二,能夠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以電子商務平臺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為鄉村產業的宣傳與銷售提供渠道,提高信息匹配程度,在提升供給體系質量的同時[83],進一步提高鄉村產業的效益、競爭力以及生產經營效率[84, 16],從而實現產業價值增值[85, 86]。
第三,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形成鄉村產業自主生產、自主創新的良性循環。物聯網、智能化設備等數字技術的應用,推動鄉村產業內部產生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13, 68],提高生產效率[87, 88],加快鄉村產業革新步伐,改善鄉村產業的生產組織形式,促進鄉村產業提質增效,從而激發鄉村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形成鄉村產業自主生產、自主創新的良性循環[89]。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數字化也會對鄉村產業發展產生一些不利影響。一方面,數字化的應用需以數字化基礎設施為前提,不同區域數字基礎設施的差異會造成鄉村產業間的發展不平衡[1]。在實踐中,信息質量和技術的差異使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存在異質性[22],進而會加重收入不平等現象[90],可能加大地區間乃至全球各國間的貧富差距[91]。另一方面,數字化發展對鄉村產業從事者的數字技能提出較高的要求,擁有數字技能已成為農戶獲得數字紅利的前提條件[41],而當前農村產業勞動者素質難以滿足數字化發展的需要,難以激發鄉村振興參與主體的積極性[92],在一定程度上制約鄉村產業的進一步發展[1]。
從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發展環節的影響來看,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的影響貫穿產前、產中和產后三個環節。在產前階段,數字化平臺為鄉村產業傳遞市場信息,能夠降低市場信息不匹配程度,同時數字金融也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93]。在產中階段,借助農業傳感器、航空植保技術、農業機器人技術等現代化農業技術可以實現精準農業生產[94, 27]。通過物聯網建立可追溯體系為農產品質量提供保障[93]。在產后階段,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電商信息平臺能夠為鄉村產業打開銷量[95],互聯網平臺可以達到宣傳推廣效果[93],數字化物流能夠為產品配送提供保障。總的來說,數字化技術將農業供應鏈中的生產方、銷售方以及用戶與三方物流系統連接,減少信息交換成本與資源浪費問題[96]。數字化有效延長鄉村產業的產業鏈條,構建從初級產品到終端消費一體化的農業產業新體系[97],推動形成農業生產前向一體化與后向一體化的多元產業形態[98],為“數字鄉村”的建立和發展提供新動能[7]。
2.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影響的研究
關于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影響的研究,當前國內外學者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側重研究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的影響機制,大體可以分為鮑莫爾的供給側影響機制以及恩格爾的需求側影響機制[99]。對于前者,數字化通過革新鄉村產業的生產方式與經濟模式,推動鄉村產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與公共服務的優化配置[1];對于后者,學者們普遍認為鄉村產業轉型主要受部門間產品需求收入彈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因時空特征與產業特性而存在異質性[22, 100]。
二是側重研究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造成影響的性質。一方面,數字化對鄉村產業有正面影響。第一,數字化有利于加快鄉村產業的智能化、科技化發展。數字化的普及有利于加速鄉村創新,拓展農業產業鏈,優化鄉村產業結構,進而推動鄉村三產融合以及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現[101-104]。第二,數字化技術的應用能夠推動鄉村產業的綠色轉型發展。數字經濟的普及使民眾的綠色發展意識增強,環保意識有所提高,同時數字化的技術應用也為政府執行環保政策提供監管平臺,對鄉村產業的排污減排度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有利于推動鄉村產業向綠色循環方向發展[105]。第三,數字化有利于提高鄉村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106]。數字化平臺的建設為城鄉信息流、物流、商流的自由流動提供機遇[107],推動涉農產業的系統重組與多樣化集聚[108],在推動鄉村產業生產鏈條升級的同時,也提高其生產效率[109]。
另一方面,數字化也會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造成負面影響。供需雙層次的數字鴻溝制約數字技術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促進作用[110]。而且,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存在地域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大區域間的不平衡狀況[16, 82]。即使彌補了上述數字鴻溝,異質性農民的能力差異和數字化技術使用滯后問題也會造成數字化的運用差異[111-114],導致數字化紅利差距較大[115]。另外,數字化也存在一定的門檻效應[116],對我國數字基建與信息化技術提出較高的要求。此外,產業結構存在偏差、三產融合程度較低等問題也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產生負面影響[117, 5, 118]。
三是側重研究調節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影響的因素。圍繞這個問題,國內外研究者通過構建動態面板模型、二元選擇模型、固定效應模型或門檻效應模型等方法,利用研發投入強度[119]、技術進步比值[22]、科研人數比值等作為代理變量[120],實證考察調節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影響的關鍵因素和作用機制。研究發現,貨幣資本[121-124]、人力資本[125, 126]、科技創新[127]、環境規制[128, 129]、金融發展[130]、基礎設施建設[131]、研發投入強度[119]、政府支持政策等因素均正向調節數字化鄉村產業的轉型升級[41]。
整體而言,關于數字化對我國鄉村產業發展和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影響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層面,主要分析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的影響、影響機制與調節因素三個方面,運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較少,缺乏對影響程度的實證分析,對影響機制的探索還處于起步階段,導致數字化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機理尚未探究清楚。
三、文獻評析和結論
通過上文關于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相關文獻的分析,可以發現:從研究內容來看,現有研究側重對數字經濟與數字化轉型的專題研究,特別關注鄉村產業轉型的過程研究,重點考察鄉村產業轉型的路徑和影響因素,為學界進一步推進數字化對鄉村產業影響機制的研究作出學術貢獻、積累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基礎。
盡管現有文獻對數字化和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問題分別進行廣泛的研究,但仍存在三個不足。第一,忽視鄉村產業主體異質性造成的產業轉型的路徑選擇偏好問題。產業主體如農戶在數字化信息化發展大潮中能否獲得數字紅利與其信息可及性和使用能力密切相關[131, 115]。第二,在數字化對產業轉型不同階段產生的差別影響研究較少。數字化對產業轉型的影響存在階段性特征,具有差別化的影響機制。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現有研究以定性分析為主,亟待進一步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對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的影響程度與機制開展更為深入的實證研究。
基于此,未來可以著力的方向是,從產業主體特質和鄉村產業發展階段特征出發,聚焦于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具體路徑,探究數字化對鄉村產業升級的影響機制。不僅要對數字化與鄉村產業轉型升級之間關系進行定性分析,更要進一步梳理鄉村產業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主體特質,厘清鄉村產業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量化分析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程度和數字化程度。通過質性研究、計量分析和模型模擬,深入揭示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理,系統探討數字化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具體推動機制。基于科學研究,才能夠提出數字化背景下促進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可行政策建議,促進鄉村產業在數字化浪潮中避開“數字鴻溝”,充分收獲數字紅利,加快數字化轉型進程,順利實現向數字化產業的轉型升級,促進鄉村產業在新發展格局中獲得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 殷浩棟,霍鵬,汪三貴.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現實表征、影響機理與推進策略[J]. 改革, 2020(12):48-56.
[2] 李川川,劉剛. 發達經濟體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及對中國的啟示[J]. 當代經濟管理,2022:1-10.
[3] 呂鐵. 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趨向與路徑[J].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19(18):13-19.
[4] 林毅夫. 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N]. 人民日報, 2022-3-28(11).
[5] 郭蕓蕓,楊久棟,曹斌.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鄉村產業結構演進歷程、特點、問題與對策[J]. 農業經濟問題, 2019(10):24-35.
[6] 劉明月,馮曉龍,冷淦瀟,等. 從產業扶貧到產業興旺:制約因素與模式選擇[J]. 農業經濟問題, 2021(10):51-63.
[7] 夏顯力,陳哲,張慧利,等. 農業高質量發展:數字賦能與實現路徑[J]. 中國農村經濟, 2019(12):2-15.
[8] 黃季焜. 以數字技術引領農業農村創新發展[J]. 農村工作通訊, 2021(05):44-46.
[9] 李春發,李冬冬,周馳. 數字經濟驅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理——基于產業鏈視角的分析[J]. 商業研究, 2020(02):73-82.
[10] 鐘真,劉育權. 數據生產要素何以賦能農業現代化[J]. 教學與研究, 2021(12):53-67.
[11] 余娟. 農村電商模式選擇對食品工業發展的影響分析[J]. 食品工業, 2020(6):283-286.
[12] 任航. 山東省農產品電商發展研究[D]. 山東農業大學, 2020.
[13] 馬曉河,胡擁軍. “互聯網+”推動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框架與政策設計[J]. 宏觀經濟研究, 2020(07):5-16.
[14] 肖若晨. 大數據助推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與實踐策略[J]. 中州學刊, 2019(12):48-53.
[15] 朱秋博,白軍飛,彭超,等. 信息化提升了農業生產率嗎?[J]. 中國農村經濟, 2019(04):22-40.
[16] 李瑾,馬晨,趙春江,等. “互聯網+”現代農業的戰略路徑與對策建議[J]. 中國工程科學, 2020, 22(04):50-57.
[17] 郭凱明. 人工智能發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勞動收入份額變動[J]. 管理世界, 2019, 35(07):60-77+202-203.
[18] MEHRABI Z, MCDOWELL M J, RICCIARDI V, et al. The global divide in data-driven farming[J].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1, 4(02):154-160.
[19] 曾億武, 宋逸香, 林夏珍, 等. 中國數字鄉村建設若干問題芻議[J]. 中國農村經濟, 2021(04):21-35.
[20] DIMAGGIO P, HARGITTAI E, CELESTE C, et al. From unequal access to differentiated us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on digital inequality[J]. Social inequality, 2004, 1: 355-400.
[21] GAO Y, ZANG L, SUN J. Does Computer Penetratio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18, 42(05):345-360.
[22] 白雪潔,宋培,李琳,等. 數字經濟能否推動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基于效率型技術進步視角[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41(06):1-15.
[23] WARNER K, WAEGER M. Buil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 ongoing process of strategic renewal[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9, 52(03):326-349.
[24] CENNAMO C, DAGNINO G B, MININ A D, et al. Manag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cope of Transformation and Modalities of Value Co-Generation and Delivery[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20, 62(04):5-16.
[25] 姚小濤,亓暉,劉琳琳,等. 企業數字化轉型:再認識與再出發[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3):1-13.
[26] KARAGIANNAKI A, VERGADOS G, FOUSKAS K.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sights from an open innovation initiative in fintech in Greece[C].//Mediterran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MCIS).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17.
[27] 劉海啟. 以精準農業驅動農業現代化加速現代農業數字化轉型[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19, 40(01):1-6+73.
[28] FITZGERALD M, KRUSCHWITZ N, BONNET D, et al. Embracing Digital Technology: A New Strategic Imperative[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14, 55(02):1-12.
[29] ILVONEN I, THALMANN S, MANHART M, et al. Reconcil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knowledge protection: A research agenda[J].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 2018, 16(02):235-244.
[30] LI 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model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 holistic framework and emerging trends[J]. Technovation, 2020,92-93: 102012.
[31] FARRELL M A, OCZKOWSKI E, KHARABSHEH R. Market orientation, learning orientation and organisational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 Logistics, 2008, 20(03):289-308.
[32] LOEBBECKE C, PICOT A. Reflections on societal and business model transformation arising from digitization and big data analytics: A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5, 24(03):149-157.
[33] TEECE D J.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echnologies, standards, and licensing models in the wireless world[J]. Research Policy, 2018, 47(04): 1367-1387.
[34] GREGORY V.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9, 28(02):118-144.
[35] LIERE-NETHELER K, PACKMOHR S, VOGELSANG K. Driver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Manufacturing[C].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2018, 3926-3935.
[36] 徐偉呈,范愛軍.? “互聯網+”驅動下的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J]. 財經科學, 2018(03):119-132.
[37] 李彥龍,彭錦,羅天正. 數字化、溢出效應與企業績效[J]. 工業技術經濟, 2022, 41(03):25-33.
[38] 許冠南,王秀芹,潘美娟,等. 戰略性新興產業國外經典政策工具分析——政府采購與補貼政策[J]. 中國工程科學,2016,18(04):113-120.
[39] 那丹丹,李英. 我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工具研究[J].行政論壇, 2021, 28(01):92-97.
[40] 楊巧云,梁詩露,楊丹. 國外政府數字化轉型政策比較研究[J]. 情報雜志, 2021,40(10):128-138.
[41] 邱澤奇,喬天宇. 電商技術變革與農戶共同發展[J]. 中國社會科學, 2021(10):145-166+207.
[42] EDLER J, GEORGHIOU L. Public procurement and innovation—Resurrecting the demand side[J]. Research Policy, 2007, 36(07):949-963.
[43] ROTHWELL R. Technology-Based Small Firm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otential: The Role of Public Proc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84, 4(04):307-332.
[44] 宋河發,穆榮平,任中保. 促進自主創新的政府采購政策與實施細則關聯性研究[J]. 科學學研究, 2011, 29(02):291-299.
[45] 趙春江,李瑾,馮獻. 面向2035年智慧農業發展戰略研究[J]. 中國工程科學, 2021, 23(04):1-9.
[46] 馬洪福,郝壽義. 產業轉型升級水平測度及其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以長江中游城市群26個城市為例[J]. 經濟地理 ,2017, 37(10):116-125.
[47] BETTIS R A, PRAHALAD C K. The dominant logic:retrospective and extens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6(01):5-14.
[48] YOO Y, HENFRIDSSON O, LYYTINEN K. Research commentary—The new organizing logic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 agenda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0, 21(04):724-735.
[49] HANELT A, BOHNSACK R, D MARZ,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21, 58 (05):1159-1197.
[50] ETTER M, FIESELER C, WHELAN G. Sharing Economy, Sharing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Digital 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9(04):1-8.
[51] 劉洋,李亮. 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全球視角與中國故事[J]. 研究與發展管理, 2022, 34(01):1-7.
[52] 萬文海,孫銳. 傳統產業借力O2O進行創新性轉型升級的路徑與政策研究——以福建鞋服產業為例[J]. 甘肅社會科學, 2016(03):250-255.
[53] 張翠菊,張宗益. 中國省域產業結構升級影響因素的空間計量分析[J]. 統計研究,2015(10):32-37.
[54] 高遠東,張衛國,陽琴. 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因素研究[J]. 經濟地理,2015, 35(06):96-101.
[55] 郭熙保,冷成英. 區位與家庭農場發展路徑:理論與實證[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20, 30(05):137-146.
[56] 彭靜,何蒲明. 要素稟賦與農業轉型升級研究——基于典型相關分析[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20, 41(02):116-121.
[57] 祁明德. 珠三角企業轉型升級績效研究[J]. 社會科學家, 2015(12): 68-71.
[58] 羅浩軒. 要素稟賦結構變遷中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研究[J]. 西部論壇, 2016, 26(05):9-19.
[59] JI Y, HU X, ZHU J, et al.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farmers' field production decision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3:64-71.
[60] 楊海鈺,馬興棟,邵礫群. 區域要素稟賦變化與農業技術變遷路徑差異——基于蘋果產業視角和7個主產省的數據[J]. 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 19(02):16-22.
[61] 林毅夫.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研究[J]. 現代產業經濟, 2013(Z1):18-23.
[62] 劉勇. 新時代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動力、路徑與政策[J]. 學習與探索, 2018(11):102-109.
[63] 李鵬飛. 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轉型研究——基于產業技術經濟特征的分析[J]. 當代經濟管理, 2017, 39(10):44-48.
[64] 郭克莎. 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趨勢與“十四五”時期政策思路[J]. 中國工業經濟, 2019(07):24-41.
[65] 肖昕,景一伶. 中國文化產業數字化政策及其策略研究[J]. 民族藝術研究, 2021, 34(03):130-136.
[66] 安同信,范躍進,劉祥霞. 日本戰后產業政策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經驗及啟示研究[J]. 東岳論叢, 2014, 35(10):132-136.
[67] 陳永清,夏青,周小櫻. 產業政策研究及其爭論述評[J]. 經濟評論, 2016(06):150-158.
[68] 孔祥智,周振. 我國農村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歷程、基本經驗與深化路徑[J]. 改革, 2020(07):27-38.
[69] 林毅夫. 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 [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70] STIGLITZ J E, LIN J Y, MONGA C. The Rejuven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M]. The World Bank, 2013: 24.
[71] WADE R. After the Crisi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Low-Income Countries[J]. Global Policy, 2010, 1(02):150-161.
[72] 錢學鋒,張潔,毛海濤. 垂直結構、資源誤置與產業政策[J]. 經濟研究, 2019, 54(02):54-67.
[73] 林毅夫. 經濟轉型離不開“有為政府”[N]. 人民日報, 2013-11-26(05).
[74] SOLOW R M. Wed Better Watch Out[J].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7(07): 36.
[75] JORGENSON, DALE W, KEVIN J, et 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 (02):109-115.
[76] DEICHMANN U, GOYAL A, MISHRA D. Will digital technologies transform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47(S1):21-33.
[77] FABREGAS R, KREMER M, SCHILBACH F.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agricultural advice[J]. Science, 2019,366(6471): y3038.
[78] 袁冬梅,魏后凱. 對外開放促進產業集聚的機理及效應研究——基于中國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J]. 財貿經濟, 2011(12):120-126.
[79] 魏后凱. “三化”融合加快推進智慧鄉村建設[J]. 農村工作通訊, 2019(06):22-23.
[80] 趙春江,高飛:加快數字技術應用于農業農村[N]. 農民日報, 2020-12-19(003).
[81] 劉誠,夏杰長. 數字經濟助推共同富裕[J]. 智慧中國, 2021(09):3.
[82] 宋以,陳圖. 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機理、問題與對策[J].晨刊, 2022(01):29-31.
[83] 楊佩卿. 數字經濟的價值、發展重點及政策供給[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0(02):57-65+144.
[84] HAILU B K, ABRHA B K, WELDEGIORGIS K A. Adoption and Impa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on Farm Income: Evidence from Southern Tigray, Northern Ethiop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 (IJFAEC), 2014, 2(04):91-106.
[85] MATT C, HESS T, BENLIAN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J].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2015, 57(05):339-343.
[86]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01):3-43.
[87] 林毅夫. 產業政策與我國經濟的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J].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 59(02):148-153.
[88] 彭超,劉合光. “十四五”時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形勢、問題與對策[J]. 改革, 2020(02):20-29.
[89] 陳一明. 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機制創新[J]. 農業經濟問題, 2021(12):81-91.
[90] 王瑜,汪三貴. 互聯網促進普惠發展的基本經驗:成本分擔與多層面賦能[J]. 貴州社會科學, 2020(11):132-140.
[91] 殷曉紅.應對新經濟挑戰的數字鴻溝[J]. 國際經貿探索, 2003(01):64-66.
[92] 劉合光. 激活參與主體積極性,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J]. 農業經濟問題, 2018(01):14-20.
[93] 張在一,毛學峰. “互聯網+”重塑中國農業:表征、機制與本質[J]. 改革, 2020(07):134-144.
[94] 李瑾,馮獻,郭美榮,等. “互聯網+”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的國際比較與借鑒[J]. 農業現代化研究, 2018, 39(02):194-202.
[95] 楚明欽. 數字經濟下農業生產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 理論月刊, 2020(08):64-69.
[96] 李谷成,蔡慕寧,葉鋒. 互聯網、人力資本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J]. 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22(04):16-23.
[97] 肖衛東,杜志雄. 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內涵要解、發展現狀與未來思路[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06):120-129.
[98] 劉合光,潘啟龍,謝思娜. 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中美農業產業關聯效應比較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 2012(11):4-10+20.
[99] 郭凱明,杭靜,顏色.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轉型的影響因素[J]. 經濟研究, 2017, 52(03):32-46.
[100] XIAO W, PAN J D, LIU L Y.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in the “new normal”: empirical test and determinants[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17,63(04): 1037-1058.
[101] 程國強. 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新階段與新機遇[J]. 中國鄉村發現, 2021(02):12-16.
[102] 趙成偉,許竹青. 高質量發展視閾下數字鄉村建設的機理、問題與策略[J]. 求是學刊, 2021, 48(05):44-52.
[103] 劉合光,樊琴琴,韓旭東. 鄉村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研究[J]. 農村工作通訊,2022(06):52-54.
[104] 胡艷,陳雨琪,李彥. 數字經濟對長三角地區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研究[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54(01):143-154+175-176.
[105] 周清香,李仙娥. 數字經濟與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內在機理及實證檢驗[J]. 統計與決策, 2022,38(04):15-20.
[106] NAMBISAN S, LYYTINEN K, MAJCHRZAK A, et al. 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 digital world[J]. MIS Quarterly, 2017, 41(01): 223-238.
[107] 彭超. 數字鄉村戰略推進的邏輯[J]. 人民論壇, 2019(33):72-73.
[108] 秦建群,戶艷領,李佩. 互聯網發展促進了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嗎?——中介機制與經驗證據[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41(06):26-35.
[109] 宋常迎,鄭少鋒,于重陽.? “十四五”時期數字鄉村發展的創新驅動體系建設[J]. 科學管理研究, 2021, 39(03):100-107.
[110] 高彥彥. 互聯網信息技術如何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J]. 現代經濟探討, 2018(04):94-100.
[111] DI MAGGIO P, HARGITTAI E. From the“Digital Divide”to“Digital Inequality”: Studying Internet Use as Penetration Increases [J]. Princeton: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Woodrow Wilson School,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1, 4(01): 4-2.
[112] BONFADELLI H. The Internet and knowledge gap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 17(01): 65-84.
[113] HARGITTAI E. 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 Mapping Differences in People's Online Skills[J]. ArXiv, 2001,cs.CY/0109068.
[114] 黃祖輝.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農業產業組織的變革與前瞻[J]. 農業經濟問題, 2018(11):61-69.
[115] 邱澤奇,張樹沁,劉世定,等. 從數字鴻溝到紅利差異——互聯網資本的視角[J]. 中國社會科學, 2016(10):93-115+203-204.
[116] 劉達禹,徐斌,劉金全. 數字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增長門檻還是增長瓶頸?[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41(06):16-25.
[117] 羅必良. 廣東產業結構升級:進展、問題與選擇[J]. 廣東社會科學, 2007(06):42-47.
[118] 杜志雄,羅千峰,楊鑫. 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特征、發展困境與實現路徑:一個文獻綜述[J]. 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21(04):14-25.
[119] 姚維瀚,姚戰琪. 數字經濟、研發投入強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41(05):11-21.
[120] 蔡延澤,龔新蜀,靳媚. 數字經濟、創新環境與制造業轉型升級[J]. 統計與決策, 2021, 37(17):20-24.
[121] LIU Y, WANG X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growth in the 1990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 16(04): 419-440.
[122] BRAUW A D, ROZELLE S.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19(02):320-335.
[123] 馬永斌,閆佳. 產融結合與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J]. 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7(03):110-114.
[124] 高彥彥,榮宇鵬,紀帥. 農村電商的農民增收效應估計——來自浙江省淘寶村鎮的證據[J]. 現代管理科學, 2021(02):112-120.
[125] BACH A, SHAFFER G, WOLFSON T. Digital human capital: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igital exclusion in low-income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 2013, 3(01): 247-266.
[126] 李輝,梁丹丹.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機制、路徑與對策[J]. 貴州社會科學, 2020(10):120-125.
[127] 金碚. 中國工業的轉型升級[J]. 中國工業經濟, 2011(07):5-14+25.
[128] GALLEGO J M, GUTIéRREZ L H, Taborda R.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Colombian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5, 51(03): 612-634.
[129] 龐瑞芝,張帥,王群勇. 數字化能提升環境治理績效嗎?——來自省際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41(05):1-10.
[130] 何宏慶. 數字金融助推鄉村產業融合發展:優勢、困境與進路[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 20(03):118-125.
[131]邱澤奇,李由君,徐婉婷. 數字化與鄉村治理結構變遷[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 42(02):74-84.
[132] 許竹青,鄭風田,陳潔. “數字鴻溝”還是“信息紅利”?信息的有效供給與農民的銷售價格——一個微觀角度的實證研究[J]. 經濟學(季刊), 2013 , 12(04):1513-1536.
(中文校對:李陽)
The Approach and Strategy for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n Digitalization Process: Background of Development and Literature Review
PENG Chao LI Tingting QI Xin MA Jiujie ZHU Tiehui CHEN Jueying LIU Heguang
(1.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2208;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3.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fields, all links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is influence also extends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top priorit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digitalization.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have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ization, wider enabling range and stronger innovation drive. It is urgent to study the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policy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ization, so as to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optimizing and expanding rural digital econom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uch as ignor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rural industry subjects, rarely considering the stage differenc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ack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subjects and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ge, focus on the specific path of rural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ization on rural industry upgrading.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rur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英文校譯: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