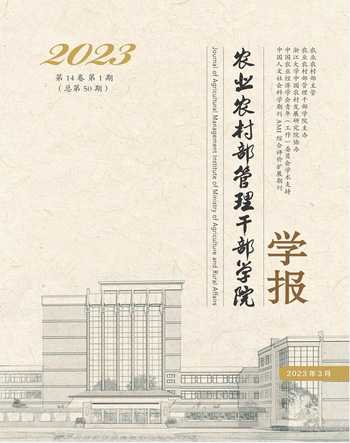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生產及作用機制研究
李朝柱 李榮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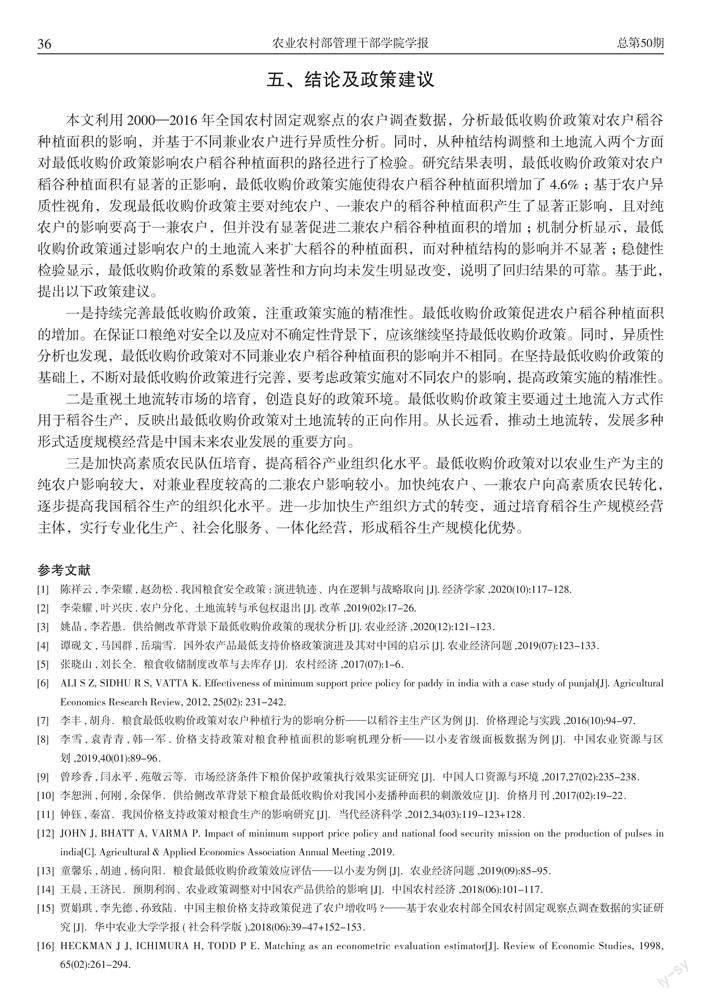

摘 要:基于2000—2016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數據,采用傾向得分匹配下的雙重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應模型,分析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研究表明: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有顯著正向影響,最低收購價政策實施后,政策組農戶稻谷種植面積比對照組增加4.60%;異質性分析顯示:最低收購價政策有效促進純農戶、一兼農戶增加稻谷種植面積;中介效應分析顯示:最低收購價政策通過土地流入影響農戶稻谷種植面積,其中介效應為20.07%。因此,在更加復雜的糧食安全形勢下,應繼續堅持和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提高政策針對性和實施對象的精準性。同時,要不斷加大土地流轉市場的建設,加快培育高素質農民。
關鍵詞:最低收購價政策;種植面積;作用機制;PSM-DID
一、引言
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糧食安全自古就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關乎一個國家最基本的經濟、社會、政治等制度安排,具有獨特的社會屬性。在中國特殊的人口和資源稟賦條件下,保障糧食安全是確保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永恒主題[1]。為保障糧食生產,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農民增收,21世紀以來,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針下,我國持續把促進糧食等大宗農產品增產放在農業發展優先位置,逐步減免直至取消農業稅,全面推行糧食市場化改革,建立對種糧農民的補貼制度,對主要糧食品種稻谷和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對主產區棉花、玉米、大豆、油菜籽實行臨時收儲等,逐步構建了增產導向的糧食支持保護政策體系。其中,2004年出臺的最低收購價政策備受關注。國務院在《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明確,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糧食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強調一般情況下糧食收購價格根據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當糧食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時,必要時可由國務院決定對短缺的重點糧食品種,在糧食主產區實行最低收購價格。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最低收購價政策逐漸偏離了政策初衷,通過穩定釋放價格引導產業發展的信號,成為刺激農民增加生產的政策工具,政策效應遠大于各類補貼政策對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作用[2]。
圍繞最低收購價政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學界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并沒有形成一致結論,主要形成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最低收購價政策調動了農戶糧食生產的積極性[3],促進了糧食種植面積的增加[4-5]。Ali等基于印度的農戶調查數據,研究得出最低收購價政策整體上促進了稻谷種植面積的擴大[6]。李豐等建立農戶供給行為模型,分析得出最低收購價政策對早秈稻、中晚秈稻、粳稻的種植面積均有顯著正向影響[7]。李雪等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發現,最低收購價政策通過提高農戶對價格的預期顯著促進了小麥種植面積增加[8]。曾珍香等基于糧食主產省的數據,分析發現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實施扭轉了執行區糧食種植面積持續減少的趨勢,促進了糧食種植面積增加[9];第二種觀點認為最低收購價政策對提高農戶糧食生產積極性影響不大,對穩定糧食種植面積效果并不顯著[10]。鐘鈺等利用稻谷主產區樣本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法研究得出,最低收購價政策對稻谷種植面積擴大并沒有明顯的激勵作用[11]。John等研究發現,盡管政府提高了豆類的最低收購價格,以鼓勵農民生產更多的豆類,但是并沒有取得明顯的政策效果[12]。第三種觀點認為最低收購價政策效應逐年變化,呈現出先增強后減弱的趨勢。童馨樂等研究發現最低收購價政策增加小麥種植面積的效應集中在政策實施初期,從長期來看,政策效應逐漸減弱甚至消失[13]。
總體而言,已有研究取得一系列極具價值的研究結論,在其基礎上仍存在進一步拓展的空間。第一,從研究內容來看,現有研究較為關注最低收購價政策實施的直接效果,而最低收購價政策最終需要通過作用于農戶實現其政策效能,對最低收購價政策如何影響農戶糧食生產的作用機制仍需深入分析;第二,從研究視角來看,農戶異質性導致最低收購價政策對不同兼業農戶糧食生產行為作用機制存在差異,有待補充農戶異質性視角研究;第三,從研究數據來看,已有分析以個別省份或少數省份的區域性調研數據為主,具有全國代表性樣本的研究成果較少,仍需進一步豐富。
中國是稻谷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稻谷作為最重要的口糧作物,在保障口糧絕對安全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因此,本文以稻谷最低收購價政策為例,使用2000—2016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數據,基于農戶視角,采用傾向得分匹配下的雙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深入分析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并基于不同兼業農戶進行異質性分析,為進一步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提供更精準的政策依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三、模型設定、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
(一)數據來源
1.傾向得分匹配下的雙重差分法(PSM-DID)
2.中介效應模型
(二)數據來源
考慮到最低收購價政策實施時間較長,分布省份較廣,需要全國性的、長期跟蹤的大樣本數據進行研究。因此,采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進行分析。該數據庫按類型和抽樣相結合選定村莊和農戶進行連續跟蹤調查,每年在全國31個省份調查300多個建制村,2萬多農戶。同時,該數據庫對農戶稻谷生產經營信息調查比較全面。本文主要使用了2000—2016年調查數據,研究中對數據集進行如下處理:一是將2000—2016年的農戶調查數據和村莊調查數據進行匹配,并以2003年的調查問卷為基準進行合并,保留稻谷種植戶;二是剔除稻谷生產、家庭特征等關鍵變量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有效樣本64 503個,分布于15個省份,如表1所示。
(三)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
農戶稻谷種植面積。選取農戶當年稻谷種植面積來表示,在回歸分析中采用對數形式。
2.核心解釋變量
是否實施最低收購價政策,使用虛擬變量形式進行識別。最低收購價政策2004年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黑龍江、吉林、四川等地實施,如果樣本農戶所在省份屬于上述地區且時間在2004年及以后,該變量取值為1;否則,該變量取值為0。
3.中介變量
種植結構和土地流入。其中種植結構使用稻谷種植面積占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比例來衡量,取值在0—1之間。土地流入使用二值變量來反映,如果農戶流入了土地則記為1,否則記為0。
4.控制變量
本文還控制了一些可能影響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變量,包括戶主特征(年齡、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勞動力人數、是否受過農業生產培訓、生產性資本)、其他政策(臨時收儲政策、補貼政策)、價格特征(替代作物價格、化肥價格)、村莊特征(村經濟發展水平、地勢)。各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四)平衡性分析
在使用PSM-DID分析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時,為了考察傾向得分匹配的效果,需要對匹配前后各變量的平衡性進行檢驗。表3報告了各控制變量的平衡性檢驗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到,T檢驗顯示,匹配后政策組和對照組大部分控制變量均不存在系統性差異,說明匹配效果較好。同時,匹配后模型總體擬合優度統計量Pseudo R2值顯著降低,LR統計量不再顯著①,表明匹配結果能較好地平穩兩組樣本控制變量的分布。因此,可以采用PSM-DID方法分析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
四、實證分析結果及解釋
(一)基準回歸
運用PSM-DID分析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同時為了對比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匯報了沒有加入控制變量的OLS估計結果。通過對比最低收購價政策估計系數的顯著性和大小,發現并未出現明顯的變化,說明回歸結果的可靠性。
表4中,模型(1)沒有控制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僅考慮最低收購價政策對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模型(2)加入影響種植面積的其他控制變量,并控制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以模型(2)為基準進行分析,回歸結果顯示最低收購價政策對稻谷種植面積有正影響,并在5%水平上顯著,估計系數為0.046。反映出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實施使農戶對稻谷生產有穩定的預期收益,降低了農戶的風險感知,調動了農戶從事稻谷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戶稻谷種植面積擴大。這一結論與李雪等的研究結果互相印證,即最低收購價政策能夠通過提高農戶對價格的預期增加糧食種植面積[19]。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看,勞動力人數對稻谷種植面積有顯著正影響,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稻谷生產是一項體力勞動,家庭勞動力人數越多,越有可能擴大稻谷種植面積。農業生產培訓對稻谷種植面積有顯著正影響,且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參加過農業生產培訓的農戶掌握更多農業生產技能,對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更加了解,對農業生產也更有信心,因此會擴大稻谷種植面積。替代作物價格對稻谷種植面積有顯著負影響,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可能的原因是替代作物的價格越高,在比較預期收益的情況下,農戶可能會減少稻谷種植,轉而種植價格更高的替代作物。補貼金額對稻谷種植面積有顯著正影響,說明補貼金額越高,農戶越有資金實力去流入土地和增加農業生產投資,從而擴大稻谷種植面積。村地形地貌對稻谷種植面積有顯著負影響,與平原和丘陵地區相比,山區土地細碎化更加嚴重,不利于規模化經營,種植稻谷的投入成本較高,不利于稻谷種植面積的擴大。
(二)異質性分析
上文僅分析了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影響的平均效應,而未考慮農戶的群體差異性,由于農戶異質性的存在,最低收購價政策對不同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可能并不相同。參考農業農村部合作經濟指導司的做法,按照家庭收入中非農收入的比重作為劃分兼業農戶的標準。定義上一年度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小于20%的農戶為純農戶,20%—50%的農戶為一兼農戶,超過50%的農戶為二兼農戶。從農戶兼業類型的視角來分析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影響。
表5列出了最低收購價政策對不同兼業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最低收購價政策對純農戶和一兼農戶稻谷種植面積有正向影響,且在5%水平上顯著。從估計系數來看,純農戶的估計系數為0.070,高于一兼農戶的0.056,說明最低收購價政策對純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要高于一兼農戶。一般來說,純農戶和一兼農戶仍然以農業生產為主,純農戶的收入絕大部分來自農業,而一兼農戶的收入一部分來自非農就業。相比較而言,純農戶更看重種稻收入,最低收購價政策實施后,使得農戶種稻收益更有保障,因此純農戶和一兼農戶會增加稻谷種植面積,且純農戶增加稻谷種植面積更大。最低收購價政策對二兼農戶稻谷種植面積影響為正,但并不顯著。由于二兼農戶的收入來源主要為非農收入,雖然實施最低收購價政策改變了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之間的比價,但由于非農收入的增加高于農業收入,因此二兼農戶也不會擴大稻谷種植面積。
(三)機制分析
上文分析了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得出最低收購價政策顯著促進了農戶稻谷種植面積擴大的結論。那么農戶擴大稻谷種植面積的途徑是什么。從理論分析得出,農戶可能通過種植結構調整和土地流入來擴大稻谷種植面積。接下來以種植結構和土地流入作為中介變量,來檢驗最低收購價政策擴大稻谷種植面積的作用機制。
1.種植結構調整的中介效應檢驗
選取稻谷種植面積占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比例來表示種植結構,取值在0—1之間,采用Tobit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從模型(4)中可以看到最低收購價政策對種植結構有正向影響,但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第一,稻谷是水田作物,區別于其他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稻谷生長過程中對灌溉用水的需求量比較大,如果該地區缺乏水源,即使稻谷的價格很高,也無法通過調整種植結構來增加稻谷的種植面積。此外,具備水源地區,如果其沒有完善的灌溉渠道,而要通過打井等方式來滿足稻谷生產過程中灌溉用水需求時,農戶也會在打井成本和種植結構調整獲得的收益之間進行衡量;第二,由于不同農作物和經濟作物之間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并不相同,有些甚至差異較大。農戶可能出于日常耕作習慣的路徑依賴以及資產專用性等原因不會輕易調整種植結構[20]。因此,種植結構調整在最低收購價政策擴大稻谷種植面積中并沒有起到中介作用。
2.土地流入的中介效應檢驗
由于土地流入的取值為二值變量0和1,采用Logit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從模型(7)中可以看到,最低收購價政策對土地流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336,通過求邊際效應得出系數為0.0504,即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實施使得稻農流入土地的概率增加了5.04%。從模型(8)中可以看到,在加入土地流入中介變量后,最低收購價政策和土地流入兩個變量均對種植面積產生了正影響,并在1%水平上顯著。根據中介效應的計算公式,如果三個系數均顯著,且的符號與相同,說明最低收購價政策通過土地流入影響稻谷種植面積的中介效應存在,由于比小,因此僅為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的大小,表明最低收購價政策對稻谷種植面積的增加有20.07%是通過土地流入引起的。最低收購價政策穩定了農戶種植稻谷的預期收益,從而促使有流入意愿、生產能力較強的農戶通過土地流入的方式增加稻谷種植面積,進而獲得更大收益。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驗證回歸結論,通過替換回歸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國家在出臺稻谷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中明確規定了執行預案的省份,沒在預案里的省份,其是否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則由省級人民政府自主決定。在其他省份中,廣東、浙江、福建三省緊跟國家的最低收購價政策,由省級人民政府自主出臺稻谷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因此將廣東、浙江、福建三省作為對照組可能會造成一定的估計偏差。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剔除廣東、浙江、福建三省樣本農戶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到,最低收購價政策仍然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產生正向影響,并在5%水平上顯著。最低收購價政策系數的顯著性和大小均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驗證了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00—2016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農戶調查數據,分析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并基于不同兼業農戶進行異質性分析。同時,從種植結構調整和土地流入兩個方面對最低收購價政策影響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路徑進行了檢驗。研究結果表明,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稻谷種植面積有顯著的正影響,最低收購價政策實施使得農戶稻谷種植面積增加了4.6%;基于農戶異質性視角,發現最低收購價政策主要對純農戶、一兼農戶的稻谷種植面積產生了顯著正影響,且對純農戶的影響要高于一兼農戶,但并沒有顯著促進二兼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增加;機制分析顯示,最低收購價政策通過影響農戶的土地流入來擴大稻谷的種植面積,而對種植結構的影響并不顯著;穩健性檢驗顯示,最低收購價政策的系數顯著性和方向均未發生明顯改變,說明了回歸結果的可靠。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持續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注重政策實施的精準性。最低收購價政策促進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增加。在保證口糧絕對安全以及應對不確定性背景下,應該繼續堅持最低收購價政策。同時,異質性分析也發現,最低收購價政策對不同兼業農戶稻谷種植面積的影響并不相同。在堅持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基礎上,不斷對最低收購價政策進行完善,要考慮政策實施對不同農戶的影響,提高政策實施的精準性。
二是重視土地流轉市場的培育,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最低收購價政策主要通過土地流入方式作用于稻谷生產,反映出最低收購價政策對土地流轉的正向作用。從長遠看,推動土地流轉,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是中國未來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三是加快高素質農民隊伍培育,提高稻谷產業組織化水平。最低收購價政策對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純農戶影響較大,對兼業程度較高的二兼農戶影響較小。加快純農戶、一兼農戶向高素質農民轉化,逐步提高我國稻谷生產的組織化水平。進一步加快生產組織方式的轉變,通過培育稻谷生產規模經營主體,實行專業化生產、社會化服務、一體化經營,形成稻谷生產規模化優勢。
參考文獻
[1] 陳祥云,李榮耀,趙勁松.我國糧食安全政策:演進軌跡、內在邏輯與戰略取向[J].經濟學家,2020(10):117-128.
[2] 李榮耀,葉興慶. 農戶分化、土地流轉與承包權退出[J].改革,2019(02):17-26.
[3] 姚晶,李若愚.供給側改革背景下最低收購價政策的現狀分析[J]. 農業經濟,2020(12):121-123.
[4] 譚硯文,馬國群,岳瑞雪.國外農產品最低支持價格政策演進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 農業經濟問題,2019(07):123-133.
[5] 張曉山,劉長全.糧食收儲制度改革與去庫存[J].農村經濟,2017(07):1-6.
[6] ALI S Z, SIDHU R S, VATTA K. Effectiveness of minimum support price policy for paddy in india with a case study of punjab[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Review, 2012, 25(02): 231-242.
[7] 李豐,胡舟.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對農戶種植行為的影響分析——以稻谷主生產區為例[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6(10):94-97.
[8] 李雪,袁青青,韓一軍. 價格支持政策對糧食種植面積的影響機理分析——以小麥省級面板數據為例[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9,40(01):89-96.
[9] 曾珍香,閆永平,苑敬云等.市場經濟條件下糧價保護政策執行效果實證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27(02):235-238.
[10] 李恕洲,何剛,余保華.供給側改革背景下糧食最低收購價對我國小麥播種面積的刺激效應[J].價格月刊,2017(02):19-22.
[11] 鐘鈺,秦富.我國價格支持政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12,34(03):119-123+128.
[12] JOHN J, BHATT A, VARMA P. Impact of minimum support price policy an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pulses in india[C]. Agricultural &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19.
[13] 童馨樂,胡迪,楊向陽.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效應評估——以小麥為例[J].農業經濟問題,2019(09):85-95.
[14] 王晨,王濟民.預期利潤、農業政策調整對中國農產品供給的影響[J].中國農村經濟,2018(06):101-117.
[15] 賈娟琪,李先德,孫致陸.中國主糧價格支持政策促進了農戶增收嗎?——基于農業農村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6):39-47+152-153.
[16] HECKMAN J J, ICHIMURA H, TODD P E.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8, 65(02):261-294.
[17] HIRANO K, IMBENS G.W, RIDDER G.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using the estimated propensity score[J]. Econometrica,2003, 71(04):1161-1189.
[18]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14,22(05):731-745.
[19] 李雪,袁青青,韓一軍.價格支持政策對糧食種植面積的影響機理分析——以小麥省級面板數據為例[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9,40(01):89-96.
[20] 許慶,陸鈺鳳,張恒春.農業支持保護補貼促進規模農戶種糧了嗎?——基于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的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20(04):15-33.
(中文校對:黃玉璽)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on FarmersPaddy Production and its Mechanism
LI Chaozhu LI Rongyao
(1.China Institute for R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22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National Fixed-site Rural Survey from 2000 to2016, the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PSM-DID)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under tendency score matching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on farmersrice acreag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rice acreag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rice acreage. The rice planting acreage of farmers in the policy group increased by 4.6%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effectively promotes pure farmers and part-time farmers to increase rice acreag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shows that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affects farmersrice acreage through land transfer-in, and its intermediary effect is 20.07%. Therefore, in the more complex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we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the policy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targe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of a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Keywords:?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planting acreage; mechanism of action; PSM-DID
(英文校譯: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