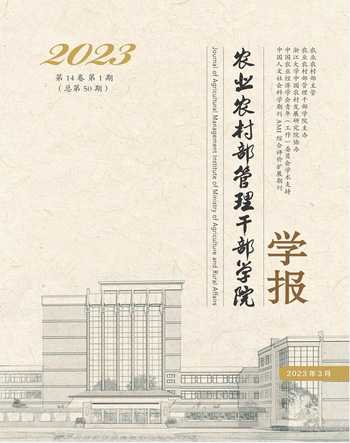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歷史演變、突出特征、邏輯理路及未來指向
李明星 馬永騰 任玉麗莉 羅曉宇
摘 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圍繞農村土地實施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意義的顛覆性改革舉措,最終構建起以集體所有和家庭承包經營為支撐的農村土地制度體系,并以此為基礎,持續推動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走向深入。本文立足對改革歷程的系統回顧,分析總結了貫穿改革始終的演進主線和突出特征,借助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范式對改革邏輯進行闡釋,分別將改革的動因、核心和方式錨定到基于交易成本考量、產權結構創新、制度變遷方式選擇之上。同時,以此為啟發,對未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價值取向和目標指向進行了展望,最終形成關于土地所有制形式、所有權主體、產權結構及權能、土地收益分配和土地管理模式等的預判,以期為國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價值參考。
關鍵詞:土地制度改革;歷史演變;突出特征;邏輯理路;未來指向
一、引 言
農村土地制度是我國農村改革最關鍵的部分之一。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針對農村土地制度實施了系列改革舉措,逐步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土地制度體系,并最終成就了當前農村發展的良好局面。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研究從未中斷,其中既有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有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思考,這些研究最終繪就成農村改革的理論版圖。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思想主線,貫穿在整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過程之中。同時,基于改革開放基本國策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探索的時代背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大量吸收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諸多合理成分,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嵌入了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范式。但是,在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給予價值指導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深入思考其面臨的現實問題,以便更好地對其進行創新改造與實踐運用。
二、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歷史演變
就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演變歷程來看,學術界存在不同維度的劃分,典型的有:“傳統集體化體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地三權分置”“平均地權、產權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集體所有、兩權分離→集體所有、三權分置”“分地→合地→承包→集中”“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家庭承包責任制→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村土地公有制度的初步形成→人民公社時期的土地制度→‘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形成時期→土地承包經營權穩定時期→‘長久不變和土地制度的動態穩定時期”等[1-5]。當然,在此不必贅述不同劃分標準的合理性。但總體而言,學界通識的原則都是以土地產權關系的調整為依據,農地制度的變遷都是圍繞著農地產權制度的改革[6],而土地產權又是中國百年農村制度變遷的核心所決定的[7]。鑒于此,筆者試從土地產權結構的變化,重新將其劃分為“‘集體所有制的穩固→‘兩權分離的成熟→‘三權分置的實踐”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穩固(1949 —1978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是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根本性和顛覆性演變的階段。這一時期的改革指向是農村土地的所有權,這不僅是土地制度的核心,也是后來其他相關制度改革的前提。
就時間跨度來看,經歷了近30年。首先,新中國成立初期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之前,農村土地政策主要還是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政策的延續和發展,以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發布《共同綱領》,決定逐步“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①為始,到1952年年底,連同老解放區,完成土地改革地區的農業人口已占全國農業人口總數的90%以上②為止,實現了農村土地地主私有制向農民私有制的調整。其次,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農村土地政策開始轉向集中化和集權化,以1953年2月中旬,黨中央正式發布《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明確提出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基本方針、政策和指導原則為始,到1962年2月中央出臺《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為止,有效實現了農村土地農民私有制向傳統集體所有制的轉變。最后是人民公社的調整到改革開放前期,以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為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并在中央層面引發關于“包產到戶”大討論為止,期間雖然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農村土地政策還是成功實現從傳統集體所有制向新型集體所有制的首次改造,“三級所有”和“恢復并適當擴大自留地”等政策得到了明確堅持。
(二)第二階段:“兩權分離”的成熟(1979 —2012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拉開改革開放的帷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也邁入新的歷史進程。這一時期的改革指向是農村土地的使用權,這是農村土地所有權的首要衍生權,也是農戶土地權益體現的主要依托。
就時間跨度來看,經歷了30多年。首先是改革開放戰略方針的確立到“包干到戶”普遍推開,農村土地政策主要集中于生產經營模式的深化探索,以1979年9月中央解除“不許包產到戶”的禁令為始,到1984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歷史性的最高峰為止,實現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和家庭包產經營的全面性融合,全國實行包產、包干到戶的生產隊占比達到99.96%[8]。其次是對“包干到戶”的開始反思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正式確立,農村土地政策開始側重于從所有權中分離使用權。以1985年我國糧食生產跌入低谷而引發農業生產矛盾為始,到1991年11月十三屆八中全會為止,實現了我國農村土地產權結構的首次分化,構建起“所有權+承包經營權”的兩權分離結構。再次,鄧小平南巡講話到對農村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經驗的總結反思,農村土地政策側重于各種經營制度上的創新實踐,以1992年決定對即將到期的農村土地承包權再延長30年不變為始,到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止,實現了對實施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歷史定性。最后,關于繼續穩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到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探索,農村土地政策開始面向實現與市場深度融合的再次創新,以1999年1月1日正式實施新的《土地管理法》并開啟我國農村土地的第二輪承包為始,到2012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賦予承包農戶的承包權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轉權,賦予流入土地的經營者抵押權和擔保權等為止,標志著農村土地制度即將開啟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三權分置”的再一次跨越。
(三)第三階段:“三權分置”的實踐(2013年以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提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步入深水區。這一時期的改革指向是農村土地的流轉經營和抵押融資等他項權利的賦予,同時也標定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未來方向。
就時間跨度來看,目前已歷經了近10年。首先,“土地經營權”的正式確立到“三權分置”政策的全面實施,農村土地政策圍繞對土地所有權的衍生權,重點是經營權進行放活,以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對土地所有權及承包經營權進行確認頒證為始,到2014年11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首次提出要“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為止,實現了農村土地權能體系的第二次歷史性重構。其次,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以來,農村土地政策將改革重心進一步擴大到除承包經營權之外的農村土地物權。以2015年初,根據中央要求和全國人大授權,國土資源部選擇全國33個地區進行“三塊地”改革封閉試點為始,到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訂完成并于2020年起正式實施為止,實現了對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的進一步強化,并同時實現了對農村土地所有權衍生的使用、經營、抵押等他項權能的全面激活。最后,2020年以來,伴隨制度層面的全面放活放寬,農村土地管理和利用全面走向市場化,產權交易與土地創新經營成為土地制度改革的下一步重點,對土地的產權管理逐步轉變為市場運營管理。
三、聚焦: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出特征
關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特征,學界從不同視角進行深入分析。就改革方式來看,認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模式多樣、進展各異、成效不一,但具有十分明顯的漸進性變遷特征[9];就改革內容來看,認為主要有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兩權分離”,國家、集體與農戶之間的合約議定,農地產權權能的明確與強化等[1];就改革的原則來看,認為是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基本方向,堅持因時制宜、循序漸進的工作方法,堅持以實現共同富裕為價值宗旨[10];就改革的目標來看,認為關鍵是要盤活農村土地資產,通過制度變革的力量將農村土地資產盡快轉化為土地資本[11];就改革的動力來看,認為土地改革以來各種農地制度創新形式的不同經濟績效都與產權清晰程度和實施機制有關[12]。而筆者補充認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特征不僅局限在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是彰顯于不同時期國家基于整體視角下對改革戰略選擇的價值考量,而這也構成了其主要特征。
(一)制度改革的總體特征
總體上看,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本上是在維護社會主義民主政權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之間進行階段性平衡,而結合上文梳理來看,明顯呈現從“重維護輕發展”到“重發展輕維護”,再到“重發展重維護”的總體特征。
重維護輕發展的特征。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解決農民土地訴求贏得了最廣大農民的支持,實施土地集體化防止了私有化,同時也在最大程度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但就其近30年的農村經濟發展而言,生產力并未實現質的提升,人民公社等組織體系更是降低了農業產出效率,使農民收入長期在低水平上徘徊[13]。因此,可以說這一階段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本上就是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甚至不惜以一定程度上的生產力犧牲作為代價。
重發展輕維護的特征。推動土地“包產到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實踐,其事實上對集體所有制表現形式有所放松,而農村土地的“兩權分離”實現和“三權分置”的探索,則更是為農村土地資產化打開了方便之門。雖然這一時期的農村土地政策招致諸多捍衛馬克思主義公有制思想的學者們的質疑[14],但國家的基本方向卻始終沒有動搖。而反觀這一時期的農村發展,農業產量穩步增加,糧食總產量跨過萬億斤大關,農機總動力增長5倍以上,農村基礎設施明顯加強,公路、電話、通電和電視信號等覆蓋率達到90%左右,生產條件和生活水平實現了跨越式提高,交通、教育、醫療衛生等服務覆蓋率基本達到80%以上①。因此,可以說這一階段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本上是要加快農業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故而以傳統土地集體所有制關系剛性的削弱作為條件交換。
重維護重發展的特征。以確權頒證進一步強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根本地位,同時也進一步強化農戶個體作為土地經營收益主體的合法地位。以土地市場化流轉交易試點改革暢通土地價值彰顯和資產、資本價值實現的方式與渠道,夯實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基礎,激發其內生潛能,從根本上改變三農的弱勢地位。這些措施既聚力于多所有權關系和主體的強化與維護,同時又聚力于對生產力和生產條件的優化提升。因此,可以說這一階段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根本上是為了將鞏固國家政權與發展農業農村生產力更好統一起來。
(二)改革特征的突出體現
基于農村土地制度在政權維護與生產力發展中不斷平衡的總體特征下,其還表現出諸多具體性的路線選擇特征。最典型的有以下三種。
往復式向螺旋式轉變。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對土地交易和家庭經營等方面的政策規制與制度約束。就土地交易而言,我國195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承認農民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但1956年及之后相繼頒發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等政策性文件,卻要求逐步實行以公社或生產隊為主體的集體所有制,明文禁止土地買賣和出租,并一直延續到1984年。198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之后的1986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做了相應表述,1988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則從法律層面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農村土地流轉經營再次被放開并一直延續至今。但這期間,尤其是1997年《關于進一步穩定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通知》和1998年《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政策文件,又對土地流轉做了一些方式和條件約束。就家庭經營而言,最早引進家庭經營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合作化后期,但很快受到“左”的思想路線的指責、批判和打擊[15]。后來由于“大躍進”對農村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按勞分田”“包產到戶”“分口糧田”等形式再度出現,但很快又遭到遏制,甚至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也仍然不被允許[16]。后來,一直到1979年9月中央才又正式解除“不許包產到戶”的禁令,但強調“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地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①。再后來,1980年5月,鄧小平對“包產到戶”明確表達了認可[17],而這最終也引發了黨中央的總結反思,并促成了政策表達。最后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所以,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充滿了反復性,但伴隨改革的發展,這種反復性最終演變成螺旋式上升。
單線程向多線程轉變。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對農村土地產權調整及權能賦予和新一輪的農村土地制度聯動改革上。就農村土地產權調整及權能賦予而言,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土地所有權的歸屬。新中國成立初期,在1950年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通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土地管理的法律——《土地改革法》,其頒布與實施被評論為“中國人民對于殘余的封建制度所發動的一場最猛烈的經濟的政治的戰爭”“將在實際上結束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質”②,其根本任務就是要將農村土地的所有權賦予農民個體。但之后,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尤其是“合作化運動”及“人民公社運動”期間,農民個體土地所有權又被收回而被賦予農民集體。接下來,盡管改革對土地所有權主體進行了適度分化,衍生了包括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在內的“三級所有”的主體結構,但對所有權的權能本身沒有動搖。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家庭經營模式被適度放寬,土地所有權開始實現“兩權分離”,而改革的重心也轉移到以承包經營關系為紐帶的使用權上。一直到黨的十八大,黨中央關于農村土地承包權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轉權賦予的政策出臺,“三權分置”政策理念推動改革開始同時面向農村土地多項權能的探索完善。就新一輪的農村土地制度聯動改革而言,主要是2015年關于農村“三塊地”改革試點的正式鋪開。這一次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相較于以往有明顯不同,其針對的“三塊地”屬性有明顯差異,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的涉及對象是集體經濟組織及其土地使用權,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涉及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并同時涉及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宅基地制度改革涉及農戶及其土地使用權。“三塊地”改革絕不可能僅僅依托對所有權、使用權或是他項權利的調整能夠實現,且每一項改革都無可避免地與另兩項改革密切關聯。所以,不難發現,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情況日益復雜化——從當初僅針對所有權抑或是使用權的單線程改革,到今天同步推進所有權、使用權及他項權利的多線程同步改革。
被動型向主動型轉變。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探索與全面推開、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的深化上。就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探索與全面推開而言,其本質是公社化運動后期“包產到戶”的進一步演變,而這種演變是有其時代必然性的。1958年前后,“公社化運動”和“共產風”進入高潮,但1959年到1961年的自然災害接踵而來,農業生產的物質積累迅速消耗殆盡,早期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優勢無法得到有效體現,全國人民的生活進入困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基層農民開始內生性地尋求解決辦法,“包產到戶”也就被孕育開來,但受當時國家政權基礎和對共產主義思想理念理解等方面的局限,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包產到戶”都無法得到認可,所以也就導致了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枚紅手印”改革故事的發生。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中央科學研判農村基層形勢,最終在1982年全面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性質[18],進而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就“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的深化而言,其本質是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進一步引導,而這種引導卻更多來自政策的或然性。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開以后,農村生產力得到快速提升,但與此同時,20世紀末的鄉鎮企業迎來了發展的小高潮,加上發展外向型經濟和加快城鎮化進程的國家戰略疊加,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農村首次出現土地閑置、拋荒等現象。在保證農村集體土地產權關系穩定和引導農民合理擇業就業的雙重考量下,1995年中央印發《關于做好1995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要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制度”,從而拉開了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序幕。所以,不難發現,同樣是對農村土地所有權派生權能的賦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明顯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被動激發式改革,而“三權分置”卻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主動引導式改革。事實上,如果將后來農村“三塊地”改革等也一并納入比較就更明顯。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之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經實現了從被動型向主動型的邏輯轉變,并一直延續下來。
四、闡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邏輯理路
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演變歷程和改革特征的梳理總結自然會衍生一個關鍵問題:貫穿改革始終的邏輯理路是什么?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對過去實踐的認真反思,更關系到對未來進程的選擇。而鑒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本身就是關于制度理論與經濟理論的融合實踐,故筆者嘗試以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來闡釋,以期獲得價值性的思想指導。事實上,學界已有研究也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范式的嵌入是合時宜的,這既源于改革開放戰略鋪開與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及傳播在時間上的同步[19],也源于“個人理性主義”假設暫時合理、邊際分析方法適于漸進式改革、中國經濟改革的后發性特征等因素[20]。不過,迄今為止新制度經濟學都還沒有形成獨立、完整而嚴密的理論體系[21, 22],但其已有的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有效支撐。
(一)改革的動因:基于“交易成本理論”的闡釋
一般來說,學界公認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范式是以“交易成本理論”為基礎的,注重制度和經濟增長的研究。“交易成本理論”由科斯最先創立,包括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其中,交易成本是與交易有關的制度運行成本,科斯定理則將其界定為引發產權關系界定的主要因素[23]。同時,交易成本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交易成本僅指交易過程中發生的費用,而廣義的交易成本則包括制度維持和制度變動的成本。在此,我們將用制度成本和制度變動的成本來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動因作出闡釋。
探析動因必然要立足于特定的起點,當然,這里所謂的起點是一個比較概念,相對于每一個新制度的誕生,其對應的舊制度就是改革的起點。對此,我們重點闡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的起點邏輯。如前文所述,對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而言,公社化運動的過分激進導致生產效率的低下可以說是其根本起點,“大躍進”“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調”的集體所有制模式下,國家要承擔勞動監督、生產部署和收益分配調節等諸多不具備主動趨向的制度建設與維系成本。而比較來看,適度放寬農村土地家庭經營,以讓渡超額勞動收益激發人的勞動積極性,將制度約束轉變為經濟激勵,則大大降低了國家進行社會管理的機會成本。對于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而言,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戰略之所需和離農群體土地權益保障之必要是其根本起點,家庭承包經營雖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土地單位面積產出效益不足,土地閑置、拋荒風險增加等社會性問題,在回歸集體經營的非現實情況下,國家就要承擔繼續維持農村土地產出效益和離地農民生活生產權益等社會性成本。而比較來看,放活農村土地流轉經營,依托社會資源對農村土地重新賦能,可以有效緩解政府公共保障的成本壓力。同時,這也有助于實現社會風險的分化處理,這一理論邏輯同樣契合當前新一輪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其實,面向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交易、農村土地征收和農村宅基地管理的創新改革,其基本原則仍然是基于對改革前后綜合效益與制度成本的比較,尤其是從被動型改革向主動型改革的轉變中,制度變動成本更是其做出變革與否決策的首要準則。因此,不難看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過程中重大制度調整的動因,本質上都是基于對“交易成本”的考量,當制度變動成本大于制度成本的時候,改革表現出重維護輕發展的往復式、單線程、被動型特征,當制度成本大于制度變動成本的時候,改革表現出重發展輕維護的螺旋式、多線程、主動型特征。
(二)改革的核心:基于“產權理論”的闡釋
產權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科斯對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的重大貢獻。繼科斯之后,德姆塞茨、波斯納、巴澤爾、諾思等進一步發展完善了產權理論[24]。尤其是德姆塞茨認為“權利之所以常常變得殘缺,是因為一些代理者(如國家)獲得了允許其他人改變所有制安排的權利” [25]。土地的產權安排,事實上就是基于交易成本考量下的具體手段。基于此,反觀我國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對改革核心內容的認識有所助益。
前文提到,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都是圍繞產權進行的。因為農村改革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關系[26]。對此,我們將重點關注基于改革而產生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就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而言,無論是出于何種解釋,都不可否認其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尤其是物質積累不足的階段很難跨越自身的三個內在矛盾[27],這被“產權理論”視為是缺乏效率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夕,從我國的社會發展實際也可以得到佐證。從這個層面上講,改變公有制低效性,可以算作是對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進行變革的底層動因。但顯然,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私有制是絕然不可行的,故如何對集體所有制進行準私有化的改造就成為改革的關鍵。就土地承包權而言,其產生于對土地集體產權的權能分化,是具有一定自物權屬性的且呈現具有普遍意義的物權化變遷趨勢的特殊的土地權利[28],現行《民法典》也將其界定為用益物權。事實上,用益物權是指非所有人對他人所有之物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雖然有別于物權的絕對性,但其中的物權成分在事實上已經是對公有制條件下的集體所有權私益化。就土地經營權而言,作為從承包經營權中分化而來的權能,盡管學界對其爭論不休,既有“物權觀”[29-31],也有“債權觀”[32],但事實上,就“三權分置”改革的創意及指向來看,明顯傾向于物權,其核心目的是要賦予土地經營權更多的財產權屬性。因此,不難看出:盡管針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并不是完全依照產權理論所推崇的私有產權論,但從集體所有權中不斷進行物權(用益物權)的改造,本質上還是立足于對產權理論關于產權界定的清晰度與生產效率成正相關的原理嵌套與修正。
(三)改革的方式:基于“制度變遷理論”的闡釋
制度變遷理論始見于20世紀70年代,由諾思基于經濟史學研究而最先創立,其核心內容包括:描述一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團體的產權理論、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變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識形態理論[33]。而伴隨其發展,制度變遷理論不斷豐富并形成了集“經濟增長推動說、利益格局調整說、技術決定論、制度變遷自我循環累積論、技術與制度互動論”等為一體的理論體系。結合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進程及特征來看,在改革方式的選擇上,無疑蘊含了十分豐富的理論精髓。
事實上,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總體上可以概括為經歷了所有權制度變革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體系重構兩個大的跨度,但這兩次跨度卻表現出十分明顯的方式差異。就所有制變革而言,其主導力來自中央政府,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以國家政策、行政命令或法律法規為依托的[34]。這期間,尤為明顯的政策舉措就包括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以及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項運動完全都是基于行政命令而完成的,但“土地改革”運動表現得相對激進,而“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運動”相對舒緩,盡管期間也因政治號召等原因表現出階段性的激進。究其深層原因來看,強制性是由于階級關系與利益格局的完全契合,代表工農無產階級利益的新生社會主義政權天然地要沖擊半封建體制,故土地農民私有化能獲得最廣大群體的絕對性支持。但土地農民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轉變就存在一定的個人利益約束,故農民對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積極性相對就弱一些。就土地承包經營權體系重構而言,雖然其主導力也來自中央政府,但在前文特征分析中已有闡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質上是一種被動型改革,而中央政府的主導力事實上是對這種改革的修正與維系,屬于誘致性的。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當時環境下體現出超越公社化體制的優勢,故變革呈現激進的態勢。不過,進入21世紀之后,尤其是在土地“三權分置”探索階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些弊端暴露出來,農民追求經濟效益的目的與當時制度的適配性降低,但由于這些弊端暫時尚未觸及農民個體的深層利益,故新的改革進程開始進入平緩期。因此,不難看出:我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總體上是沿著利益格局調整和助力經濟發展進行推動的,并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通過強制性與誘致性、激進式與漸進式的錯位選擇來實現的,表現為“強制性激進式→強制性漸進式→誘致性激進式→誘致性漸進式”的規律[35],客觀上是符合“制度變遷理論”的基本范式的。
五、展望: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創新的未來指向
筆者認為,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演變回顧,以及改革的特征梳理和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闡釋,基本上可以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未來指向作出總體預判。總體上講,未來將繼續并始終立足于集體所有制基礎,通過豐富產權結構和創新權能實現方式來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進而更好地保障以土地為紐帶的相關主體權益。具體來看,將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基本制度不變
當前,有很多學者就第二步農村土地改革的突破口主張通過調整土地所有制關系來實現,并形成了“以國有制取代集體所有制”“以私有制取代集體所有制”“在堅持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完善之”三種代表性觀點[36]。展望未來,應當堅持集體所有制基本制度不變的觀點。原因有三:其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符合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基本路線。一方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制度。其中,社會主義是靈魂,中國特色堪稱血肉。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雖然其允許一定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存在,但本質上是與私有制不相容的,這是共產主義最終目標和主旨任務所決定的,不允許也不可能改變;另一方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國一以貫之的經濟社會建設基本路線,其核心表征就是對廣大勞動人民切身利益的有效回應,將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所有的土地歸還農民集體是黨獲得群眾擁護的基礎,這個基礎絕不能因為時代的發展而有所改變。其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改變不具有成本收益的經濟性。從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范式來思考,一方面,農村土地私有化將面臨的首個問題就是土地產權分割的標準設定與形式選擇,而在已經成型的集體所有制現狀下,無論誰來執行這一決策,都毋庸置疑會面臨包括信息、議價、決策等方面的高額成本;另一方面,農村土地國有化又將更加虛化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系,既降低了農民的土地權益獲得感,也限制了農民土地的自主經營權;此外,無論是私有化還是國有化,都會因為土地權益的落差變化而引致城鄉關系的尖銳對立。因此,從任何角度來比較,對現行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進行變革都是不經濟的行為。其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改變可能帶來更大的土地經營管理問題。如果是實行私有化,那么,政府實施土地用途管制的法律依據將受到巨大挑戰,農村土地利用將更趨于隨意化、亂序化。而如果是實行國有化,那么,就我國的地理條件來看,尤其是山區地帶,顯然是不利于集中經營管理的,而政府要行使土地管理權,將面臨巨大人力和財力投入的壓力。
(二)土地所有權主體組織形式不斷創新
事實上,雖然比較來看,現行的集體所有制是農村土地制度安排的優選,但這并不代表就是有效和完善的,理論界對其進行的最廣泛而顯著的詰難就是所有權主體的虛位甚至是缺位[37-39],進而引發對農民權益侵犯的問題。因此,如何實現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具象化、明確化將是當前及今后改革的必然任務,而其根本又在于對“農民集體”這一組織形式的創新。展望未來,主要是完成三個關鍵任務:其一,推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重建。將面向破解“農村集體組織”概念的泛化、模糊化等問題,圍繞起點公平的邏輯,逐步開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重構工作,準確厘定基于生產合作和生產要素聯合的農民合作組織差異,劃清農民專業合作社與農民經濟合作社的邊界,通過民主決策程序明確并制定成員標準,組建由確定對象組成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并行使合法權利。同時,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按成員數進行土地股份權利劃分。其二,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變更。將面向破解集體所有制條件下成員追求自身利益與以集合方式共同占有財產之間的矛盾,圍繞過程公平的邏輯,逐步開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動態變更機制的創新探索,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退出機制,在確保集體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合理保障退出成員的權益。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建立之后,其管理將極大可能轉向現代企業制度,原則上實現成員靶向向股權靶向的轉變。其三,創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市場銜接機制。破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于特殊主體形式下的市場交互壁壘,圍繞結果導向的邏輯,不斷探索適合不同情況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運營代理模式。可以借鑒市場化公司的人事管理機制,并圍繞“委托-代理”機制建立法人代表和職業經理人管理制度,創新性地規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從事市場運營的能力素養短板。
(三)土地產權結構及權能演化趨向完善
從整個土地制度改革的演進規律,以及當前新一輪土地制度改革的任務指向可以看出,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在產權上的作為,必然是繼續探索基于產權衍生的權能演化與完善。統而言之,就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基礎上,繼續沿著產權分割、產權明晰、產權流動的路徑推進。未來農村土地產權結構及權能演化必然會呈現多個維度的完善與發展:其一,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將衍生出更多其他權利。事實上,無論是就集體所有的公有權屬性,還是按照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農村集體土地都不具備一般意義上的市場化交易基礎。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土地價值的顯性化不僅依賴于其物質產出功能,同樣依賴于特定的產權交易基礎。從這個層面上看,未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要聚力在土地集體所有權基礎上進行可交易產權的衍生,尤其是衍生出更多物權屬性的新型產權約束。其二,土地的用益物權將呈現多元復合。雖然改革將會面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衍生產權方向演進,但這并不代表著衍生權將會具有絕對的完全權屬性,畢竟所有權的集體公有屬性已經對這一取向進行了限制。不過,最大程度上完善衍生權的權能,尤其是面向用益物權的方向完善則是必要的。目前來看,只有用益物權的權能才能夠較好地規避所有權約束與其他功能性物權實現的矛盾,才能確保衍生性土地物權的邊界清晰但又不完全脫離于土地所有權主體。其三,土地產權權能實現形式將更加創新。結合改革的歷史經驗來看,土地承包權實現了土地家庭經營,進而催生了土地使用權權能的實現,土地經營權推動了土地流轉,進而保障了土地收益權權能的實現,這一過程清晰地顯示了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不斷強化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利[4]。而筆者認為,伴隨國家公共管理智能和社會保障能力的完善與提升,包括繼承、抵押、作價、入股、托管等在內,更多的土地發展權能實現形式將陸續呈現。對于這一點,當前試點開展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實際上已經較大程度體現了這種趨向。
(四)土地收益及分配機制更加復雜多元
鑒于農村土地產權結構的豐富演化,未來農村土地勢必成為越來越多利益相關方的紐帶,這就自然會引發關于土地收益調節機制的改革創新。而目前來看,學界已有諸多關于宅基地資本化、土地流轉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調節的研究[40-42],主要關注的是對國家、集體和農戶三方權益的平衡。基于此,筆者分析認為,未來改革將聚力幾個方面的突破:其一,對農村土地發展投入的權責劃分。事實上,農村土地收益分配問題的由來主要是對土地發展投入成本的爭議,因為現行制度條件下,土地發展潛力是政府管理及公共投入、集體經濟組織產權讓渡、市場及個人經營行為等合力實現的,多元投入的邊界不清自然導致土地收益分配缺乏明確標的。因此,未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應當要面向土地投入權責邊界劃清著力。其二,對農村土地增值收益核算體系的建立。通識而言,收益分配應當是建立在對成本的扣除,也就是增值收益部分。但農村土地增值收益核算還面臨成本的來源、構成和表現形式復雜的限制,而在基層財會系統不健全的情況下,這更是一筆糊涂賬。因此,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核算體系將是一個重點任務。其三,對農村土地收益分配標準及形式的創新。實際上,這個問題是上述問題的衍生。農村土地收益不僅表現為貨幣表現形式,往往還有包括風貌改造、人文提升、生產生活條件優化等非量化表現形式,如何將這些收益納入統一的成本扣除及核算體系,將是今后改革要進一步深入探索的重要內容。
(五)土地管理從產權側重轉向利用側重
基于上述四個方面趨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未來農村土地的產權賦予及權能體系將會越來越完善,這就促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個體擁有更多土地發展的自主權。換言之,農村土地開發利用將更多由產權主體決定,這就對傳統以產權收緊作為手段的土地管理職能提出挑戰。鑒于此,筆者認為未來農村土地管理將實現邏輯轉變,尤其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弱化產權約束而強化產權權能服務。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產權界定越清晰越有利于發揮市場作用,進而降低交易成本。伴隨我國農村產權體系的日益健全,政府將逐步退出產權干預,轉而為產權市場化交易等提供服務,以確保產權權能實現,保障產權主體的合法權益。其二,強化土地規劃和利用管控。由于產權賦予讓產權人擁有更多的土地開發利用自由空間,就很容易引致土地用途隨意變更,尤其是可能會造成基本農田和生態用地被侵占。對此,國家應當提升國土空間規劃的合理性,注重與地方產業和群眾生產生活的適配,并強化土地利用管控,完善多種有效措施與手段,讓農村土地保護與產權主體權益保護有機融合。其三,創新完善農村土地利用保護的立法規制。未來我國的農村土地管理立法立規將重點指向土地用途管制,著力在保障土地產權權能自由前提下進行開發利用引導,不斷深化國家土地立法研究,深入探索相關法理及立法闡釋,進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好踐行依法治國、依法管土的經濟社會發展理念。
六、結語
土地是財富之母,是立國之基、安邦之要、富民之本。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是顯著的,獲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面臨的問題也是不能回避的。誠然,基于特殊的歷史契合,改革進程中無不滲透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其為我國改革實踐提供了有益的指導。不過,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立論基礎仍然是理性經濟人假設,具有濃厚的資本主義意識特征,其私有化的價值導向更是有悖于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演變的必然性歷史邏輯,難以恰適我國在社會制度改革變遷過程中的社會主義共同價值取向。因此,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我們既要善于吸收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成分,注重階段性使用其理論工具,同時更要提防其價值迷惑,時刻謹記以馬克思主義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行修正,讓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在我國國情環境下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益服務。
參考文獻
[1] 劉守英.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三權分置[J].經濟研究,2022,57(02):18-26.
[2] 朱曉哲,劉瑞峰,馬恒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歷史演變、動因及效果:一個文獻綜述視角[J].農業經濟問題,2021(08):90-103.
[3] 劉乃安.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演變及其特點分析[J].農業經濟,2017(07):75-77.
[4] 顧鈺民.建國60年農村土地制度四次變革的產權分析[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04):72-76.
[5] 孔祥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形成、演變與完善[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6(04):16-22+2.
[6] 黃祖輝,王朋.我國農地產權制度的變遷歷史——基于農地供求關系視角的分析[J].甘肅社會科學,2009(03):1-5.
[7] 溫鐵軍.重新解讀我國農村的制度變遷[J].中國國情國力,2000(04):35-36.
[8] 王志成,史學軍.制度變遷與中國改革[J].經濟學家,1998(05):13-17.
[9] 郭曉鳴.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需求、困境與發展態勢[J].中國農村經濟,2011(04):4-8+17.
[10] 范丹.農村土地制度:變遷歷程、基本特征與經驗啟示——基于百年黨史的視角[J].農業考古,2021(04):86-94.
[11] 吳曉華.改革農地制度 增加農民收入[J].改革,2002(02):119-124.
[12] 袁鋮.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一個產權的視角[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05):18-22+109+142.
[13] 常明明.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經濟行為研究[J].中國農史,2020,39(04):61-71.
[14] 黃道霞.堅持和反對“家庭承包經營”的斗爭歷程[J].支部建設,2002(04):37.
[15] 周其仁.家庭經營的再發現——論聯產承包制引起的農業經營組織形式的變革[J].中國社會科學,1985(02):31-47.
[16] 許人俊.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爭論中艱難推進[J]. 中國糧食經濟, 2012.
[17] 張學兵.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J].中共黨史研究,2018(10):39-49.
[18] 舒展,羅小燕.新中國70年農村集體經濟回顧與展望[J].當代經濟研究,2019(11):13-21.
[19] 楊德才,郭婷婷,唐悅.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改革的推進[J].華東經濟管理,2014,28(03):1-6.
[20] 榮兆梓.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為什么是適用的[J].經濟學家,2004(02):17-22.
[21] 張亦工.交易費用、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透視[J].東岳論叢,2000(05):33-36.
[22] 苗金萍.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述評[J].甘肅科技縱橫,2004(06):104-106.
[23] 彭真善,宋德勇.交易成本理論的現實意義[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6(04):15-18.
[24] 袁慶明.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界定理論述評[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8(06):25-30+142-143.
[25] 鄧大才.通向權利的階梯:產權過程與國家治理——中西方比較視角下的中國經驗[J].中國社會科學,2018(04):42-66+205.
[26] 蓋軍.中共關于農民土地所有權實行公有的錯誤及糾正與共產國際[J].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01):9-15.
[27] 劉世錦.公有制經濟內在矛盾及其解決方式比較[J].經濟研究,1991(01):3-9.
[28] 錢忠好.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產權殘缺與市場流轉困境:理論與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2002(06):35-45+154-155.
[29] 靳相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法律性質及其發展趨勢[J].中國農村經濟,2001(02):23-26.
[30] 陶鐘太朗,楊遂全.農村土地經營權認知與物權塑造——從既有法制到未來立法[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02):73-79+127.
[31] 丁文.論“三權分置”中的土地經營權[J].清華法學,2018,12(01):114-128.
[32] 單平基.“三權分置”中土地經營權債權定性的證成[J].法學,2018(10):37-51.
[33] 馬廣奇.制度變遷理論:評述與啟示[J].生產力研究,2005(07):225-227+230-243.
[34] 徐建飛.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多維表征[J].學術探索,2018(10):91-98.
[35] 劉廣棟,程久苗.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理論和實踐[J].中國農村觀察,2007(02):70-80.
[36] 靳相木.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研究的述評[J].中國農村觀察,2003(02):14-24.
[37] 王洪友,鄒麗萍.論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主體虛位性[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5(01):24-26.DOI:10.16523/j.45-1319.2005.01.006.
[38] 宋旭明.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之積弊及其改革[J].江西社會科學,2009(05):177-181.
[39] 孟勤國.論新時代農村土地產權制度[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8(01):11-21.
[40] 朱新華,張金明.農村宅基地資本化及其收益分配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14(05):73-76.
[41] 聶英,聶鑫宇.農村土地流轉增值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8(03):122-132.
[42] 劉曉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20(10):137-144.
(中文校對:丁立江)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cal Evolution,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Logical Path and Future Direction
-Based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ory Paradigm Perspective
LI Mingxing MA Yongteng REN Yulili LUO Xiaoyu
(1.School of Economics,Sichuan University,Sichuan 610041;? 2.School of Economics,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nzhou,730000;
3.Sichuan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 LTD, Chengdu, 610066;
4.CNpC Chuanging Drilling Engineering Co. LTD, 610000)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subversive reform measures with epochal significance around rural land, and finally built a rural land system supported by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household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on this basis,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form process,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line of evolution and prominent features throughout the reform, explains the reform logic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anchors the motivation, core and mode of reform on the basis of transaction cost considerations,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ode sel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nspired by this, this paper looks forward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arget orientation of the future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in China, and finally forms a preliminary judgment on the form of land ownership, the subject of ownership,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income and the land management model,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value reference for the na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land system reform; historical evolution;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logical path; future direction
(英文校譯: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