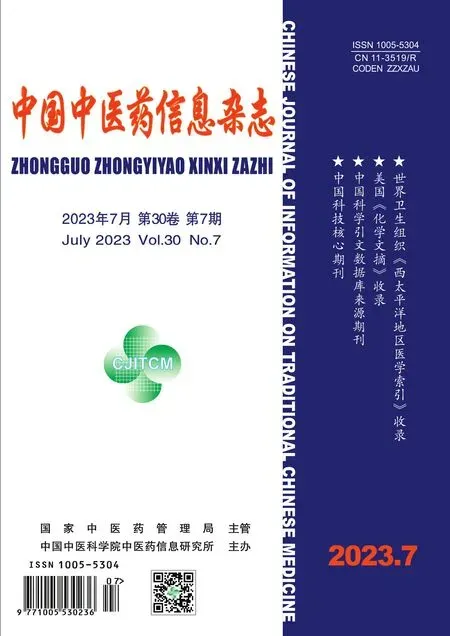國醫(yī)大師王慶國“扶正祛邪、調樞守神”法治療胃癌前病變思路
邵威 ,馬小娜 ,邵奇 趙京博 王曉慧 ,指導:王慶國
1.北京中醫(yī)藥大學,北京 100029;
2.北京中醫(y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yī)院,北京 100029
胃癌前病變(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rcinoma,PLGC)是指胃黏膜的異型增生和腸上皮化生,主要伴存于慢性萎縮性胃炎(CAG)。中華醫(yī)學會消化內鏡學分會調查顯示,我國慢性胃炎患者中,CAG診斷率為25.8%,腸上皮化生患病率為23.6%,異型增生患病率為7.3%[1]。
根據PLGC 臨床上腹部脹滿疼痛、噯氣、納差、消瘦等主要表現,可將其歸屬于中醫(yī)學“嘈雜”“痞滿”“胃脘痛”等范疇。《傷寒論》瀉心劑相關條文為PLGC治療提供了開拓性的思路和方法。中醫(yī)學從整體觀出發(fā)進行辨證論治,不良反應小,為臨床治療PLGC提供了方案。PLGC發(fā)病多與飲食不節(jié)、勞倦太過、情志不暢、先天稟賦有關,《靈樞·百病始生》謂“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祛邪不能脫離扶正,扶正能調整機體的陰陽平衡,提高機體的抗病能力;扶正不能忘記祛邪,祛邪能消除致病因素,故前人有“正足邪自去”“邪去正自安”之說。《靈樞·九針十二原》有“粗守形,上守神”,針對PLGC的病機,應治以調暢肝膽、脾胃之樞,以守其神,形神兼顧。
王慶國教授為第四屆國醫(yī)大師,北京中醫(yī)藥大學終身教授、主任醫(yī)師,博士生導師,第五批全國老中醫(y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從醫(yī)50余載,學驗頗豐。王教授精通傷寒、金匱學說,臨床擅長應用柴胡劑、苓桂劑、瀉心劑等類方治療消化系統(tǒng)疾病。王教授認為,PLGC發(fā)生發(fā)展皆由肝膽、脾胃樞機不利引起,因其病程綿延漫長,故正虛邪實并見。余有幸侍診于側,獲益匪淺。茲結合隨師體驗,對其治療PLGC思路整理如下。
1 扶正祛邪
脾胃為后天之本,因此PLGC潛移默化地影響人體各個器官系統(tǒng)。中醫(yī)學以哲學二分法方式,概括性地將治療方向分為正與邪兩方面,有助于從整體角度辨析病勢,為治療奠定基礎。“正氣內存,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王教授認為,PLGC病情綿延漫長,會導致正氣虧虛,兼有邪氣盛實,臨證應扶正祛邪貫穿治療全程。
1.1 扶正為主,脾胃優(yōu)先
脾主運化水谷精微,為“氣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脾氣充盛,氣血津液得以化生,五臟六腑得以濡養(yǎng),人體才能正常運行。PLGC患者因病情遷延不愈,致脾運失常,胃納失司,納運失常致升降失和,中焦失暢,食入難化,水谷精微不化,氣血生化乏源,胃體失于營養(yǎng),漸而枯萎,終致脾胃虛弱。王教授認為,PLGC的演化過程取決于正氣盛衰。脾胃虧虛,運化無力,氣血生化無源,正氣不足,邪有可乘,則PLGC繼續(xù)發(fā)展;脾胃充盛,氣血津液充盈,正盛邪退,可阻止甚至逆轉疾病惡性進展,因而顧護脾胃尤為重要。
腸型胃癌疾病進展模式恰是正不勝邪、邪毒內聚的結果,故辨治常以顧護脾胃為第一要義,調補氣血陰陽,扶助正氣。張元素言:“壯盛人無積,虛人則有之,故養(yǎng)正則邪自除。”因此,對正氣不足的PLGC患者應治以健脾和胃、益氣養(yǎng)陰,王教授常用黃芪、人參、太子參、白術益氣健脾;當歸、白芍、甘草、大棗養(yǎng)血和胃;附子、肉蓯蓉、淫羊藿、仙茅溫補陽氣;沙參、麥冬、生地黃、石斛養(yǎng)陰益胃。
1.2 權衡力度,活血解毒
《丹溪心法·六郁》言:“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王教授認為,由于內外病因的影響,臟腑氣機不通致邪毒內生,故以有形瘀血、熱毒之邪為主要病理因素。《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余,是其義也。”邪之屬性既明,遂遵經旨而予以消除。
1.2.1 活血化瘀
《臨證指南醫(yī)案·胃脘痛》言:“初病在經,久病入絡。”王教授認為,PLGC的發(fā)展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病久由氣及血,氣血失和,由經及絡,入絡成瘀;或因病情發(fā)展加劇,常伴有不同程度瘀滯。可見胃脘部疼痛,痛有定處而拒按,舌質黯或舌下脈絡瘀滯,脈象芤澀。同時,PLGC是以胃黏膜血流和微循環(huán)障礙為基礎引發(fā)。胃鏡下所見的胃黏膜糜爛、紅斑、血管顯露,都與瘀密切相關。故在辨證論治基礎上,王教授常加入三棱、莪術、丹參、延胡索等活血化瘀之品,對促進胃黏膜血流、改善微循環(huán)及促進病灶恢復有良好效果。PLGC伴胃出血者,可酌加三七粉、仙鶴草等活血止血之品,以通暢血脈,止血不留瘀。
1.2.2 清熱解毒
現代醫(yī)學認為,幽門螺桿菌(Hp)是導致PLGC的主要因素。Hp感染誘發(fā)并促進了從慢性淺表性胃炎到胃癌的腸型胃癌疾病進展模式全過程[2]。王教授臨證發(fā)現,感染Hp者以脾胃濕熱型最為多見,Hp感染可歸為邪客于胃,影響中焦氣機升降,運化失常,日久則蘊生濕熱。苦寒清熱之品具有瀉火解毒、清熱利濕的作用。王教授在辨證論治基礎上常加入針對Hp的清熱解毒類藥物,如黃連、紫花地丁、黃芩、白花蛇舌草、蒲公英、連翹等,以發(fā)揮抗菌抑菌作用[3]。
王教授臨證經驗示,方中酌加活血解毒等祛邪之品,往往收效更佳。因PLGC有較高癌變風險,王教授常佐具有抗癌功效的半枝蓮、白花蛇舌草、石見穿等,以達到“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目的。
2 調樞守神
人體內環(huán)境平和是維持健康的前提條件,其中又以氣的正常運行為核心。《素問·六微旨大論篇》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王教授認為,PLGC常由飲食失節(jié)、工作勞累、精神緊張、寒涼誤治導致中焦與少陽樞轉失常,氣機開闔不利而誘發(fā),故當以調樞守神為法治療,以恢復氣機之升降出入。
2.1 疏肝利膽寧神,調暢肝膽之樞
肝主疏泄,脾主運化,木疏土運與氣機的條暢、水谷的輸轉關系密切。肝失疏泄,木不疏土,則脾胃受病。王教授認為,PLGC的發(fā)展是由于正虛致氣機無力運轉,加之有形實邪阻滯則,二者互為影響,易形成惡性循環(huán),故疏調氣機勢在必行。《素問·陰陽離合論篇》有“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劉渡舟先生認為,“少陽樞機具有疏通、調節(jié)表里內外的作用,樞機利,表里之邪得以透達”[4],少陽能樞達氣機,為表里、陰陽、情志之樞紐,因此調氣必調樞。臨床對于癥見胃脘脹滿、食欲不振、情志不舒,或有脅肋脹滿、善太息,舌淡、苔薄白,脈弦或緊者,王教授常以融小柴胡湯與桂枝湯二者之長的柴胡桂枝湯作為主方加減化裁,治以疏利肝膽氣機,調和脾胃氣血。方中以桂枝、白芍、生姜、大棗、甘草之桂枝湯調和脾胃、氣血、陰陽;以柴胡、半夏、黃芩、人參之小柴胡湯和解少陽、宣展樞機。肝主情志,藏血舍魂;膽主決斷,與心主神志密切相關。王教授認為,以柴胡桂枝湯治療PLGC,調暢少陽樞機,可以起到形神同治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患者的緊張情緒,以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2.2 辛開苦降甘補,恢復脾胃之樞
脾居中焦,其性主升,又為陰土,易損陽氣;胃主受納,其性主降,又為陽土,其性主燥,最易受熱邪影響而耗傷胃津,脾升胃降,共為升降之樞。升降有序,中焦氣機調暢,并使水谷精微輸布全身,營養(yǎng)機體;升降失司,氣滯中焦,運化失常,則成寒熱錯雜之象。王教授認為,脾胃的生理特性決定了寒與熱兩種邪氣并非同時存在于脾或胃,而是分別存在于脾和胃,即“胃熱脾寒”證[5]。《臨證醫(yī)案指南》有“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味辛發(fā)散可助脾升清,味苦主降可助胃和降,故“辛開苦降”之法與脾胃升降之理相和。《靈樞·本神》有“脾藏營,營舍意”,“心有所憶謂之意”。人的意念思維活動與脾相關,恢復脾胃升降之樞,神亦得以內守。故臨床對于癥見胃脘部隱痛、脘腹痞脹不適、喜溫喜按、胃中灼熱、反酸嘈雜、口苦或口淡、納差惡心、腸鳴便溏、神疲乏力、舌質淡或紅、苔薄黃或黃白相兼、脈滑或沉細等寒熱錯雜之象,王教授常用半夏瀉心湯作為主方加減,治以辛開苦降甘補之法。方中以半夏為主藥以和降胃氣,黃芩、黃連苦寒以泄熱,干姜、半夏辛溫以散寒,人參、甘草、大棗甘溫,補脾胃之虛,復升降之職。諸藥配伍,辛開苦降,寒溫并用,陰陽并調,從而達到恢復中焦升降,消除痞滿之目的。臨床若兼脘腹痞滿,舌苔白厚膩者,加蒼術、厚樸等燥濕健脾;胃脘疼痛明顯者,加百合、烏藥等益氣調中;胃寒怕冷、喜溫喜按者,加高良姜、附子、吳茱萸等溫胃散寒止痛;噯腐脹滿者,加焦三仙、雞內金、焦檳榔等消食化積;胃中返酸明顯者,加煅瓦楞子、海螵蛸、浙貝母等制酸止痛;燒心明顯者,加生石膏、知母、蒲公英、連翹等清熱瀉火。
藥理研究表明,半夏瀉心湯可通過減輕胃黏膜炎癥、保護胃黏膜、促進萎縮腺體再生、逆轉腸上皮化生對PLGC胃黏膜病損發(fā)揮顯著的促進修復作用[6];可通過抑制癌基因的表達,促進抑癌因子表達,從而阻斷癌前病變的發(fā)生發(fā)展[7];同時具有抑制Hp 功效[8],從而治療PLGC。
“五臟元真通暢”是健康的條件,“氣血通暢”與“條達平衡”相輔相成,王教授強調治療時應通平和諧。在通暢氣機、調和陰陽的功能上,少陽之樞與脾胃之樞相互協調,若單和少陽之表里而不運其中焦,因正氣不續(xù),少陽樞機也難以通利[5]。肝膽疏泄正常,脾胃升降有序,則全身氣機得以升降出入自如。
3 典型病例
患者,男,64歲。主因心下脹滿疼痛20年,加重1個月,于2017年7月26日就診。患者胃病史20年,之前為司機,飲食不規(guī)律,2016年6月2日于某三甲醫(yī)院查胃鏡顯示:中度腸上皮化生,灶性腸化萎縮,黏膜肌增生。近1個月無明顯誘因加重。刻下:心下脹滿疼痛,空腹加重,大便不成形,3次/d,胃中如有水流感,腸鳴,呃逆,眠可,形體消瘦,舌質淡黯,苔少,脈弦細,按之軟。中醫(yī)診斷:胃痛。辨證為脾胃大虛、寒熱錯雜。治法:辛開苦降,理氣和胃,緩急止痛。予百烏瀉心湯加味。處方:百合30 g,烏藥10 g,法半夏10 g,黃連10 g,炒黃芩10 g,干姜15 g,黨參10 g,炙甘草15 g,大棗10 g,黃芪25 g,當歸10 g,浙貝母10 g,益智仁10 g,煅牡蠣12 g,海螵蛸10 g,醋三棱8 g,蒲公英15 g,三七粉(沖服)6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早晚溫服。
2017年8月9日二診:患者自覺疼痛較前減輕,呃逆脹減,近日新發(fā)口瘡,大便初硬后溏,3次/d。上方干姜減至10 g,黃芪減至10 g,烏藥減至6 g,加黃柏8 g、龜甲10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早晚溫服。
2017年8月23日三診:胃痛好轉,空腹仍脹疼、食后減輕,口瘡減,脈弦。上方加桂枝10 g、白芍15 g,煅牡蠣加至20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早晚溫服。
2017年9月13日四診:空腹仍痛,有口瘡,呃逆,大便正常,舌質紅嫩,苔白滑。2017年9月11日于上述三甲醫(yī)院檢查胃鏡示:CAG,輕度腸上皮化生,輕度萎縮。上方黃芪加至30 g,吳茱萸6 g,延胡索10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早晚溫服。后患者繼續(xù)服藥16個療程,期間根據證候略做加減,至2021年6月復查胃鏡顯示:淺表性胃炎,輕度腸上皮化生。
按:本案患者心下脹滿疼痛20年,加重1個月,胃鏡顯示CAG伴中度腸上皮化生,為典型PLGC。患者患病日久,正氣不足,脾胃大虛。結合心下脹滿疼痛、大便不成形、胃中如有水流感、腸鳴、呃逆,為脾胃升降失司,后天生化乏源,氣血陰陽失和,寒熱錯雜。王教授以百合、烏藥養(yǎng)陰和胃、行氣止痛,以法半夏降逆止嘔,炒黃芩、黃連苦寒以泄熱,干姜、法半夏辛溫以散寒,黨參、黃芪、炙甘草、大棗甘溫,行辛開苦降甘補。患者空腹脹痛加重、大便不成形,為脾腎陽虛,故加益智仁、煅牡蠣;再酌加活血化瘀、清熱解毒之品消炎、改善微循環(huán)。又現口瘡,為虛火上炎,故加入封髓丹降心火、益腎水。以此為法,堅持服藥,隨證加減,恰中病機。經治療,患者胃鏡報告由萎縮性胃炎轉為淺表性胃炎,由中度腸上皮化生轉為輕度腸上皮化生,逆轉了PLGC的腸型胃癌疾病進展模式,效果卓著。
4 結語
對PLGC的早期干預可以有效逆轉疾病的惡性進展,是預防胃癌的重點,與中醫(yī)學“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治未病思想相符。王教授主研《傷寒雜病論》數十年,深諳仲景醫(yī)學之精髓,受先師劉渡舟先生教誨,博采時方而不拒,對PLGC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臨床證治與用藥思路,具有寶貴的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