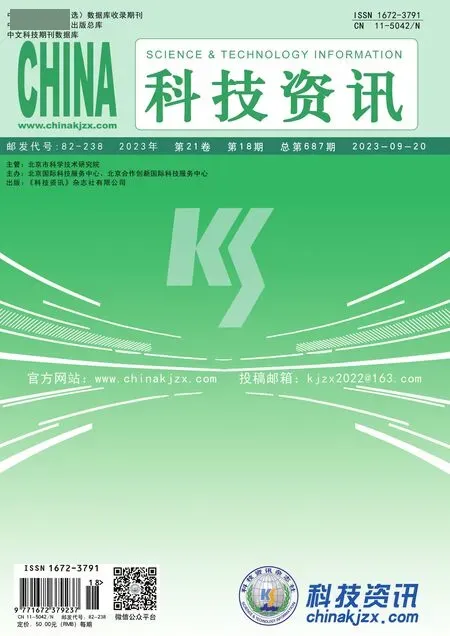碳中和背景下土地利用變化的碳排放效應分析
——以慈利縣為例
姚偉 趙晨迪 雷志剛
(湖南省第三測繪院 湖南長沙 410007)
“碳達峰、碳中和”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被納入整體布局進行戰略性的研究部署。深入分析碳排放與土地利用變化的內在聯系,為提出有效的節能減排措施和制定區域差別化的碳排放政策以及建設低碳城市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1]。慈利縣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近年來,慈利縣經濟快速發展,隨著蔣家坪新區和各旅游景點相繼建設,土地利用類型變化較大,碳排放的速度明顯增快。因此,本文采用土地利用碳排放風險指數和碳足跡壓力指數等方法研究國土空間用地布局與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從而研究慈利縣碳排放量的時空差異與排放效應分析,以期在國土空間規劃編制中為慈利縣國土空間用地布局優化和生態環境保護提出相關建議。
1 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為了便于更直觀地分析不同土地用途與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 21010-2017),將土地用途分為即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6種土地用途[2]。相關數據通過收集慈利縣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這4個年份的土地利用現狀變更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相關年度的社會經濟數據來自張家界市和慈利縣統計年鑒及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IPCC報告以及相關文獻。
1.2 碳排放量計算
通過查閱相關權威文獻關于各類用地碳排放的研究數據,結合慈利縣實際情況,確定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碳排放系數,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各土地利用類型碳排放系數 (單位:t/hm2)
1.3 碳足跡壓力指數和土地利用產生的碳排放風險
本文通過碳足跡壓力指數來間接反映人類社會和經濟活動對區域生態系統的影響,其表示土地利用碳源與碳匯之比[3],為了對土地利用產生的碳排放風險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本文利用土地利用碳排放風險指數對其進行測算[4-5]。
2 結果與討論
2.1 土地利用變化分析
根據土地利用變化重要性指數和土地利用變化面積比重計算結果,除去草地和未利用地的特殊因素,如表2所示,建設用地增幅達到13.5%,土地利用變化面積比重為0.01,土地利用變化重要性指數為0.06;耕地變化幅度達到17.03%,土地利用變化面積比重為0.03,土地利用變化重要性指數為0.09;水域增幅達到7.83%,土地利用變化重要性指數為0.04,水域面積增加主要是由于退耕還湖,還有生態保護紅線的設立,大大增加了水域的面積。綜上所述,隨著慈利縣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新城區的不斷建設,張家界旅游東線的不斷發展以及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土地利用結構變化較大,土地利用的非農化較為明顯。

表2 慈利縣2014—2020年土地利用變化表
2.2 土地利用變化碳排放效應研究
2.2.1 土地利用變化碳排放效應時間變化
將文中涉及的各個用地類型的面積和相應的各類用地的碳排放系數相乘,可以得到慈利縣各類用地的碳排放量。由此可計算出不同時期、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碳排放量及其變化情況,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慈利縣各類用地類型碳排放量匯總表
由表3可知,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總碳排放量分別為-122 498 t、-115 962 t、-125 201 t 和-130 501 t。慈利縣總碳排放量在研究期內為負數,碳吸收量遠遠大于碳排放量。
耕地和建設用地是主要的碳源。其中,耕地碳排放量分別為2014 年、2016 年、2018 年和2020 年分別為31 461.43 t、31 468.29 t、26 850.79 t 和26 104.81t,而建設用地碳排放量分別為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分別為10 677.27 t、10 756.43 t、11 045.98 t和12 118.35 t。
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是碳匯[6]。其中,林地的碳吸收總量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分別為163 773 t、157 323 t、162 232 t、167 746 t,因此林地是最主要的碳匯。
由圖1 可以看出,碳足跡壓力指數整體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表明碳足跡壓力指數的趨勢跟耕地碳排放量的趨勢具有一致性,耕地數量的減少引起人為活動量的減少,從而引起碳足跡壓力指數的減少。因此,退耕還湖、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和慈利縣“旅游旺縣”發展戰略等政策對減少碳排放具有重要作用。碳排放風險指數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這表明建設用地的碳排放量的增加會引起碳排放風險指數的增加,因此慈利縣的節能減排、綠色發展政策對減少碳排放量有一定的效果,但碳排放的風險程度仍舊比較高。這主要是由于蔣家坪新城區的建立、城鎮化的不斷進展及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快速推進,導致建設用地能源消費碳排放量持續增加,且區域發展布局不均衡引起地域間的碳排放量不均衡。

圖1 慈利縣碳足跡壓力指數和碳排放風險指數圖
2.2.2 土地利用變化碳排放效應空間變化
慈利縣中心城區位于整個縣的中東部,高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慈利縣中東部地區(見圖2)。中心城區零陽鎮和蔣家坪新區主要以盆地為主,近年來建設用地擴展迅速,經濟發展較快,是最主要的碳源。低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北部和南部地區,因為這兩個部分地理條件差,交通不便,經濟條件不發達,同時森林覆蓋率高,碳吸收能力強,整體碳排放量就少。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碳排放量相對較大,較2014年增長較快,主要集中在江埡鎮、三官寺土家族鄉、陽和土家族鄉等鄉鎮。

圖2 慈利縣2014年和2020年碳排放量密度分布圖
3 結論與討論
3.1 主要結論
(1)慈利縣總碳排放量在研究期內為負數,其碳吸收量遠遠大于碳排放量,在“碳中和、碳達峰”中一直發揮著積極作用。2014—2020年慈利縣不同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變化明顯,耕地和未利用地土地面積總體上表現出下降趨勢,下降幅度分別為17.03%和53.70%;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設用地面積總體上表現出上升的趨勢,上升幅度分別為2.43%、174.75%、7.83%、13.50%,草地面積上升幅度最大,建設用地次之。草地增加最為明顯,是由于影像分辨率差異導致面積明顯增加;建設用地的擴張是耕地、未利用地面積減少的其他原因。
(2)慈利縣土地利用碳排放風險指數表現出先增后降的變化趨勢,建設用地碳排放量的增加是由于建設用地面積增加所致,因此減少建設用地的比例有利于低碳發展。說明慈利縣實行綠色低碳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碳排放風險程度仍然較高,急需進行調整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構建低碳土地利用模式,提高土地生態系統的固碳減排能力。
(3)從2014—2020年慈利縣整體碳足跡壓力指數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碳足跡壓力指數的趨勢跟耕地碳排放量的趨勢具有一致性,耕地數量的減少引起人為活動量的減少,從而引起碳足跡壓力指數的減少。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慈利縣中東部地區,中心城區零陽鎮和蔣家坪新區是最主要的碳源;低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北部和南部地區,由于森林覆蓋率高,碳吸收能力強,經濟條件不發達,整體碳排放量就少;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碳排放量相對較大,主要集中在江埡鎮、三官寺土家族鄉、陽和土家族鄉等鄉鎮。這是由于慈利縣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建設用地的相應增加,導致慈利碳排放總量的增加。
3.2 對策及建議
3.2.1 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減少碳排放風險
慈利縣土地利用類型中,耕地、建設用地是主要的碳源,林地是主要的碳匯,但建設用地碳排放量逐年增加。在本輪國土空間規劃編制過程中,嚴格執行“三區三線”的基礎上,嚴控新增建設用地總量,盤活現有庫存建設用地,防止因建設用地擴張侵占耕地、林地、草地等。減緩建設用地的擴張速度和增加碳匯等措施來降低慈利縣的碳排放量,有利于“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的實現。
3.2.2 加強耕地耕作管理,提高農業技術
降低農田生態系統的碳排放量,主要是依靠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技術、農田耕作方式和有效的管理措施來提高土壤的碳儲存能力,達到固碳減排,實現綠色農業的目標,對實現“碳中和、碳達峰” 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3.2.3 進一步細分研究碳排放與土地利用的關系
下一步將結合國土調查、空間規劃、及用地用海分類指南中的分類進一步細化研究碳排放與各地類之間的關系,比如說建設用地細分到農業設施建設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商貿服務業用地、工礦用地、倉儲用地、交通運輸用地、綠地與開放空間用地和特殊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