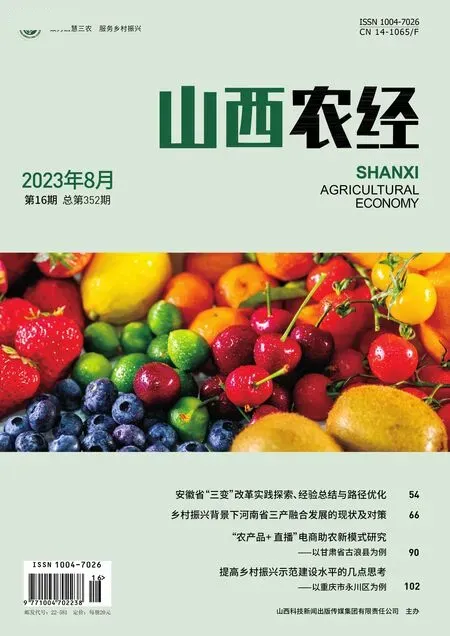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研究
□祁馨馨,朱 捷
(煙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5)
隨著數字信息技術與傳統普惠金融模式的融合創新,金融數字化為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打破城鄉二元金融結構、破除農業農村發展瓶頸提供新動能。因此,數字普惠金融成為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隨著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賦能,學術界在農業農村領域圍繞數字普惠金融展開多方面的研究。
在居民消費方面,岳喜優和陳桂生(2022)[1]從動態視角對財政支農、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居民消費關系進行分析。王雄等(2022)[2]基于空間聯動角度,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空間外溢效應的規律性。在農村減貧方面,陳平和王書華(2022)[3]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可有效緩解老年群體貧困。劉魏(2021)[4]從主客觀相對貧困角度驗證數字普惠金融紓解貧困效果在城鄉居民及不同年齡群體間的差異。在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方面,鄭宏運和李谷成(2022)[5]從異質性角度運用分位數固定效應模型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任健華和雷宏振(2022)[6]通過中介效應模型,證實數字普惠金融直接和間接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在其他方面,孫學濤等(2022)[7]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可促進農業機械化發展。
基于上述分析發現,多數研究側重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與單一農業農村要素之間的關系,農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性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文章通過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利用2011—2020 年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數字普惠金融是否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
1 變量及數據說明、模型設定
1.1 變量及數據說明
1.1.1 被解釋變量
農業高質量發展(AG)。結合農業高質量發展實際情況,參考相關研究成果,從農業提質增產、產業結構、綠色發展、協調共享4 個方面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其中農業提質增產層面包括農業機械化程度、農業勞動生產率、糧食單產3 個正向指標;產業結構層面包括財政支農力度、產業結構協調、農業地區經濟貢獻3 個正向指標;綠色發展層面包括化肥、農藥、農用薄膜使用強度3 個負向指標;協調共享層面包括負向指標農村恩格爾系數和正向指標農村醫療機構水平,運用熵值法測算農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
1.1.2 解釋變量
1)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DFI)選取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并從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DFI1)、使用深度(DFI2)、數字化程度(DFI3)進一步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2)控制變量: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借鑒已有研究,選取了城鄉化水平(TC)、農業規模程度(AS)、農業生產環境(DR)以及農村教育水平(CE)作為控制變量。分別采用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播種面積與農業從業人員比、成災率水平、農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3)工具變量:借鑒已有研究將移動電話普及率(MT)納入工具變量范疇,用每人擁有移動電話數量表示。
1.1.3 數據說明
文章以我國2011—2020 年30 個省際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因港澳臺及西藏地區部分數據缺失嚴重,故將其剔除。
其中,數字普惠金融數據來自北京大學發布的2011—2020 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報告。其他相關數據來自各省市區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等。針對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移動平移法或插值法填補。
2 實證檢驗
2.1 基準回歸
經Hausman 檢驗,選取固定效應模型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于已有理論及現實因素考慮,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因此,選用移動電話普及率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回歸結果進行矯正,如表1 所示。其中列(1)、(2)分別表示是否引入控制變量時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列(3)表示引入控制變量時最小二乘估計模型的回歸結果。實證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回歸系數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為正,證實數字普惠金融有效推動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在控制變量中,農業規模化程度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可能因為數字普惠金融為擴大農戶土地規模經營提供了資金支持,間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第一、第二產業轉移,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農業生產環境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可能因為農村地區經濟韌性較弱、抵御風險能力較差,當面對突發性災害時,極易給農業農村發展造成巨大沖擊,擾亂農業生產體系正常運行。

表1 基準回歸分析
2.2 異質性分析
2.2.1 區分數字普惠金融維度結構
為深入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選用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3 個次級維度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 中列(1)、列(2)、列(3)所示。研究發現,各維度系數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且使用深度顯著性最高,表明各維度在不同程度上均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在覆蓋廣度層面,數字普惠金融將農村地區及農村融資弱勢群體作為金融服務重點扶持對象,覆蓋范圍日益廣泛;在使用深度層面,數字技術與傳統金融融合發展,有利于金融資本均衡配置,緩解農村地區信貸約束,為農業產業改革創新提供資金支持;在數字化程度層面,依托移動終端開展金融服務,擺脫了傳統金融服務時空約束,降低了金融服務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務滲透性。

表2 異質性結果分析
2.2.2 區分地理區域
考慮到我國各區域發展情況存在差異,故按照地理位置將研究樣本劃分為沿海和內陸地區進行深入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 中列(4)、列(5)所示。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對兩個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提升效應均顯著,且對沿海地區作用最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沿海地區金融體制相對完善,科技創新能力較高,利于數據技術賦能金融體系,推動數字普惠金融向農村地區延伸。內陸地區多以粗放型經濟發展為主,經濟與信息技術發展相對緩慢,從而導致數字普惠金融紅利滲透到農業領域存在一定滯后性。
3 結論與建議
文章選用我國2011—2020 年30 個省際面板數據,旨在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推動作用,經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舊成立,且存在異質性。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各維度均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影響顯著,但使用深度影響效應最大。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對沿海和內陸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強度不同,沿海地區高于內陸地區。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提升金融服務有效性。一是政府機構制定可行性農村經濟發展扶持政策,及時調整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執行方案,推動多層次金融業務穩步落實,確保助農資金合理配置。二是注重農戶數字普惠金融知識普及和數字技能指導,培養農戶正確金融認知,增強農戶數字金融使用效度。
2)多維度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一是打破阻礙資金流動的二元經濟體制,聚焦各地區實際發展情況及弱勢群體信貸需求,拓寬金融服務覆蓋廣度,喚醒農業農村資源生產活力。二是加強城鄉金融機構聯動發展,非金融機構與傳統金融機構協同發展,數字信息技術與金融服務融合發展,延伸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涉農服務深度。三是完善農村地區數字建設,保障農戶使用數字金融服務的基準條件,提高金融服務機構數字化業務辦理效率。
3)促進農業發展綠色轉型。一是利用數字普惠金融低成本、低門檻優勢,升級傳統農業設施,創新發展新型農業模式,打造智慧化農業數據平臺,提升農業綠色發展指標。二是發揮政府機構環境管制作用,建立農業綠色發展宣傳、督察、評價、防治、跟蹤體系,制定有效的農業環境保護政策。三是注重發揮區域與產業內外部輻射帶動作用,加快新舊要素稟賦與農業產業有效結合,從而提供良好的農業綠色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