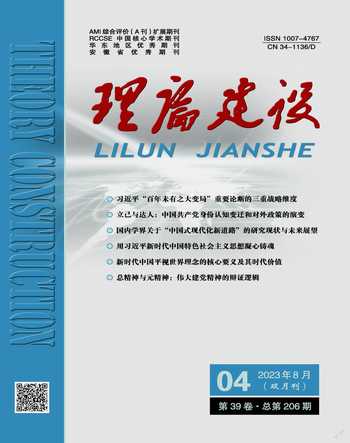習近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要論斷的三重戰略維度
牛一凡 吳家丞
摘 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全球金融危機與世紀疫情帶來的新挑戰,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非凡勇氣準確識變,原創性提出“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戰略論斷。立足時代之變,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科學應變,敏銳把握戰略機遇;以高超的斗爭本領應對風險挑戰,領導黨以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確保黨在大變局中永葆政治底色。面對全球發展難題與治理赤字,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強烈使命擔當主動求變,用新發展理念推進高質量發展,用全人類共同價值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彌合全球治理鴻溝,用中國式現代化形塑“東升西降”的國際戰略新格局,展現馬克思主義強大的感召力,為引領世界性大變局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與中國力量。
關鍵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馬克思主義戰略家;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4767(2023)04-0001-12
國際金融危機催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影響了國際格局與發展態勢。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習近平總書記準確洞察歷史發展大勢,科學把握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嫻熟化解國內外重大風險,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應對變局的重大理念,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扭轉變局的根本道路,牢牢掌握住中華民族發展的主動權,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戰略家所獨具的非凡理論勇氣、卓越政治智慧與強烈使命擔當。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識變”“應變”“求變”中彰顯的戰略家品格及歷史主動精神,對于深刻理解黨的二十大精神,深入領會新時代偉大變革所具有的里程碑意義,從而在黨的二十大開辟的新征程上保持戰略定力、堅定戰略自信、增強戰略主動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一、識變:把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緣起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首先是“能變之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面對世界性戰爭和戰后兩強爭霸帶來的世界變局,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眼光精準把握變局態勢,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贏得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成功實現了戰略突破,雄辯地證明了變局之能變。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立足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以卓越戰略定力充分把握內外發展機遇,穩中求進推動改革開放和發展建設事業,以和平發展加快國際力量的此消彼長,世界大勢悄然改變,形成“漸變之局”。進入新時代,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終成“突變之局”;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強大的歷史耐心和高超的戰略智慧準確識變,加快布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下好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先手棋,牢牢掌握應變、求變的戰略主動,必將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取得更大勝利。
(一)能變之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邏輯
善弈者謀勢,善治者謀全局。毛澤東同志指出:“世界上沒有絕對不變的東西。變,不變,又變,又不變,這就是宇宙的發展。”[1]392“能變”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屬性,也是我們黨百年奮斗成功的歷史條件。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中國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災難。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李鴻章等人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晚清變局,各種進步政治力量也在為挽救民族危亡進行積極探索,先是引進西方先進器物,再是學習西方政治體制,如青年毛澤東就觀察到“中國時機的轉變,在那時候為一個大樞紐”[2]。但這種轉變只是中國被動卷入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體系后產生的浮躁盲動、應急的變化,并未徹底扭轉變局。這些探索缺乏對變局由何而來、由誰主導、往何處去的體認。
資本主義是造成近代世界性大危機的主要原因。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3]資本主義天然地向外尋求擴張,靠戰爭起家,以掠奪致富,使大多數國家成為殖民地。到了二十世紀,“資本家撞了資本家,市場少了,有的搶到的地方廣一些,有的搶到的地方狹一些”[4]288,最后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階級矛盾激化。十月革命的爆發使世界形勢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中華民族“求變”的歷程也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恰如毛澤東同志所言,“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5]。
面對世界變局,毛澤東同志展現出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深邃洞見,他于1935年11月剛抵達延安時就對世界時局作出了“突變性”與“急轉性”的戰略分析[6],提出了“持久戰”與“游擊戰爭”的戰略構想。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同志清醒地預見到,“時局的黑暗只是暫時的,是要變化的。整個世界,整個中國,在不久的將來,都會有一個變化的”[7]411,展現了馬克思主義戰略家敏銳的戰略預判。至于變局向何處去,1943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講話中明確給出了答案:“我們的社會的性質已經改變了三次,現在要改變第四次。”[4]56所謂“第四次”,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說,就是“換兩回朝”,先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變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后再變為社會主義社會。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冷戰陰影下的兩極格局,中國共產黨人靈活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了外交新局面,實現了戰略新突破[8]。蘇東劇變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度陷入低潮,以鄧小平、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處變不驚,臨危不亂,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成功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新世紀。面對全球競爭的新態勢,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準確研判國際局勢,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帶領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戰略,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各種變局關頭積累了豐富應變經驗,形成了強大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理論與現實、歷史與實踐生動地詮釋了變局可變、變局能變,雄辯地證明了只有我們黨才能帶領人民解變局、開新局,只有我們黨才能帶領人民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從而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突變之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實邏輯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把握好戰略節奏,既要有條不紊、漸進發展,又要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充分利用戰略機遇期完成躍遷式突變。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漸變之局”,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保持戰略定力,充分把握內外機遇,穩中求進,銳意進取,贏得了歷史性戰略主動。恰如毛澤東同志所言,“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1]108。實現共產主義這個質變的飛躍,要通過量變來完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想一下子、兩下子就進入共產主義,那是不切實際的。”[9]115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以堅定的戰略決心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1956年11月,毛澤東同志熱情洋溢地展望道:“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10]156所謂“大變”,就是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強大的工業國,探索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1964年周恩來同志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實現“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戰略目標及“兩步走”戰略規劃,基本明確了“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路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于1979年底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具體來說,是在二十世紀末實現“小康之家”[11],提出“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戰略,強調穩扎穩打、有條不紊地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12]402。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種歷史機遇,是我們黨在變局時刻扭轉戰略態勢、取得戰略突破的寶貴經驗。所謂變局,意味著內部要素在新的條件下發生矛盾沖突進而分化重組。1990年前后,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鄧小平同志保持高度的戰略清醒,判斷可供我們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機遇[13]354。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告誡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明確提出“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13]383,進一步解放思想,釋放市場活力,為擴大改革開放創造有利條件。進入新世紀,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格局,同時也意味著直面更為復雜的國際局勢,要更加深入地參與世界經濟治理。對此,黨的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是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14]413,力爭在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牢牢掌握主動權。
進入新時代,在瞬息萬變的世情、國情下漸變之局已成突變之局,原先的順勢而上變成了“頂風”而上。中國能有多久戰略機遇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自己的內外政策和應對能力[15]。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16]294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深刻調整,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風險挑戰加劇,地區沖突不斷,“很多情況是改革開放以來沒有碰到過的”[12]60。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由外生性機遇為主逐步轉向內生性機遇為主,前所未有之大變局逐漸形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去大環境相對平穩,風險挑戰比較容易看清楚;現在世界形勢動蕩復雜,地緣政治挑戰風高浪急。”[17]121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保持強大戰略定力,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作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的戰略論斷[18]821,尤其強調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以戰略眼光抓住機遇、利用機遇、擴大機遇、轉化機遇,化被動為主動,穩穩地把握戰略機遇期的“時”與“勢”,牢牢地守住應對變局的戰略基點,掌握了突破變局的戰略主動。
二、應變:明確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準備
變與應變,貫穿于黨的百年奮斗歷程。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重心出現“自西向東”的位移,世界格局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帶來大挑戰的同時,也蘊藏大機遇。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科學應變,提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恢宏命題,以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捕捉世界變局中的發展機遇,以頑強的斗爭精神應對國際亂局中的風險挑戰,以偉大的自我革命確保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從而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為引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供了充足的戰略準備。
(一)以非凡的戰略眼光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命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反映了世界力量分合的變化[19]165。新世紀初,江澤民同志判斷“世界正處在大變革時期”,國際局勢總體趨于和平、緩和與穩定,局部仍伴隨戰亂、緊張與動蕩[14]520。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急劇動蕩,某些西方國家妄圖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世界經濟版圖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于2012年12月所指出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五年來,對世界經濟以及政治、安全形勢產生了深刻影響”“這個大變局,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19]165-166。
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的背后,是國力之爭、制度之爭與理念之爭。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從近代數百年世界大歷史視野出發,強調發展中國家的快速發展,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逐步向各國以制度規則協調關系和利益的方式演進”[20]241,“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世界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大變局”[21]。大變局中,既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衰落,也有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國家的整體性崛起;既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等逆向變量,也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等正向變量;既有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削弱,又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形成。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歷史機遇,同時也帶來了挑戰。
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總部的演講中坦言:“當今世界充滿不確定性,人們對未來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22]537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3]。這場變局實質上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相互交織、相互激蕩,這場變局不限于一時一事、一國一域。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洞察大勢和歷史規律基礎上作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戰略論斷,迅速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接受與認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更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局勢動蕩不安,“各國的領導力和制度優越性如何,高下立判”[17]164。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4]397習近平總書記對當下國際態勢作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精準戰略預判,使我們充分把握了世界格局發展的“時”與“勢”,我們才有定力、底氣與決心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牢牢掌握中華民族發展的主動權。
(二)以清醒的戰略思維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危機轉化
在亂云飛渡的復雜環境中鎮定自若,在泰山壓頂的巨大壓力下越戰越勇,是馬克思主義戰略家應有的戰略品格。“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考驗之大都前所未有”[17]30,“如果防范不及、應對不力,就會傳導、疊加、演變、升級,使小的矛盾風險挑戰發展成大的矛盾風險挑戰”[24]143,因此,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偉大氣魄,清醒地作出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論斷,“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變中我國的地位和作用,科學制定我國對外方針政策”[25]428。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26]60。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富有戰略前瞻性和強大號召力的科學論斷,勢必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巍巍燈塔。
是否善于把握“危機”辯證關系,做到臨危不亂、危中尋機、化危為機、轉危為安,能充分彰顯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政治素養與戰略定力。危險與機遇往往相互轉化,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戰爭能轉化為和平,和平也能轉化成戰爭[10]374。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12]419。當前,我國處在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要戰略機遇期易失難得,抓住機遇就能贏得戰略主動,反之將會陷入戰略被動。早在200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地方工作時就極具先見之明地指出,“能否把戰略機遇期提供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主要取決于人的主觀能動性特別是宏觀的戰略決策”,強調“搶抓戰略機遇期要有歷史緊迫感”,“只有抓得早、抓得緊、抓得實、用得好,才能搶占先機,贏得優勢”[27]。這些重要論述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戰略緊迫感與高度責任感。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相互交織的時代之變,習近平總書記以非凡的戰略眼光判斷當下“機遇更具有戰略性、可塑性,挑戰更具有復雜性、全局性,挑戰前所未有,應對好了,機遇也就前所未有”[17]122。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25]219-220習近平總書記總是諄諄告誡要“舍得花錢,舍得下功夫,寧肯十防九空,有些領域要做好應對百年一遇災害的準備”[18]497,凡事“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12]423。習近平總書記這種對潛在風險作出科學預判的危機意識與戰略思維,為我們打贏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的總體戰、阻擊戰贏得了極大的戰略主動,使我國成為全球抗疫成功的典范,成為化危為機的絕佳案例。
(三)以超前的戰略自覺回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在要求
馬克思主義戰略家是經過歷史檢驗、實踐考驗與斗爭歷練的戰略家,馬克思主義戰略家品格是積淀了生動斗爭本領與卓越政治智慧的戰略家品格。1916年,毛澤東同志在日記中寫到:“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28]透過文字的背后,我們充分感受到一種戰略家獨有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躍然紙上。在生產勞動、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中,毛澤東同志積累了豐富斗爭經驗,提出了諸如“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等戰略構想。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體現了老一輩馬克思主義戰略家高度的戰略清醒。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指出,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斗爭實踐中,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質[16]287。黨的十八大以來,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我們面臨的斗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17]83。新時代這十年,習近平總書記以頑強的斗爭意志和豐富的斗爭經驗,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打贏脫貧攻堅戰,打勝“打虎”“拍蠅”“獵狐”的反腐敗斗爭持久戰,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及常態化疫情防控攻堅戰等一系列戰役,“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25]7。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新的歷史“趕考路”開始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將“兩個務必”拓展成“三個務必”,尤其強調發揚斗爭精神,凸顯了新一代馬克思主義戰略家高度的戰略主動精神。
從“兩個務必”到“三個務必”,深刻反映了兩代馬克思主義戰略家始終保持憂患意識與底線思維,彰顯了黨不斷錘煉斗爭本領以應對世界性大變局的戰略自覺。中國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12]258,“不是為了斗爭而斗爭,也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斗爭,而是為了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知重負重、苦干實干、攻堅克難”[25]542。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種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在我國制造‘顏色革命,妄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政權安全面臨的現實危險。”[20]118面對意識形態領域尖銳復雜的斗爭,尤其是顏色革命的危險,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面對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特別是外部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施壓,我們必須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這場斗爭既包括硬實力的斗爭,也包括軟實力的較量”[24]141。唯有主動迎戰,堅決斗爭,勇于亮劍,才能有生路出路,才能躍過層層關山,踏過重重疊嶂,不斷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
從“兩個務必”到“三個務必”,深刻體現了新時代我們黨以刀刃向內的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著力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即“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十年磨一劍,新時代這十年,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找出這個問題的第二個答案,即“黨的自我革命”。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自我革命旨在提高黨不斷發現并及時解決自身存在問題的能力。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定力全面從嚴治黨,形成一套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規范體系。自我革命是主體在主動意義上和自覺意義上的自我揚棄[29],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政治品格。立足黨的二十大開辟的新征程,我們“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持之以恒地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意志,以刀刃向內、自剜腐肉的膽氣自我革命,確保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領導我們把握變局、應對變局、扭轉變局。
三、求變:增強引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主動
戰略問題是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國際金融危機催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使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這兩種全球格局中的最新“矢量”,突出投射在當今人類所共同面臨的發展窘境與治理赤字上。如何破解世界經濟發展難題、協調各國參與全球問題治理、取得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突破,極其考驗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政治智慧與戰略思維。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以強烈的使命擔當主動求變,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拓展全球治理空間,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重塑人類文明新形態,牢牢掌握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主動。
(一)堅定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
在百年變局當口,從戰略上準確判斷當前所處發展階段,進而創新發展思路、贏得戰略主動,是馬克思主義戰略家雄韜偉略的充分體現。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我國發展格局演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17]155,此后我國經濟受外部危機沖擊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對此,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前瞻性地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戰略判斷。所謂新常態,“新”就新在經濟發展從以往量的增長轉向質的飛躍,從依賴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22]245-246,更是習近平總書記立足發展大局從大時空角度對百年大變局下我國經濟運行態勢作出的超前戰略謀劃和定位。
越是壯闊的征程,越需要正確理念與政策來領航,從而下好先手棋,掌握“兩個大局”的戰略主動。理念是行動的先導。“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22]1972015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首次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并強調要以此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習近平總書記洞察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指出“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22]253。對此,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突出強調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改革之力化解過剩產能,實現了經濟重大結構性變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新發展理念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問題,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重要、最主要的系統理論體系[17]170。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原創性地提出了區別于西方供給學派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框架,從而全面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這是適應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更是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統籌“兩個大局”、破解發展難題的理論自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后,面對國際經濟循環格局的深度調整,習近平總書記展現了馬克思主義戰略家所獨具的“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見微知著的非凡能力。2020年3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調研期間發現“在疫情沖擊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生局部斷裂,直接影響到我國國內經濟循環”[17]174,立刻根據環境之變作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決策。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意識到要想在世界大變局中占據主動地位,“只有立足自身,把國內大循環暢通起來,努力練就百毒不侵、金剛不壞之身,才能任由國際風云變幻,始終充滿朝氣生存和發展下去”[17]175。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在全球配置資源能力,更好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17]156,是順應國內發展態勢、應對世界大變局的戰略舉措,可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正是有了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戰略性思想的科學領航,我們才得以有效應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接踵而至的風險挑戰,以奮發有為的精神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前進。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拓寬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維度
準確把握時代主題,科學回答世界之問,引領人類文明進步,體現著馬克思主義戰略家協和萬邦的戰略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壯大,“紅旗漫卷西風”,亞非拉被壓迫民族和人民解放斗爭如火如荼。馬克思主義戰略家毛澤東同志精準把握時勢,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深刻影響了世界格局。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科學研判國際局勢,確立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新認識,推動了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成為危機中的希望,卻觸動了西方某些國家敏感神經,拿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來說事,鼓吹“中國威脅論”,“甚至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國就要攝取世界的靈魂”[30]264。對此,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向國際社會莊嚴宣告:“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31]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9月在華盛頓演講時所說:“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32]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正是習近平總書記保持高度戰略清醒、作出正確戰略判斷的必然體現。
推動世界和平穩定,破解世界發展難題,是大國擔當的充分彰顯,更是戰略家天下情懷的自然流露。長征途中,毛澤東同志創作《念奴嬌·昆侖》,其中提到“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戰略家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切。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前所未有。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3月就強調人類“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30]272。世界不是被海洋分割成各個孤島,而是被海洋連接成了命運共同體,“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22]478。黨的十八大以來,從構建睦鄰友好的雙邊命運共同體,到向世界發出“一帶一路”倡議;從推動打造網絡空間、衛生健康等命運共同體,到共同建設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全球視野,用一系列新戰略新舉措,響亮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時代之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傳承了中華文明“天下大同”的理念,超越了西方一國一域的狹隘國際關系桎梏,為人類審視自身命運與未來前途提供了一種全新視角,充分表明了習近平總書記自覺擔當為人民謀幸福、為世界謀大同的歷史責任,彰顯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引領人類前進方向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時代覺悟。
摒棄意識形態紛爭,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必要之舉,更是馬克思主義戰略家寬闊胸襟的體現。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各國經濟發展雪上加霜。習近平總書記說:“在全球性危機的驚濤駭浪里,各國不是乘坐在190多條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小船經不起風浪,巨艦才能頂住驚濤駭浪。”[17]483-484面對世紀疫情,有人作出戰略誤判,幻想“躲進小樓成一統”。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也無奈地發問:“我們能夠攜手并肩對付一個共同且危險的敵人嗎?還是我們任由恐懼、懷疑和非理性左右,四分五裂?”[33]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給出了答案:“團結合作是戰勝疫情最有力的武器”[17]417,只有“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維,樹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贏理念”[18]712,讓世界多樣性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世界才能撥云見日,走出迷霧。長期以來,西方一些學者過度放大文明異質性,強調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將文明沖突視為世界對立與割裂的根源,并在西方中心主義邏輯下認定歷史將“終結”于西方發展模式中。某些西方國家更沉迷于推廣其所謂“普世價值”,肆意激化族群矛盾和意識形態沖突。對于此種行徑,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中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22]522,這與唯我獨尊、強行攤派的“普世價值”有本質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不應該以獨尊某一種文明或者貶損某一種文明為前提”[24]229,面對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形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25]441,既是對西方所謂“文明威脅論”最好回擊,又是馬克思主義戰略家天下情懷的生動演繹。
(三)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方案
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擺脫“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思維定式,沖破西方現代性的發展“牢籠”。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新航路的開辟揭開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從十七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十九世紀的維也納體系,到二十世紀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世界先后經歷大殖民時代、大解放時代、大變革時代,這一過程與其說是一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毋寧說是一部廣大亞非拉國家被侵略被奴役的血淚史,其血腥度與野蠻性令人發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建立在對其他文明的破壞與征服的原罪之上,“是以其他國家落后為代價的現代化”[17]124。這種以資本無限無序擴張為驅動的現代化,先天地帶有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9]117孕育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周期性的危機與動蕩,勢必會引發兩極分化、社會對立和精神焦慮等治理危機。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更催化了政治極化、地區沖突、民粹主義等問題,暴露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嚴重弊端,人類社會亟待找到一條破解西方現代化問題癥結的發展正道。
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7]407,堅定不移地走中國式現代化這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現代化的發展方向是確定無疑的,但現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34]。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串聯式”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國要想實現發展目標,就不能亦步亦趨地照搬西方模式。早在1983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3]29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12]367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更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必須從新時代的生動實踐中發掘原生材料,提出本土問題,開辟中國道路。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26]22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全面超越了西方國家人為制造沖突以圖渾水摸魚的現代化歪路,既不是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牢牢掌握中國發展命運主動權的應變之路,是我們黨扎根中國大地獨立自主探索出來的創新之路,是新時代新征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勝利之路。
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深刻把握國際格局“東升西降”的趨勢,為人類文明探索更好的社會制度提供中國方案。超越資本主義舊秩序是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變局向縱深發展,國際上出現“東風壓倒西風”的氣象,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探索現代化道路。對于一些國家而言,現代化是被迫西化的過程,似乎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然而,對外擴張的西方現代化路徑早已行不通,反而使一些國家陷入黨爭分歧與社會動蕩中。西方一些國家更不失時機地兜售“華盛頓共識”,開出“新自由主義”藥方,而恰恰是其鼓噪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使國際壟斷資本自由游走于世界各地,收割全球眾多國家經濟發展成果,加劇世界經濟的不穩定和動蕩,縮短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放大了全球經濟運行風險,釀成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乃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金融危機是“金融資本過度逐利、金融監管嚴重缺失的結果”[22]477。與之相反,我國的現代化道路并沒有采用西方主流理論倡導的“休克療法”,更看清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底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不斷以中國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更雄辯地宣示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生命力與感召力,展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的蓬勃生機,使“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35]。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新時代的偉大實踐,開創性地對現代化作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全新定義,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與中國力量,深刻重塑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格局與趨勢,開創了人類文明形態的新境界,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戰略家強烈的使命擔當。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333.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24.
[4]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9.
[6]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6.
[7]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蕭冬連.關于改革開放起步時期國際環境的考察[J].中共黨史研究,2022(4):87.
[9]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10]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12]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江澤民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909.
[16]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8] 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
[19] 曲青山.從五個維度認識把握“兩個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0] 習近平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
[21]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10.
[2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3] 習近平接見二〇一七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與會使節并發表重要講話[N].人民日報,2017-12-29(01).
[24]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6]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7] 習近平.之江新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6.
[2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4.
[29] 曲青山.曲青山黨史論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1031.
[30]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31] 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107.
[32]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689.
[33] 守護文明精神的特殊戰斗[N].人民日報,2020-02-20(03).
[34]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7.
[35]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3-64.
The Tripl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Judgment of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NIU Yifana, WU Jiachengb
(a. School of History; b.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deeply grasped the new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andemic of the century. With the extraordinary courage of a Marxist strategist, he has accurately identified changes and creatively proposed strategic propositions such as "unprecedented changes" and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ith the remarkable political wisdom of a Marxist strategist, has scientifically responded to the changes, keenly grasp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responded to risks and challenges with his superior struggle skills, and ensured that the Party would always maintain her vibrant strategic undertones in the midst of the great changes with the spirit of self-revolution. In the face of glob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 deficit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ith his strong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 a Marxist strategist,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eek change, promo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bridged the gap in global governance with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n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osture of "rising east and falling west"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demonstrates the powerful appeal of Marxism, providing Chinese wisdom, Chinese solutions, and Chinese strength to lead global changes.
Key words: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Marxist strategis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責任編輯:王 磊,孔令仙]
收稿日期:2023-03-01
基金項目: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創新項目:“中共革命中‘反動派概念的生成與流布研究”(KYCX2200_57)
作者簡介:牛一凡(1997—),男,安徽阜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吳家丞(1996—),男,江蘇常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