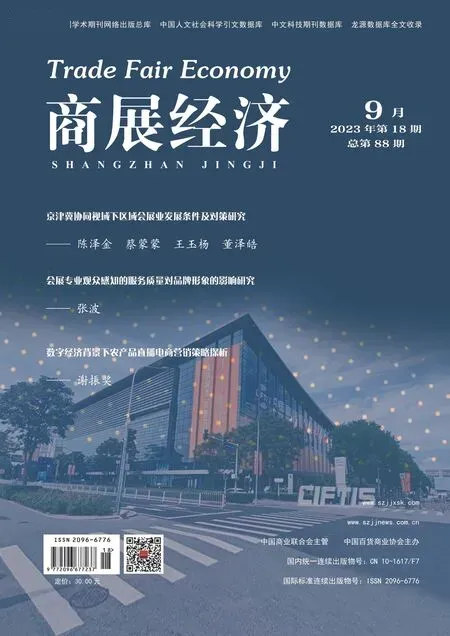碳中和視角下產業協調對碳排放的影響研究
田家豪噓 劉思佳 李運瑋噓
(1.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天津 300222;2.天津財經大學統計學院 天津 300221)
傳統的綠色發展傾向于節能減排,從源頭上進行限制,中國在此方面做出過許多貢獻。現代的綠色發展不再把節能減排作為唯一途徑,還添加了碳中和的方式來減少碳排放凈值。隨著碳吸收行業的不斷發展,碳吸收量逐步向碳排放量靠齊,最終兩者相等,實現進入大氣的溫室氣體排放和吸收達到平衡,這被稱為中和或凈零排放。
張琳杰等基于長江中游城市群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碳減排作用相較產業結構合理化更加顯著。劉青利等(2021)利用DEA-SBM模型來測算河南省工業綠色發展效率,并提出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對河南省工業綠色發展有明顯的正向驅動。劉楊等(2019)利用非期望產出的DEA-SBM模型對城市群綠色發展效率在2011—2015年的變化情況進行了分析,并構造均衡函數研究城市群的均衡特征。
本文基于碳中和視角,分析產業協調度對碳排放的影響及其中的作用機制。基于此,提出對策建議,這對碳排放、碳吸收企業有較強的實踐價值,對新時代的綠色發展及幫助中國盡早實現碳達峰也具有現實意義。
1 理論機制
H1:每個產業均有能產生碳排放的部門與能產生碳吸收的部門,其碳排放量與碳吸收量的差值可以大致計量。
任何一個碳排放產業與碳吸收產業都不是絕對的,對于一些社會公認的碳排放產業,如火力發電、水泥、交通運輸等會存在碳吸收部門,如使用新能源,人工碳儲存、碳轉換等來減少碳能源的依賴。自然生態系統的碳吸收不只是單純的光合作用,由于呼吸作用的存在,生態系統的碳排放也是不可避免的。
H2: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內,某一產業所產生的碳排放量與碳吸收量之間的差值大于零,或差值約為零,但其生產要素的差值大于零,將此類產業定義為碳排放產業。
H3: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內,某一產業所產生的碳排放量與碳吸收量之間的差值小于零,或相對減少了社會的碳排放量,將此類產業定義為碳吸收產業。
2 研究設計
2.1 指標體系構建
綜合指標體系能將碳排放產業與碳吸收產業兩個既相對獨立又有相互聯系的研究對象按其本質屬性和特征,由抽象分解成具體化、可量化、可操作結構。借鑒已有的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本文設計了表1。

表1 發展指標體系
2.2 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以我國13個省級行政區為研究對象,即甘肅、山西、云南、貴州、四川、廣東、福建、山東、河北、黑龍江、吉林、遼寧、新疆,中國各省份碳排放凈值采用碳排放量與碳吸收量的差值,碳吸收的計算采用裴銀寶等(2015)生態系統碳吸收計算方法。
3 研究方法
3.1 熵值法計算綜合發展水平評價
本文采用謝明義等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方法,對碳排放產業水平與碳吸收產業水平進行測度。
3.1.1 數據標準化
對碳排放產業與碳吸收產業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主要采用極值標準化方法:
式(1)(2)中:Xij表示第i(i=1,2,…,n)年第j(j=1,2,…,m)項指標的原始值和標準化處理后的數值;maxXij和minXij分別表示第j列指標中的最大值與最小值。
3.1.2 指標權重計算
采用熵值法計算兩產業的評價指標權重,其步驟如下:
(1)求取指標比重。第i年(或行)第j項(或列)指標的比重Pij為:
(2)求取指標熵值。第j項指標的熵值Ej為:
式(4)中:k=1/lnn,n為年數(或行數);0≤Ej≤1;當Pij=0時,令PijlnPij=0。
(3)求取指標熵冗余度Dj:
(4)計算權重結果Wj:
(5)綜合評價指數計算
采用權重和指標加權求和的方法,計算綜合評價指數Sj:
3.2 耦合協調模型
本文采用王淑佳等的耦合協調模型。計算碳排放產業與碳吸收產業之間的產業協調關系。
式(8)中:n為子系統個數(個);U為各子系統值,其分布區間為[0,1],故耦合度C值區間為[0,1]。C值越大,子系統間離散程度越小,耦合度C值越高;反之,子系統間耦合度C值越低。
式(9)中:Ui為第i個子系統的標準化值;αi為第i個子系統的權重,此處令兩者權重相等,各為0.5。
因此,耦合協調度D的計算公式為:
式(10)中:D為耦合協調度,取值范圍是[0, 1],本文根據耦合協調度數據將其劃分為 10個等級,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協調度等級
4 實證分析
4.1 熵值法與耦合協調度
4.1.1 指標權重
指標權重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指標權重結果
4.1.2 耦合協調度
耦合協調度部分統計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耦合協調度結算結果
整體來說,從各個省份的碳排放與碳吸收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及其均值來看,大部分省份處于0.3~0.8。工業發達的地區,如廣東、福建、山東、河北等地碳排放產業占主體,產業協調處于失調狀態;相反,甘肅、云南、貴州等地工業發展程度稍弱,自然環境優越,自然碳吸收能力強,產業協調處于協調狀態。
4.2 回歸實證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根據擬合結果可以看出,模型R2值為0.860,通過F檢驗,模型不存在共線性問題及自相關性,模型較好,同時根據系數可得方程:
根據分析結果可知,產業協調度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碳排放產業和碳吸收產業之間的協調度越高,碳排放凈值越少,即產業協調度對碳排放凈值具有明顯的抑制效果;研發投入的估計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即研發投入對碳排放凈值具有抑制效果;環境制度強度的估計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加大環境治理投資,可有效緩解碳排放導致的環境污染,從而降低碳排放凈值。
5 規模異質性分析
5.1 城市規模差異
經過對樣本城市的產業協調度計算發現,不同區域及同一區域內的省市在產業協調度上均存在一定的差異。據此,為探究城市規模對省市碳排放水平的影響,本文基于樣本省市規模的分類標準,建立固定效應模型。
5.2 規模異質性
5.2.1 樣本省市規模分類
在樣本省市規模分類上,本文將年末常住人口作為量化指標,將樣本城市分為三類,年末常住人口低于3000萬的省市定義為小規模省市,低于5000萬并高于3000萬的省市定義為中等規模省市,5000萬人口以上定義為大規模省市。
5.2.2 分規模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固定效用模型對面板數據中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效應進行分析,如表6所示。電力產業、農業的發展對不同規模省市地區的碳排放水平都有顯著的相關效應。

表6 FE模型回歸數據
從大、中、小規模省市的實證結果可知不同規模的省市之間產業協調度對碳排放水平影響存在差異性,可以看出存在不同規模的省市具有不同的對碳中和系統的影響因素,同時同一因素可能在不同規模的省市造成不同性質的影響,對農業、電力產業等在碳中和系統中有顯著影響的產業,本文將其放在不同的框架中分析對比,最終得出不同規模省市其產業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具有異質性結論。
6 結語
本文通過樣本數據分析,思考城市碳中和程度影響機制,得出的主要結論包含以下三點:第一,產業協調度對碳排放量起抑制性作用,提高產業協調度有利于減少碳排放;第二,人力資本對環境效率的作用由于受到經濟發展和物質資本積累程度的影響,在我國產業協調度和碳排放水平的關系中呈負向調節作用;第三,從城市規模異質性分析視角來看,不同規模省市具有不同的對碳中和系統的影響因素,同一因素在不同規模的省市會造成不同性質的影響。
在人力資本對環境效率的作用中,經濟發展和物質資本積累水平作為無關變量產生了顯著影響,在該種經濟環境下,建立完善的生態補償機制、頂層制度設計及環境制度供給已成為經濟制度改革的必經之路。因此,要重點提高經濟高發展區技術型人力資本的投入,提升經濟低發展區人力資本的存量水平,更要優化物質資本中等地區以上的產業間結構,加大吸引頂尖人力資本需求的產業投資,并注意兩者之間的優化配置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