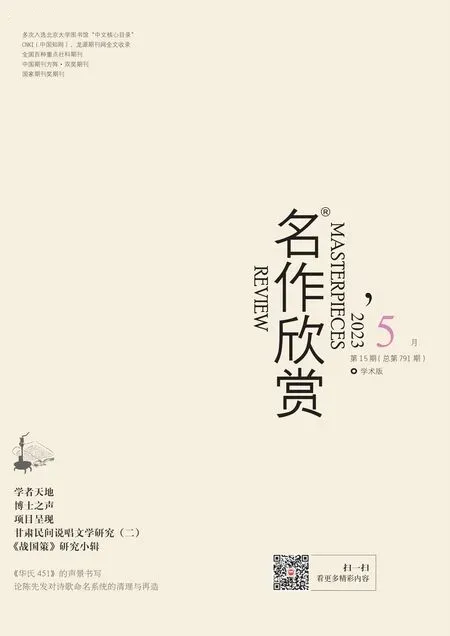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蕭紅的創作
——以《呼蘭河傳》與《生死場》為例
⊙楊嵐[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0]
1974年,法國女性主義者奧波妮最先提出了“生態女性主義”這一名詞,該理論認為父權制對婦女的壓迫與對自然的壓迫有直接的聯系,具體觀點因內部流派眾多而各有不同。蕭紅作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她的創作中常會涉及自然與女性這兩個對象,其作品《生死場》與《呼蘭河傳》便透露出較為明顯的女性意識與生態意識,因此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出發,以這兩部作品為研究對象,來探究蕭紅在創作中所流露出的平等和諧的生態女性主義觀。
一、女性與自然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自然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即生理上的創造、養育生命與精神上的情感共通。在《呼蘭河傳》與《生死場》里,自然與女性在孕育生命的過程中,感知彼此情緒,相互理解與慰藉,成為各自在父權制社會里最可靠的同盟者。
(一)生理上的聯系
1.女性與大地
文化生態女性主義關注女性與自然生理上的天然聯系,即從女性的生物特征來看,女性孕育生命、哺育嬰孩的經歷與自然創造、滋養萬物的過程存在相似性。在《呼蘭河傳》與《生死場》中,廣袤肥沃的土地為人們耕種莊稼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人們得以在此安居樂業;而女性則承擔了一個家族傳宗接代與打理家庭的重要職責。“我們知道我們由大地而生,我們知道這大地由我們而生。因為我們了解自己,我們是自然。”①蘇珊·格里芬的話語點出了女性與“大地”的生理聯系,這里的“大地”指代的正是自然。自然為一切生命創造了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如水、食物、工具等,而這些條件多以大地為媒介產生,因此便有了“大地之母”一說。
在《生死場》中,“麥地”成為“大地之母”的一個重要象征。對于農民而言,“麥子是發財之道”,柿子、白菜一類的蔬果都只是低賤的東西,他們對麥子的看重甚至超過對孩子的愛。王婆的孩子在收麥時節意外摔死,但她忙于麥子的收割,滴淚未流。在寒冷干裂的北方大地,麥子的收成是當地農民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麥子可謂是他們的命。同樣,在封建鄉村社會中,女性雖因地位低下而屢遭男性的辱罵與虐待,可村里的每一戶人家幾乎都有女性的存在。她們不停歇地忙碌在家庭內外,而她們的子宮更是一直在孕育生命的路上,從未停止。
2.女性與動物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動物都屬于弱勢群體,并處于父權制文化中的邊緣地位,因此長期受到男性的壓迫與剝削,缺少應有的平等與尊重。在《生死場》中,蕭紅巧妙地選取了“生育”這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符號,并將女性的生育繁衍與自然界的萬物繁殖,尤其是動物的生殖作類比,展現了女性與自然之間的原始聯系。
《刑罰的日子里》講述的便是一個全村生產的故事。在這個關于“刑罰”的故事里,蕭紅大膽準確地描繪了女性孕育生命的全過程,展現了女性在生育時所承受的丈夫的恐嚇、“全身將被熱力所撕碎一般”等多重“刑罰”,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女性生殖能力的肯定與贊頌。不僅如此,作者還將女性的生育與動物的生殖置于平等的地位來書寫,可見其對于自然萬物都持以一視同仁的態度。在這里,一切雌性生物都是“受刑”的對象,都要承受由生育帶來的痛苦與考驗。只不過,同為生育對象,女性連動物的生存境況都不如。村莊里的四月,有隨處可見的黃嘴小雀、壯大的小豬隊伍,“只有女人在鄉村夏季更貧瘦,和耕種的馬一般”②,人與動物的處境對比鮮明,頗具諷刺意味。而在諷刺背后,是蕭紅對男性無情壓榨與迫害女性的有力控訴。
(二)精神上的共通
1.自然的共鳴者
文化生態女性主義除了重視女性與自然生理上的特殊聯系,還從文化意義上建立起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由于具有創造和養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樣),女性歷來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靈更適合于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③不同于熱衷追名逐利、剝削自然與女性的男性,孕育生命的經歷與敏感多情的性格,使得女性對于自然萬物的變化有著更細微的體察與更深切的認同,因而在精神上與自然有了更多共通之處,也更容易與自然產生共鳴。
《生死場》中的王婆便是這樣一位自然的共鳴者。對于夏天這個灼熱喧鬧且被眾人怨恨的季節,她卻永久歡迎,因為夏天的一切能喚起她“詩意的心田”。而《老馬走進屠場》更是充分展現了她送老馬進屠場時不舍、糾結與悲痛的情感歷程。在去屠場的路上,王婆一邊輕聲呼喚老馬前進,一邊以“到日子了”來自我安慰,承受著內心的掙扎與煎熬。她甚至一度將自身代入老馬,幻想自己的背脊經屠刀穿過的恐怖場景。對于人與動物的關系,生態女性主義提出了同情和關懷的倫理價值,即人類應同情與關愛被壓迫的動物。文中王婆雖是人類女性,卻能對即將被屠戮的老馬產生強烈的共情心理,可見她十分關注老馬這一受迫害的動物,這也印證了女性這一性別主體與自然之間所特有的聯系。只是“不下湯鍋,還不是等著餓死嗎”,最終王婆因苦難生活的壓迫與封建地主的剝削未能對老馬施以援助,這也是其所處的社會與時代的局限所致。
2.女性的精神寄托
傳統父權制框架確立了自然須屈服于社會、女性須服務于男性的宇宙觀,對此,生態女性主義提出要發掘具有“親和自然特質”的女性氣質,并借此重建一個肯定生命、關系平等與和諧友愛的世界觀。《呼蘭河傳》里的后花園便是這樣一個小世界,平等、自由與友愛的環境使它成為“我”童年時期最珍貴的精神家園。
“我家是荒涼的”,這不僅有房子多、院子大與人少的緣故,更因為除了祖父,常與“我”為伴的只有孤單,因此后花園成了“我”重要的心靈棲息地。新鮮明亮的花朵、放肆生長的蔬菜、自由飛舞的昆蟲,還有盡情玩耍的“我”。即便是挨了祖母的罵,“我”只要拉上祖父到后院,在寬廣的天地間用盡力氣跑上一回,心情便會煥然一新。《呼蘭河傳》作為半自傳體小說,書中的“我”也是童年蕭紅的一個側面展現。身處父親冷淡、生母早亡、繼母刻薄與祖母古怪的家庭里,寂寞與痛苦是“我”的常態,唯有祖父與后院的大自然能撫慰“我”幼小的心靈。而蕭紅也通過描寫“我”與自然之間親密無間的交往,展示出自身尊重、熱愛與親近自然的女性氣質。
二、女性與社會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自然與女性除了生理與精神上的聯系,還同處于二元論中的附屬地位,受到父權制文化的壓迫與建構。在《呼蘭河傳》與《生死場》中,蕭紅就書寫了女性與自然在父權制文化社會中所遭受的來自異性、同性與戰爭的多重迫害。
(一)異性的壓迫
社會生態女性主義強調社會倫理對女性的建構,認為女性是通過自身的社會角色與自然產生聯系的。傳統的父權制文化確立了男性在家庭、社會等各個領域的主導地位,反之,女性則始終是男性的附屬,扮演著哺育生命、打理家庭的社會角色,麻面婆就是一個由社會倫理所建構的典型女性。每天忙于家務的她從不抱怨與反抗,對于丈夫的話,更是言聽計從。而這一逆來順受、麻木愚昧的女性形象恰恰對應了父權制文化下所構筑的自然形象——始終無條件服從人類統治。文中,同樣是打麥子,小馬因未受人類馴化,弄得麥穗常飛濺出場,故而屢遭鞭打;但老馬平靜順利地完成了全程,鞭子也很少落到其皮骨,“因為一切過去的年代規定了它”。
父權制文化內部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它認為文化優于自然、男性優于女性。這種二元對立觀產生了人類中心主義與男性中心主義,并使得自然與女性共同淪為父權制社會中工具性的對象。在《生死場》中,自然尚且因給人類提供生存資源而備受男性關注,但女性幾乎完全被“物化”,成為男性泄欲與理家的工具。成業每與未出嫁的金枝私會,不為說情話或接吻,而只是為了滿足自己泛濫的性欲。至于理家則更是村中所有出嫁女性都無法逃避的,只是她們除了要承擔所有家務,還要取悅男人,飯燒晚了,笑久了,都可能招致一頓咒罵甚至毆打。可一旦女性因疾病或死亡喪失了這兩種工具性作用,便會一文不值,成為被男性拋棄的重擔,打魚村美麗且溫和的月英的慘死便是證明。而蕭紅也通過展現自然與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工具化形象與悲劇性命運,表達其對于深受父權制文化迫害的自然與女性群體的同情與觀照。
(二)同性的傷害
生態女性主義強調人與人應當和諧共處,相互尊重與照顧,這也是人類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基礎。因而身為父權制社會里的被迫害者,女性群體更應團結起來,共同對抗不公正的父權制文化。《呼蘭河傳》中有這樣一群婆婆,身為女性長輩,不僅未給小團圓媳婦應有的關懷與照顧,反而仰仗“婆婆”身份對其非議眾多,只因她“不怕羞”、吃得多、長得高、“走得飛快”,不像個小團圓媳婦。而“親婆婆”更是進行了拿烙鐵烙腳心、用針刺手指等所謂的“矯正”,最終將她折磨致死。深究根源,這都是父權制文化中的傳統封建思想所致。
傳統封建思想規定了女性作為妻子,就應溫柔瘦小,無條件地順從與忍受丈夫。可小團圓的出現打破了這群“婆婆”對兒媳的傳統認知,因此她們極力想要矯正這種“病”。或許她們少女時也有這般自然的天性與情感,但封建文化的長期摧殘使得她們從受害者轉變為忠實的遵循者與維護者,最終造成了同性相殘的悲劇。面對這種不平等甚至異化的兩性文化,蕭紅是憤怒的,因此她以犀利的筆觸揭露父權制文化的罪惡,也借此表達對自然平等的性別精神生態的強烈渴求,而這恰與生態女性主義對平等和諧的生態關系與兩性關系的追求不謀而合。
(三)戰爭的犧牲品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男性與女性是相互依存、和諧共生的關系。因此為維護社會的和諧友好,她們強烈抵制戰爭與暴力。蕭紅的《生死場》后半部分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展開的,她對戰爭的態度也近于生態女性主義觀。在書寫戰爭時,蕭紅并未正面描寫宏大的戰爭場面,而是通過描繪一個生活平靜的鄉村因遭遇戰爭而走向衰敗的過程,從而揭露戰爭給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尤其是女性群體帶來的巨大打擊。在炮火與日本兵的摧殘下,農田荒蕪、動物消失,鄉村成了一片連野狗都不愿來的荒野。而隨著秩序井然的鄉村生活被打破,女性也因戰爭陷入無以復加的悲慘境遇:死亡的威脅、子死夫亡的痛苦,孕婦甚至可能被“破開肚子去破紅槍會”。小說最后,悲憤交加的寡婦們大多加入了李青山的革命軍,而她們在宣誓會上為消滅日本子“千刀萬剮也愿意”的盟誓也暗示了蕭紅對于戰爭的憎恨與厭惡,以及對自然和婦女淪為戰爭犧牲品的憐憫與同情。
三、結語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自然存在天然的聯系,在生理與精神上都更接近自然,且同處于二元對立觀與父權制文化中的附屬地位。因此,該理論主張人、社會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整體;人類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之間都應平等互助,共同維護世界的多元化。蕭紅創作的《生死場》與《呼蘭河傳》雖早于該理論的誕生,但自身特殊的人生經歷,使得她在對女性、自然與社會這三者關系的理解上與該理論有許多相近之處。總體而言,蕭紅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對自然的尊重與熱愛、對父權制文化下被壓迫女性的深切同情與關懷以及對和諧友好兩性關系與生態關系的追求,為當下構建平等和諧的兩性關系與生態關系、建設美麗和諧的現代社會提供了許多借鑒意義。
①〔美〕蘇珊·格里芬:《女性與自然:她內心的呼號》,毛喻元譯,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頁。
② 蕭紅:《呼蘭河傳》,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美〕納什:《大自然的權利》,楊通進譯,青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