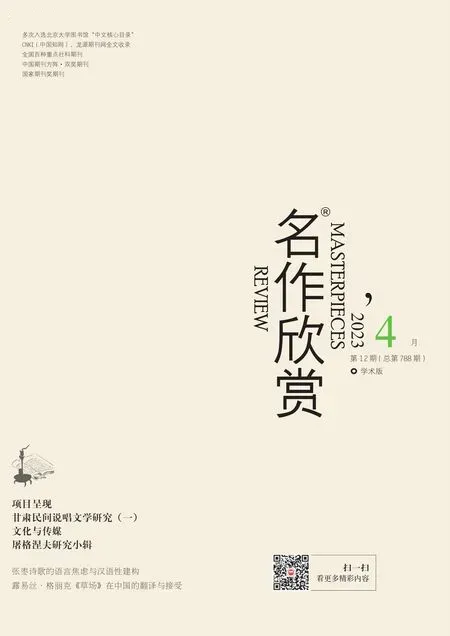《琵琶行(并序)》經典化的重要途徑
⊙黃曉璐[重慶師范大學,重慶 401331]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著名詩人,留存到現在的作品有三千多篇。《長恨歌》和《琵琶行》是其最為成功的作品,直至現在也是為人稱道的名作佳篇。本文以白居易的《琵琶行》為例,探討其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的一些重要途徑。
一、《琵琶行》的寫作背景
元和十年,白居易因觸犯權貴,慘遭誣陷而被貶為江州司馬。江州司馬名義上是江州司馬的副官,但其實就是個虛職,到江州以后的白居易在思想情感和人生態度等各方面都出現了巨大的轉變。在到達江州的第二年,白居易就寫下了讓人稱嘆的經典名篇——《琵琶行》。
二、經典化的重要途徑
在元和十一年的秋天里的那一日,白居易送客到了湓浦口,忽然聽見了琵琶聲響,原來是一個來自長安的歌女在演奏。這時候的白居易剛被貶謫不久,又聽見了歌女如歌如泣的傾訴,一時感慨萬千,便寫出了《琵琶行》。《琵琶行》是白居易在任江州司馬時期寫下的最優秀詩作,其問世后至今膾炙人口,并漸漸變成經典名篇。
(一)他人評點
《琵琶行》在流傳過程當中,歷代文人對其評點不斷。評點的范圍非常廣泛,涉及《琵琶行》的敘事、情感、語言和影響地位等諸多方面,多角度闡釋了《琵琶行》的文學內涵。
首先是評內容敘事。《琵琶行》是一首長篇敘事詩,詩的主要內容是寫白居易偶遇一位長安歌妓,聽她彈琵琶訴說往事繼而感慨萬千。謝思煒基于《琵琶行》的敘事給出了以下評價:“在其典范作品《琵琶引》中,隨著敘事的展開,作者也自然實現了敘事焦點的變化:通過作者的自述而引入琵琶女的自述。”①謝思煒認為《琵琶行》的敘事語式同時包含了“主人公(江州司馬)講他的故事”與“旁觀者(江州司馬)講主人公(琵琶女)的故事”這兩種語式,第一人稱敘述者既可以作為主人公又可以切換為旁觀者。白居易以這樣的方式,將自己與琵琶女相似的境遇結合在了一起,兩相慨嘆從而凝結了抒情意味,讓人感傷。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敘寫了兩條線的故事,明線暗線交叉,在闡發琵琶女故事的同時還包含了“我”(江州司馬)自己的故事,這樣就使得敘事人物更加血肉飽滿,敘事情節更加波瀾起伏,敘事詩的張力得到擴展,敘事詩的小說性得到加強。
《琵琶行》雖然是一首長篇敘事詩,但是白居易在敘述歌女彈奏琵琶的高超技藝和她不幸的過往里,聯想到了自己的遭遇,融入了真情實感,全詩敘事與抒情相結合。明代的李沂在《唐詩援》里說初唐時期的文人喜歡寫長篇詩歌,但是大多只注重辭藻風采而缺少了神韻,到了中唐時期,“惟《連昌宮詞》直陳時事,可為龜鑒;《琵琶行》情文兼美,故特取之”②。李沂在評價時是以神韻為主要標準的,他以為《琵琶行》描寫細致,抒情與文采兼備,因此可以采納。民國的劉衍文在《雕蟲詩話》中說白香山的《長恨歌》,敘事多過抒情,《琵琶行》雖為敘事詩,但還是以抒情為主。
在敘事語言方面,劉勰肯定了《琵琶行》多用比興的敘事特點,生動形象,極具畫面感。白居易寫作力求語言質樸,平易近人。清朝的趙翼在《甌北詩話》里評價元稹和白居易的敘事語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還認為《長恨歌》一篇“為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既嘆為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③
趙翼說《長恨歌》已經十分絕妙,喜聞樂見廣為流傳,再加上一首《琵琶行》,兩首詩自問世以來就已足夠不朽,更何況白居易的作品并不止這兩篇。趙翼不僅肯定了元白創作平易、坦然的特點,更是肯定了《長恨歌》《琵琶行》的影響和地位。
二是評藝術情感。白居易在《琵琶行》自序言:“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④僅僅通過這二十個字,白居易就已經表明了自己當時的情感——和琵琶女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惺惺相惜,以及自己遠離長安被貶江州的惆悵萬千。明代的唐汝詢在《唐詩解》中寫道:“此宦游不遂,因琵琶以托興也。”⑤愛新覺羅·弘歷在《唐宋詩醇》里點評:“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⑥他們的評論明確了《琵琶行》所傳達的情感,都認為《琵琶行》所要表現的是詞人和琵琶藝術女“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惺惺相惜之情;是對他們有著相同境遇者的共鳴,是為琵琶女而感傷,也是為自己遷謫的失意所作。
三是評影響地位。宋代的錢易把白居易和李白、李賀相提并論,宋代的張戒認為白居易才多而意切。明代的何良俊直言自己最愛的是白居易的詩,因為白居易寫詩不事雕飾,直寫性情。清朝的趙翼更是毫不吝嗇對于白居易的贊美,說他詩名最著,及身已風行海內,是繼李白之后唯一人而已。趙翼直接將白居易與李白的地位相提并論,并以為《長恨歌》和《琵琶行》,對于成就白居易的聲譽和地位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在白居易去世之后不久,宣宗還為之寫詩憑吊:“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⑦這一句一是指出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廣受民間的歡迎,連毛頭小孩兒都能說會唱的,二是透露出在當時,甚至是皇帝都知道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皇帝對他的文采是頗為欣賞的,由此足可以見白居易及其作品的影響之深,流傳之廣。
不少文人都把白居易的《琵琶行》推崇到了一個很高的地位。《歲寒堂詩話》里說白居易貶謫江州十一年期間寫下的《琵琶行》,雖然在文字表達上有些太過詳盡,但總歸表述恰當,后來還沒有人能夠超越。明末清初賀貽孫在《詩筏》里認為白樂天的《長恨歌》《琵琶行》和元微之的《連昌宮詞》,堪稱才子之冠。
明代的何良俊和賀貽孫一樣,將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和元稹的《連昌宮詞》聯系在一起作評價,認為這三篇皆是直陳時事,鋪寫詳密,為古今長歌第一。
清代的鄒弢以為《琵琶行》的結尾尤其精妙,似江潮涌雪,余波蕩漾,有悠然不盡之妙,更認為在筆意鮮艷這方面沒有人能夠超過白居易。
不管是賀貽孫、毛先舒還是鄒弢,都把《琵琶行》放到了一個無法超越的地位,認為它是長篇敘事詩歌里的創作巔峰。
(二)化用《琵琶行》
在《琵琶行》寫成之后,后人為之建造了一個亭,命名為“琵琶亭”。不少文人墨客路過此地,紛紛“琵琶亭前說司馬”。后人或化用《琵琶行》的句式,或取其詞語意象,或沿用主題改編,詩詞、雜劇、傳奇等各種體裁都有涉及。
曹秀先的《衍琵琶行》,將白居易的《琵琶行》的每一句詩化為了四句詩,如:“江州司馬青衫濕,半世豪雄付歌什。酒闌歸散客亦行,商婦回向客船泣。”⑧
宋代詩人張耒路過琵琶亭時寫下了《題江州琵琶亭》一詩,表達了自己的惆悵與悲傷。
歐陽修被貶為夷陵縣令之后,登上了琵琶亭,一時間感慨萬千,遂寫下《琵琶亭上作》,表達了詩人哀傷的情緒。
馬致遠的《四塊玉·潯陽江》是他在潯陽江邊,憶起同樣慘遭貶謫、官場失意的白居易而創作的一首散曲。借著《琵琶行》,以白居易在潯陽江頭送客時遇到琵琶女,聽到琵琶聲的故事,懷古傷今,以他人之悲抒發了個人失意的情懷。
《琵琶行》歷來受到戲曲改編者的偏愛。早在宋代的時候,《琵琶行》就被改編為《琵琶亭》,但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這部戲沒能夠保存下來。到了元、明、清時代,對于《琵琶行》的改編就更多了,如元代馬致遠的《青衫淚》,元末高明的《琵琶記》,明朝顧大典的《青衫記》,清代蔣士銓的《四弦秋》等。
《琵琶行》歷來被視作長篇敘事詩里的佳作,不少文人爭相模仿,但不是哪一篇名作都能被成功復制。《琵琶行》被效仿的頻率越高,經典化的概率也就越大。
(三)教育傳播
元稹在給白居易的詩集作序時評價白居易的作品,在當時就沒有人不知道的:“禁省、觀寺、郵侯墻壁之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炫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⑨
白居易自己也說他自己的作品:“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婿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⑩由此可見,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婦人孺子,白居易的詩備受歡迎,流傳廣泛。
沈復的妻子陳蕓喜歡讀書,擅長吟詠。沈復在敘述與她的閨房趣事時,言:“陳蕓生而穎慧,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誦。……一日,于書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認,始識字。”?
陳蕓以《琵琶行》作為啟蒙讀物,靠幼時的熟背而挨個識字,自然敬仰白居易且熟悉其作品,還以白居易作為自己的啟蒙老師,時常銘記在心。沈復說陳蕓以白樂天為啟蒙老師,以李太白為知己,而自己字三白,又為她的夫婿,覺得陳蕓與“白”字當真是有緣,戲謔陳蕓將來恐怕是要白字連篇了。這雖然是沈復和陳蕓夫妻倆之間打趣說的話,但值得注意的是,像陳蕓這樣把白居易的文章拿來啟蒙的人并不少,學習《琵琶行》的人還有很多。
到了民國時期,《琵琶行》被選錄的選本數量大大增加。這得益于以下幾點原因:首先,當時的大環境動蕩不已,人們普遍關注社會現實,白居易作為杜甫思想的繼承人,作為一名現實主義詩人,自然會受到許多文人學士的關注。其次,胡適等人大力提倡使用白話文,通俗曉暢,清新自然的文章越來越被文人學士所推崇。白居易的詩具有質樸平易的特點,因此很受時人青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民國沿用了清朝癸卯學制,對教材實行審定制,大量高質量的教材就在出版社互相競爭的情況下出版了。
《琵琶行》是民國時期教材選錄次數最高的篇目之一,初中選了《琵琶行》的有2本教材,高中選了《琵琶行》的有8本教材,綜合性教材選了《琵琶行》的有10本。如浙江省戰時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編注的《活頁初中國文講義第六組》、大東書局編輯所編輯的《分組編制自修國文講座》、南開中學編《南開中學高一國文教本)(上冊)》等。直到現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還在高中語文教材當中。
三、結語
《琵琶行》經典化的過程,也是讀者對其逐步認識的過程。從唐代以來,關于《琵琶行》的解讀就沒有停止過,對于《琵琶行》的解讀大多是對它進行評點,將它運用到自己的創作當中,以及通過教學來展示其文學內涵。通過分析歷代讀者對于《琵琶行》的評點,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代的讀者對于《琵琶行》的見解各有不同,這是受到時代背景、學術流派、個人思想等因素的影響。《琵琶行》里面的經典名句有很多,很多文人在寫作時會化用《琵琶行》當中的某些詩句,如張耒、歐陽修、黃庭堅等。《琵琶行》被效仿越多,經典化的概率就越大。由于白居易本人提倡要讓自己的詩老嫗能解,他的詩質樸坦然,普遍利于傳唱,受追捧程度很高。再加上社會、文化、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影響,《琵琶行》被書籍收錄的頻率很高,直至今天我們仍能在教材中看到它的身影。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琵琶行》的文學意義被后人反復地多角度地闡釋,它的文學價值在不斷的解讀當中得到發掘、認可和傳播,它的經典化過程得以逐漸推動。
①付興林:《白居易〈夜聞歌者〉〈琵琶引〉之異同比較——兼論洪邁、陳寅恪對兩詩的錯解誤讀》,《甘肅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第5頁。
② 〔明〕李沂:《唐詩援》,明崇禎五年(1632)宗元豫刻本。
③陳友琴:《白居易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5 年版,第330 頁。
④ 白居易著,朱金城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5頁。
⑤ 〔明〕唐汝詢選釋:《唐詩解》,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93頁。
⑥ 〔清〕乾隆御選:《唐宋詩醇》,中國三峽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頁。
⑦ 陳友琴:《白居易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5 年版,第88 頁。
⑧ 〔清〕蟲天子:《中國香艷全書》,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頁。
⑨ 陳友琴:《白居易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頁。
⑩ 〔后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85年版,4349頁。
? 〔清〕沈復:《浮生六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