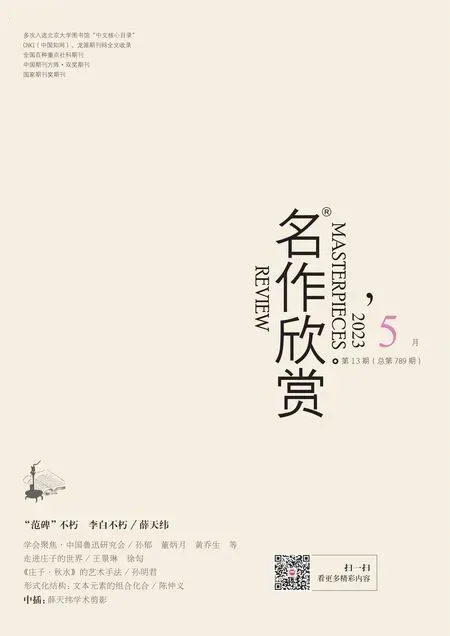充實之謂美,積健而為雄
——簡述薛天緯先生的李白及唐詩研究
海南 海濱
薛天緯先生是知名的李白與唐詩研究專家。薛先生曾自述其治學原則曰:“我做研究、寫文章,堅持一個原則,就是言之有物,不說無謂的話,不說無個人看法的話。因此,我做的題目無論大小,寫的文章無論長短,自己覺得絕無虛文。”薛先生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閱讀古往今來學人的研究成果,發現或提出問題;問題包含問題,問題帶出問題,小問題匯聚成大問題。數十年來,薛先生遵從傅庚生先生“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遺訓,解決了一系列學術問題,取得了學術界認可的成果。
薛先生治學,其研究內容是“言之有物”的“實”,其學術表達是“絕無虛文”的“實”,真體內充,超心煉冶,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充實之謂美,積健而為雄。
沉潛于李白全面研究,集其大成
薛先生以清醒的理性熱愛鐘愛酷愛李白,長期沉潛于李白研究,既有機地置李白研究于唐詩研究中,又智慧地把握李白研究的相對獨立性,聚力于文獻考證與文學探究,以李白作品編年為主線,以《李白全集編年箋注》《李白詩解》《李白詩選》三部著作集其大成。
薛先生師從安旗先生讀碩士研究生期間,在安旗先生指導下,完成了《李白年譜》(齊魯書社1982 年版),奠定了李集編年的史學基礎。1983 年,安旗先生讀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大野實之助教授將李詩進行編年的著作《李太白歌詩全解》,對日本同行欽敬之余,發愿要自己完成一部李白作品編年集。1984 年,《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項目啟動,安旗先生攜薛天緯、閻琦、房日晰三位先生,“夏戰三伏,冬戰三九”,備極艱辛,以六個春秋克竟其功,由巴蜀書社1990 年首度付梓,2000 年修訂再版;2015 年由中華書局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易名《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出第三版,2020 年修訂重版。此書以清通簡要的校勘、精警暢達的箋注、條貫融通的年譜、雄健飛揚的序跋,具足四美,大面積解決了李白詩文的編年問題,并以一條紅線將李白的人生、思想、創作連綴貫穿起來,系統地為李白詩文的解釋提供了比較信實的答案及比較有效的解決方法。從1982 年《李白年譜》出版到2020 年《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重版的近四十年間,薛先生全程參與李集編年箋注,筆者有《四美具二難并——評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載《中國詩歌研究動態》第二十輯,2017 年)專文研討,茲不贅述。
正是在這深度沉潛的李集編年過程中,薛先生李白研究的兩類問題陸續展開。一類是文獻考證型的,以認知的準確性為目標;一類是文學探究型的,以理解的合理性為目標。當然還有兩類交織兼美的。文獻考證型的問題,既有探討李白生平行跡方面的,如李白出蜀、兩入長安、幽州之行、李白與唐肅宗關系、卒年問題等;也有考證李詩的具體創作背景或者旨歸的,如辨正《別匡山》,推原“學劍來山東”,考索《上皇西巡南京歌》詩旨等,這一類問題是李集編年得以實證建構的骨骼與基礎。文學探究型的問題,從薛先生的碩士學位論文《李白詩歌思想綜論》就已經開啟,其后比較典型的探究主題有:李白詩歌與盛唐氣象、李白對“左思之嘆”的歷史性回答、人性與李白的愛情觀、李白批判現實的個人抒情詩、李白詩歌中的傳統現實主義內容、李白的游仙詩、“太白遺風”及李白的飲酒詩、道教與李白之精神自由、李白的宇宙人生觀、李白情系謝朓等,從各個方面拓展了我們理解李白的厚度、深度、溫度與柔韌度,而這樣的探索恰恰是李集編年得以脈絡貫通的血肉與氣韻。將兩類問題交織兼美者則以《蜀道難》《靜夜思》《夢游天姥吟》《古風》的研究為代表,既能工筆為細,精研章句,考據“微言”,又善寫意雕龍,窮究義理,縱論“大義”;代表性成果如《漫說〈靜夜思〉》《〈靜夜思〉的前話與后話》《〈靜夜思〉的討論該畫句號了》與《〈夢游天姥吟留別〉詩題詩旨辨》《〈夢游天姥吟留別〉詩題辨誤》兩組系列文章,以及《也談〈蜀道難〉寓意》《圣代復元古 大雅振新聲——李白〈古風〉(其一)再解讀》兩篇文章。以《圣代復元古 大雅振新聲——李白〈古風〉(其一)再解讀》為例,薛先生認為:此詩從社會與文學兩方面標舉的最高理想是西周,其文學為大雅;其次是在歷史上亦堪稱盛世的漢武帝時代,其文學為揚、馬之賦;與此同時,詩人對唐王朝的盛世寄予極高期望,既望其政治清明,亦望其文學昌盛;他明顯是將“圣代”擬為西周,又將詩歌在當代的振興擬為“大雅”重現,即:圣代復元古,大雅振新聲。得出這一結論的關鍵環節是對“揚馬激頹波”句中“激”字的理解,薛先生在袁行霈、林繼中等先生推倒眾家貶語舊說而正面解讀“揚馬激頹波”意涵的基礎上,引經據典,詳盡辨析,認為此處“激”字當作“遏制”解,“揚馬激頹波”即揚、馬以其宏大的辭賦成就遏制了文學衰頹的趨勢。此句含義由是暢達,上下詩句各得其所,全篇意脈自然貫通。
基于以上成果的長期積累,薛先生著《李白詩解》,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11 月出版。本書對20 世紀及21 世紀前10 年學界諸家著述中涉及李白詩歌的實證性研究以及立足于實證性研究的詩旨闡釋的成果做了盡可能全面的檢視,廣泛汲取各家原創型成果,并融匯自己的研究所得,對所涉及的李白詩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新解讀,具有集大成、實證性、畫句號、善創新的明顯特征,洵為李白研究學術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要成果。全書選入李白詩歌298 題484 首,約為李白詩歌總數的一半。入選解讀的詩歌,至少涉及了李白研究的數百個各類大大小小的實證性問題,其中,李白研究學術史上最主要的問題有27 個。薛先生進行的實證性研究,具體有三大類:詩篇所涉及史實與詩人事跡的考訂、詩中語詞的訓釋、詩篇題旨的探究。正是薛天緯先生對李白、對李白詩歌、對李白研究動態的熟稔與精深,不少李白研究的重大問題才有可能在《李白詩解》中“截斷眾流”或者“畫上句號”。筆者另有專文《李白研究學術史上的標志性成果——評薛天緯〈李白詩解〉》(《綿陽師范學院學報》38卷,2019年第7期),茲不一一。
相對來說,薛先生《李白詩解》的專業性很強,偏向學術圈,而薛先生選注《李白詩選》則兼具學術權威性與大眾影響力。《李白詩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1 月出版,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至2022 年9 月已印刷8 次。薛先生《李白詩選》選詩289 題343 首,為李白傳世詩作的三分之一強;按照責編李俊先生《〈李白詩選〉編輯閱讀瑣記》的評價,此書具有詩歌編年更加準確,充分吸收學界文獻、名物、史跡研究新證,燭幽照微地細讀文本三大突出優勢。2021 年3 月3 日,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國推薦的40 種經典古籍及其179 個優秀整理版本,《李白詩選》即在推薦目錄中。
以上三種著作的出版順序,《李白詩選》最新,其字斟句酌的《前言》6500 余言亦可視為薛先生李白研究成果的最新最全面的高度濃縮與提煉。隱括這篇苦心經營、筆力千鈞、思理綿密、持論公允的文字,可以得到如下認識:
薛先生研判,李白(701—763),字太白。祖籍(族望)隴西,漢飛將軍李廣之后,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即與李唐王室同宗。先世于隋末竄于碎葉,其家于中宗神龍之初(705)潛回蜀地,居住廣漢。李白的生平經歷可分為六個時期,即:蜀中時期、“酒隱安陸”及“初入長安”前后、移家東魯及供奉翰林時期、去朝十年、從璘及長流夜郎前后、晚年。貫穿其一生的,是為了實現從政理想而發生過的初入長安、供奉翰林、北游幽州、入永王軍幕、投李光弼軍五次重大行動。廣德元年冬,李白逝于當涂,初葬于龍山,范傳正為其遷葬謝家青山,成全了他的“終焉之志”。
薛先生認為,李白詩歌以書寫人性為主。李白詩歌傳世約千首。李白的優秀詩篇之所以不朽,是因為它張揚了人性。李白屬于“主觀之詩人”,他的作品大多是以“我”為主體的抒情詩。李白的詩歌崇尚本真,絕去人工,絕去雕飾,追求天然真率之美。他抒寫情感,一任真情流注,沒有任何顧慮,不受任何成規約束,甚至看不出藝術上的追求而獨臻大匠運斤之境。他最擅于歌行與絕句這兩種利于自由抒寫的詩體。他的歌行隨手揮灑,恣意鋪張,渾灝流轉,起落無跡;他的絕句脫口而出,信手而成,清澈如水,流轉如珠。李白的詩無從效仿,無法復制,真正是自由的藝術、解放的藝術、高度人性化的藝術。
薛先生總結,天才詩人李白以其獨特的人格才情與藝術個性創造了既反映時代精神又張揚人類本性的不朽詩篇,詩人因而站上了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頂峰。他的詩歌則成了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垂輝映千春”的寶貴文化遺產。
潛心杜甫專題研究,獨出新解
李杜齊名,萬古流芳。如何認識和評價李杜,幾乎成為有影響力的唐詩研究學者必須直面的問題。薛天緯先生雖然以李白研究為重點,亦酷愛杜甫并長期關注杜甫研究,近年來發表了若干杜甫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引起學界的關注。
一是《杜甫“陷賊”辨》。杜甫善陳時事,世號“詩史”,安史亂起,杜甫入、出長安城的經歷以及由此引發的詩歌創作,更是彌足珍貴。天寶十四載(755)十月,杜甫得授京中八品下的微官——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初,杜甫從長安到奉先縣探家,寫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同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起兵作亂;十五載(756)六月,安史叛軍破潼關,入長安;杜甫攜家北上避亂。至德元載(756)七月,肅宗在靈武即位,杜甫奔赴靈武行在不果,約九月間又出現在長安,到至德二載(757)四月,出京奔赴鳳翔行在。從至德元載九月到二載四月,杜甫是以何種身份居留長安的?自北宋王洙在《杜工部集記》中提出杜甫“陷賊”之說,至《新唐書·杜甫傳》更為明確表述為“為賊所得”,關于杜甫在安史之亂中這段經歷的敘述已成為千年來學界共識。
如果從“為賊所得”的角度,細繹這一時期杜甫的詩作,卻又生出很多疑惑甚至矛盾。如果杜甫是在只身投奔靈武行在過程中為叛軍俘獲帶到長安城,其家人恐怕無從知悉這個消息,《春望》中“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家書”也許是泛指,但《月夜》寫“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妻子所思憶的丈夫杜甫在長安則是確指的,類似問題還有不少。所以,杜甫“陷賊”需要重新認真辨析,尋找更為合理的解釋。
薛先生積年讀杜,對這個“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問題進行了長期的“上下而求索”,提出了杜甫“潛回”長安的見解。
薛先生從三個方面進行辨析。
第一,還原杜甫被“陷賊”說法的歷史形成過程。記載杜甫生平最早的文獻如唐代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以及五代后晉劉昫《舊唐書·杜甫傳》均未有“陷賊”之說。杜甫自己的詩句回憶這段經歷稱“沒賊中”“墮胡塵”“在賊”,都是表達自己身處安史叛軍占領的長安城中,并未有“為賊所得”的說法或者語氣。那么,從現有文獻看,杜甫被“陷賊”的說法是如何形成的呢?北宋王洙在寶元二年(1039)編就《杜工部集》,并在其撰寫的《杜工部集記》中綜觀杜甫詩,得出“以家避亂鄜州,獨轉陷賊中”的結論;二十年后,嘉祐四年(1059),在王琪主持下,《杜工部集》經裴煜覆視(終審)而刊行,“陷賊”說在集部被寫定。裴煜覆視極其認真,并補遺詩文9 篇,可見其工作細致深入。次年,嘉祐五年(1060),《新唐書》撰成,宋仁宗任命裴煜校勘,經裴煜勘定的《新唐書》刊行,其《杜甫傳》中的“為賊所得”在史部被寫定。此說在杜集祖本和正史中被寫定后,相沿千年,未見異議。既然“陷賊”說有這樣一個被寫定的過程,那么,對此說進行質疑、辨析乃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薛先生從《資治通鑒》等史書對安史之亂的詳細記載入手,結合杜甫詩歌中的自述,詳盡梳理了天寶十五載五月至至德二載八月的三條線索。線索一是安史叛軍如何推進并占領長安城,如何對待唐朝皇族與文武官員和百姓,以及是否實際有效地掌控“淪陷區”;線索二是玄宗肅宗如何進行皇權更替,唐朝軍隊如何抵御安史叛軍,以及有關“淪陷區”的百姓的實際生存狀態;線索三是杜甫及其家人的顛沛流亡歷程、茍且安居狀態,以及杜甫試圖奔赴靈武行在未果轉念又勇赴長安城的努力情況。三條線索整合,就比較清晰地再現了杜甫此間的時空定位與活動軌跡,也從客觀上排除了杜甫“為賊所得”的可能性。
第三,薛先生從兩個方面論證了杜甫“潛回”長安的觀點。一方面,杜甫關切時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懷,使他不會在小小山村安住下來避亂;他至德八月奔靈武行在,次年四月奔鳳翔行在,真可謂每飯不忘君,在這一以貫之的情懷和行動鏈條中,他九月“潛回”長安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杜甫的“潛回”長安也是基于對當時形勢的了解與評估,安史叛軍在長安以搶掠財物為主,并未大開殺戒,所殺對象也主要不是“長安民”;杜甫“潛回”長安有些冒險,但不一定是冒死,所以,他在奔靈武行在未成后,回鄜州安頓家人并交代了赴京計劃,才有所行動。“潛回”長安說證成,不僅類似“未解憶長安”的疑竇自然冰釋,其長安諸詩所記錄的杜甫邂逅故人、過訪友朋等情節也就比較合理了。正因為如此,杜甫在長安城里做“長安民”,不僅創作了大量安史之亂的“實錄”“詩史”性作品,而且當平叛形勢發生轉折,肅宗移駕距離長安更近的鳳翔時,杜甫就冒險逃出長安城奔赴鳳翔行在。戰亂之中,“潛回”并逃出長安當然是有危險的,但這危險,并不是從叛軍羈押下逃脫的冒死驚險,否則,“陷賊”而大難不死的杜甫恐怕當有更多詩作回顧其驚心動魄的經歷。
薛先生在《杜甫“陷賊”辨》一文中論證了上述觀點后,認為我們確實不能低估了杜甫的膽識和勇氣,并表示稍后還要就這個題目再寫一篇續作,以繕其說。我們期待薛先生的后續成果。
二是《李杜互通互補論》。薛先生認為,“互通”是指李、杜之間的共同性;“互補”是指李、杜之間的差異性。李杜互通的基礎有三:時代、文化傳統和人性;互補則源于李、杜性格與藝術趣味的差異。
在思想傾向方面,李、杜以互通為主。他們都具有強烈的用世熱情和宏偉的功業抱負,這是盛唐時代精神的反應,也是對儒家傳統的繼承與實踐,又從本質上體現著人性之“發展”欲望;他們都渴望精神自由,堅持人格獨立,而李白顯得更為突出,這與開明向上的盛唐時代有關,與道家遺世獨立的思想意識有關,更來源于人類擺脫約束、自由生存的天性。
在詩歌內容方面,李、杜的主導傾向是互補。李白是“主觀之詩人”,詩歌抒寫自我,鑄就“詩仙”,讀李白,我們知道了人應該有怎樣的生活;杜甫是“客觀之詩人”,詩歌反映社會,著就“詩史”,讀杜甫,我們知道了人實際上是怎樣生活的。李白表現著沖破世俗約束的解放精神,杜甫體現著“仁者”的偉大情懷;二者都是出于人性。前者針對自己,針對個體,后者針對他人,針對群體,二者互為補充。當然,“主觀之詩人”李白筆下也會有客觀展示,“客觀之詩人”杜甫不少作品中的狂放激情也絲毫不讓李白。這又是二者的共通之處。
就詩歌藝術風貌而言,李、杜個性鮮明,區別明顯,是互補的,但也不乏互通的一面。李擅七絕,杜長七律,李、杜皆以歌行為勝,二者在詩體方面互補互通;李以樂府舊題抒寫個人懷抱,杜則以樂府新題寫時事,互相分工補充,又共同推動樂府詩的創新;李白詩風飄逸,杜甫詩風沉郁,互補的詩風又統一在他們作為盛唐詩壇領袖的大氣——這是在政治開明、思想解放的時代,詩人真實性情的自由表達、真實感情的自由宣泄,是詩人藝術天才與藝術創造力淋漓盡致的發揮。
薛先生在為鄭慧霞博士《盧仝綜論》一書所作序《文獻學與文藝學研究的結合》中表述,在其心目中,李白、杜甫是“頂極作家”,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隱等是“一流作家”,而該書所研究的對象盧仝可列為“二流作家”;而且,他主張作家研究大體應止于“二流”。薛先生的研究踐行了他的主張,在李、杜之外,他圍繞王維研究作《詩意與禪意——王維〈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賞析》《家貧才食粥》,圍繞孟浩然研究作《重讀〈孟浩然〉》《杜甫詠孟浩然詩一首臆讀》《孟浩然爽約事平議》,圍繞白居易研究作《白居易的“大裘”》《何物“云母粥”》,圍繞李商隱研究作《義山詩的清境》,近來又為李賀故里河南宜陽縣撰成《李賀新墓碑》,這些成果或考證詩人生平,或推敲章句解讀,或探究情辭義理,或追索詩歌境界,皆有感而發,有為而作,分別放在王維、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隱、李賀研究界也都是上乘的佳作。
專注唐代歌行研究,窮究名實
對于很多人來說,作為詩體的歌行,與樂府性質相類,大概率是這樣——人人都能說幾句,人人都難以說清說透說通。所以薛先生在其著作《唐代歌行論》的“引論”中感嘆:“歌行這種詩體似乎與生俱來地具有某種質的不確定性,使人們對它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處于模糊狀態。”薛先生長期關注并深入研究這個課題,在通覽唐前詩歌發展史的基礎上,考察了所有歌行作品,殫精竭慮,窮究名實,結晶為《唐代歌行論》,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8 月出版,列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叢書”;全書38 萬字的篇幅,分為“溯源”“衍流”和“正名”三篇。《唐代歌行論》解決的就是唐代歌行的“實至名歸”問題。“溯源”篇梳理了從“古歌”在先秦出現,“樂府歌行”在漢代流傳,到“文人歌行”在魏晉形成并在南北朝和隋代發展,最終在唐代實現歌行詩體獨立的詩學歷程,厘清了歌行的“實至”過程。“衍流”篇以“四唐”為序,詳盡展開了唐代歌行“實至”的具體細節,在研討唐代歌行創作盛況、解析唐人歌行觀念的同時,深入探究唐代歌行衍變流播進程中所體現的詩體學之“實”,水到渠成地進入“正名”篇。“正名”篇深入對比研究古今中外詩人、學人對歌行的詩體學認識,辨析了四種“小歌行”觀的合理性與局限性,創造性地提出了“大歌行”觀,給歌行做了精準的“名歸”即詩體學定義——歌行是七言(及包含了七言句的雜言)自由體詩歌。歌行研究的“實至名歸”,為唐詩詩體學研究填補了空白,拓展了空間,很快引起學界重視。胡可先教授與陶然教授在其著作《唐詩經典研讀》(商務印書館2015 年版)中提出了《唐詩經典研讀推薦閱讀書目100 種》,50 種為文獻類,50 種為研究類,《唐代歌行論》被列入研究類。薛先生又把《唐代歌行論》中關于歌行詩體的內容抽繹、概括成《歌行詩體論》一文,在2007 年第6 期《文學評論》發表;嗣后,這篇文章又被陳平原先生收入他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前沿》2010 年第5 期(英文版,譯文為王佺完成),題目為《釋“歌行”》。
與薛先生唐代歌行研究相伴而生的諸多話題中,薛先生曾專文討論一種別有意味的現象。他發現,唐代歌行中,有一類作品,形如七律,是七言八句,但卻并非七律,在《全唐詩》中竟有300 首之多。薛先生將這類貌似七律而實非七律的歌行命名為“反七律體”,并在《唐詩之反七律體說略》一文中論述這是唐詩作者們在創作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著的一種與格律嚴整的七律情趣迥異的詩歌形式,其客觀存在的實踐意義比理論價值更大,充分顯示了唐詩創作的豐富性。
重視唐人干謁現象,探幽拓域
薛天緯先生的“唐代干謁與詩歌”研究,與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研究、王勛成先生的“唐代銓選與文學”研究相類,都是著眼于研究唐詩創作的內外部關系。無論是否參加科舉考試還是接受銓選,大多數唐代詩人步入仕途都有過干謁經歷,科舉、銓選、干謁三類活動都直接關聯著詩人的身世沉浮、心態抑揚,并進而影響詩歌創作。相對來說,科舉與銓選有著明確的制度化保障,有大量的案例為史書、政書記載,也是筆記、小說的熱門話題,現象層面的研究做實了,本質層面的問題自然可以順藤摸瓜;而干謁則是實際存在但又難以說清、更缺乏大量史料支撐的問題,與科舉、銓選問題足夠豐富的“旁證”“他證”相比,干謁更需要詩人的“自證”,而這樣的“自證”恰恰也是當事人最不愿留下的。干謁現象的研究難度大,更偏向“務虛”,而這種難以名狀的“務虛”則更加接近詩人心態的本真,也就更加接近詩歌緣情言志的本質。薛先生的研究成果,是發表于《西北大學學報》1994 年第1 期、并為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4 年第4 期轉載的《干謁與唐代詩人心態》一文。文章認為:“干謁的實質是本身才具的自鬻,它當然不能沒有一定的才具為資本。但有才者未必能被當權者賞識,未必干謁有成,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難于說清楚的人為因素,其中并無公道可言。正因為如此,從事干謁的士子們的遭遇境況和感情動蕩,較之單純的科場應試就要激烈得多、復雜得多……圍繞干謁考察其感情活動,是我們了解唐代詩人內心世界的一個重要窺孔。”薛先生創造性地提出了“自矜與躁進”“委屈與自飾”“感激與感憤”三組概念來探析詩人干謁活動現象背后的復雜心態,建構了“唐代干謁與詩歌”研究的基本框架,為更多后來者研究這一選題奠定了基礎,指點了方向,示范了方法。這一重要學術貢獻,不僅至今鮮活生新,未來尚有相當大的踵武空間。薛先生的碩士研究生王佺在袁行霈先生門下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代干謁與文學》(中華書局2011 年版),即是一例。
寄心西域唐詩之路,知行合一
薛先生長期在新疆工作,西域邊塞又是關聯唐詩研究的重要學術話題,于是薛先生知行合一,解決了一系列學術難題,走出了一條西域唐詩之路。主要成就可概括為“一題一集一著作”。
一題,是指“唐輪臺”這個千百年來撲朔迷離、聚訟紛紜的問題。他發表于《文學遺產》2005 年第5 期的論文《岑參詩與唐輪臺》,及后續的《尋找詩意輪臺》《八月梨花何處開?——岑參詩“輪臺”考辨》,廓清重重迷霧,探討了漢輪臺、唐輪臺縣、唐輪臺州都督府、唐人語匯中的輪臺、岑參詩中的輪臺這五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指出岑參詩中的“輪臺”,就是他供職的伊西北庭節度使駐地,即今吉木薩爾縣境內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庭故城遺址”,從而解決了岑參詩研究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集,是詩歌選集——《高適岑參詩選評》,這是薛先生應三秦出版社“名家注評古典文學”系列叢書而作,2010 年9 月出版。這部關于高、岑詩作的選注本,其可寶可藏之處,在于一篇高屋建瓴的“導言”與二百余首高、岑佳作的獨特注釋與評點。
一著作,則是薛先生于2020 年9 月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從長安到天山:絲綢之路訪唐詩》。這本書貌似搖曳多姿的游記,實則不啻一本圖文資料翔實、史地考證嚴謹、詩史相參相證、精彩創見迭出的“新文科”學術著作。這本書最大的成就在于以科學的、實證的筆觸貫通了從大唐長安城到中亞碎葉城的西域唐詩之路,又以鮮活的詩意的文字帶領讀者神游這條唐詩之路。
本書從今天的西安啟程,內容涉及唐代長安城、大明宮、興慶宮、大雁塔、大唐芙蓉園、曲江池、華清宮、西市、終南山、杜公祠、樂游原與青龍寺、渭城等重要的歷史文化遺跡;一路迤邐西去,在天水境內,記錄了隴山、秦州(天水郡)、南郭寺、同谷、麥積山、成紀等勝景;進入河西走廊,涼州(武威郡)、甘州(張掖郡)與居延、肅州(酒泉郡)、沙州(敦煌郡)、玉門關、陽關等歷史地名與唐詩故實接踵而來;在新疆境內,盤桓過哈密的伊州(伊吾郡)、蒲類津、大河古城與甘露川,沿天山北麓,訪達吉木薩爾的北庭,沿南麓西行至吐魯番的火焰山和交河、高昌兩座故城,天山路(他地道)則連通著天山南北的城池,出了交河城繼續西南行,則可造訪庫爾勒的鐵門關、庫車的龜茲;翻越或飛越西天山,最終抵達吉爾吉斯斯坦的碎葉城與碎葉川(熱海)。
這本書的打卡線路,與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中《唐代長安西通隴右河西道圖》和《唐代瓜州、伊、西、安西、北庭交通圖》的地理交通線路基本重合,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非常清晰的西域唐詩之路。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絲綢之路訪唐詩”,唐詩是貫通地理線路的最重要的元素。全書九章三十七個小節(篇)的標題都以唐人詩句命名,正文中李白、杜甫、王維、高適、岑參、白居易等詩人的名篇奔競而來,李世民、駱賓王、王之渙、王梵志等詩人的佳句絡繹不絕。更重要的是,薛先生以自己長期從事唐詩研究尤其是李白研究的開闊視野、硬核學問與學術新鮮感,為讀者進行了很有趣味的唐詩導讀。作者在長安城的翰林院里夢李白,展示李白《清平調》所蘊蓄的大唐王朝文化軟實力;在解析李白哭晁衡詩作的來龍去脈后,感嘆李白的淚雖然白流了,但卻意外地收獲了詩;在解讀祖詠的《終南望余雪》時順便討論了唐朝空氣的能見度;在流連于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館時,提及館藏碑刻《許肅之墓志》經學者解讀后刷新了學界對李白與許氏夫人婚姻狀況的認識;在盩厔話及白居易《長恨歌》時,不經意舉出CCTV 電視節目《經典詠流傳》關于上海老中醫王之煬譜曲《長恨歌》瞬間網紅的案例;在探討杜甫于天水寫作“罷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時,順手普及了“罷官”有罷官和被罷官兩種理解的學界訟案;在《成紀》篇中,除了普及李白身世之外,更以諺語“秦安的褐子清水的麻,天水出的白娃娃”聊了聊“釋褐”話題;在《涼州》篇,圍繞高適《無題》“一隊風來一隊砂”,作者補充了兩個硬核知識點:傳世《高適集》原無此詩,孫欽善《高適集校注》據敦煌殘卷伯3619 補入;“一隊”就是“一陣”,詩人這里用了西北方言。再比如,關于“長河落日圓”中長河所指為弱水、“黃沙(河)遠上白云間”、駱賓王從軍西域、唐玄奘與高昌國王麴文泰、李白出生地碎葉等一系列學術問題的研討成果,在作者筆下都如鹽入水一般,在潤物無聲中流露出一種學術風骨與魅力。
留心唐代文史知識,博學明辨
如果從薛先生1982 年研究生畢業返回新疆師范大學算起,薛先生從事學術研究至今整整40 年。薛先生在李白研究、唐詩研究領域成果豐碩,蔚為大家,雖然與先生之天性穎悟、精力充沛、閱歷豐富、勤奮超于常人有關,但也不能忽略先生長期堅持的學術理念與治學路徑。筆者有專文《薛天緯先生的治學理念與方法》(《古典文學知識》2022 年第5 期)總結這方面經驗,此處僅就重視細讀文本、考辨文史知識做點兒簡介。
細讀文本需要從認字斷句、識物辨義開始。飽學博聞如薛先生,在這方面也毫不含糊。薛先生在治學過程中,發現李白詩《答友人贈烏紗帽》中的“烏紗帽”似與官帽無關,經檢索考證,撰《“烏紗帽”小考》,認為,烏紗帽在唐代不是官帽,是老百姓都可以戴的帽子;發現李白《行路難》(金樽清酒斗十千)詩句“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中的“歧路”不宜做岔路、錯路、離別之路解,經過長期檢索、積累、思考、辨證,形成了《“岐路”解》一文解釋唐詩里的“歧路”,歧就是路,路就是歧,“歧路”也常說成“路歧”,在這里其實就作“道路”解,由地面的道路借喻仕進之路,“多岐路”,就是一條條道路、許多條道路;然而“多歧路,今安在”?李白卻寸步難行,處處碰壁,硬是找不到出路在哪里;發現白居易《晨興》詩句“一杯云母粥”的“云母粥”的解釋被注家忽略,而《漢語大詞典》卻給出了錯誤解釋,于是孜孜以求正解,認為服用“云母粥”是白居易在修煉道教時養成的一種生活習慣,“云母粥”是用云母粉做原料煮成的粥,云母無毒,喝了對人無大害,并寫成文章《何物“云母粥”》,孫昌武先生當面稱譽此文“把白居易研究的一個具體問題解決了”。此外,薛先生考證并理順李白《靜夜思》《將進酒》文本的衍變過程,考證并還原了《古風五十九首》的命題、創編與擴容、刊刻過程,考證并論述《夢游天姥吟留別》詩名應歸正為《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都是典型案例。
薛先生人生春秋八旬,鶴發童顏,精神矍鑠,真力彌滿,心宅充實而無往不適,與歲月健行而格局闊大、氣韻沉雄;薛先生學術春秋四十,元氣鼎盛,體大思精,更欲拓進李、杜生平考論,打磨唐代歌行研究,完成唐詩縱橫篇章,以雅健之思鑄成充實之文章,以從容之筆書寫雄渾之氣象。他給予我們的是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