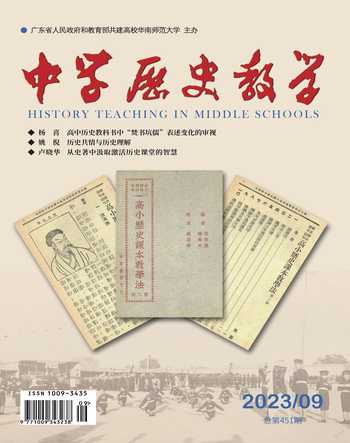由“亂”而進于“平”,由“爭”而趨于“鳴”
張俊 蘇莎
一、由“治”到“亂”:諸子之“興”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諸侯紛爭、社會動蕩、禮崩樂壞。“戰(zhàn)國”較之“春秋”而言,更是各種矛盾錯綜復(fù)雜,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西漢劉向在《戰(zhàn)國策·書錄》中概括戰(zhàn)國時期的混亂局面時所說:“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是以傳相放效,后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jīng)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quán),蓋為戰(zhàn)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1]各諸侯王為了完成霸業(yè),擴充或保衛(wèi)疆土,迫使各國進行社會改革,如楚之吳起、魏之李悝、秦之商鞅等等,皆屬此流。改革的重點大都是對傳統(tǒng)的貴族政治的革弊,使得分封制、宗法制進一步瓦解,士階層逐步獲得自由,士屬于貴族的最低階層,據(jù)《左傳·昭公七年》記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2]可見,士需要依附大夫,占有一定數(shù)量的“食田”,隨著“禮崩樂壞”,宗族已無力庇護士,無法為其提供“地”和“祿”,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士的社會地位,士在失去生活保障的同時,也擺脫了宗法制的枷鎖,不再依附宗族,也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從而獲得基本的人身自由,成為相對獨立的知識階層,在失去依托之后,必須依靠文化知識自食其力,這一批人是士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3]并逐漸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通稱。
二、由“亂”到“平”:諸子之“爭”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急劇轉(zhuǎn)型,沖突和矛盾愈演愈烈,面對社會中的諸多問題,人們紛紛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提出自己的主張、愿望和要求。所以諸子的興起,具有鮮明的“救時之弊”,是尋求治國平天下之道。[4]士不僅出于安身立命的需要,也是出于文化上的使命感,關(guān)注和擔憂社會發(fā)展方向,積極思考解決的辦法,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張[5],他們希望得到統(tǒng)治者的任用,由于他們所投靠的對象的不同,或者出身經(jīng)歷不同,成了各階級在思想上的代言人,他們可以各持一說,在諸侯之間奔走游說,合則留,不合則去。[6]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曾按照諸子各派的主要傾向,將其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而班固則不然,將諸子劃分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nóng)、小說十家,然“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7]而儒、墨、道、法又為其要者。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是其中最大的一家,提出“禮治”與“仁政”。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通過探究夏商周三代因革,得出“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8]的論斷,孔子非常推崇周公的政治,希望能夠達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9]的目的。如何實現(xiàn)之?孔子認為,必須借助“德政”,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0]。要想實行“德政”,就必須提倡“仁”,何為“仁”?一曰“仁者愛人”,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曰“克己復(fù)禮為仁”。由此可見,孔子是想用“德”“仁”“禮”等方法,恢復(fù)穩(wěn)定當時動亂的社會。孟子生活在戰(zhàn)國時期,彼時,周代的舊秩序已基本摧毀,諸侯大國的國君皆已稱王,故而不再提周天子之事,孟子繼承孔子“仁”的學說,將其發(fā)展為“仁政”,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1],除此之外,孟子還倡導(dǎo)“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可見,在孟子的治國主張中,“民”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實際上,孟子的“仁政”乃孔子“德政”的進一步發(fā)展。[12]
墨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墨翟,是當時下層民眾的代言人,他的學說往往反映“農(nóng)與工肆之人”的利益。[13]在治國主張上,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墨子認為,天下大亂的根源在于人與人,國與國“不相愛”,只知道“自愛”“自利”,從而導(dǎo)致戰(zhàn)爭不斷,“亂者不得治”。[14]因此,如果天下人都能夠“愛人若愛其身”“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其國”,則可天下大治。[15]墨家學派具有強烈的平民色彩,其學派成員也多是來自社會下層。也正因為此,墨家在當時的影響很大,故“世之顯學,儒、墨也。”[16]
道家學說以老莊為主要代表,其思想核心內(nèi)容為“道”,在其支配下,政治上則主張“無為而治”“政順民心”,進而臻至“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道德經(jīng)》:“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fù)結(jié)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17]顯然,老子所向往的并不是未來的理想社會,而是早已在歷史上消逝了的,經(jīng)他美化了的保有原始公社遺跡的早期奴隸制社會,[18]這種理想社會是與人類文明歷史的進步背道而馳的。戰(zhàn)國時期的莊子繼承和發(fā)展了老子之“道”,在治理社會方面,莊子似乎走向另一個的極端,認為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可怕和痛苦的,竭力逃避現(xiàn)實,追求精神上的絕對自由,把現(xiàn)實的王權(quán)看成贓物,仁義是非看成刑具,因而不要有任何作為。[19]
法家學說上可追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chǎn),但實際的創(chuàng)始人是戰(zhàn)國的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慎到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可以說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是法家思想的總結(jié)者。法家在治國主張上,提出具有發(fā)展進化因素的歷史觀,力圖論證戰(zhàn)國時期政治、經(jīng)濟的變動是合理的、進步的,同時批評儒家的守舊思想,韓非認為歷史是不斷進步發(fā)展的,復(fù)古的主張是行不通的。諸家之中,法家思想可以說是最具進取精神的,極力主張加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quán),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shù)”,慎到重“勢”,均是從不同角度加強君權(quán),韓非則認為,要想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quán),“法”、“術(shù)”、“勢”三者缺一不可,[20]也只有這樣,才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21]。
綜上而言,儒、墨、道、法四家在治國方略上,均提出了各自主張,實是各有千秋,各有所“爭”。儒家積極入世,道家則主張出世。對于民眾的欲望,也是有所“爭”的,法家不像儒家或道家那樣主張寡欲或無欲,而是承認人的欲望,[22]“設(shè)民所欲,以求其功。”[23]不僅如此,韓非還批評儒家的“德政”和“仁政”。[24]墨家也是對儒家的一些主張?zhí)岢雠u,是孔子思想的反對者。[25]道家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評儒、墨的[26]。等等。
三、由“爭”到“鳴”:諸子之“融”
前文已述,諸子之思想,實則是為“救時之弊”而提出諸家各派之主張,此則眾家“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27]諸家學說的出發(fā)點和最終歸宿都是為了尋求治國平天下之道,諸子雖“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28]可見,諸子百家雖“爭”,卻也有“共鳴”“共融”之處。試舉幾例,以求證于方家。世言荀子乃儒家思想之代表,然而荀子既非正統(tǒng)的儒家,亦非典型的法家,而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chǔ),吸取各家之所長,自成一系的思想家。[29]“禮治”與“法治”本是儒、法兩家對立的主張,但荀子卻既主張“隆禮”,又主張“重法”,他認為“禮者,法之大分。”[30]二者并非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其弟子韓非、李斯皆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的思想淵源也有來自于老子、商鞅、申不害等人。李悝、吳起也曾是子夏的弟子,也可見諸子之“共鳴”“共融”。墨子相傳早年曾受儒家教育,后拋棄儒學,自成一家之言,[31]孔子講“仁愛”,墨子言“兼愛”亦有相同之處,所唯不同在“愛有差等”與“愛無差等”。諸子之“共鳴”“共融”的精神,也影響其后世中國學術(shù)思想之發(fā)展,如董仲舒之新儒術(shù),糅合了道、法、陰陽五行等學派;此后,中國的學術(shù)也沒有純粹的儒、墨、道、法等諸家思想,而是達到了彼此“共鳴”“共融”“共生”,遂成中國博大精深之體系。正如張豈之先生所言“中國諸子各派學者……一開始就綜合地、辯證地、現(xiàn)實地觀宇宙,悟人生,而不是專門地、分析地、抽象地求知識,愛智慧是諸子學的特點。這個特點,也極大地影響了后來的中國思想文化歷史進程。”[32]
【注釋】
[1][西漢]劉向:《戰(zhàn)國策箋證》(上)“劉向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頁。
[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284頁。
[3][5]《中外歷史綱要(上)》教師教學用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21—22頁。
[4]何靜主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9頁。
[6][13][18][19][20][25][29][31]朱紹侯等:《中國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6、157、118、158—159、162、157、161、157頁。
[7]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28—1746頁。
[8]張燕嬰譯注:《論語》,為政第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2頁。
[9]張燕嬰譯注:《論語》,季氏第十六,第253頁。
[10]張燕嬰譯注:《論語》,為政第二,第12頁。
[11]萬麗華、藍旭譯注:《孟子》,公孫丑上,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0頁。
[12]萬麗華、藍旭譯注:《孟子》,前言,第3頁。
[14]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卷二,尚賢下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98—99頁。
[15][22][26][32]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文化史》,第105、165、86、91—92頁。
[16][清]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顯學第五十,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56頁。
[17][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jīng)注》,八十章,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98頁。
[21] [清]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第二,揚權(quán)第八,第44頁。
[23] [清]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五,難一第三十六,第352頁。
[24]具體可參見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文化史》,第168—172頁。
[27] 金景芳、呂紹剛:《周易全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79頁。
[28]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第1746頁。
[30][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勸學篇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