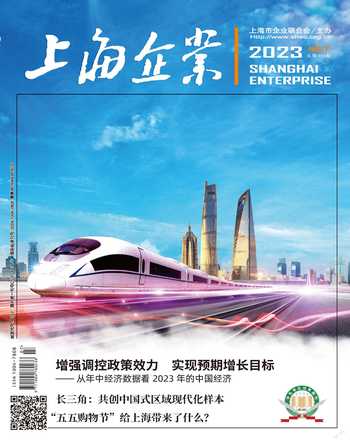數字經濟下跨境稅收征管問題研究
王美茵

一、數字經濟的內涵與特征
(一)數字經濟的內涵
自進入信息時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全球開始衍生出與農耕時代、工業時代經濟形態不同的數字經濟,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新型業態,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影響。數字經濟本質在于信息化,依托于網絡基礎設施,利用互聯網、區塊鏈等信息技術,以數據為核心要素,將人類經濟形態由傳統的工業經濟轉向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信息化經濟,極大降低了各類交易方式的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推動社會經濟、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二)數字經濟的特征
1. 以數據為核心
數字經濟的發展以數據為核心。數字經濟時代下,數據支撐起社會的正常經濟運轉,所有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都被數據化,所有企業的發展都離不開數據信息,企業利用數字經濟技術搜集、分析數據,能夠清楚把握數據的實際價值,提升市場經濟效率。因此,數據已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下企業發展不可替代的要素。
2.交易虛擬化
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交易過程逐漸拋棄傳統的“實體”特征,數字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搭建一個虛擬的交易平臺,將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在該虛擬平臺進行交易,用戶可以直接在線上選購商品或服務,企業無需設置實體經營場所,單純依靠數字技術就可以完成交易,為用戶帶來方便的同時節約成本、提升效率。
3.助力產業融合
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產業與數字產業正在逐漸融合,把新興的數字技術應用于傳統產業,可以提升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提高傳統生產性能,推動傳統技術革新,促進傳統產業向數字化、智能化產業方向轉變。同時,利用數字技術可以幫助傳統產業產生新型經濟模式與行業模式,逐步加深產業融合,提高資源利用率。
二、數字經濟給跨境稅收征管帶來的影響
(一)數字經濟影響國際稅收規則
1.常設機構規則界定失效
各個國家都將“常設機構”作為掌握經營者收入情況、監督經營者納稅情況的依據。國際稅收規則對跨國經營者的收入以及納稅情況有著以下規則:跨國企業在境外取得的收入,由企業所在國按照收入額行使居民管轄權來征收所得稅;跨國企業在境外發生的交易,由交易發生所在國按照具體交易額行使來源地稅收管轄區來征收增值稅。而數字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去實體化”,數字企業發生的各項交易都是利用互聯網等數字技術來完成,不需要設立傳統的“常設機構”,因此,實際中企業為了避稅,在跨國交易中不在收入來源地設立常設機構,也就無需繳納相關稅收。收入來源國無法準確掌握經營者取得的真實收入,常設機構的規則界定也由此失效。
2.企業逃避稅更加便捷
由于數字經濟具有快捷性、去實體性、流動性等特征,使得數字企業容易通過跨國重組價值鏈等手段,將盈利額轉移到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例如Google、蘋果、Facebook公司曾采用“愛爾蘭-荷蘭三明治架構”來避稅,按照愛爾蘭國家政策,如果企業的運營管理權和控制權都不在愛爾蘭,則該企業在愛爾蘭的分公司可以享受零稅率的優惠。荷蘭則允許歐盟境內公司交易無需支付企業所得稅。而如今數字企業的利潤來源絕大多數是專利授權等無形資產轉讓,所以這些跨國企業利用數字企業的產品或服務高度依賴無形資產這一特點,將企業的收入與利潤轉化為無形資產即知識產權等形態,通過這種手段把巨額利潤注入在愛爾蘭注冊的公司中,該公司由“避稅天堂”控制,美國的跨國公司就曾利用該運作方式避稅1000億美元,因此,數字經濟為數字跨國企業利用全球各國稅收制度的差異來避稅提供了平臺。
(二)數字經濟影響稅收管轄權的判定
數字經濟的發展與相關產業融合衍生出了大量無形的產品(例如數字加密貨幣)與虛擬服務,數字化跨境交易的交易雙方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彼此信息隱蔽,傳統的稅收管轄權難以有效確定交易雙方的真實身份。我國對于所得稅按照收入來源地進行征稅,對于增值稅、消費稅等流轉稅按照產品實際消費地進行征稅,而企業則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完成產品的銷售與運輸,通過云端辦公、遠程控制等方式管理生產運營;同時,還可以將企業注冊地設置到“避稅天堂”。此外,企業的財務狀況也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隱藏,制作備份。因此,產品的實際消費地與所得來源地難以確認,傳統的稅收管轄權已然不能解決,稅務機關如何判定所得來源地以及產品消費地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數字經濟干擾稅務機關獲取涉稅信息
數字經濟的發展催生出第三方支付平臺、虛擬貨幣與虛擬資產等數字經濟交易,其具有隱蔽收入、節約交易成本、即時性等特點,雙方交易僅在線上支付平臺就可以完成,使得國內與國際上的稅務機關獲取涉稅信息的困難加大。在稅務機關與數字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稅務機關難以準確掌握數字經濟的真實交易量與交易額。另外,現如今有許多不法分子通過“搭橋”等方式完成線上跨境交易,現有的稽查工具無法有效應對獲取交易證據的難題,為稅務機關增加了稅務監管難度。
(四)數字經濟對稅務人員專業水準提出挑戰

如今跨國、跨境交易繁多,數字企業經濟體量大、交易流程監管難度增加等問題層出不窮,為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稅務機關不僅需要先進的稅收征管技術,更加需要復合型數字化人才。在稅收征管實踐中,稅務人員多以稅收專業知識人才為主,熟練掌握相應信息系統運用的人才較少,導致基層稅務機關監管稅收動態、核查數字化風險能力不足,無法適應我國信息化建設進程。
三、數字經濟下加強跨境稅收征管的對策
(一)積極參與國際稅收規則制定
一方面,可以在判定規則中引入“顯著經濟”的存在和設置“虛擬常設機構”的內涵,主要是應對為規避納稅不設立常設機構而利用線上完成跨境交易的情況。雖然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存在差異,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常設機構,但用戶也從線上平臺的產品與服務中獲取收入,因此可以將線上完成交易的平臺、服務器作為虛擬常設機構,分析用戶交易信息,對收入來源地進行精準定位,以避免避稅的情況,減少稅收流失;另一方面,要加強無形資產反避稅管理。數字經濟企業避稅的一大特點就是利用無形資產轉讓給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因此,一是要按照OECD發布的《關于難以估值的無形資產稅務管理應用指南》有關規定,增加無形資產交易事后稅務審核機制,主要是限制企業無限將收入與利潤轉化為無形資產再轉讓給其他關聯企業的行為。二是制定稅收管理指引,判定各關聯企業對集團總收益的實際貢獻價值量,以此分析取得無形資產交易結果的準確性,確保企業研發成本與利潤一致。
(二)健全稅收管轄權的界定規則
數字經濟的發展導致收入來源地與產品消費地難以準確確定,單純依靠傳統的稅收規則來界定稅收管轄權已經不能適應數字經濟時代。因此,健全稅收管轄權的界定規則應該建立在遵循稅收法定原則的基礎上,結合數字經濟的特征,對收入來源地與產品消費地的內涵進行重塑。一方面,要在法律法規上做出修訂,相關部門應結合數字經濟的特征、范圍,根據各企業的多種跨境交易方式的經濟實質,對收入來源地與產品消費地做出準確的判定標準,為數字經濟稅收征管實踐提供法律依據;另一方面,要完善產品消費地的稅收征管機制,堅持消費地征稅原則。數字經濟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構成了企業數字經濟價值中的數據價值,由于數字經濟具有交易虛擬性的特征,就不易確定實際交易所在地,因此可以通過對數字經濟企業交易中的電子稅票的支付者的相關信息先進行了解和綜合判斷的方式確定數字經濟消費所在地。同時,還應完善消費地原則,在流轉稅的征收范圍中增加數字服務,設定稅率,調整數字經濟企業的相關稅收優惠措施,采用第三方支付平臺代收代繳稅款的制度。
(三)提高涉稅信息獲取能力
隨著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數字企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數字貨幣等新的經營結算方式,利用先進的信息化技術完成跨境交易,為稅務機關的稅收征收管理增加了難度。面對數字經濟的發展形勢,稅務機關首先要培養稅收信息化、數字化人才,做好人力資源保障;其次,要盡快建設系統的信息收集方案,完善涉稅信息與其他部門之間的共享機制,使各種涉稅事項的辦理更加規范,有效監控稅源,爭取從源頭上消除信息不對稱;最后,要建立稅務數據信息分析與預警系統,能夠對大量的稅務數據進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以此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與效率。
(四)建設復合型人才隊伍
如今數字經濟發展迅猛,建設一支數字經濟稅收征管人才的隊伍勢在必行。首先,要優化人才選拔機制,在選拔公務員考試中增設招收精通信息技術、計算技術的選項,專門招收信息技術人才;其次,稅務機關對工作人員的培訓需要與時俱進,稅務人員應及時掌握最新的政策動態和導向,加強對信息技術的學習,避免因為業務不熟練和知識欠缺而出現的工作障礙。此外,還應定期對稅務人員的學習教育進行考核,落實學習效果,避免重形式輕實效,確保教育培訓工作提質增效。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