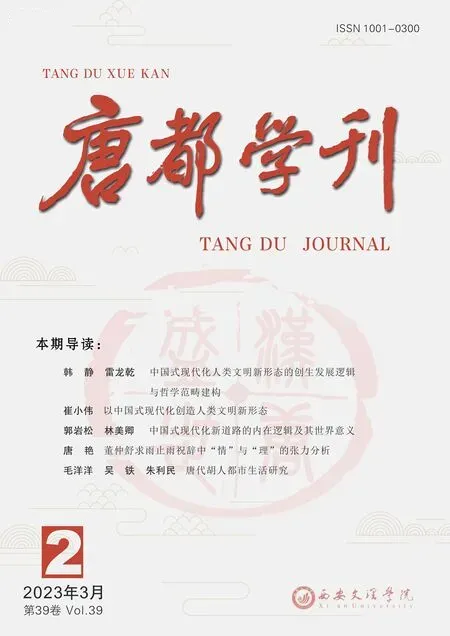論先秦儒家“善”的三重境界
廉天嬌
(江蘇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關于境界,湯一介認為“境界”是人們達到的修養境地[1],故以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境界對照“真、美、善”,并將“善”看作是“知行合一”。馮友蘭認為境界“是人對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底覺解”[2]43,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說。本文論述的主體境界,主要是人們所追求的道德修養、思想覺悟、精神價值層次和價值目標的達成。一般來說,境界是對人生價值的認同,價值指向的不同往往會達至不同境域。“善”作為價值判斷、道德基礎,已然包括人在自然、社會中的價值的滿足,就其本質來看,“善”是實現主體必然性的境界。在先秦儒者們看來,由于人的精神心理層次的體悟不同,“善”的境界也有不同的層級:一般境界的自足其樂、漸次境界的淑世情懷、最高境界的止于至善。
一、先秦儒家“善”的一般境界:自足其樂
先秦儒家“善”的一般境界是最為基礎的,旨在個人身心的愉悅和滿足,類似西方哲學家所說的快樂,但不同于西方的快樂主義。中國哲學當中也講“樂”,但并非停留在物質層面的享樂或欲望的滿足,而是包含了“樂”的道德精神,即“自足其樂”“樂山樂水”“安貧樂道”的曠達超脫,是心靈境界的一種提升,這樣的“樂”才是中國哲學語境下“善”的境界。
李澤厚將中國古代這樣的“樂”的精神概括為“樂感文化”(1)“因為西方文化被稱為‘罪感文化’,于是有人以‘恥感文化’或‘憂患意識’來相對照以概括中國文化。我以為這仍不免模擬‘罪感’之意,不如用‘樂感文化’更為恰當。”參見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288頁。是極為恰當的。先秦時期儒道兩家皆講“樂”,表現出積極豁達的超脫境界。《論語》開篇就談到學習之樂、朋友之樂和君子之樂。生活中是需要樂的,并且要以“善”為樂。那么這就要求“樂”不是停留在耳目聲色的歡愉,而是心靈的超越和善的追求,具有積極向上的價值訴求。《論語》中記載孔子及其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子侍坐”的故事,夫子讓學生們各言其志,其中曾皙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3]123-124曾皙描繪的是一幅詩情畫意的場景,于暮春時節出游,一群人乘興而來,盡興而歸,每個人都逍遙快樂,能夠讓人產生共鳴,正是表達出儒家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和理想追求,展現儒者“樂”的情懷。儒家的“樂”能夠寄情山水,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正如《論語·雍也》所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3]87。孔子對山水十分熱愛,山之沉穩,水之靈動,樂山樂水,將山水與人的心靈感情聯系起來,知者動,仁者靜,人性在這樣的環境中,與大自然融合為一,所以這也是一種“樂”的情懷。
不過,理想終歸與現實有很大差距,與“樂”相伴隨的還有“苦”,譬如佛教把人生看作是苦的,基督教把人生看作是贖罪的,皆是為了教人向善。實際上,儒家、道家談樂,亦是具有善的導向。人在現實生活中,難免會面對各種各樣的磨難和挫折,因此儒家教人要苦中作樂,道家教人知足常樂。尤其儒家提倡“安貧樂道”的精神: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3]93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3]85
孔子非常贊賞顏回樂的境界,這就是宋代理學家一直探討的“孔顏樂處”。宋代周敦頤追慕孔顏之樂,并讓二程兄弟去探尋孔子和顏回所樂為何。“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4]16程顥認為:“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4]135所以,這里的“其”樂究竟是何樂?簞食、瓢飲、陋巷是如此艱苦的環境,外界不足以為樂,而是自己內心的超脫的快樂,即超然的精神境界。周敦頤認為是“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5]“忘其小”是超越小我而證悟本體,物我兩忘則能體察萬物之自然之性,與莊子所講的“坐忘”類同,如果能忘記周遭環境的苦難,心靈就會得到升華。因為人本身都是趨樂避苦的,若能在艱苦條件下仍得到提升,成就自我,亦是一件快樂的事。“孔顏之樂是超越了眼前貧困境遇與個人富貴得失之后自我心靈的價值抉擇,與外在環境是窮通或是榮辱并無必然關聯。”[6]所以,在孔子看來,顏回能夠苦中作樂,不改其樂是一種境界,超脫了物質生活條件的享受,內心是充實快樂的。因此,人的內心保持樂境,并以此實現自我的價值,發揮善的潛質,最終達到理想人格,這樣的“樂”才是積極向上的。
然而西方倫理學中的快樂,往往與人的自然生理、心理欲望聯系在一起,常常把快樂主義等同于善,甚至把實現人的欲望稱之為善。在先秦儒家哲學中,孟子曾對“欲”與“善”的關系做出界定,即“可欲之謂善”。而這一命題引起廣泛爭論,這還要從“欲”的概念切入探討。在先秦儒家典籍中,“欲”字出現比較頻繁,歸結起來,大致有兩個含義:一是表示喜歡,想要得到的,這種欲求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比如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69這里是將“欲”與“惡”相對來說,“欲”表示的是喜歡。二是人的自然生理欲望,如耳目口腹之欲,人的這種欲望絕大多數時候,是被排斥的。耳目口腹之欲對于個人的身心修養是不利的,所以孟子曰:“養成心莫善于寡欲。其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他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3]350然而,孟子卻以“可欲”論“善”,“可欲”應作何理解?朱熹曰: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3]346
朱熹的觀點表明善的事物必定可欲,這是現實世界一種普遍認同的定理,反過來,可欲的是否都是善的呢?這不一定成立。張奇偉認為:“‘可欲是善’是指引起人們歡悅的價值或具有這種價值的物都是善或善的。而‘善是可欲’強調善是能夠滿足人們欲望、需要,從而帶來歡樂、愉快的價值或具有這種價值的物。”[7]前者的說法,傾向于西方快樂主義和享樂主義,以滿足個人欲望為主,是不符合孟子本義的。因而“善是可欲”應是孟子“可欲之謂善”的正解。既然“善是可欲的”,那么“可欲”的內容是什么?換句話說,能夠滿足人的欲望、需求的價值或具有這種價值的事物是什么?“可欲”實際上強調人們內心最直接對仁義禮智的欲求,無一絲一毫私心驅動,或為名,或為利去追逐善,那樣并不是真正的善。因此,“可欲之謂善”,一定是無偏私的、純粹的、直接的欲求,沒有這一前提,則不能謂之“善”。換言之,從“欲”的角度來說,分為“可欲”和“不可欲”兩部分,“可欲”是人的仁義禮智四德,發端于人之本心,故而善。“不可欲”的是人的自然生理欲求,盡管原本無所謂善惡,但僅僅停留物欲的享受,欲求過多,就必定滑向惡。因此,“善必定可欲”,而可欲不一定是善的。
因此,在厘清了樂與善、欲與善的關系之后,不難理解,先秦哲學家那里的“樂”并非純粹的物質層面的享樂或欲望的滿足,而是具有“樂”的精神,即“自足其樂”“樂山樂水”“安貧樂道”的曠達超脫,心靈境界的一種提升,而這樣的“樂”才是“善”。進而將個人之樂加以推廣,擴充到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中,則進入另一層境界——淑世情懷,能夠胸懷天下,博施濟眾。
二、先秦儒家“善”的漸次境界:淑世情懷
先秦儒家思想極具淑世情懷,致力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盡管這一社會理想不能稱之為境界,但儒者博施濟眾、修己安人的精神值得推崇。因此它作為“善”的漸次境界,即由個人之樂,推向兼濟天下人之樂的高度。那么這種精神境界,在宋代被稱為“圣賢氣象”,倡導“以天下為己任、以名節相高的人格精神”[8]。尤其是以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為代表,展現出儒者崇高的濟世情懷。
在先秦儒家道德體系中,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稱頌的圣人均是修己安民、博施濟眾的理想人格。“內圣外王”不僅強調個人內在品格的培養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而且強調經世濟民的淑世情懷。孔子談到自己的志向,是希望讓老人能安度晚年,由此朋友信賴他,年輕人懷念他。再接續上文所說的個人之樂,在孟子那里,這一“樂”的精神被加以推廣和普及,轉變成為“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樂民之樂”“與民同樂”等,諸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201。“與民同樂”強調的是與群體的和諧,所以孟子更為注重現實社會中個體與群體的關系,也就是君王與百姓的和睦關系。孟子所說的“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3]332,皆是與國家、社會緊密聯系的,以自我道德的完善為起點,并推己及人,使天下百姓都能快樂自足。自我價值的實現以群體的幸福快樂為目標,展現出的就是一種濟世情懷。實際上,先秦諸子都有這樣的價值傾向,如孔子向往“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大同社會;孟子倡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理念;墨子主張“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的兼愛思想。莊子描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天、地、人、萬物彼此和諧的圖景,皆是自我與他者、個人與群體關系達到的一種和睦,也就是“善”的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淑世情懷并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成王成圣或者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功績(2)參閱《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里概括了“三不朽”的意義和價值,其疏曰:“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圣德立于上代,惠澤被于無窮;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三立”中,立德是基礎,立功是核心,立言是對前兩者的概括總結。古人常把“三不朽”作為最高的精神追求。。因為現實中,并非每個人都能立功、立言,絕大多數人都是獨善其身。那么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之間,二者是否是矛盾的?《孟子·盡心上》有云:
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3]329
當人們“獨善其身”時,能夠“窮不失義”,履行社會賦予的責任和義務,并在道德修養上自我提升,這也是一種淑世的行為,譬如《大學》講“八條目”,雖然是一套個人道德的修養功夫,其中蘊含了濟世救民的崇高政治理想,這對于我國當前公民道德建設具有重要啟示。實際上“八條目”涵蓋個人、家庭、社會三個領域,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主要針對個人層面來說,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接觸各種各樣的人和事物,不僅增加閱歷且增長見識,從中可探究為人處世之道、待人接物之禮等。除了經驗所獲,還能從書本中獲取學問知識,這里的“知”,不僅是一般的學問知識,也指道德認知。當一個人具備思維能力和道德認知能力,才能明辨是非善惡,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這樣“物格而后知至”。至于“誠意”,則強調意念真誠,不自欺,不欺人,通過不斷的修養,提高自身的德性,最后去除內心的私欲雜念,保持心靈澄明,心得其正,不偏不倚,不涉感情,即“意誠而后心正”。由此可見,只有經過個人道德境界提升,方可彰顯出“善”。后四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在家庭、社會場域中對個人和全體成員提出新的要求,“修身”是溝通個人和社會的紐帶,既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落腳點,又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當一個人修之以身,樹立正確的道德觀,自身品行端正,方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促使家庭和睦。齊家之后,進一步向外推廣,教化百姓大眾。這也就是儒家所倡導的推己及人,仁者愛人。賢明的君主應為政以德,實行德治,以至善之德化育百姓。不僅使本國百姓獲益,若推而廣之,布仁政于天下,使天下太平。因此,人們應當具有“兼濟天下”的抱負和志向,推動社會群體朝“善”的方向推進。即使當因外在因素一時無法做到時,不妨“獨善其身”,端正自身的言語行為,亦能夠修己安人,止于至善。
三、先秦儒家“善”的最高境界:止于至善
“至善”究竟是什么?不同的思想家曾給出不同的答案,一種認為至善就是快樂,另一種認為至善是幸福,幸福是一切行為的終極目的。例如伊壁鳩魯學派提出快樂是至善,“心靈的快樂就是觀賞肉體的快樂;德行是指追求快樂時的審慎權衡;正義在于不擔心自己的行為會引起別人的憤恨”[9],認為生命之善是最重要的,尤其感官、肉體所感知的快樂是最直接的,西方的享樂主義者注重的就是這樣一種快樂,顯然與中國古代哲學家的觀點相異。
“善”的最高境界是“至善”,原自先秦儒家典籍《大學》,被視為“三綱領”,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以及“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首先來看“明明德”,第一個“明”是通曉之意,就是要使“明德”彰顯明白,肯定了人們與生俱來的靈明德性,需要通過后天的努力學習,才能進一步顯現出來。人人皆有趨善避惡的心理,這是人所固有的,并非外在社會規范強加的,而道德實踐往往是由內而外展開的。因此說“善”是道德的基礎,而德的顯現亦是善的落實。再來看“親民”,學界存在兩種說法:一是“親近“之意,二是“新”的意思。朱熹和王陽明都對此進行了解釋,朱熹認為“親”乃是“新”意,世界不停變化,每一天都是新的,那么人無時無刻不在行善之途上前進,永遠是個新人。而王陽明認為是“親民”,因為“新”與后文的治國平天下無緊密聯系,且說“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10]。明明德即是實現“仁”,就是親民。王陽明將“親民”和“明明德”看作一件事。筆者認為“親民”主要是個體善德彰顯之后,能夠影響并幫助其他的人,使人們提升道德境界,從而在群體中獲得認同感,這也就是“善”的漸次境界中濟世情懷的效應。而“至善”是指心靈獲得最大程度的自由,達到外界與事物發展相統一的境界。“止于至善”則是最高的價值目標和道德境界,也是“明明德”和“親民”的最終價值導向。
儒家講的“至善”,相當于道家老子的“上善”,指天地間最高的“善”的美德。二者相比較來說,老子的哲學體系是在其“道”的框架之下建構的。道是天地萬物的根源,是不可言說的、形而上的實存之道,而“善”則是道在天地之間流轉而產生的。這與儒家思孟學派所說“善”根源于人的內心、先天稟賦是不同的。《大學》里的“至善”是人的道德達到的完善境界,“至善”作為境界,并不是形而上的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張岱年《真與善的探索》一書中說道:“所謂至善是矛盾的,善要求二事,一完滿,二進步。此二者不能并存,故至極之善是不可達到的。完全之善包含靜止,絕對和諧將是寂靜。然宇宙無靜止,故絕對的善為不可能。”[11]不同于西方哲學家所言的至善是最高的善,是絕對的。所以這就要進一步理解“止于至善”的“止”,究竟是停止不動,抑或是窮盡之意。《說文解字》中解釋“止”為“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12]。這就是說“止”本身是草木的根,象征埋在地底下的基礎,引申為停止、居所等。如《詩經·商頌·玄鳥》說“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便有“住所”之意。《大學》中還強調“知止而后有定”,當人有明確目標歸所的時候,內心安定,只要朝著它前進,進而通達道德境界。唯有“知其所止”方能“止于至善”。來處亦是歸途,王陽明《傳習錄》中將“止”看作是對本性的一種復歸,他說:“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10]24當然,這樣的前提是“善”在心之內,才能恢復本然狀態。止于至善,是自我境界的升華,也是“善”的最高境界,復歸本然。因此,“止于至善”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圣人境界,心之澄明,善之復歸,人格之完滿。
由此可見,“至善”不是別的,應是能夠滿足人們身體、心靈、精神等需要的價值歸宿。西方哲學家將其稱之為“幸福”,即至善是幸福。康德認為至善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無條件的,是整個人類行為的最終目的和人生理想。他說:“既然德行和幸福一起構成一個人對至善的占有,但與此同時,幸福在完全精確地按照與德性的比例(作為個人的價值及其配享幸福的資格)來分配時,也構成一個可能世界的至善:那么這種至善就意味著整體,意味著完滿的善,然而德行在其中始終作為條件而是至上的善,因為它不再具有超越于自己之上的任何條件,而幸福始終是這種東西,它雖然使占有它的人感到快適,但卻并不單獨就是絕對善的和從一切方面考慮都是善的,而是任何時候都以道德的合乎法則的行為作為前提條件的。”[13]德行和幸福共同構成至善,至善是完美的,盡管幸福使人感到愉悅,但是它并不能成為全部的至善。至善是從動機到結果都是善的。人的行為表現出的善惡,往往和動機有關。康德認為一種行為是否合乎道德,關鍵在于動機是否出于善良意志,其判定標準是“道德律”——實踐理性法則。“道德律”作為一種法則和衡量標尺,能夠判定行為的善惡,它也是至善的根據。先秦儒家哲學所講的道德,則是人之內心稟賦,是人之為善的動力。由此觀之,至善在中國哲學中并不能等同于幸福,實際上先秦思想家更強調“德福一致”,那么至善可以等同于最高的道德準則“仁”,這是由于“仁”都是在內心中培養出來,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因此達到至善,就是彰顯了仁,實現了個體道德境界和人生境界完滿。
綜上所述,作為境界的“善”應包含三重境界,每重境界都是層層遞進的。第一重境界的“善”是自足其樂,是以自我之樂為滿足,盡管孔顏樂處所求的快樂與其他人不同,并且更加高等,但仍屬于自我的層面,因此馮友蘭認為“以求‘我的’快樂為目的者,不論其所求是何種高尚底快樂,其境界只是功利境界”[2]37-38。作為第二重境界的“善”展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關涉的是群體中大多數人的快樂和需求的滿足。最高境界的“善”是止于至善,這是在個人道德修養提升、親民的基礎之上獲得的價值追求,復歸原初之善,人格達至圣人境界。由此可見,“善”作為一個哲學概念,不僅僅停留于“好”“美好”等表達語詞的層次,而是具有深刻的義理,與中國哲學中的其他范疇交相輝映,賦予傳統哲學以活力和生命力。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