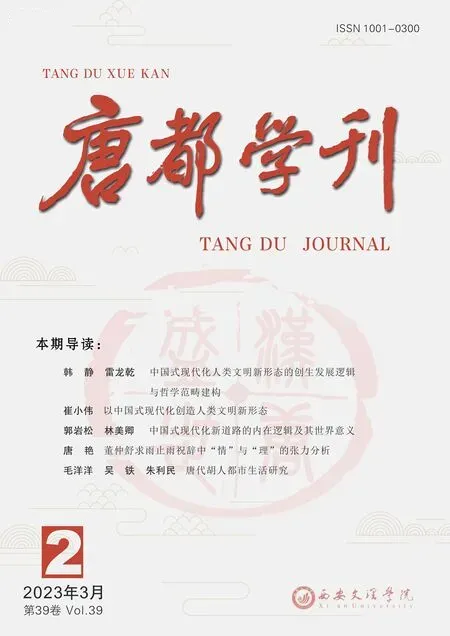先秦儒家義利觀探析
郭諾明,張麗華
(1.中央民族大學 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北京 100081;2.南昌職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昌 330500)
義利觀是關于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個人私利與社會公義等孰先孰后、孰輕孰重的基本觀念。從文字演變的角度來看,“義”字的基本意涵有天道義(宗教義)、規范義(禮義)、德性義(仁義),這三層含義是人類精神生活所展開的主要面向,義也成為調節人們精神生活和利益沖突的基本范疇和手段。“利”字的基本含義為工具義(鋒利之刃對農事的幫助)、物質義(能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吉利義(物質財富多,是為五福之一),利是調節人們物質利益的基本范疇和手段。自覺地將義利作為一組范疇,并作為其道德哲學的基本內容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儒家對義利問題傾注了大量的心力,朱熹甚至以“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1]來標舉其重要性。義利觀作為道德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中國古代,它與“人禽之辨”“王霸之辯”“理欲之辯”等密切相關,又與心性、規范、人格、實踐等維度緊密相連。義利觀之演進,是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發展和演變的縮影。先秦儒家的義利觀奠定了中國古代義利觀的主要論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利益沖突解決機制的建構。本文以孔、孟、荀三家所論義利觀為契入點,考察其義利觀之基本內涵,揭示其歷史影響與現實意義。
一、“利者,義之和也”:義利的兩有與和諧
儒家重視道德價值之義,但并非否定、忽視物質之利。《周易》有云:“利者,義之和也。”[2]這一觀點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物質利益都與道德價值相違背,在很多時候,物質利益與道德價值有相統一的一面。孔子就承認富貴是人之所欲,而貧賤是人之所惡。在孔子看來,這種欲富惡賤的意欲是一種自然的傾向。在符合道義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有實現和滿足其物質利益的欲求,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孔子自己就認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3]99也就是說,如果能求得富貴,即使是從事卑賤的工作,那也是可以去做的。縱觀孔孟荀的論述可以看出,他們都自覺地將利作為義的前提與基礎,義是對利的調節。他們承認在義利相符合的前提下,“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4]414。因此,不要簡單地將義利進行割截對立,去此取彼,認為儒家只講義,不講利,這是不全面、不客觀的;也不要簡單地混同義利之分,以利為義,須知儒家的基本立場是見利思義。特別是對于統治者而言,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是其大義之所在。如果統治者只顧滿足自己的私欲,見利忘義,先利后義,就會造成社會動蕩。在儒家看來,“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5]4要行王道,實現社會普遍公正的義,就要首先實現人們生活的普遍富足。《論語》有一段對話充分地展現了儒家的這種追求: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193
在孔子看來,國家治理首先要增加人口,其次要通過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使人們的生活富足,再次才是道德教化。“富之”“庶之”,是滿足百姓對利的追求;“教之”,是教導百姓要過文明的生活方式,以道義主導人們的行為。儒家雖然強調道德之義在人們生活中的統帥作用,但他們也清晰地意識到,無恒產而有恒心的,只能是對士君子的道德要求;對于普通人而言,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則無恒心。道德教化固然是儒家精神命脈之所在,但其維系之前提仍是物質生活的基本保障。不然,“講道德,說仁義”就只能蛻化為少數人所能堅執的道德軌范,而無法成為社會大眾所能遵循、所愿遵循的價值理念,也就必然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因此,孟子之論王道,必先“制民之產”[5]13,使得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5]13,然后才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5]13,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實現王道政治。荀子之論王事,也認為“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4]410,所謂的“民情”就是人們的欲利之心,荀子認為“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4]414,故所謂的“養民情”“理民性”就是因勢利導,化性起偽,教之誨之,使百姓的行為合于禮義法度。先富后教,可謂儒家之通義。以百姓之富庶為天下大義之基本內涵,是儒家所主張的君子成德之教的重要特征。
在孔孟荀的論述中也都隱含著這么一層意思,那就是物質利益之滿足,特別是對于百姓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對于執政者而言,滿足和實現百姓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實現社會正義的基本內涵。因此,對于百姓而言,為其美好生活而努力拼搏是其利,循禮而行是其義;對于統治者來說,努力創造條件讓百姓生活穩定、福樂安康是其義,也是其利,他們是以義為利。不同的階層對于義利有不同的要求,統治者、士君子、百姓各有其道,又共同聚合在王道政治的普遍正義之中。當義利相沖突的時候,應該用利益沖突解決機制(禮義)去調節和矯正利,使得義利達到統一、和諧的狀態。
二、“義之與比”:義利沖突的抉擇原則
利益雖然有與道德價值相符合的一面,但也有相矛盾的一面。在面對這種矛盾時,就必須建立利益沖突解決機制。儒家的利益沖突解決機制和原則就是禮義。禮是社會道德價值體系的制度性規范和準則,是義的外在表現;義是社會道德價值體系的基本原則,是禮的內在精神。符合禮義的利,就是正當的利;不符合禮義的利,就是需要調節和矯正的利。
對于儒家而言,物質利益固然可以追求,但要求行為要符合義。孔子認為:“放于利而行,多怨。”[3]53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以利益欲求為其行為準則,就會招致很多的怨恨。又正如孟子在面對梁惠王“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5]1的發問時,警醒地提示到,如果整個國家的行為都以利益為導向,“上下交征利”[5]2,諸侯認為可以取代天子之位而亟欲為之,卿大夫亦以諸侯之位可取而代之,則必然導致國家混亂,勾心斗角,相互傾軋,永無寧日。荀子也同樣認為,“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4]39,成為天子之尊,富有四海之大,這是人情所同具的欲望。如果順從這種欲望,從權勢上是不能容許的,因為天子只有一個,故曰“勢不能容”;從物質上是不能滿足的,因為只有天子才能富有四海,擁有天下,故曰“物不能贍”。然而人的欲求是無窮的,而滿足欲望的手段卻是有限的。無窮的欲望與有限的手段之間必然發生尖銳的矛盾。人的欲求得不到滿足就會導致紛爭,紛爭就會導致混亂,從而陷入戰爭的困境之中,最終使得大家都不能得其所得、欲其所欲,所以要“制禮義以分之”[4]265。荀子試圖通過制定禮義的方式來確認人們的名分,通過禮義的分配與調節,以實現“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4]265的目的,這樣人們的欲望不會由于物質的原因得不到滿足,物質也不會因為人們的欲望而枯竭,從而實現物質欲求與禮義的和諧統一。
基于此,孔孟荀等為代表的儒家認為任何人要獲得利益皆須符合義。當義利二者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孔子提出了“義以為上”“義之與比”“見利思義”“義然后取”的義利抉擇原則,認為求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3]49;去貧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49,求富貴、去貧賤皆須以是否符合義為準繩,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3]101。在孔子看來,借助不符合道義原則的手段而獲得的富貴,就如浮云一般,是不具有道德價值的,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3]52。人的行為應當以“義”作為準則,儒家從孔子開始就建立了以義作為處理義利關系的基本準則,也把義作為人們行為的應然之則。
應然與實然,有時陷入矛盾。如孔子所謂的“見利思義”與“見利忘義”、孟子所謂的“懷義”與“懷利”、荀子所謂的“先利后義”與“先義后利”,就是兩種相互沖突的價值觀的斗爭。在不能兩全的前提下,是追求物質利益還是精神利益,是追求個人私利還是國家公義,是追求短期利益還是追求長遠利益,就構成了義利沖突的角斗場。孔子以君子須見利思義為儒家之立場。孟子通過事利而亡與懷義而王的對比,進一步強調了“去利懷義”的必要性,也集中反映了孟子對義利之道德評價。荀子以為:“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4]414當一個社會能夠依據義來獲得利,道義能夠戰勝私利,這就是風清氣正的治世,相反則為亂世。故義利雖為人之兩有,但有輕重之別,有本末之差,不得不辨,不得不知。義為重、為本;利為輕、為末。如果一個人不知道“懷義”而只知道“懷利”,就會是如孟子所說的自暴自棄,從而流于“小人之無忌憚”。
既然以“義”為重,則必然以“義”以歸,故以義制利,以義制事,以義為先。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孔子提出了“君子義以為質”[3]235的觀點。孔子以義為制事之本,故君子以義為其本質。也就是說,孔子不僅將義視為對倫理規范、風俗習慣之自覺遵守,更重要的是把義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所在。孟子接續了這一點,認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5]241,提出“天爵”“人爵”的觀點。孟子認為“仁義忠信”是“良貴”的“天爵”,是“自然之貴”[6]314,是“本然之善”[6]314;人爵則是指富貴利祿權位等。修“天爵”是修人之所當然的本分,是成為人所以為人的本質性屬性。修“天爵”本諸己,是定然可以實現的;求“人爵”,則是或然的,它可能實現,但也有可能實現不了,它不完全取決于人之主觀意志。因此,修“天爵”的意義就比求“人爵”的意義更大了。
不僅如此,在儒家看來,如果將義利沖突推到極致的情況下,為了保證義的絕對性和優先性,即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孔子認為君子不僅要“見利思義”[3]211,還應該“見危授命”[3]211。孟子認為魚和熊掌皆為人所欲,不論是取魚還是取熊掌,其所欲者小,去取之機即便艱難,也無關生死存亡;如果碰到國家大義、民族存亡、大災大難等緊要關頭,是存身保利還是舍生取義,是為小我還是為大我,就是義利觀沖突之大關節。對此,孔子提出“殺身以成仁”[3]231,孟子提出“舍生以取義”[5]205,荀子亦以為“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4]32。儒家以為于生死一節看不破、透不過,則所謂的“義以為質”就會流于道德說教,無法引導人們形成正確的義利觀,自覺踐行仁義道德。因此,儒家不僅建構了“禮義”為上、為本、為先的義利觀,更是講求在實踐中涵養人性,修成君子人格。
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人格的養成
“君子”本意為貴族,孔子將“君子”這一概念轉化為儒家道德人格、道德境界的概念。孔子將培育君子人格作為儒學之主題,奠定了中華美德的基礎,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依據道德高低的層次不同,把人分為圣賢、士君子、眾人、小人四類。圣賢是人倫之至,是士君子之所愿學者;士君子以德修身,嚴于律己,關愛他人,是眾人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眾人則做人雖然有底線,但不重涵養,難免有不良之積習;小人則是只顧眼前私利,而罔顧他人與公共利益。小人如果墮落則為罪人,需要繩之以法、齊之以刑。孔孟荀等諸位大儒皆將士君子放在提升人們道德境界的關鍵位置上。這是因為在道德評判標準上,如果以圣賢的標準要求眾人,則標準失之過高,也容易出現偽善,從而走向道德的反面;若果以眾人作為標準,則標準失之過低,缺乏激勵作用。士君子既寄托了儒家的道德理想,又是可以效仿的榜樣。學做君子是儒家推行道德教化的有效途徑。
儒家對士君子的界定,是在君子與小人的對比中不斷澄清的。不僅先秦儒家,歷代儒者皆以辨君子小人作為其學問思辨的重要入路。《論語》中“君子”一詞出現107次,可見孔子對“君子”論說之頻繁,亦可知“君子”是孔子仁學思想體系的重要概念。牟鐘鑒將儒家對君子的論述凝練為“六有”:有仁義、有涵養、有操守、有容量、有坦誠、有擔當[7]。從中可以體會儒家君子的主要品格。從形式而言,君子注重禮義規范,具有莊嚴、莊重的外在形態,表現為謙虛謹慎、剛健自強的生命氣象,呈現在容貌、顏色、形體的自覺調適與時中,展現為行動的得體與合宜,代表了文明的交往方式;從實質而言,君子是正面人格的象征。他們自覺把握和體認人與世界是一個有情的意義結構,他們自覺承擔責任與義務,急公好義,見義勇為,在為學、為人、為政的社會實踐中自然地展現其仁愛之心,在與天地萬物相往來的過程中實現其參贊化育的價值與使命。從人格而言,君子是坦蕩蕩的;從志向而言,君子是謀道的;從路徑而言,君子是求諸己的;從整全性而言,君子是不器的。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3]55君子小人之別、義利之分,可以說集中體現了儒家在義利觀問題上的基本態度與價值抉擇。君子自覺以實現社會公義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其所喻就是其所志,君子之所以為君子,正是在于行義;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就在于只趨利,不知向義,故君子見利思義,小人見利忘義。孔子通過對義利的不同態度來判定君子小人,這也就從道德領域劃清了“君子”“小人”的價值標準,也清晰地表明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在義利觀上的道義論特色。孔子、孟子、荀子皆通過對“君子”“小人”與“義”“利”這兩對范疇不斷對舉,深化君子求義、小人求利的理論定勢與價值評判標準,深化“君子”與“小人”人格追求之不同。在孟子看來,“道一而已矣”[5]84,仁與不仁二者之間必然擇其一作為人生的準則。“孳孳為善”,即心心念念志在為仁義,如此即為“舜之徒”;反之,“孳孳為利”,即心心念念意欲為私利,如此則為“跖之徒”[5]243。其所區分,義與利而已矣,其志不同,其趨各異,這便是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其機如此,可不慎乎!荀子則直接認為“君子,小人之反也”[4]23,出君子,即為小人。君子“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小人則“違禮義”“縱性情”“安恣孳”[4]337。先秦儒家通過不斷褒揚君子人格之高,貶抑小人人格之卑,不斷樹立對君子人格之向往與追求,將人之何以為人的問題轉化為人應該如何成為君子的問題,從而奠定了儒家在義利問題上基本的理論致思。
從義利之辨的角度審視儒家的君子成德之教,可謂意味深長。首先,要求問學者能夠以君子為楷模,自覺認同君子人格。君子仁以為己任,克己復禮,敬天愛人,參贊化育;君子以仁為體,以忠信為矩,以義為質,以禮為行;君子時中,思不出位,絜矩上下,道行天下;君子法乾之健,剛健自強,效坤之順,厚德載物;君子理道順義,上律下襲,窮神知化,盡性至命。可以說,自覺認同君子,是君子成德之教的前提與基礎,它將做什么人、怎樣做人這一根本問題潤化在如何做君子之中。其次,要求問學者博學審問,富有學習精神。儒者以六藝為學,以四科為教,以德行為重。《論語》開篇即講“學而時習”,顏子述學,標之以博文約禮。學習不僅要追求知識的廣博,還要學會約之以禮義;不僅要善學,還要善思。義利之辨,就得辨何者為義,何者為利,一己之利與天下之利,小義與大義,百姓之利與國家之義,道德與利益,權益與正義,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等等,可謂千頭萬緒,不學何以成才,不思何以辨義。在學與思的辯證中深刻領悟義利之辨,在學而時習中深化天道性命貫通之樂。再次,要求問學者勤于自省、內自訟,在慎獨誠意的生命修養中純化道德意識,挺立道德人格。慎獨者,于人所不知己所獨知處省察;誠意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立誠以發其志意。慎獨誠意側重于在事前省察;而“三省吾身”則側重于事后警醒。事前省察重心志之純,是動機省察;事后反省重志行是否統一,看效果是否合宜。有人以為儒家的義利觀是唯動機論,這是不準確的。儒家主張的是達則兼善天下,放在義利觀的角度,那就是追求動機與效果的統一。儒者之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儒者之志,在平治天下。只有在退而求其次或者二者不可兼得的條件下,才會把動機放在首位,凸顯義的引領性和統帥性。最后,要求問學者在行動中實踐義以為質、見利思義、見義勇為、見危授命、義然后取的價值原則。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見孺子之將入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沛然莫御。簞食豆羹,得之生,失之死,乞人不受嗟來之食。人們在履仁戴義的實踐中不斷涵養人性,變自發為自覺,積習成性,積性成命,培育為義之勇,澄明天人之知,深化惻怛之仁,在實踐中修成君子。
概而言之,孔孟荀諸位大儒皆注重從君子小人之辨入手,要求人們以學做君子為起點,以成為君子為目標,在知情意行的往復中深辨義利,將“義之與比”的義利觀貫穿在一言一行之中,以此挺立以義制利的價值要求,錘煉高尚的道德品質,塑造偉岸人格的感染力,從而形成人人勇于踐行正確的義利觀的社會氛圍,建設普遍和諧正義的社會。
四、先秦儒家義利觀的現實啟示
先秦儒家在處理義利關系上,承認物質利益和精神追求的合理性,義利為人之兩有,但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人類處于物質利益與精神追求、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持續沖突之中,他們主張通過禮義的方式去解決和調節公私、群己、人我的利益沖突。這種理論的內在根據是“義以為質”,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所在。在儒家看來,正是禮義將人與動物真正地區分開來。人能夠意識并自覺調整對利的意欲,使得人們可以在各種利益沖突中做出選擇和取舍,從而維系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儒家在堅持“義以為質”的同時也完成了對義利的價值判斷,從而為其“義之與比”“義以為上”的義利判斷原則做了理論論證。同樣,“義以為質”這一命題也將人是什么、應該做什么人、怎樣做人這些根本問題統合到如何做一個仁人義士的問題上,為儒家君子成德之教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正確認識先秦儒家的義利觀,還需要仔細體會儒家的立言宗旨,那就是它主要為士君子立言,立論卻指向統治者。儒家之所以倡導重義輕利、先義后利、以義為利的義利觀,除了儒家自身的理論定勢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勸誡統治者要發仁心、行仁政、去苛政,收斂其貪得無厭的意欲,遏制其好大喜功、殺人屠城的暴力之心,不要與民爭利,減輕百姓的負擔,要以百姓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樂為樂,俱立俱達,實現王道政治。可以說,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對義利觀的深刻致思,構成了中國古代倫理思想重要的理論積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是中華傳統美德的重要內涵。先秦儒家義利觀中所秉持的講仁愛、重公義、重整體、崇正義等觀念,對于新時代社會主義義利觀的建構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先秦儒家所秉承的以君子小人分義利的觀念,可以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提供參考。我們應該積極借鑒先秦儒家“君子之道”的積極因素,以新時代新型君子建設為抓手,以君子人格養成為基本途徑,勉力廣大人民群眾成為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要引導人們在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的道德認知與實踐中,辨別義利之分,塑造時代新人,堅持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堅持利與義的統一、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旗幟鮮明地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
其次,先秦儒家所秉承的私德與公德的統一、“義然后取”的觀念,可以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思想資源。儒家既重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私德,又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12的公德;既強調“父為子隱,子為父隱”[3]197的私德,又重視“為民父母”的公德;既不以私廢公,也不因公廢私,追求的是私德與公德的辯證統一。在當代,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城市化的茁壯成長,中國已然由熟人社會轉變為陌生人社會,經濟發展呈現勃勃生機,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溫情脈脈的人情往來卻逐漸消隱,冷冰冰的利益關系日益膨脹,使得社會上急功近利、見利忘義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人只顧個人、小團體之私德,不顧集體、社會之公德,這種私德就會蛻化為私利。私德近于公,則為大義;私德遠于公,則為私利。從私德與公德統一的角度看當代義利觀建設,那就是要樹立“義然后取”的道德觀念,主張先公后私、公私兩便,弘揚大公無私,積極培育良好的社會風氣,營造“急公好義光榮、唯利是圖可恥”的社會氛圍,積極推動私德不私、積極為公的正確義利觀;同時也要反對將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對立,甚至脫離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空談道義等錯誤義利觀,要在公與私、義與利的辯證理解中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最后,儒家主張德法兼備、以德為先的道德觀念,如孔子的“道之以政,齊之以禮,有恥且格”[3]15、孟子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5]121等,德治即禮義之治,法制即制利之術。只講德治不講法制則無以興民之利,將會流于偽善;光講法制不論德治則不能徙義向善,將會流于機巧。因此,德與法的統一、義與利的統一,不僅是古代國家治理的基本軌范,也為當代國家治理所吸納。同時,儒家堅持義利兩有,追求義利協調的精神,對于當下也有重要的意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興人民群眾之利,努力增進人民福祉;守人民群眾之義,嚴肅政治生活倫理。總之,積極踐行正確的義利觀,促進國家、社會、個人的協調發展,仍是時代留給我們的艱巨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