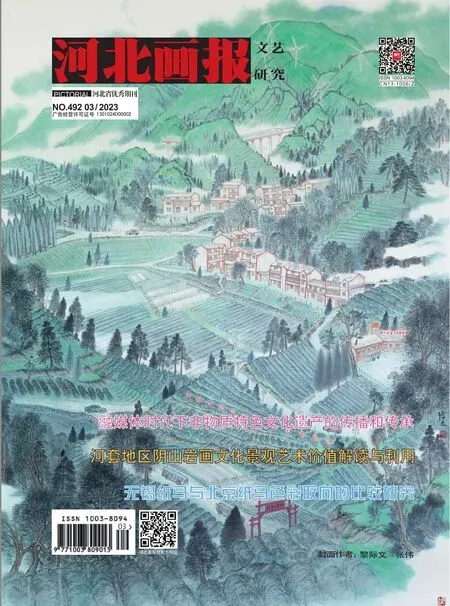科爾沁蒙古族薩滿祭祖儀式音樂考察
——以左翼中旗白滿達薩滿為例
溫昭娟
(內蒙古師范大學)
一、科爾沁蒙古薩滿的概況
(一)科爾沁蒙古薩滿的形成
學術界普遍認為薩滿和薩滿信仰最早起源于通古斯。薩滿一詞通常被認為是來自滿族語或其他通古斯族語。在通古斯語中,“薩滿”指的是興奮、狂舞和激動不安的人。原始社會人們對自然的了解有限,遂將主觀意識賦予在自然事物和自然現象中并對其敬奉,形成最初的萬物有靈的信仰觀念。他們認為地球上的動植物都有神,萬物有祖先,形成了普遍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薩滿信奉萬物有靈,將人們的祈禱傳遞給神,把神的意志傳達給人,成為神與人之間的媒介。科爾沁薩滿書無系統、成文的經典教義,地無寺廟建筑,多是通過薩滿們的口傳身授,世代嬗遞。
科爾沁蒙古族薩滿主要分布在內蒙古東部科爾沁草原,其保存原因復雜。首先,它與科爾沁蒙古各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關。科爾沁地區位于內蒙古草原東北部,藏傳喇嘛教從蒙古各地傳入,然后逐漸向東傳入科爾沁各地,時間相對較晚。其次,與科爾沁薩滿的斗爭策略有關。在同喇嘛教的斗爭中,一部分科爾沁薩滿采取了靈活的策略,一度巧妙地運用和吸收了喇嘛教的一些教俗來掩蓋其原有的面目,從而達到“明降暗保”的目的。因此,近代科爾沁地區的薩滿明顯呈現出喇嘛教色彩。科爾沁薩滿(也稱“博”)分為黑方博與白方博(因藏傳佛教的傳入發生的分化,親佛派稱白方博,排佛派稱黑方博。白方博積極吸收藏傳佛教的諸多因素,而黑方博頑固地保留著薩滿的古老傳統)、世襲和非世襲薩滿(世襲薩滿一般都有自己的譜系),女薩滿又稱“渥都干”。
(二)科爾沁蒙古薩滿的斷裂與復蘇
喇嘛教傳入蒙古前,薩滿信仰曾在蒙古各部落中長期盛行。十六世紀,格魯派喇嘛教傳入蒙古成為主要宗教,薩滿遭到遏制。1570年由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大力傳播推行佛教思想并強制取締蒙古薩滿,薩滿與喇嘛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矛盾與較量。1603年,林丹汗繼承汗位并繼續推崇藏傳佛教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1618年,蒙古部族的薩滿信仰遭到了明文禁止并被宣布以“科以財產刑”的法律手段懲罰違者。薩滿在與佛教的激烈抗爭中頑強生存又有所妥協,因而出現了黑方博和白方博之分。民間大多數皈依于喇嘛教的蒙古族仍然沒有真正擺脫薩滿的影響,根深蒂固的歷史淵源和頑強的宗教影響力使得出現了一些混合形態的祭祀儀式,如祭敖包。明末,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達到鼎盛時期。薩滿殘余勢力以科爾沁草原為依托,并在后金統治者的庇佑下得以留存。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由國家推動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在這延續了近10年的全國性田野調查工作中,薩滿研究也成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內容之一。1966年到1976年,中國陷入了十年動亂之中,包括民族學在內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事業都處于停滯狀態,薩滿信仰在此背景中再次出現斷裂的局面。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逐漸復蘇,在薩滿相關研究方面,中國的學者開始通過翻譯和學術交流了解到國內外有關薩滿研究的信息和學術成就。2005年,國際教科文組織將薩滿文化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三)科爾沁蒙古薩滿的儀式概況
科爾沁蒙古薩滿的儀式主要有成巫儀式、祭祀儀式、祈愿儀式等。祭祀儀式包括祭天儀式、祭火儀式、祭祖儀式、祭敖包儀式等。薩滿把長生天稱為“孟和騰格里”,是薩滿的最高神明。認為長生天具有主宰世間萬物的神秘力量,故予之無限的崇拜和敬仰。蒙古人認為火是天地分離之時產生的圣物,對火特別崇拜,認為火神是一個民族興旺的象征、圣潔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明。按照蒙古人的習俗,把祭火同所崇拜的天地和祖先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祭火時除了念唱祭詞之外,還要向火神敬獻食品、酒和水果。祭敖包也是傳統祭祀活動之一,薩滿認為敖包是草原的守護神,通常設在被視為風水寶地的高山丘陵上,用石頭壘起,插上柳條,柳條上掛滿五顏六色的布條和白、藍色哈達。祭敖包時在敖包前擺設祭祀臺,供上煮熟的全羊或牛馬肉、牛奶、糕點、水果等,然后搏擊鼓念咒,邊唱邊舞,帶領農牧民們順時針轉三圈,以此祈求風調雨順、農牧豐收。
二、科爾沁蒙古薩滿祭祖儀式
(一)祭祀儀式的程式
筆者于2018年10月17日(農歷九月九日)下午三點到達祭祖儀式地點左翼中旗后滿金敖嘎查白滿達①家,儀式在他的家神堂(東屋)舉行。因儀式是在天黑(星星出來后)開始,所以天黑前進行儀式的相關準備工作。筆者到時人們正在室外宰殺此次請神儀式中用來祭祀的活牛(祭祀品不是固定的,牛馬羊均可),這些人都是從各地趕來為儀式幫忙的王特格喜②的徒弟們。在室內,筆者觀察到白滿達端來一碗祭祀牛的鮮血和一些生大米放入了碗裝容器中,放到了供桌上。(祖先祭拜是蒙古薩滿神靈崇拜的主體,每個薩滿都有自己的祖神,供奉著祖神的偶體或偶像。翁袞一詞是這種祖神偶體的蒙古語音譯,屬薩滿師的神具之一,供祭祀或作法時用。各地薩滿的翁袞各式各樣、形狀不一,白滿達所供是青銅制的人形翁袞)。祭祀的牛分割好后便在室外架起了大鍋煮牛肉,待煮熟的肉用大盤乘出,放在祭祀臺上。臺上還擺放著水果、香燭,容器中斟滿白酒,寓意敬請神靈享用,祈求保佑。
傍晚七點二十分,白滿達薩滿更換好法服(法冠、法裙〈由寬圍腰和多條彩帶組成〉腰間佩戴銅鏡),去往室外朝天跪拜隨后起身向四方獻酒,回到屋內又向師父王特格喜跪拜后敬酒,隨后前往神堂。儀式禁忌是懷孕、坐月子的女性不可以在場。在供桌前所有參與儀式的薩滿們都對供桌點香祭拜后,由師父王特格喜腰系神裙手持單面鼓和鼓鞭在前面,白滿達跪在供桌前一手拿著斟滿酒的酒杯一手拿著白布點、撒白酒,徒弟們在其身后著法服手持單面鼓和鼓鞭。眾薩滿開始邊擊鼓邊唱誦神歌,一共唱誦了十一首神歌,歌唱曲調均不同。白滿達薩滿伴著最后一首神歌手持抓鼓,全身進行騰挪、進退、搖擺等舞蹈動作,隨后開始神靈附體、師父王特格喜與其對話、神靈附體后的白滿達傳神諭,達到請神目的。最后附體神靈的白滿達薩滿又唱又跳,請來的神靈離開。這時白滿達在恍惚中醒過來,神智漸漸恢復,然后到室外跪地磕頭、敬酒,表示對離去神靈的誠摯敬意。整個儀式過程持續了兩個半 小時。
(二)儀式的音樂及功能
王特格喜的演唱旋律順暢,帶有濃重的蒙古族音樂風格。他左手持鼓,右手持鞭,手腕松弛靈活,鼓鞭在鼓面上輕點重擊、錯落有致、韻味十足。嚴昌洪、蒲亨強所著《中國鼓文化研究》一書中指出:“在薩滿教這一比較完備的原始宗教中,鼓的神秘保存比較多,它是薩滿(巫師)請神和驅鬼的重要法器。”③這次的儀式中主要用到的神鼓有單面鼓和抓鼓兩種,據白滿達所述:抓鼓與單面鼓一樣,同為單面帶環、蒙革的鼓,用鼓鞭(木質,其外以紅布纏裹,下部垂以彩色綢布為穗)擊奏。兩者不同之處在于鼓框用料不同;抓鼓沒有柄,而單面鼓則是有柄的,鼓環每三個一組套在鼓尾的 圓圈上。
儀式唱誦的神歌有《請蜜蜂精靈》《降神》《咳朗咳》《祭天獻牲》《送神》《薩滿蘇醒歌》等等。神歌的數目繁多。這些神歌曲調古樸簡潔,保留著古老的音樂形態。曲調多為單樂句結構,樂句內部劃分為兩個樂節,歌舞過程中無限反復,帶有一定的原始性。節奏和速度,是歌舞最基本的表現手段,節奏由簡入繁,速度由慢到快,以致達到高潮。這些神歌共同點在于鼓點節奏不盡相同,王特格喜善于發揮鼓尾子的作用,將“刷拉”的鼓環聲音與“咚咚”的鼓點巧妙而又結合起來使用。鼓點,是整個請神儀式音樂中的核心和精華,它在整個儀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出現頻率高的節奏型為前十六和附點二分音符,這種節奏型體現著“短、緊、密”的特點,與現代蒙古族草原牧歌的舒緩悠長節奏是迥然不同的。顯然在科爾沁蒙古薩滿音樂中,鮮明的節奏型是極為關鍵的。
(三)儀式音樂的意義
科爾沁蒙古族薩滿在蒙古族人民過去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祭祀主持、祛災求福、慶祝娛樂等多種職能。薩滿儀式是信仰薩滿的人們用來為神靈祈禱和祭祀的,儀式中的音樂屬于宗教音樂范疇,集歌舞樂為一體。科爾沁蒙古薩滿信仰的存在和傳播,便是以其儀式為主要載體的。儀式中薩滿呈現了獨特的信仰化的舞蹈形式,其內在具有特定的儀式功能和特定的表演程式,請神舞、送神舞過程中塑造的律動化、個性化的幻神藝術形象,使儀式具有觀賞性,信仰易于在群體中傳播接受。蒙古族民間歌舞中流行于庫倫旗、蒙古貞一帶的安代和流行于敖汗旗一帶的呼圖克沁儀式性歌舞也是以此演化而來的。
神秘的職能和狂烈的歌舞樂,二者的巧妙結合,是蒙古薩滿文化的主流。職能和歌舞樂,像是一對孿生兄弟,是構成薩滿的兩個基本要素。綜合文獻記載中無數薩滿的儀式表明:歌舞樂是薩滿儀式的主體部分,亦是其得以實現其信仰目的的主要形式。由此來看,薩滿歌舞樂就是蒙古薩滿信仰的活的靈魂,職能與歌舞樂的完美結合,即呈現出活態的蒙古薩滿信仰文化。
三、科爾沁蒙古薩滿傳承與文化價值闡述
(一)科爾沁蒙古薩滿的傳承現狀
科爾沁蒙古薩滿在發展至今流傳至各地,當下從事薩滿職業的人數日趨上漲,以女性人數偏多,并存在薩滿有真有假的情況。出現這樣的現象也使人們開始反思:是不是薩滿信仰文化賴以生存的民間生態環境不斷地受到現代文明的沖擊而瀕臨消亡,又是什么促使人們推崇起這一職業的熱潮…
據了解,在科爾沁蒙古薩滿的流傳中,神靈在逝世之后靈魂不會投胎轉世,而是會找一個“人選”附體。在找到可以附體的合適“人選”并選定之后便會給選中的人附以病痛。意為這個人必須要接受其選擇并承受其附體,不然病痛無論如何都不會治愈。薩滿們看到這種情況便能確定這種患病的人為“合適人選”并收其為徒弟,協助其請神附體后病痛隨之消失。神靈在選擇的人選身上給予病痛一是為了培養他的憐憫之心,另一方面也是讓他甘心成為薩滿。所以薩滿們都不是自愿讓自己成為一個薩滿,只是因為曾有過無法擺脫病痛的折磨才會選擇薩滿這個職業。盡管其傳承充滿神秘的力量,但由此看來薩滿的存承暫未衰竭。
(二)科爾沁蒙古薩滿的文化與社會價值
科爾沁蒙古薩滿是蒙古薩滿信仰的一個分支。它不僅具有蒙古薩滿教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較強的地方特色。科爾沁蒙古族薩滿音樂是蒙古族傳統音樂文化中一種獨特的藝術類型,它由樂器、神歌、舞蹈和儀式內容組成。薩滿音樂文化與原始的生態音樂文化一樣,有著不間斷的現實選擇和對自身文化傳統的詮釋。一方面,蒙古族音樂特性隱匿在薩滿音樂中,神歌的旋律中保留了濃厚的蒙古族音樂風格;另一方面,器樂的鼓點節拍與神歌、舞蹈融為一體。科爾沁蒙古族薩滿歌舞樂的文化特征,典型地反映了其與本民族其他音樂文化融合的基本 規律。
科爾沁蒙古族薩滿是古代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上現存的蒙古族薩滿的一個分支,在蒙古族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價值,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近年來國內外各學科領域興起對薩滿文化研究的高潮,專家學者們結合書籍文獻和實地調查,進行搜集、整理與相關研究。薩滿信仰作為一個世界性的研究課題,其內在的萬物有靈、多崇拜的信仰價值體系,亦使它充滿了無窮的文化魅力。大浪淘沙,薩滿信仰能流傳至今,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科爾沁蒙古族薩滿的保存與傳承,亦豐富了科爾沁蒙古族博大精深的音樂內涵。
注釋
①白滿達(1987-),左翼中旗后滿金敖嘎查人,2014年成為薩滿(黑 方博)。
②王特格喜(1969-),左翼中旗布敦毛都嘎查人,2000年成為薩滿(世襲制黑方博),是白滿達的師父。
③嚴昌洪、蒲亨強.中國鼓文化研究[M].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