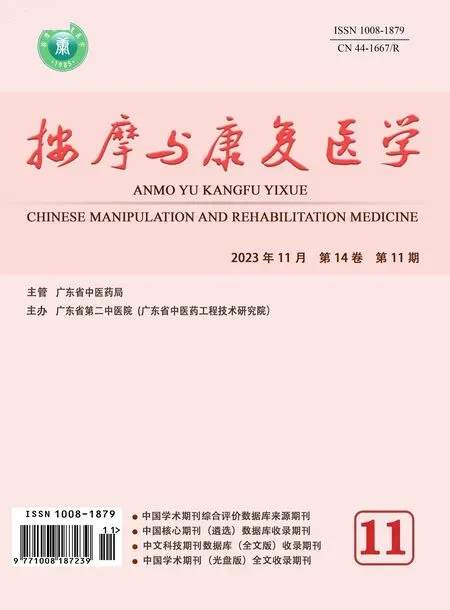omega-3多不飽和脂肪酸治療孤獨癥譜系障礙的研究進展*
汪波波,劉安南,公 超,孫加興,吳緒波
(1.佳木斯大學,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2.上海中醫藥大學,上海 201203)
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種起病于幼兒期,以社會交往障礙、限制性重復行為和狹隘興趣為核心特征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其相關癥狀可持續終身[1]。近年來,ASD 患病率持續增加,全球患病率約為7.6‰[2]。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最新數據顯示,8 歲兒童的ASD 發病率已升至1/34,超過了世界三大疾病(艾滋病、癌癥、糖尿病)之和[3]。給患者及其家庭和社會造成沉重的精神、經濟和醫療負擔,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4]。迄今為止,尚無治療ASD 核心癥狀的特效藥,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僅批準兩種藥物(利培酮和阿立哌唑)用于治療ASD,但副作用大[5-6]。考慮到ASD的早發性和慢性性質[7],由于膳食補充劑可以在幼兒早期及長期服用,且相對安全、便宜、有效和節省時間,可能是ASD家庭的優先選擇[8]。
當前,ASD 患者的膳食補充劑主要有ω-3PUFAs、維生素D、駱駝奶、葉酸、益生菌、消化酶和蘿卜硫素等,其中ω-3PUFAs 是當前的研究熱點[9]。ω-3PUFAs 為人體必需脂肪酸,包括α-亞油酸(alphalinoleic acid,ALA)、硬脂酸(stearidonic acid, SDA)、二十碳五烯酸(eisosapentaenoic acid, EPA)、二十二碳五烯酸(docosapentaenoic acid,DPA)、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與維生素和礦物質一樣,是人體的必需品。其中,DHA和EPA是對人體最重要的兩種ω-3PUFAs[10]。當前,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了ω-3PUFAs對大腦結構和功能的重要性,ω-3PUFAs 已被提倡用于治療多種神經發育障礙,包括情緒障礙(mood disorder, MD)、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 SP)、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和ASD[11]。有研究表明[12],ω-3PUFAs 的缺乏和不平衡與ASD 有關。因此,ω-3PUFAs作為補充和替代治療在ASD 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鑒于此,本文就ω-3PUFAs 在ASD 中的治療作用的最新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為ω-3PUFAs 在ASD 中的廣泛應用提供參考。
1 ω-3PUFAs的結構、代謝和轉化率
ω-3PUFAs 在化學結構上是一條由碳、氫原子相互連結而成的長鏈(18 個碳原子以上),其第一個不飽和雙鍵位于碳鏈甲基末端的第三個碳原子上,因此命名omega-3,屬于長鏈多不飽和脂肪酸(long chain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LCPUFAs)。ALA是ω-3PUFAs 的母體,一種18 碳必需不飽和脂肪酸,可在內質網中通過延長碳鏈和去飽和作用轉化為其他的ω-3PUFAs。ALA合成其他ω-3PUFAs的詳細代謝途徑見圖1,整個過程均在酶的作用下進行。圖中括號里的數字代表以α-亞麻酸(ALA,18:3,ω-3)為例,18 代表碳原子數目,3 代表雙鍵數目。人體組織中的ω-3PUFAs 主要為EPA、DPA 和DHA,其他的中間產物和長鏈衍生物只能在健康人群中發現微量水平。另一個主要途徑是從亞油酸(Linoleic acid,LA)合成ω-6PUFAs,主要的最終產物為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其代謝途徑需要的酶與ω-3PUFAs 相同,二者互為競爭反應[13-14]。AA 和EPA 在酶的作用下可分別轉化為促炎類和抗炎類花生酸,DHA可轉化為分解素和保護蛋白,詳見圖2。LCPUFAs是促炎和抗炎分子的前體,這些相互拮抗的化合物之間的平衡可能決定疾病發生過程的最終結果[15]。哺乳動物不具備合成這些LCPUFAs 的酶系統,可通過食物補充或ALA 和AA 轉化,由于人類飲食中的ALA 水平通常低于AA,因此ω-3PUFAs 的血漿和細胞水平往往比ω-6PUFAs 低得多[16]。此外,ALA 轉化為EPA、DPA 和DHA 的效率極低(<5%),這取決于飲食中ω-6PUFAs 和其他LCPUFAs 的濃度[14,17]。因此,想要攝入足量的ω-3PUFAs,必須通過富含ω-3PUFAs的膳食或補充劑補充。

圖1 α-亞麻酸合成ω-3PUFAs的代謝過程

圖2 AA、EPA和DHA的代謝過程
2 ω-3PUFAs對大腦結構和功能的重要性
ω-3PUFAs 主要以酯化形式存在,與細胞膜中的磷脂(phospholipids,PLs)和儲存脂質的甘油三酯(triacylglycero, TAG)形式有關。人腦是僅次于脂肪組織的含脂量最高的組織,在中樞神經系統中,神經元膜磷脂含量豐富且磷脂富含LCPUFAs(尤其是DHA和AA),約占大腦干重的20%。在胎兒大腦快速生長的階段,LCPUFAs 開始積累,并持續到2歲,然后在整個生命周期保持高水平[18]。有研究表明[19],膳食ω-3PUFAs攝入量低會增加產前或產后發育過程中大腦AA/DHA 的比例,使神經元的遷移、神經發生、突觸修剪、腦葡萄糖攝取減少和新陳代謝延遲,并導致谷氨酸和單胺突觸功能受損。DHA還是視覺系統內的視網膜光感受器和皮質灰質的重要結構成分,懷孕期間補充DHA有助于大腦和視覺系統的發育[20-21]。此外,Shahidi F 等[13]就ω-3PUFAs 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進行較全面的總結,表明ω-3PUFAs 與心臟、癌癥、阿爾茲海默癥和癡呆癥、抑郁、孕期孕婦和孩子的健康均有關。因此,ω-3PUFAs對大腦的結構、功能和人體健康均至關重要,合理補充ω-3PUFAs對人體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3 ω-3PUFAs的補充方式
生活中,ω-3PUFAs(主要為DHA 和EPA)可通過食物、膳食補充劑和處方魚油制劑補充。ALA 主要來源于植物,EPA和DHA主要來源于鱈魚和大比目魚等瘦肉白魚的肝臟,鯖魚、鯡魚和鮭魚等油性魚類的身體,以及海豹和鯨魚等海洋哺乳動物的脂肪,主要是EPA 和DHA,DPA 在大多數魚油中的含量非常低。其中鱈魚肉、大比目魚和鰹魚金槍魚的DHA 含量最高,鱈魚肉、鯡魚、比目魚類和黑線鱈的EPA 含量最高[13]。由于膳食補充劑和處方魚油制劑規格標準和食用便利,通常作為臨床干預研究和家庭的營養補充,其含量詳見表1。

表1 膳食補充劑與處方魚油補充劑中DHA與EPA含量
4 ω-3PUFAs在ASD個體中的水平及治療作用
4.1 ASD兒童的總LCPUFAs水平降低
研究表明[22-23],發育中的大腦和視網膜通過血液運輸獲得脂肪酸(特別是DHA),血漿和紅細胞膜磷脂脂肪酸是反映組織器官(包括大腦)中脂肪酸狀態的可靠生物標志物,因此當前臨床中主要通過檢測血漿和紅細胞膜磷脂的LCPUFAs 含量來反映大腦LCPUFAs 的含量。研究發現[24-25],與非ASD 個體相比,ASD 個體的血漿總ω-3PUFAs 水平降低。Ⅴancassel S 等[24]對法國15 名3~17 歲(4 名女孩、11名男孩)的ASD 兒童和18 名1~19 歲(5 名女孩、13名男孩)的智力障礙兒童進行了血漿生物學的參數測定,比較兩組的血漿磷脂水平。結果發現,與智力障礙患者相比,ASD 患者的ω-6PUFAs、ALA 水平均有降低,但無顯著性差異;而DHA 水平降低了23%,總ω-3PUFAs 水平顯著降低了20%,導致ω-6PUFAs/ω-3PUFAs 的比值顯著增加。同樣,Weist MM 等[25]進行了一項樣本量更大的研究,研究對象為美國加州153 名2~5 歲的ASD 兒童和97 名正常發育兒童,結果發現ASD 組中的血漿DHA 濃度顯著低于正常發育組兒童。
2004 年,Bell JG等[26]發現ASD組紅細胞磷脂中的AA 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而后在2015 年,Brigandi SA 等[27]比較了受試者年齡均為3~17 歲的121 名ASD 兒童和110 名非ASD、非發育遲緩兒童的紅細胞膜磷脂脂肪酸組成。結果表明,ASD 個體總的一些LCPUFAs,尤其是AA 和DHA,顯著低于對照組,ω-6PUFAs和ω-3PUFAs的總和在ASD個體中均顯著降低。同時還發現AA 促炎類代謝物PEG2 的血漿水平高于對照組,并排除了ASD 個體PEG2 升高是由于組間飲食差異的原因,這與El-Ansary A 等[28]之前的研究一致。這些較低水平的LCPUFAs 和較高水平的促炎類代謝物PEG2 表明ASD 個體的脂質代謝可能是異常的。反映ASD 個體脂質代謝異常的其他現有證據表明[12,29],與對照組相比,ASD 個體中負責分解磷脂的磷脂酶和氧化應激增加。此外,研究表明神經炎癥會損害大腦發育,并與ASD相關[30-31],ASD個體神經炎癥的增加也可能與其促炎類代謝物PEG2水平的增加有關[32]。
這些證據表明,ASD 個體的總ω-3PUFAs、總ω-6PUFAs、AA 和DHA 水平均低于非ASD 個體,ASD個體的脂質代謝可能異常,LCPUFAs代謝可能過度活躍。若ASD 個體組織的LCPUFAs 水平降低確實是由PUFAs 代謝過度活躍引起,則補充ω-3PUFAs作為一種治療ASD 的補充與替代治療可能是有效的[26]。尤其是DHA 和EPA,有研究已經確定了一組新的介質,稱為E 系列(EPA 形成)和D 系列(DHA形成)分解素,與DHA 通過多種反應形成的神經保護素D1一起,似乎發揮了強烈的消炎作用[33]。
4.2 ω-3PUFAs治療ASD的有效性
雖然ASD 的確切病因尚不明確,但已有研究表明遺傳、神經、代謝和免疫因素參與了復雜的發病機制[34-35]。ASD 的遺傳結構非常復雜,遺傳率約為50%[36]。其風險最有可能來自零星的基因突變和環境因素導致的神經、代謝和免疫異常。ASD 可能與其脂質代謝異常和ω-3PUFAs 水平降低有關。目前,ω-3PUFAs 改善ASD 癥狀的潛在作用機制尚不清楚,但可能與5-羥色胺和多巴胺能系統的調節有關;DHA或DHA/AA比率可能與去甲腎上能系統有關[37-38]。關于ω-3PUFAs 治療ASD 的有效性已進行了較多的研究。
2007 年,Amminger GP 等[39]進行了一項初步研究,在22 名5~17 歲ASD 兒童中選擇13 名每天服用ω-3PUFAs補充劑1.54g(840mgEPA+700mgDHA),6周后異常行為檢查表(aberrant behavior checklist,ABC)在統計學上無顯著改善,但分量表(易怒、社交退縮、刻板行為、多動和不當言語)中的每一個菌顯示出ω-3PUFAs 有利于治療的非顯著趨勢,其中多動癥和刻板行為的改善最大。2015年,Mankad D等[40]進行了服用周期(24 周)更長、劑量相同的隨機對照研究,結果表明廣泛性發育障礙行為量表(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Behavioral Inventory, PDDBI)的孤獨癥綜合評分、臨床總體印象改善量表(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Scale of Improvement,CGI-I)評分和適應性功能的組別效應均有統計學意義。
Bent S 等[41]進行了服用劑量1.3g(700mgEPA+460mgDHA)的ω-3PUFAs補充劑、周期為12周的隨機雙盲對照研究來檢查ω-3PUFAs治療ASD兒童多動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干預組(14 名)、安慰劑組(13名),結果發現ASD兒童核心癥狀的改善并不顯著,但與安慰劑組相比,其多動性降低更多。幾年后,Bent S 等[42]發表了其在一項更大樣本量(n=57)的試驗中的新發現,觀察到ABC的刻板印象和嗜睡子量表有顯著改善,但在社會反應量表(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 SRS)和臨床總體印象改善量表(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Scale of Improvement,CGI-I)等其他指標上無顯著性差異。
Yui K 等[43]選取13 名6~28 歲的ASD 患者每天服用劑量為0.58g(DHA240mg+240mgAA)、持續12周后,ABC 的社交退縮子量表、孤獨癥診斷訪談-修訂版(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 ADOS)的刻板和重復行為及SRS 的交流子量表觀察到顯著改善。Ⅴoigt RG 等[44]對3~10 歲的48 名ASD 兒童進行了一項隨機雙盲對照試驗,干預組每天攝入低劑量的ω-3PUFAs(200mgDHA),持續6 個月后未發現CGI-I 或其他組間測量值的顯著差異。以上研究結果與Fraguas D等[45]的一項薈萃分析結果一致。
最近,Doaei S等[46]對54名ASD 兒童(干預組28名、安慰劑組26名)進行了一項隨機雙盲臨床試驗,干預組每天服用一粒1000mg 的ω-3PUFAs 膠囊(180mgEPA+120mgDHA)。持續8 周后,干預組的刻板行為和社會交往有所改善。黃永平等[47]調查了41 名7~18 歲 的ASD 兒 童 每 天 服 用840mgDHA+192mgEPA+144mgALA+66mgAA+60mg 維生素D+3mg 百里香油,持續6 周后,與基線相比,SRS 量表中的ASD 核心癥狀顯著改善,包括社會意識、社會認知、社會溝通、社會動機和行為,兒童行為檢查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的社會和注意力問題也顯著改善。以上所有研究均無嚴重不良事件發生。
由此可見,對比安慰劑組,補充ω-3PUFAs 可改善ASD 的相關癥狀,如降低多動性,減少刻板印象、嗜睡,總體上是安全的和耐受性良好的。基于目前的證據,尚不能得出補充ω-3PUFAs 治療可以改善ASD 核心癥狀的結論,這可能與研究者在試驗設計上有很大關系(例如:樣本量、年齡范圍、劑量、服用周期),但ω-3PUFAs 是潛在有效的,其仍然可能對ASD 兒童的神經發育有益。ω-3PUFAs 聯合其他營養物質治療ASD 核心癥狀也表現出初步的有效性。有必要進行大規模、周期更長、更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來確定ω-3PUFAs治療ASD的療效。
5 結語
近年來,ASD 的患病率持續上升,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許多研究證明了ASD 與ω-3PUFAs 缺乏有關;也有研究報告稱,孕前或孕期母親攝入的ALA 與患ASD 的風險顯著相關[48]。補充ω-3PUFAs 可能成為預防和治療ASD 的潛在措施,但目前對于補充ω-3PUFAs治療ASD的作用和具體機制還需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