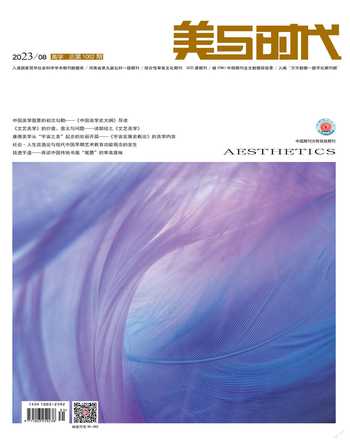《文藝美學》的價值、意義與問題
摘? 要:按照教育部頒布的學科分類,文藝學和美學分屬不同的學科門類。文藝學是文學學科下的分支學科,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研究文學基本規律,它有三個分支,即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美學是哲學學科下的分支學科,以審美活動為研究對象,美學研究的的基本問題是:什么是美。那么,文藝學與美學交叉后形成一個什么學科呢?那就是文藝美學。胡經之是國內最早從事文藝美學研究的學者之一。胡經之的《文藝美學》(1989年版,北京大學出版社)也是國內最早的對文藝美學進行總體闡釋的著作之一。
關鍵詞:胡經之;文藝美學;價值;意義;問題
一、《文藝美學》內容結構
作為最早對文藝美學進行系統論述的專著之一,《文藝美學》一書對文藝美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明確的界定:“文藝美學就應著重研究藝術活動這一特殊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以及審美活動規律在藝術領域中的特殊表現。”[1]2書中認為“黑格爾的美學研究中心已轉移到藝術領域”[1]2,正是基于此,胡經之認為,中國的美學研究也應該不僅僅停留在哲學美學原理研究,而應該開拓和發展文藝美學。
1981年,胡經之著手撰寫《文藝美學》第一稿,直至1983年,《文藝美學》第二稿寫出后,胡經之陷入了沉思。最初,他以藝術形象為分析的出發點,從靜態分析進入動態考察,“由藝術形象的特性引出藝術的內容、形式、構成、形態等等,然后再轉入創作活動和欣賞活動”[1]3,經過思考后,他放棄了這種由靜態分析進入動態考察的寫作路徑,選擇了一條由動態分析進入靜態考察的路徑,把審美活動、藝術本體、審美體驗等放到前半部分,以此為基礎,再進入藝術美、藝術意境的論述。
《文藝美學》全書十一章,分為兩大部分,體現了胡經之對文藝美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即研究藝術活動這一特殊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審美活動規律在藝術領域中的特殊表現。研究對象以兩大部分內容體現在本書中,分別是:
第一部分集中于對審美活動進行論述,分為審美活動、審美體驗、審美超越。書中在對以上三部分進行論述時,并未進行宏觀的審美活動、審美體驗、審美超越論述,而是將審美活動、審美體驗、審美超越中與藝術相關的部分提煉出來,論述藝術審美活動、藝術審美體驗、藝術審美超越,展現藝術活動過程中審美的特殊規律,體現出藝術活動審美的特殊性。
第二部分集中于對藝術審美進行論述,分為藝術掌握、藝術真實、藝術美、藝術形象、藝術意境、藝術形態、藝術接受和藝術審美教育。此部分也未進行宏觀的藝術掌握、藝術真實、藝術美、藝術形象、藝術意境、藝術形態、藝術接受和藝術審美教育論述,而是著重提煉出藝術中的審美部分,論述藝術掌握、藝術真實、藝術美、藝術形象、藝術意境、藝術形態、藝術接受、藝術審美教育中與審美密切相關的內容,將審美與藝術結合起來,論述藝術活動中的審美。
總的來看,《文藝美學》一書從藝術審美活動、藝術審美體驗、藝術審美超越、藝術掌握、藝術真實、藝術美、藝術形象、藝術意境、藝術形態、藝術接受和藝術審美教育等方面對文藝美學進行了全方位的論述,是國內最早對文藝美學進行系統性論述的專著之一。本書出版于20世紀80年代,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對今天文藝美學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二、《文藝美學》的價值
《文藝美學》寫作于1984年到1989年之間,其內容、體系、觀點等是20世紀80年代的產物,到了21世紀的今天,隨著學科門類的豐富,藝術學從文學中單列出來,各種藝術門類:戲劇、電影、電視、美術、音樂、舞蹈、繪畫、書法、雕塑等都完善并發展起來,文藝美學學科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有著巨大變化,書中部分理論觀點可供當下借鑒與學習,但是,某些內容仍值得當今學者關注并深入研究。閱讀此書,需要持辯證觀念,既看到書中可供當下學術借鑒、啟發學術觀點與方法的內容、價值、意義,也應該看到書中呈現出的時代造成的學科問題、觀點問題、內容問題。
胡經之《文藝美學》具有一定的時代價值、學科價值,對文藝學、美學兩門學科的交叉點模糊概念進行了闡釋,形成了系統的學科理論框架,能系統運用文藝美學研究方法研究文藝美學各問題。
(一)將文藝與美學兩門學科進行交叉,找到了兩門學科的交叉點,對交叉點里的模糊概念進行了闡釋
胡經之的《文藝美學》作為最早的文藝美學專著之一,具有很大的勇氣。在書里對文藝學、美學之間交叉點中的概念進行了闡釋,詳細闡釋了藝術審美活動、藝術審美體驗、藝術審美超越、藝術掌握、藝術真實、藝術美、藝術形象、藝術意境、藝術形態、藝術接受和藝術審美教育等,每種概念都進行詳細論述,并顯示出自己獨特的思考。
以藝術審美活動為例,書中將藝術審美活動視為藝術審美主體與藝術審美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論述藝術審美活動之前,先論述什么是藝術審美客體?什么是藝術審美主體?
中國美學發展史上,對藝術審美活動的認識經歷了從主客二分觀念到主客融合觀念的變化,20世紀初,西方美學傳入中國時,朱光潛先生試圖用西方美學方法闡釋中國美學思想,力求從主客二分觀念進入主客融合,朱光潛先生也積極翻譯了西方心理學著作,用西方心理學思想解釋中國美學思想中的主客融合觀念。宗白華先生的美學思想立足點是中國美學,提出了美在意象的觀點。
胡經之在《文藝美學》中總結前人經驗,將藝術審美活動中藝術審美主體、藝術審美客體、藝術審美活動都定義為客觀的存在,在客觀性基礎上,進而認為藝術審美活動是客觀存在的藝術審美主體與客觀存在的藝術審美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也是客觀存在的,也具有客觀性。
雖然胡經之對藝術審美活動的客觀性認識有一定局限性,但是,他將藝術審美活動視為一個藝術審美主體、客體的相互作用過程,有一定的開拓性,沒有機械地、僵化地認識藝術審美活動,也沒有給藝術審美活動一個固定的標準。
在對其他概念的論述中,胡經之的觀點也展現出一種客觀性,并未主觀臆斷,如在對藝術審美體驗的認識上,胡經之認為藝術審美體驗是潛藏在內心的,其狀態,或者是一閃而過的,或者是存在記憶里的,但是,審美體驗總是眼前的審美感知與既往審美經驗的結合。這些認識都是基于中國美學意象觀念基礎上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二)對文藝、藝術與美學相結合的各種概念進行系統整理,形成了系統的理論框架
胡經之《文藝美學》考察藝術創作、藝術欣賞等實踐過程,將實踐上升到理論,對文藝、藝術與美學相結合的各種概念進行歸納,形成系統的文藝美學理論框架,為文藝美學研究提供了系統深入的理論思路和理論基礎。
20世紀初創立的中國美學學科,以東西方美學思想融合為基本目標。試圖通過西方美學思想與中國美學思想的融合,使美學體系兼顧東方與西方美學思想的精髓,成為一個綜合東西方美學思想的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但是,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探索,美學依然很難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文藝美學想要成為一個美學研究方向,必然也需要形成自己系統的理論體系。胡經之的《文藝美學》構造了系統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將文藝美學理論分為四大部分理論體系,在這四大部分理論體系中,又劃分成更小的理論體系,以小的理論體系來支撐大的理論體系。胡經之的《文藝美學》先將文藝美學整體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藝術審美、藝術活動、藝術美、藝術接受。
在藝術審美部分,提煉出藝術審美活動、藝術審美體驗和藝術審美超越三個核心概念;
在藝術活動部分,提煉出藝術掌握、藝術真實兩個核心概念;
在藝術美部分,提煉出藝術美、藝術意境、藝術形象、藝術意境、藝術形態五個核心概念;
在藝術接受部分,提煉出藝術接受、藝術審美教育兩個核心概念。
四個部分概括了藝術從醞釀到產生到被欣賞全過程中的主要美學概念。四部分以及每一部分中每一基層概念的提煉都是圍繞著動態的藝術過程進行的。
(三)系統運用文藝美學研究方法
胡經之《文藝美學》從美學和詩學研究方法里獲得啟發,提煉出三類文藝美學研究方法,分別是:1.從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出發,研究藝術審美心理;2.從藝術作品本體出發,研究藝術作品自身的美學特征;3.從藝術作品欣賞出發,研究藝術作品的接受。書中各部分內容綜合運用三種研究方法進行論述。以書中對藝術掌握的論述為例,藝術掌握是該書著重論述的一個概念,書中用了一章內容進行論述,藝術掌握涉及藝術審美心理,也涉及對藝術品的美學特征的確定,包括藝術作品接受問題。書中,從人與世界的關系分為主動和被動,來論述審美掌握的四種不同方式,特別提到藝術掌握主要從精神層面進行,體現出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在對藝術品進行審美掌握的同時,審美主體還會對藝術品進行精神的改造。
將美學和詩學方法綜合起來,形成文藝美學研究方法,對文藝美學各概念進行綜合論證,提升了文藝美學研究的理論性與科學性,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三、《文藝美學》的意義
胡經之《文藝美學》開拓出新的學科研究領域:文藝美學,也將文藝美學領域拓寬到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層面。
(一)開拓出新的學科研究領域:文藝美學,為文藝學、美學提供了新的研究內容
中國美學思想存在兩千多年,先秦諸子百家思想中就有中國美學思想,發展到明代,中國美學思想里積累了非常優秀的美學概念,比如:意象、意境、賦比興等等。中國古代文藝學里,也包含了部分中國美學思想。自古而來,中國美學思想與中國文藝思想交叉領域很多,不少概念既屬于中國美學又屬于中國文藝學。西方文藝學與西方美學發展也同樣如此,西方文藝學概念、觀點與西方美學概念、觀點也經常是同一的。
胡經之《文藝美學》將西方美學、西方文藝學、中國美學、中國文藝學進行融合、貫通,把其中交叉的概念、觀點進行歸納,形成集中西方文藝學、美學為一體的新的《文藝美學》,為文藝學、美學開拓新的研究內容。
(二)深入到人與人、人與社會等關系層面,拓寬了文藝美學研究領域
胡經之《文藝美學》里特別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并將這種關系作為書中審美活動、藝術美、藝術接受等的重要觀點。在對文藝美學學科價值進行論述時,書中認為文藝美學是對文學藝術活動奧秘的揭示,而文學藝術活動奧秘里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藝術活動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書中認為,藝術活動是相對獨立的,它是人類社會活動的而義不分,社會活動激發藝術家、作家的創作靈感,藝術家、作家從社會活動中獲得藝術創作的題材,進而投入到創作活動中,當藝術作品產生后,藝術欣賞者又受到藝術欣賞的啟發付諸實踐活動,藝術欣賞者的實踐活動又對藝術家、作家產生影響,從而激發藝術家、作家進行新的創作。在對文學藝術審美規律進行論述時,書中認為,“美的規律”更體現在審美主客體相互作用中,文藝創造(體驗)美學、文藝作品(本體)美學、文藝享受(闡釋)美學里都有審美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在對審美活動進行論述時,也將審美活動定義為:審美活動主體與審美活動客體的相互作用,并認為審美體驗也是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進行相互作用時產生的一種特殊體驗。
雷禮錫也對藝術美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界定,認為“藝術美學的研究對象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研究和解釋人與藝術對象之間的審美關系所形成的諸多理論與實踐問題”[2]1。雷禮錫對文藝美學的界定里也著重突出了“審美關系”,也可以說是對胡經之《文藝美學》的一種繼承與呼應。
四、《文藝美學》呈現的問題
《文藝美學》開拓了文藝學、美學研究領域,也對文藝學、美學交叉領域的一些概念進行了詳細定義,對當代文藝學、美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該書中呈現出的一些問題,也是值得思考的,甚至有些問題值得當代文藝學界、美學界深入研究。
(一)研究對象的不確定
胡經之認為:“文藝美學就應著重研究藝術活動這一特殊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以及審美活動規律在藝術領域中的特殊表現。”[1]2很顯然,胡經之將文藝美學放在一個交叉學科的位置上,其研究對象是藝術的審美規律和審美活動。
按照習慣性的學科思維,美學研究美是什么,文藝學則研究文學基本規律,將文藝學與美學進行交叉而形成的文藝美學應是研究文學的審美規律和審美活動。
“藝術”的外延遠遠大于“文學”。從廣義上看,“藝術”包含“文學”。狹義的“藝術”也包括音樂、舞蹈、美術、戲劇、戲曲、影視、設計藝術等。正因為《文藝美學》一開始將研究對象外延擴大為藝術,實際上,美學、文藝學學科交叉后外延只能停留于文學,造成《文藝美學》書中所明示的研究對象大于書中實際的部分論述,書中一部分內容以藝術為論述對象,而另一部分內容又以文學為研究對象。在研究對象上,《文藝美學》就出現了對象的不確定性,在論述中呈現出藝術與文學同時成為研究對象、論述對象的局面。
以緒論中的文藝美學學科價值論述為例,緒論中有三個小節論述了文藝美學的學科價值,此三小節的論述在“文學藝術”與“藝術”之間徘徊。書中呈現的學科價值論述內容如下:
1.文藝美學是對文學藝術活動系統奧秘的揭示;
2.文藝美學是對文學藝術活動多層審美規律的把握;
3.文藝美學是對藝術生命底蘊的深層拓展。
前兩個小節明確提到文藝美學的“文學藝術”研究價值,第三小節則為文藝美學的“藝術”研究價值。
論述“文藝美學是對文學藝術活動系統奧秘的揭示”時,書中進行了三個層面的論述,分別是:什么是藝術活動;藝術活動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文藝美學應該研究什么。可見,這三個層面不是論述“文學藝術”,而是論述“藝術”,三個層面內容支撐的論點卻是“文藝美學是對文學藝術活動系統奧秘的揭示”,論述內容與論點不一致,在“藝術”與“文學”之間徘徊。
論述“文藝美學是對文學藝術活動多層審美規律的把握”時,書中又回到了論述“文學”,著重論述:一切審美活動的普遍審美規律;文學藝術與其他審美活動相區別的獨特的審美規律;不同文學藝術樣式、種類、體裁的相互區別的獨特的審美規律。同樣,在此部分論述中,書中還特別提到了:文藝美學要對藝術的完整過程進行研究,至此,又回到了文藝美學要研究藝術完整過程的論述里。
在文藝美學學科內容上,書中既沒有提“文學”也沒有提“藝術”,而是用了“文藝”一詞,認為文藝美學包括三個方面的美學:文藝創造(體驗)美學、文藝作品(本體)美學、文藝享受(闡釋)美學。書中又明確提到,以上三方面美學是基于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享受的藝術活動全過程提出的。
文藝美學的內容到底是“文藝”還是“文學”抑或“藝術”呢?第二小節的論述顯得游移不定。
論述“文藝美學是對藝術生命底蘊的深層拓展”時,書中非常堅定地把文藝美學研究對象聚焦于“藝術”,對藝術價值進行全方位論述。
(二)沒有給予文藝美學學科準確的定位
緒論中的文藝美學內容和研究方法中,非常明確地把文藝美學研究內容確定為美學與詩學的的結合:“文藝美學不象美學原理那樣,側重基本原理、范疇的探討;但文藝美學也不象詩學那樣,僅僅著眼于文藝的一般規律和內部特性的研究。文藝美學是將美學與詩學統一到人的詩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審美生成上,透過藝術的創造、作品、闡釋這一活動系,去看人自身審美體驗的深拓和心靈境界的超越。”(第2頁)。詩學研究屬于文學研究范疇。緒論中這一論述進一步縮小了文藝美學的研究內容,將文藝美學局限于美學和詩學的結合。
正因為緒論中對文藝美學進行了美學與詩學結合的確定,為了配合緒論中對文藝美學研究內容的詩學論述,緒論對文藝美學研究方法進行系統性論述時,直接借用20世紀西方美學和詩學研究方法,將文藝美學研究方法定為三類:1.研究創作主體精神、心理的方法,包括直覺主義和精神分析法;2.研究作品本體的方法,包括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和結構主義;3.研究讀者本體的方法,包括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映批評。
全書內容安排上,又并未僅僅只論述美學與詩學,而是將文藝美學學科研究內容歸結于以下十一個方面:審美活動、審美體驗、審美超越、藝術掌握、藝術真實、藝術美、藝術形象、藝術意境、藝術形態、藝術接受和藝術審美教育。
從十一方面所用概念看,全是以“藝術”為其概念的出發點,都是針對藝術的美進行論述。
可見,《文藝美學》全書對文藝美學研究對象未進行一致論述。書中論述文藝美學研究方法、文藝美學研究內容等時,運用文學研究方法和文學研究視角進入,運用的思維方式也是文學研究的思維方式。為了將對象不限于文學,書中又時時提到藝術,將藝術納入文藝美學研究對象里,對藝術美學概念進行詳細論述。
這就使得全書呈現如下困惑:文藝美學里的“文藝”到底是指文學還是文學和藝術呢?文藝美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還是包括文學的所有藝術門類呢?
文學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文本,而藝術的表現形式則包括萬象,比如:戲劇是綜合性的舞臺藝術,舞蹈是肢體性的舞臺藝術。文學屬于藝術,但是文學與藝術并不等同。若僅以文學為文藝美學研究對象,研究對象顯然過窄,文藝美學也成為附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學科,若將文藝美學的研究對象擴大到藝術(包括文學),則文藝美學研究的對象又太龐大,每一門藝術都有自己獨特的美學特征,文藝美學這一學科名稱很難定義為對所有藝術門類的美學進行研究。
20世紀末,藝術美學進入研究者視野,藝術美學很好地解決了文藝美學的學科局限問題,將視野擴展到藝術全域,研究藝術的審美規律和審美活動。
2006年5月,萬書元著的《藝術美學》分為八章,論述了藝術美學的基本屬性、藝術的基本結構、藝術風格及其審美形態、藝術的基本類型及其特征、藝術審美體驗、藝術的價值結構等等,已經沒有在文藝學和美學之間進行交叉研究,而是將藝術與美學結合起來,專門論述藝術的美學特征和藝術的審美特性。
雷禮錫在其編著的《藝術美學》里,也對藝術美學這門學科進行了論說,他認為“作為一門學科,藝術美學就不是‘藝術與‘美學的簡單相加。藝術美學是研究藝術美的欣賞與創造問題的學科。它既有很強的理論性,也有很強的實踐性,是理論與實踐密切相連的學科”[2]1,將藝術美學定義為“研究藝術美的欣賞與創造問題的學科”,把藝術學科的實踐性加入到藝術美學科里,不在藝術與文學之間糾纏,將藝術獨立出來。
由于藝術美學學科的發展,文藝美學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得到了解決。
(三)觀點的矛盾
美學研究美是什么。關于“美”的問題,美學界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爭論,葉朗《美學原理》里,將20世紀50年代中國美學界對“美的本質”的討論進行了闡述,總結出20世紀50年代中國美學界“美的本質”四類觀點,分別是:
1.美是客觀的,自然物本身就有美。蔡儀先生是此觀點的代表;
2.美是主觀的,美在心不在物。呂熒和高爾太是此觀點的代表;
3.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李澤厚是此觀點的代表;
4.美是主客觀的統一,美不全在物,也不全在心,而在心和物的關系上。朱光潛是此觀點的代表[3]。
《文藝美學》第一章,明確地表明了本書的唯物主義立場,認為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審美活動都是客觀存在的。在第一章第一節《審美活動中主體客體》里,書中明確寫道:“審美客體時客觀存在的”[4]21“審美主體也是客觀存在的,是世界上確實存在的主體”[4]22“審美活動也是客觀存在的活動。主體作用于客體,并非只是精神的外化,而是人作用于物或作用于其他人的客觀活動是具有精神能力的物質力量對于其他物質力量的作用”。也就是說,《文藝美學》秉持的觀點是:美是客觀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審美活動是客觀的。在第一章第二節《審美活動是特殊維度的活動》里,書中將審美活動認定為人類維持其基本生存的實踐活動,并認為審美活動與生產活動、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相結合,人與人之間形成得關系就是審美關系,當人能制造工具、能自由自覺地勞動時,人類的實踐活動才能上升為審美活動。至此,書中已經將審美活動的歸屬、審美活動的產生、審美活動的方式都進行了論述,書中總結為:“人在自由的實踐活動中,產生了審美需要,審美需要又要由審美活動來滿足,審美活動調節著人與環境(自然、社會)的關系,使環境與人和諧平衡,確立審美關系。”[4]22審美活動是在自由的實踐活動中產生的,由審美需要引發的,調節著人和環境關系的活動,審美活動確立審美關系,審美活動是客觀存在的審美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在論述審美主體、審美客體、審美活動時客觀的的同時,書中又認為審美主體、審美客體、審美活動存在著主觀因素,認為作為審美活動核心的審美體驗是純主觀的,將審美體驗形容為是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交流一致性,甚至認為審美體驗的產生與審美主體的自我經驗有著密切關系,審美主體在審美體驗中凝視與關照審美客體本身。
在對審美體驗進行闡釋時,本書更是啟動了心理學視角,考察了審美主體的審美心理,對審美體驗與審美經驗的區別進行解釋,在審美體驗之外又增設了一個非審美體驗。對審美體驗進行論述時,引入了中國傳統美學里的“興”“神思”“興會”等概念。
也就是說,書中明確表明了唯物主義的立場,甚至認為審美主體、審美客體、審美活動都是客觀的,但是,在論述作為審美活動核心的審美體驗時,書中又回到了唯心主義立場,認為審美體驗的過程是心理的過程嗎,既有經驗的存在也有感受的存在,是一個綜合的心靈感悟過程。
全書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交雜,無法明確主觀存在和客觀存在,在一些重要概念上,觀念與論述相矛盾,比如:明確以唯物主義立場認為審美活動、審美主體、審美客體都是客觀存在的,又時時表現出唯心主義觀點,認為審美主體、審美客體、審美活動存在著主觀因素,認為作為審美活動核心的審美體驗是純主觀的,客觀存在的審美活動、審美主體、審美客體中又有主觀存在的因素,到了無法自圓其說時,又將審美活動歸結為審美關系,以關系只說來模糊論說的不嚴密性。
(四)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帶來的絕對化
在一些觀念上過于絕對,缺少相對性思考。比如:第一章第一節認為審美活動中審美客體、審美主體是必然存在的,且認為審美客體“充盈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審美主體一定是社會的人,審美主體產生審美體驗后,才會有審美活動,這里,對審美客體、審美主體范圍的確定太過于絕對化。在這一節中,還將審美價值絕對化地分為肯定的審美價值和否定的審美價值,認為崇高、優美是肯定的審美價值,卑下、丑惡是否定的審美價值,大好河山是肯定的審美價值,劣山惡水是否定的審美價值,將審美價值進行肯定和否定的劃分也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既然是審美價值,“價值”二字就肯定了其意義,以肯定、否定來對審美價值進行劃分,缺乏說服力。
參考文獻:
[1]胡經之.文藝美學·序[M]//文藝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2]雷禮錫.藝術美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3]葉朗.美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4-42.
[4]胡經之.文藝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作者簡介:段緒懿,成都理工大學傳播科學與藝術學院教授。
編輯:宋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