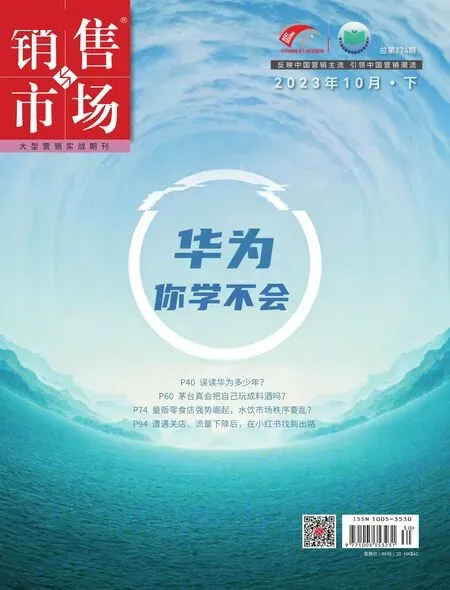華為“持久戰”:沒有退路,就是勝利之路
文/楊繼剛
2023 年8 月29 日,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華為發布了一封《致用戶信》。信中提到:華為Mate 系列手機累計發貨量已達1 億臺,為此,華為于當天12:08 推出“HUAWEI Mate 60 Pro 先鋒計劃”,讓部分消費者提前體驗。截至13:05,華為Mate 60 Pro系列所有配色均已售罄。華為這波“未發先售”,震動全球。接下來,這款Mate 60 Pro便成為全球各地“拆機直播”的主角,所有人都想搞清楚:芯片是從哪里來的,華為是如何突破制裁的,果真如華為常務董事、終端BG CEO 余承東所言的“輕舟已過萬重山”了嗎?
為此,美國彭博社通過與全球著名半導體行業觀察機構TechInsights 合作,拆解手機后得出的結論是:華為Mate 60 Pro 中使用的麒麟9000S 芯片,采用了先進的7nm 芯片技術,距離全球頂級芯片的差距僅在2—2.5 節點。而很多科技博主在對Mate 60 Pro 進行測速后發現,其下載速度在500—600Mbps(Mbps是一種傳輸速率單位,指每秒傳輸的位或比特數量),最高可達1000Mbps 以上,遠超4G 下載速度,是當之無愧的5G 速度,雖然華為Mate 60 Pro 的網絡信號欄并不顯示任何4G 或5G 信號。
7nm、5G、衛星通話、國產芯片,單單這幾個關鍵詞,就足以讓業界震撼了。要知道,華為苦制裁久矣。在被制裁的1500 余天里,不讓用高端芯片、不讓搞5G、不得不剝離榮耀、手機銷量排名從全球第二變成了“其他”。現如今,華為Mate 60 Pro 帶著7nm 回歸,1小時售罄,背后是消費者在為華為的奮斗者精神買單,是對華為突破封鎖的支持。TechInsights 副主席丹·哈徹生(Dan Hutcheson)在和央視連線中,也對華為給予高度評價:“這確實是一個令人驚嘆的質量水平,是我們始料未及的,它肯定是世界一流的。因此,我們要祝賀中國能夠制造出這樣的產品。”
這或許僅僅是開始。用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話講就是“沒有退路,就是勝利之路”。對華為而言,這是一場關系到生死存亡的“持久戰”,但現在還遠不是舉杯相慶的時刻。高端芯片制造、鴻蒙系統出海、構筑產業鏈與生態圈,每一次突圍,都需要歷盡千辛萬苦。如何打贏這場持久戰?用偉人的話講,這場持久戰既不是“亡國論”,也不是“速勝論”,而是需要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3 個階段。
戰略防御──芯片突圍
蟄伏1500 余天后,以Mate 60 Pro 上市為標志,華為手機上演王者歸來。這一局的重點是芯片。
芯片制造有多難?以Mate 60 Pro 中的那顆7nm芯片為例,相當于“把一根頭發絲劈成幾萬份,是在一根頭發幾萬分之一的地基上,蓋幾十層樓”,難度可想而知。更何況,芯片制造要經歷芯片設計、晶片制作、封裝制作以及測試等環節,EDA 仿真軟件、指令集、光刻機、激光源、鏡頭、覆膜、離子注入、原材料等,哪一項攻堅都是千難萬險,全世界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獨立建造一條完整的芯片產業鏈,都是在國際分工合作中完成的。由此不難想象,華為攻克芯片這一關,到底有多難。
時間回到2009 年。那一年,由德國知名導演羅蘭·艾默里奇執導的災難電影《2012》上映。任正非觀影后,認為華為需要防患于未然,也要建造一艘屬于自己的“挪亞方舟”。為此,華為做出了極限生存的假設,預設有一天,美國所有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為仍將持續為客戶服務。這就是華為2012 實驗室的由來,也是華為旗下海思半導體的使命所在。10 年后,也就是2019 年5 月17 日凌晨,在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的實體清單(entity list)后,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發了一封全員信,信中提到:“命運的年輪轉到這個極限而黑暗的時刻,超級大國毫不留情地中斷全球合作的技術與產業體系,做出了最瘋狂的決定,在毫無依據的條件下,把華為公司放入了實體名單。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間兌現為公司對于客戶持續服務的承諾。”看得出來,華為有備而來,至少在芯片設計領域,是有備胎的。
然而,有能力設計芯片是一回事,把芯片造出來,封裝、測試、量產、良品率是另一回事。后來,隨著制裁升級,華為手機逐漸淡出市場,從遙遙領先變成了手機銷量排行榜中的“其他”。而這次Mate 60Pro的回歸,意味著芯片領域的“卡脖子”技術獲得突破。麒麟9000S 芯片到底是誰造的,目前的傳言有三個:一個傳言是中芯國際代工,在現有14nm 的基礎上,通過N+2 工藝制程,實現7nm 效果。但這個傳言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中芯國際所采用的ASML 光刻機,屬于美國制裁范圍內的高端設備,都有遠程監控功能,如果真是中芯國際代工,消息早就可以證實了,但目前各方均未發聲。另有傳言是華為幾年前就布局了芯片代工廠,通過收購與合資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芯片生產布局,通過哈勃大舉投資國內芯片產業鏈,投資國內數百家芯片半導體企業(僅光源技術企業就投資了12 家),并和國內相關廠商合作,共同完成了芯片關鍵制造環節突破,終于可以使用自家芯片了。還有一個傳言是,國內產業鏈已經有能力打造DUVi 光刻機,或者國產EUV 光刻機取得突破,可以實現非美14nm 工藝驗證,相關的證據是,ASML 獲得許可,繼續向國內出貨2000i 等型號的光刻機。到底是哪一種情況,華為在9 月25 日秋季新品發布會上并未揭曉答案,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至少有一點是確認的,那就是國內芯片困局取得了實質性突破。
華為4 年戰略防御,初見成效。
戰略相持──系統出海
手機之后,下一個突圍點在哪里?答案是:鴻蒙系統出海。
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早已形成了雙寡頭競爭格局:一個是蘋果iOS 所代表的封閉系統,一個是谷歌Android(安卓)所代表的開源系統,前者奉行軟硬件一體化,強調安全和穩定,后者開放免費許可證,支持不同廠商深度定制,形成了安卓聯盟陣營。當然,更重要的是,蘋果和谷歌圍繞各自的系統平臺,形成了蘋果生態與安卓生態。以蘋果為例,截至2022 年年底,蘋果全球開發者突破3000 萬,在Apple APP Store 生態系統中創造了1.1 萬億美元營收,且超過90%的銷售收入歸于開發者。
一個系統,就是一條產業鏈、一條利益鏈、一個生態圈。對華為而言,智能手機(芯片)突圍僅僅是第一步,鴻蒙系統的大規模應用和普及,才是華為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關鍵。

系統難做嗎?難。難的不僅僅是系統開發本身,還有附著于系統之上的應用和生態。在PC 時代,一統江湖的是微軟Windows。而到智能手機時代,很多致力于系統突圍的廠商,并沒有突圍成功。首先看諾基亞。這個高峰期全球手機銷量占比超過4 成的傳統手機之王,早在1998 年就和愛立信、摩托羅拉合作成立塞班公司,開發塞班系統(Symbian 系統)。2008年,諾基亞收購塞班公司,而僅僅5 年之后,2013 年6 月12 日,諾基亞宣布放棄塞班智能手機,全面轉向微軟Windows Phone 平臺。其次看微軟。早在2003年6 月,微軟就發布了基于移動互聯網的Windows Mobile 2003 操作系統,幾乎是把PC 端的應用都給搬運過來了。但微軟的“路徑依賴”(認為智能手機就是更小的PC)給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鎖:智能手機不是PC,人們在智能手機上,也并非為了獲得生產力(至少在移動互聯網初期,生產力并非手機的剛需),社交、娛樂、溝通才是關鍵。直到2013 年9 月2 日,微軟收購諾基亞,Windows Phone 也并沒有成為主流,微軟系統逐漸退出了智能手機市場。還有加拿大的黑莓(BlackBerry)手機及所搭載的BlackBerry OS系統、三星手機早期搭載的Tizen 系統等。客觀上講,很多智能手機廠商都有過自研系統的努力,但后來的結果大家都清楚了。最終,銷量才是硬道理,消費者用買單的方式投票。而消費者買不買單,本質還是體驗問題,還是系統之上的應用多不多、是否好玩、流暢度以及身邊的圈子是否都在用等。這樣看來,蘋果與安卓之所以勝利,本質還是系統性能以及圍繞系統構建的應用生態圈的勝利。
對華為而言,鴻蒙依然面臨諸多挑戰。在中國市場,華為品牌的號召力沒有問題,鴻蒙生態的成長性也沒有問題,但應用市場的生態建設的確需要時間。2023年8 月4 日,在華為HarmonyOS 4 系統發布會上,余承東提到,HarmonyOS 開發者已超過220 萬。這個數據增長很快,但如果對比蘋果的3400 萬開發者、安卓的2000 萬開發者,鴻蒙只能算剛剛起步;在應用層面,截至8 月1 日,華為應用商店HarmonyOS 專區只有91 款應用,而被打上“HMOS”角標的純鴻蒙應用只有66 個,且沒有微信、支付寶、抖音與快手。相比較而言,安卓應用超過265 萬個,蘋果應用超過178 萬個,這才是鴻蒙所面臨的競爭格局。
如果把視角推到海外,我們會發現,華為的國際化之路仍將困難重重。首先,是海外市場的接受度。在過去華為使用其他芯片的情況下,在美國主導的部分歐美市場就曾遭到各種限制,制裁的大棒時時都會被掄起。其次,華為在海外市場存在應用生態系統問題。根本原因是谷歌在2019 年就停止向華為供應谷歌移動服務(Google Mobile Service,簡稱GMS),華為手機在海外無法使用谷歌的地圖、搜索、Gmail、YouTube 等應用。要知道,這些應用對海外消費者的重要性,不亞于國人的微信、支付寶、百度地圖、愛奇藝或騰訊視頻。在中國用不了谷歌(很多應用),在海外(很多地區)用不了華為,這種狀況很難在短期內改變。要先突破非美制裁地區,再進入美國制裁薄弱地區,最后靠實力突破制裁(非美國標準的制式、知識產權與專利等)。用偉人的話講,要邊打邊談,邊談邊打,打打談談,談談打打,和平是打出來的,市場是靠實力贏得的。
萬事開頭難。對于一個推出才4 年的智能終端操作系統,鴻蒙還年輕,未來可期。
戰略反攻──萬物互聯
再進一步看,作為一家科技公司,為何能引發美國“舉國之力”的圍追堵截?
這肯定不僅僅因為5G 技術,也不僅僅因為智能手機或操作系統,真正引發制裁的,其實是華為的使命與愿景:我們致力于把數字世界帶入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截至2023 年9 月21 日,作為全球領先的ICT(信息與通信)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提供商,華為20.7 萬名員工遍及170 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全球30 多億人口提供服務,近10 年的研發投入累計超過9773 億元,研發費用占比一度高達華為營收的25%,在全球的有效專利超過12 萬件,產品遍及消費者業務、運營商業務、企業業務及華為云業務。如此高的研發投入,如此高的人才密度,如此廣泛的業務范圍,在“萬物互聯”的愿景之下,重構全球ICT 技術設施,這才是華為競爭力的底層邏輯(相關數據來自華為官網)。
2023 年9 月20 日,在華為全聯接大會上,華為副董事長、輪值董事長、CFO 孟晚舟正式提出“華為全面智能化(All Intelligence)”戰略,目標是加速千行萬業智能化的轉型,這也是華為“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的一部分。從20 年前的“All Cloud”到10 年前的“All IP”,再到今年的“All Intelligence”,華為始終聚焦在ICT 領域不斷邁進。其中,“華為全面智能化(All Intelligence)”戰略的關鍵內容是:通過算力底座、AI 平臺、開發工具,支持大模型在智能化時代的“百花齊放”,而華為給自己的定位則是“百花園”的黑土地。
這樣看來,華為真正的戰略反攻,一定不是手機,而是“萬物互聯”,包括智能手機、智能汽車、智能家居、工業互聯、云計算與大數據、算力與大模型、系統生態圈等在內的互聯互通,讓數據暢通,讓數據賦能,讓數據服務于生產生活,讓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和諧共生。這種競爭,顯然不是產品級別,而是涉及標準、模式與價值觀。從這個角度而言,華為也是孤獨的,在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道路上,華為的同行者不多,能攜手出海形成背靠背信任,且能與海外競爭對手同場競技的選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用華為的話講,這場“中國科技史上最偉大的長征”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經得起誘惑(在產業紅利期,華為不做房地產,不搞互聯網),需要有戰略定力。以智能汽車為例,當華為決定進入智能汽車行業,其定位是:華為不造車,而是聚焦ICT 技術,幫助車企造好車,致力于成為面向智能網聯汽車的增量部件供應商。于是,我們看到了初具競爭力的問界M 系列,看到了“Huawei inside”與長安、北汽、廣汽的深度合作,由華為自研的HUAWEI ADS 2.0 高階智能駕駛系統,將助力更多中國新能源車企出海遠征。
此外,要實現戰略反攻,華為需要同盟軍。好消息是:近期,華為、小米宣布達成全球專利交叉許可協議,這意味著雙方在專利侵權層面的沖突和解了。在專利層面互通有無,對于華為和小米而言,當然是好事一樁,更為合作與共、攜手出海掃清障礙。對此,華為知識產權部部長樊志勇說:“華為很高興與小米公司達成許可。這份許可協議再次體現了行業對華為在通信標準領域所作貢獻的認可,也讓我們得以加強在未來移動通信技術上的研究投入。”而小米集團戰略合作部總經理徐然則表示:“我們很高興與華為達成專利交叉許可協議,這充分體現了雙方對彼此知識產權的認可和尊重。小米將一如既往地秉持小米知識產權價值觀,尊重知識產權,尋求共贏、長期可持續的知識產權伙伴關系,以知識產權推進技術普惠,讓科技惠及更廣泛人群。”抱團取暖總好過單打獨斗,對華為而言,擴大朋友圈、同盟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對華為而言,專注走好自己的路,咬定青山不放松,保持戰略定力,才是最重要的。
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革命尚未成功,華為仍需努力。中國科技企業,自強才能自立。